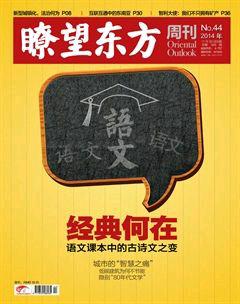为师者说:经典永不过时
于晓伟

现在我在高盛从事私人财富管理方面的工作。在这个追求效率、崇拜财富的地方,我一直以您教导的“兼庄静自得之精神,持操之在我之气概”为格言——周玥,香港,中国。
关于自由、生命与人性的普世价值的光亮,在我心中重新点燃,我甚至惊异于自己这样纯粹的信仰。现在我明白,它们来源于您的教诲,融化在血液之中——王云,匹兹堡,美国。
您就像漓江捕鱼的长者,既授吾辈以鱼(对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又授吾辈以渔(做学问的态度和对文化对生命的敬畏)——戈放、杨锐,驴行至阳朔。
……
厚厚一叠明信片,边缘都有了无数次摩挲的痕迹。此刻它们被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抱在怀里,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2014年,64岁的北京四中退休教师李家声迈入他教学生涯的第38个年头。在他位于北京市北三环的家里,家具陈设质朴简单。唯一引人注目的是客厅中央一只高大的橱柜,摆着《资治通鉴》《牛虻》等数百本书。
“语文应该讲什么?”李家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那些时髦的,没准是过眼云烟,而经典古诗文是语文学习的珍品。”
近年来,国内有些版本的教材删减了古诗文。李家声说,在这方面大陆做得不如台湾。据他介绍,台湾的国文课本,初中以上几乎全是古诗文,现代文很少,因为现代文有很多弊端,有些经不起时间考验。
在李家声看来,古诗文大多传达一种恢弘之气,“我们应该重视古诗文的价值。”
“蘑菇屯来的”李老师
“很多人说我土,我也挺尴尬,怎么自我解嘲呢?我说我内在的东西太美好了,外在不能再美好了,得拿点土的东西把内在美遮一遮。”李家声呵呵笑着。
一次,一个来自台湾的教育参访团到北京市第四中学听李家声的观摩课,校长特意嘱咐他上课时穿讲究点,“别像是蘑菇屯来的”。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课堂上,李家声低沉感伤的吟诵,将学生带回战乱频仍的晚唐时代。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大宴凝碧池,逼迫梨园弟子为他奏乐,乐工雷海清抗命不从。安禄山怒令将雷海清肢解。当时王维也被逼接受官职,听闻此事,含泪作《凝碧池》一首。
后来唐王朝清算曾给安禄山当官的人,囚禁、流放者甚多,却只给了王维较轻的处分。李家声语带激动地对学生解释:“因为王维是忠于唐朝的,他作诗赞美雷海清的气节,等于是谴责自己啊!”
结束讲课前,他深情赋诗一首,最后两句是:“我辈正吟哦,先生知不知?”
那堂课受到台湾参访团的极大好评。而王维也不再是课本上一个冷冰冰的名字,他的诗句和气节,悄悄留驻在学生心里。
李家声的学生、北京市第八中学初中部语文老师南洋,对老师李家声的第一印象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他一上讲台就完全变了个人”。
李家声讲屈原,把诗中真挚的情感和遗世独立的精神传达给学生。
“他是真喜欢屈原,而不是为了讲课而讲。”南洋觉得,这份喜欢源于一种自我认同——“文革”时李家声下放东北,生活艰苦无望,也曾思考过怎样在乱世中保持独立人格。
他为学生吟唱古诗词,学生常常在课堂上“点歌”,不唱就不下课。
他给学生讲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中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诗句。李家声模仿人鸟对话:
人说:“鸟啊,你好幸福,你住在金笼里,吃着最甜美的食物。”
鸟说:“我要出去!”
人说:“还要出去?出去你要饿肚皮!”
鸟说:“我要出去!”
人说:“还要出去?出去有枪口对着你!”
学生一齐大声代鸟说:“我要出去!”
哈哈大笑里,自由观念深深印在学生的思想中。
影响人、教化人、塑造人、匡正人
在李家声看来,古诗文之美和鲜明的思想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后者,他强调得更多的,如嵇康的傲骨、苏武的气节、苏轼的求实、司马迁的正直等。
“我最佩服苏轼,他超人的才华无人能比,但他最可悲的却是求实。”李家声说。
一次,李家声带学生去参观苏轼墓,在墓碑前他含泪说:“苏轼啊,你为什么不能稍微迁就一点儿?只要你肯迁就,就是荣华富贵、飞黄腾达。”
但反过来他又承认:“我这人死磕,就是受苏轼的影响太深。”
在李家声看来,教育的实质是文化的传代,而文化就其结果和作用来说是“化人”,即影响人、教化人、塑造人、匡正人。
他举例说,孔子“涅而不缁”的思想“化”了岳飞,岳飞的砚铭就是:“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后来这方砚台归了文天祥,他的砚铭是:“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就又“化”了文天祥。
李家声说,在教授古诗文时,他并没有刻意地去想怎么影响学生,但客观效果确实有。
学生邹菁菁,因为李家声在讲课时引用了明代义士杨继盛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因而产生兴趣,专门搜集了杨继盛的资料并写成文章投给《北京晚报》。当时《北京晚报》的编辑以为这篇文章是一位老学者写的,没想到作者只是一名17岁的中学生。
李赛,汶川地震时从国外带着募集的物资到灾区救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特意提到李家声当年讲解《离骚》《满江红》时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和对自己日后为人做事的影响。
王云,高中毕业后选择了经济学科。谈及选择初衷,她说源于李家声的教育: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负责,承担一种经世济民的使命。
在李家声退休前夕,一名学生号召大家每人给他寄一张明信片。当如雪片一般的明信片从世界各地飞来时,四中的老师们“都惊呆了”。
一名叫饶梦溪的学生这样写道:我记得您走路的样子,在楼道里,在校园里,在苏州的拙政园,在杭州的西子湖畔,您独自走着,腰挺得很直,眉眼间有些肃穆,那样子非常有精神,就像这纯白的明信片。endprint
从学生到先生
李家声对古诗词的热爱,萌芽于在北京四中读初中之时。“当时教我语文的有一位孟吉平老师,后来调任国家语委。我从孟老师那里学到很多。”
据他回忆,孟老师讲课细腻,能在学生理解不到的地方下功夫点拨,讲一首诗词经常补充好几首,“这样才能把诗人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给学生。”
所以课本所选往往不是李家声的讲课重点,他补充给学生的,都经过自己细细斟酌。
这样的教学理念也传给了南洋。28岁的南洋现在承担两个班的教学任务,师徒二人经常切磋教学。“我多少在模仿李老师,不过教学风格不同。李老师沉稳端庄,有君子之风;我还年轻,加上性格开朗外向,所以上课比较活跃。”
李家声的课堂极安静,似乎掉根针也能听见。“做老师要有读心术,讲到某一点已经引起学生内心的翻腾,就要继续往高处领。如果停下来,情绪‘哗一下就散了。”李家声说。
而南洋的课堂截然不同。如果学生能够把控,他会完全交给学生自己去讲。
“只要老师讲得好,不同时代的学生反应是一样的。”李家声说,生在信息时代的孩子们眼界更开阔,“如果引导得法,他们往往更喜欢古诗词,能够达到更好的高度。”
一次,他给学生讲严子陵。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把同学严子陵请到皇宫,与他同榻而眠,劝他出来做官,他不为所动。
“当时我说,严子陵比帮刘秀打天下的二十八宿还高尚,大家同不同意?”结果学生纷纷表示不同意,认为严子陵应该做官,“自己躲起来,回家种地、钓鱼,不是太自私了吗?”
李家声告诉学生,野心家们总想出人头地,结果往往给民众带来灾难。而严子陵,舍弃大名利,就为立一个榜样。如果人人都像他一样,人民就能安宁幸福了。
同样的大胆质疑也延续到十多年后的孩子身上。南洋说,在北京八中,几乎每个老师都有过被学生“挂”在台上的经历。
一次,南洋给学生讲周敦颐的《爱莲说》,提出一个问题:周敦颐对菊花的态度究竟怎样?结果,学生讨论的热烈程度完全超乎预料,“抛出这个问题的是我,但是争论起来后,基本上是学生在主导了。”
反对的说,如果周敦颐喜爱菊花,为什么还要写《爱莲说》?而持赞同意见的学生提出,“菊之爱,陶后鲜有闻”,从中多少能读出周敦颐的惋惜和遗憾,因此他是认可菊花的。
“孩子们能够从文本入手,挖得很细腻。”南洋说,这对老师也很有价值,促使老师不断去思考。
如果没有考试压力,对古诗文更感兴趣
“总体来说,我感觉学生们对古诗文是喜欢的。”南洋说,尤其是素质班的学生,由于可以直升高中,没有考试压力,反而对古诗文更感兴趣,“因为他们确实能从古诗文中感受到前人的智慧和历经锤炼的美。”
据了解,北京八中的素质班是北京市的一个教改项目,“学生都是小学四年级上完就招上来的,初中学制四年,课程也作了一些改革。”
南洋说,这个班的学生整体偏理科,逻辑思维较强,但也有孩子会主动阅读《古文观止》《史记》等,“不管是原本还是白话本,起码他们会有兴趣看,这已经很难得。”
但对于初中普通班的学生来说,文言文教学确实比较“麻烦”。南洋解释说,北京中考对于文言文的考察只考课内,很多学生会有明确的考试指向,“(如果补充课外古诗文)他会说这东西又不考,我就不用学了,把二十几篇背熟不就完了?”
南洋回忆,李家声跟学生的交流基本上就是在课堂的45分钟之内,毫不保留地、大容量地传授,“高中时我们班除了一些背诵任务外,几乎没有笔头作业。”
这样的教学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南洋,“向45分钟要质量,这是李老师经常跟我说的。”
而现在一些青年教师欠缺学习精神,让李家声又气又难过,“上课前5分钟,去网上拽点什么,PPT打出去,照着一捋就行了。老师是这样好当的么?好诗词都让他讲糟了。”
他给学生讲李白:其诗多描写大自然景色,寄情于山水。关于李白为什么热爱大自然,他援引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来佐证:“我不与人争,与人争我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李家声还即兴给学生秀了下英文,氛围一下子活了起来。“我的英语也许很蹩脚,但目的是让学生融会贯通,而不是迂腐地去讲。”
“教学如果没有深度,学生也不会买账。”李家声给学生讲《孟子》时,孟子指责统治者,你们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可是老百姓饿得面黄肌瘦,田野里有饥饿而死的人。你们哪是为民父母啊?你们这是率领野兽吃人,你们是野兽头儿!
学生听了都很痛快:这老头真棒!
但仅仅停留在这里显然不行。孟子骂完后还要劝喻,希望统治者与民同乐,知过即改。“当学生到了一定的高度上不去的时候,就得靠老师来帮他。”李家声说。
教材编写不能只图“新”
在北京八中初中素质班,因为课程改革,南洋需要自己给学生编写教学材料。他以人教版统编教材为蓝本,删去了不适合素质班学生的篇目,另加了一些古诗文。
比如《夸父逐日》《共工怒撞不周山》,南洋说这两篇文章太简单,没有深入分析和思考的空间,“找不到能让孩子们‘找茬的地方,他们读了不会有太大兴趣。”
初一时,出于语文课应承担情感教育功能的考虑,南洋给学生增加了《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后来又加了唐代宋之问的《渡汉江》、宋代岳飞的《满江红》等。
“背诵不是问题,也没什么特别难理解的。”比如岳飞的《满江红》,那种豪情壮志和沉重的爱国情怀,学生都能体会。
南洋说,他对学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把情感读出来。“学生会知道某一个字写得好,是能表达感情的,以后会慢慢有新的感受。”
过去,李家声经常参加一些教材编写会。他特意找出《文选》给本刊记者看,说:“这是中国第一部语文教材,距今已有约1500年历史。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就是读着这部语文教材成长起来的,所以有句话叫‘文选烂,秀才半。”
李家声觉得,这么多年来,始终都有一批有思想的老师能够把握语文教学的宗旨。但如今一些教材的盲目编写让他觉得犯了“形式主义”:就为了一个“新”字,“把屈原的《离骚》删了,把《孔雀东南飞》也删了,我真不知道作何感想。”
他觉得,要从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中学古诗文,如果没有对古诗文的热爱,就体味不到其中的美。
李家声所著的《诗经全译全评》出版时,出版社要求把原来的150万字压缩到50万字,还担心印这书“恐怕要赔钱”。
“我自己也想,现在谁还看这样的书呢?最初我不想出,学孔子述而不作,总行了吧?”李家声说,是一个朋友点悟了他,“你是受中华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现在你受到好处了,却不为我们的文化做点事,你这不是自私吗?”
后来《诗经全译全评》再版,李家声这才觉得,社会对传统文化还是认可的。
现在,否定中华文化的只有两种人,李家声直截了当:“一种是疯子,一种是傻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