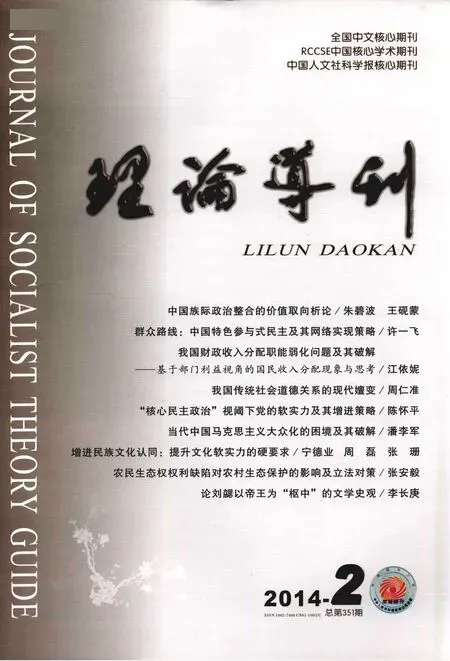农民环境抗争、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农村治理危机
张 君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541006)
随着社会逐步进入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开始凸显,集体抗争事件也越来越多。在诸多的集体性冲突中,由于环境污染对当地居民造成损害而引发的抗争呈现出日益恶化的态势。特别是在一些农村,随着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迁入,使得农民因为遭受环境污染侵害而选择了集体性抗争。近年来,农民环境抗争愈演愈烈。由于农民群体的特性,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化,导致农民在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欠缺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冲突的激化,导致治理危机在一些地方出现。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一、日趋恶化的环境状况:农民环境抗争的缘起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农村也日益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在向农村转移的工厂中,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占据了大多数,导致一些农村的环境日趋恶化。由于环境恶化给当地农民带来极大的损害,导致农民奋起抗争。和城市居民环境抗争有所不同,农民环境抗争也具有很强的乡土气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抗争与其他问题相互交融,异常复杂。在城市里,环境抗争只是单纯地为了保护所生活的家园,而农民环境抗争的问题往往更加复杂化,特别是与征地拆迁补偿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一般而言,当村庄环境还可以“忍受”时,农民也基本上宁愿息事宁人。但环境问题的产生通常是由污染企业所造成,企业要发展壮大,扩张厂房在所难免。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可能会与农民发生直接利益冲突。当协商无法解决问题时,特别是补偿款过低时,农民因长期受到污染导致损害的情绪猛烈地释放开来,形成巨大的反抗性力量。因此,农民环境抗争很多时候其诉求并不简单的是要求恢复家园的生态环境,更多是要求征地补偿的到位。因此,当环境问题升级成利益冲突时,往往使解决的难度加大了。
2.规模较大的环境群体抗争事件的出现。由于环境问题与其他问题糅合在一起,各种利益交融,使得农村环境问题牵涉到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加上环境一旦出现任何问题,遭受损害的人数规模将会激增。如果环境抗争事件发生,必然会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虽然还属于偶发态势,但由于问题比较严重,影响深远,爆发所带来的破坏性能量很大,不仅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会带来巨额的财产损失,最关键的是有可能危及社会共同体,造成社会的失序。近几年来,由于环境抗争所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已经频繁出现,如发生在浙江东阳画水镇的造成数10人受伤的群体性事件、2009年湖南浏阳镉中毒事件、安徽安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2011年浙江海宁市“9·17”环境污染群体抗争事件等。
3.出现了暴力化对抗性的群体抗争事件。当体制内的措施无法解决问题时,暴力就成为最后的选择。特别是整个社会出现“暴力化”诉求的背景下,群体性事件施行暴力就成为弱势群体的被迫行为和选择。在浙江画水事件中,外围的村民坐在路上阻止官方撤离,造成混乱,情绪激动的村民开始追打身穿警服或政府配给雨衣的执法人员,一些执法人员纷纷扔下警棍、橡皮棍、盾牌、砍刀,并脱去钢盔和制服,撤离现场。在新昌事件中,一万多名农民强烈抗议药厂污染环境的宣言是“宁愿被打死也不愿被熏死”,数百名黄泥桥村的村民聚集在化工厂门前要求工厂立即停止生产,并与保安以及前来维护治安的警察发生冲突。在2008年的舟山定海和邦化工厂污染事件中,当地近千名村民前去化工厂抗议,并引起警民冲突,导致多人受伤。
4.“弱组织化”是农民环境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农民人数虽多,但如同原子般地分散在村庄周围,组织化程度非常低,这也是农民成为弱势群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乌合之众相比有组织者而言处于劣势。在农民环境抗争中,组织化程度也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特点。总体而言,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可以概括为“弱组织化”,主要有三种形态,其一是根本无组织,纯粹是毫无目的的骚乱,因为共同的目的而临时形成了集体行动;其二是“弱组织化”,一般由农村的一些精英或积极分子所组成,由于抗争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也需要动员民众,因此极少数骨干分子经常聚会碰头协商,形成了松散的组织体,当然,这类讨论小组并没有形成正式的组织结构;其三是借助正式组织的力量开展活动。村民自治制度使得村民有权选举自己的村委会,在某种程度上基层政府并不能完全掌控村委会主要成员的任免。要当选村委会成员,理论上必须代表村民的利益。事实上,环境污染损害的往往是整个村庄的利益,当然也包括村委会成员在内。当然,由于村“两委”合署办公,基层政府可以通过控制村党支部进而控制村委会,所以村委会带领村民进行抗争的情况比较罕见。特别是一些企业通过贿赂收买村“两委”成员,分化瓦解了整个村庄的集体抗争。也有一些环境抗争依靠合作社、协会、理事会等非政府组织来进行。总体而言,农民环境抗争依然处于无组织状态。
二、沉默的大多数:集体行动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在西方国家成为一种普遍诉求,甚至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的理性价值观,环境运动在各国蔚然成风,俨然称为后现代的“后物质主义价值”。[1]与此形成鲜明比对的是,在我国,很多人对于环境保护漠不关心,即使环境污染危害到己身,也基本选择逃避或沉默,2003年的一份全国调查表明,“城镇居民在遭受环境危害后,只有38.29%的人进行过抗争,高达61.71%的人选择了沉默。”[2]显然,在环境污染面前,多数人的选择是做“沉默的羔羊”。
1.“搭便车”现象:集体行动的困境。对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一个由众多利益相同者组成的大集团中,即使所有的人都是理性和寻求自我利益的,并且他们采取行动也能从集团的共同利益中获取好处,但他们仍然不会通过自愿采取行动来促进集团的整体利益,其原因在于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现象。除非集团中的人数极少,“搭便车”会受到集体的谴责,或者集团提供了相应的激励机制或强制性措施使得单个成员采取行动从集体中所获得的收益超过他采取行动所付出的代价时,个人才会为集团整体利益而采取行动。[3]
当农民利益受损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以集体的名义表现出来。集体行动在抗争过程中因受到个人理性的选择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由于集体的行动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需求,部分农民在参加环境抗争后会一无所获,形成内部的利益冲突。对于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危害,农民所遭受影响的程度各有不同。例如采矿业所造成粉尘污染的程度会随着家庭靠近厂区距离远近有所差别。但是在集体抗争行为中,农民所承担的责任、风险是相同的。因此,集体中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冲突会影响抗争行为的最终结果。此外,部分农民的抗争意识比较淡薄,一些不愿意抗争的和环境污染对自身伤害不大的农民不会选择抗争,这就与集体行动产生了分歧,农民内部的利益冲突使抗争行为陷入困境。
2.弱势地位下的抗争组织。在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中,抗争的对象一般是企业。与松散的农民联盟不同,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组织是分工协调的统一体,更何况在很多地方,产生环境污染的企业往往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比而言,农民环境抗争可以依靠的合法组织多半是村委会。虽然村民自治制度已然实行多年,但由于农村中有同级别的党委组织来加强对村委会的指导,所以污染企业可以通过和地方政府组成联盟,利用农村党委组织来约束村民的行为。特别是当“维稳”成为压倒一切的重任时,农民环境抗争所依赖的村委会就无法代表村民利益了。最后的结果就是环境抗争陷入无组织、无领导的境地,各自为战的结果要么是忍气吞声,要么是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如此更加危险。即使通过少数农民的努力,产生了集体性的领导团体,但由于农民本身的社会资本比较少,很难获取外界的支持,领导集体依然无法成功组织环境抗争,从而使抗争陷入困境之中。正如汉尼根所言,“对于有前途的环境问题来说,要想充分而成功地抗争,应当有制度化的支持者,以确保环境问题建构的合法性和持续性。一旦环境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和法律程序,这一点就显得尤其重要。”[4]
3.低效率的集体行动策略。在集体行动中,单个个体的影响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因为存在广泛的“搭便车”行为,由于集体收益的非排他性,个体即使没有付出努力,但作为集体成员,同样可以分享收益。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时,易造成低效率的集体行动策略。
在农民抗争的前期和中期,受害者在商议行动时因过激的情绪和不同文化水平差异也会导致低效率的行动策略。这种策略往往产生低级的错误和盲目的行为,最终使农民由“有理方”转变成“无理方”。目前农民环境抗争成功的案例比较少见,虽然表面事件得到平息,但是内部矛盾依然尖锐。矛盾一般是没有得到理想的补偿和政府处理过程中的欺压行为造成,农民在抗争过程中对自身缺乏信心也会使其行为变得犹豫不决。
4.农村社会结构的巨变。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农村的人群也出现了大幅度的迁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伴随着工业化运动的加快,农村人口流动是很正常的现象。当然,这种快速流动一方面消解了共同的凝聚力,使得集体主义更加模糊。另一方面,能够正常流动的首先是农村中的精英,大量精英的出走使得农村只剩下老弱妇幼。精英的流失以及集体主义的瓦解使得农民环境抗争很难去组织。
三、地方政府能力欠缺:农村治理危机的产生
在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的行为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可以说,很多地方群体性环境抗争事件的发生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欠缺所导致的。一些地方政府与环境污染企业结成利益联盟,无法将农民群体纳入决策议程以及农民对其缺乏信任导致了农村治理危机的出现。
1.地方利益共同体:利益联盟的出现。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开始了分权改革的步伐。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一方面,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有了巨大的自主权,完全主导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和分税制改革为地方政府营造了巨大的营利空间。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常唱不衰的“主旋律”,经济发展压倒一切,这种以GDP为主要政绩的考核指标促成了“压力型体制”[5]的形成。为了在“晋升锦标赛”[6]中获得胜利,从而谋求政绩和经济利益最大化。在此过程中,牺牲环境在所难免,因为只有通过上“短、平、快”的项目才有可能最快实现短期利益,结果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形成了。在巨大的财政压力面前,培育发展壮大当地企业成为最紧迫的任务,在税源和财源面前,环保和民生等社会发展事业则被弱化和忽视。特别是残酷的地方竞争使得各地不惜一切代价招商引资,降低环境标准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共同选择,以至于当地环保部门在本地政府的压力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分权改革的同时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机会主义”使得考核机制变得简单化,为地方政府寻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环境污染企业收买地方政府相对更简单。可以说,分权分税制改革、“财政联邦主义”、GDP考核压力、地方政府竞争加上寻租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益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同的利益指向,由此个别企业行贿政府官员的个体行为有可能升级为制度化的政府企业增长联盟,从而形成利益增长共同体。在多元化利益来临之际,地方政府变成了追求利益的主体,由“裁判员”的身份变成了“运动员”,陷入利益纠葛之中而不能自拔,中立的地位一旦消失,公平公正显然很难实现。
在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中,作为维护公平正义以及弱势群体利益的地方政府,很显然并没有明确自身的职能定位。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对农民环境抗争的积极压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并没有发挥强有力的管制作用。地方政府的“亲商”行为使其陷入环境治理困境,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在地方政府的眼中,企业的经济贡献远远超过数万个小农——在免除农业税之后更是如此。[7]如此情形下,农民的环境抗争很难通过地方政府来实现。当制度内的诉求无法满足时,农民的环境抗争目标则从反对企业上升到反对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增长联盟。因此,“民企抗争”很容易上升为“官民冲突”,并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种发展趋势之所以无法避免原因在于只有通过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暴力冲突,农民才能吸引外界注意从而使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介入,增长联盟的强大利益联盟才能打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本来作为国家在地方治理的代理人——地方政府显然没有执行自己的使命,政府能力被削弱。
2.地方政府能力危机:治理的弱化。政府能力,也称作政府效能,是指政府实际能够履行职责和功能的程度,它要解决的是政府如何去做、通过什么方式去做的问题。从很多环境抗争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环境冲突之所以产生并升级,地方政府能力危机是关键性因素。地方政府在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中的能力危机,我们可以定性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政策议程上无法将绝大多数群体纳入其中,决策过程是封闭保守的,以至于不同群体的利益难以成功整合;二是被企业利益集团所“绑架”,国家的环保政策无法严格实施。
其一,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地将农民的利益诉求纳入政府决策。政府无法充分辨识或者有意忽视农民身体健康和利益所遭受的长期侵害。由此可见,地方政府由于制度因素、利益结构困境等原因而无法及时有效地平衡社会利益,体现出其在社会整合能力方面存在问题,或者说地方政府在面对强大的利益表达时,缺乏有效的反应性。当前农民的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渠道非常有限。上访是其普遍采用的体制内表达方式,而效果并不明显。农民的弱组织状态、基层党组织的弱化以及无法接触到媒体等各种因素直接压缩了农民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渠道。当农民不可能在政府框架之内解决问题之时,他们就可能通过极端的体制外方式来吸引上级政府或者舆论的支持。正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所说:“当一个社会中各种成分缺乏有组织的集体,或者无法通过现存的有组织的集团充分代表自己的利益时,一个偶然的事件或一个领袖的出现都可能促发人们积蓄的不满,并会以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发。”[8]
其二,地方政府在治理企业污染方面体现出政府管治能力的弱化。一些企业根本没有任何环保措施,或没有经过环境评价而建设运行。地方环保部门在人力、资金、技术等方面都达不到严格的环境治理要求,尤其是资金匮乏甚至使环境保护成为政府收费下的合法污染,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对抗地方的环保行为。当然,地方政府某些官员也缺乏进行严格管制的意愿,体现出地方政府缺乏克服自身利益诉求的能力。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的管制有可能被俘虏,[9]从而成为一些污染企业的“帮凶”。
3.恶性循环的互动:信任危机的激化。农民对基层政府的深刻不信任是激化环境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不信任是两者长时间恶性循环互动所产生的结果。当农民的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甚至遭到压制,他们会对地方政府产生不信任,农民开始希望通过他们的行为引起高层政府的重视。在一定的条件下,农民的集体行动开始具有较强的表演性和对抗性。在抗争过程中,农民在内部以及与外部行动者之间进行着身份的界定。在持续的互动中,受到污染侵害的农民因共同居住的地域以及遭受的共同伤害而形成自身的身份特征,并形成团结的身份认同。他们将企业和地方政府视为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他们”。重新的身份界定意味着农民开始将抗争对象由企业转到政府。在信任危机之下,真相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地方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可能被农民重新解释为某种欺骗和侵害行为,即使地方政府因为压力而表现出足够的善意。所以他们不是选择相信地方政府的说法和行动,而是选择其他体制外的方式来吸引高层政府和社会媒介的关注。“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是在地方政府遭遇信任危机下,农民采取的一种激进而理性的策略。从根本上来说,信任危机导致遭受侵害的农民不是向地方政府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希望直接寻求上级政府的支持,甚至在有些条件下,这些草根行动者会采取象征性的或者暴力性的策略,来体现自身的存在及其利益诉求。
地方政府的利益结构困境、能力危机和信任危机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地方政府具有独特的自身利益并与企业形成某种利益联盟,在利益分配和再分配上缺乏超然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既是农村环境污染恶化的一个动因,也是农民环境利益诉求受到压制的根本原因。地方政府在经济结构中的角色削弱了其管制能力,降低了民众信任。同时政府能力与民众信任也是相互影响的。这体现了地方政府面临的治理困境,直接影响到农民环境抗争过程及其方式。
四、结论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污染企业对农村带来的侵害,加上拆迁补偿所失去的利益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民走上了环境抗争之路,大规模环境性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由于农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以及农民个体的弱小,农民环境抗争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地方政府由于治理能力欠缺以及利益因素的困扰,并没有履行好保护环境、维护弱势群体的职责,使得农民的环境抗争由体制内的利益诉求转向体制外的方式,甚至通过暴力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对象也由污染企业转向地方政府。农民环境抗争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打破地方政府暂时的利益结构,并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在政策上对受害农民利益进行倾斜和补偿。然而,我们注意到,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它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地方政府的执政基础,也使得农村基层陷入治理危机之中。因此,降低和解决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打破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盟,切断两者之间密切的利益联系,使政府在利益分配上处于一个公正和超然的地位。
[1]Inglehart,Ronald.The Silent Revolution: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Inglehart,Ronald.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2]冯仕政.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3][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4.
[4][加]汉尼根.环境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2.
[5]荣敬本,崔之元.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5—35.
[6]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7]张玉林.环境抗争的中国经验[J].学海,2010,(2).
[8][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02.
[9]Stigler,G.J.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