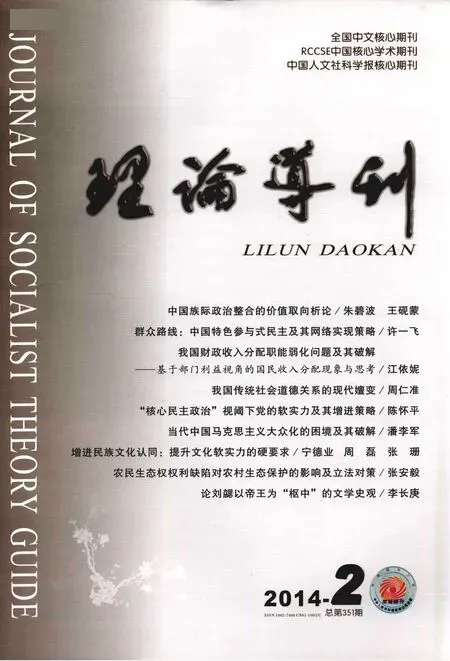我国传统社会道德关系的现代嬗变
周仁准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210098;安徽工业大学,安徽马鞍山243002)
构建一个道德关系良好的和谐社会是中国梦丰富内涵中应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道德社会著称于世。近现代以来,我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道德关系也在社会制度更替流变中发展进步。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重新审视我国社会道德关系的现代嬗变,对于推进中国梦语境的新型社会道德关系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
在现实社会中,人际间关系首先表现为道德关系,其次才是政治的、经济的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道德关系是道德规范在调节人们社会行为时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其核心为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即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关系。道德关系本质上是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它集中体现了特定社会的价值理念,尤其是体现了在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价值理念。自阶级出现与国家建立以来,道德与政治就如同连体兄弟,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我国传统社会道德关系的历史嬗变过程中,政治因素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其对道德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道德关系主导价值理念中,道德关系主导价值理念的变迁是道德关系历史嬗变最为显著的特点。
道德关系的主导价值理念是指导道德关系形成与发展的社会主流价值规范。道德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不是抽象地来自于人们的内心,也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来源于人们的现实物质生产与生活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归根到底是人们现实利益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道德关系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现实生活中调节人们行为的道德也不过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道德关系体现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与人们的内心信念等方式来促进良好人际道德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在阶级社会,道德关系所体现的利益关系总是受制于特定社会主导价值规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政治道德化表征。
在传统中国社会,道德与政治高度耦合,其中既有道德政治化,也存在政治道德化,但主要是政治道德化。政治道德化突出表现为国家治理中的“德主刑辅”现象。传统中国是典型的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德治社会,君主是家国一体的最权威治理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实施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主导和调节不同社会主体之间道德关系的价值观又主要表现为“忠孝节义”、“贵和尚中”与“天人合一”三个方面。在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中,“忠孝节义”是调节人际间道德关系的核心规范,“贵和尚中”与“天人合一”服从和服务于“忠孝节义”。“忠孝节义”的核心是“忠”,即人民要忠于统治者,尤其是忠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帝王。传统社会推行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等人伦思想就是“忠孝节义”的具体表现。在上述价值观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形成了具有浓厚等级制度色彩的人际交往道德原则,突出强调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来协调和维系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士、农、工、商”等级划分来区分人们之间的尊卑贵贱,以宗族血缘关系标准界定人际交往中亲疏远近,以强烈的家国同构思想缔造着至高无上的宗族理念、君权至上理念。在传统价值观中,既有值得后人传承的推崇人际和谐的“贵和”思想,也有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关注自然环境的人文主义情怀,同时还有强调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倡导宿命论的糟粕。显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威权治理下的社会可以达到或实现特定社会所需要的“有序”与“善”的人际关系,但是,这种“有序”与“善”具有明显的虚假与不公正,因为这种“有序”与“善”背离了人的真正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代中国社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主法制社会,指导和调节不同主体之间道德关系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社会新型道德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不同,社会主义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自由等思想,宣扬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理念,摒弃了传统社会存在于人际间的特权思想与等级观念,社会主义价值观在继承了传统中国道德文化精华的同时,又融入了时代发展的民主、科学与创新等新思想新理念新元素,并分别从国家、社会与公民等多维展开。社会主义价值观强调既尊重作为自由主体存在的个体意志,也强调对集体利益与意志的遵守与维护,强调个体与集体的辩证统一,从而摒弃了传统社会道德关系中个体利益与意志被压制或“忽视”的内在缺陷,为本真意义上社会公正与友善实现开拓新道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生产方式中,广大劳动者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解放,而且在精神层面获得了自由与独立地位,赢得了主体尊严,从而为建立在人际间真正自由平等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新型社会道德关系提供了可能。在当下社会,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基本方略,法律制度已成为政府行为的基本依据,成为调节和规范人们公共行为的主要强制性规范。
在人际间道德关系的历史变迁中,不仅存在道德关系指导价值观的变化,还存在着道德与政治之间微妙关系的调整。在阶级社会道德关系的历史流变中,政治与道德总是结伴而行,政治为道德的形成与变化设定方向与规则,道德则为政治合法性提供辩护。在当代社会,幻想没有政治的道德,或者没有道德的政治,都是不切实际的。处理不好道德与政治两者的关系,极易导致以政治取代道德的“政治无道德论”或以道德取代政治的“道德理想主义”。在传统社会道德关系走向现代的历史轨迹中,客观上存在道德与政治的高度重合向道德与政治的适度分离的趋势,即道德价值理性与政治工具理性高度同一向两者既统一又分离方向转变的趋势。
(二)
良好社会道德关系的建构应建立于对道德关系中彼此权利与义务的准确认知上,建立在对交往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科学界定上。只有这样,才有助于促进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发展,才有助于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道德关系的历史嬗变实则是道德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调整与重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体社会地位的升迁变化。道德权利是指“道德主体在道德生活中所享有的权利,包括:选择和认同某种道德价值标准的权利;进行道德行为选择的权利;要求正确评价自己品质和行为的权利;当见义勇为给自己带来损害后要求受益者和社会给以适当补偿的权利;追求德福统一、道德公正的权利”。[4]道德义务则“总是意味着对行为主体个人意欲与利益的放弃、对自身需求满足过程的推延和对个体自由的限制”。[5]从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割裂对立到两者的对立统一是传统社会道德关系现代嬗变的另一显著特点。
作为调节人们行为的道德,常以应当或“善恶”等方式影响和评判着人们的行为选择,构建具有约束力的道德关系。自古以来,道德关系从来不是单调空洞的,而是有着丰富的实在内涵,道德关系反映的其实是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以行为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方式体现出来。只有建构平衡对称的权利义务关系,人际间的道德关系才能得到维系和发展。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人际间的道德权利与义务关系基本上处于割裂对立状态,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强势群体享有道德权利,拥有道德话语权;广大劳动人民则履行道德义务,丧失道德话语权。传统社会人际道德关系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群体借助人性理论等进行自我包装,他们以圣人、道德楷模的身份自居,为他们专享道德权利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与美化。例如,董仲舒就认为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其中天子之性是“圣人之性”的现实化身,代表至善与完美,堪称万民的表率。董仲舒认为:“行天德者谓之圣人”,(《春秋繁露·威德所生》)“皇帝被渲染成父亲般的人物。官吏和绅士对于他和他的家系的忠诚,是出于具体的个人关系。”[6]以天子为中心的社会统治者担当着以德教化天下的道德责任,拥有教化存在人性缺陷的“中民”与“斗筲”的道德权利。另一方面,对社会下层民众承担道德义务的应然性进行论证与阐述。我国传统社会历来重视人际间伦理道德关系的建构,尤其是对主体道德义务的阐述与强调,例如《尚书》就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与“子孝”等思想,孟子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伦”主张,《礼记·礼运》强调“慈”、“孝”、“良”、“悌”、“义”、“贞”、“惠”、“顺”、“仁”、“忠”等“十义”理念。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强化皇权与家长制的绝对权威,强调人们应严守“孝道”,绝对服从皇权与家长,谨守忠孝的礼仪规范,忠孝不能两全时要以忠君为上,必要时“大义灭亲”。
传统文化对人性的阐述,尤其是对“气质之性”的解读,提出了作为理的化身的“天子之性”是至善代表的命题,指出“气质之性”是恶的根源,进而要求劳动人民摒弃“气质之性”的不良影响,“以吏为师”,“存天理、灭人欲”,最终方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在大力倡导义务性道德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广大劳动人民的道德义务被突出强化。在传统社会道德教化中,义务、奉献与牺牲等精神的宣传固然有其社会发展的应然性,然而,对劳动人民道德权利的回避与否定,就是对人民社会主体资格的否定,必然导致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关系的割裂,导致人们对社会秩序正义性的质疑,形成虚假的“善”与“吃人”的道德。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7]“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权利的地方,这另一个人就有义务让他行使这种权利。”[8]在个体获得充分人身自由、思想启蒙与社会解放的当代,权利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成为普遍的行为原则。社会主义社会高举人民主权大旗,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主宰者,成为“他自己的主人”,[9]为新型社会道德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真正自由平等的文化土壤与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扫除了旧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制度,而且还废除了特权制度,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自由平等,为建立真正自由平等和谐的新型社会道德关系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积极肯定人民群众在道德关系中的权利主体地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是社会从而也是自我命运的主宰,人民群众是新型社会道德关系的建构者、受益者与维护者,是道德权利的拥有者。社会主义道德从根本上扬弃了传统社会“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主张“义”“利”相统一的思想,倡导人们在谋取自身合法正当“利”的同时,兼顾社会公“义”。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10]在社会主义社会新型集体观念的培育中,强调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的集体观念建立在对个体利益与意志尊重维护基础上,而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恰恰相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积极鼓励和动员人们履行自身应尽的社会义务,倡导在奉献社会与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努力构建和谐的社会道德关系。社会主义道德在肯定人民群众在道德关系建设中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吸取传统社会道德教化中的有益成分,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角度增强人民群众的道德义务观念,倡导奉献、牺牲、责任与义务等道德意识,用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新时期道德楷模等教育人、引导人和鼓舞人,讴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倡导建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型互助合作的社会道德关系,并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道德关系的建构与发展,以“八荣八耻”来教育和指导人们,增强人们建构和谐友好社会道德关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道德关系内涵的历史变迁体现的不仅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从对立走向对立统一,其内在的逻辑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历史中是否具有主体地位的敏感问题,是国家主权的主体归属问题。
(三)
道德关系由特定社会主体基于自身特色文化与现实利益关系确立向汲取域外先进思想文化、提炼自身科学理性价值规范融会贯通的发展路径演变,即由相对封闭的内生确立向开放的、外生与内生相结合方向演变,这是我国传统社会道德关系的现代嬗变走出的一条特殊的发展之路,即由相对单一封闭的传统中华文化规范确立其内涵转向以融会中外思想文化精华为指导的发展之路,这也是中华文化再次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归根结底是现实社会人们利益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在长期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用以解决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风俗、习惯逐渐固定化、机制化,逐渐衍变成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特定场域人们的行为范式与社会文化,衍变成为用以调节人们利益关系与行为选择的道德规范。在传统社会,风俗与习惯的形成主要局限于特定利益场域,主要形成于存在彼此依存关系的特定部落、氏族或乡民之间,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的道德主要形成于熟人之间,并成为用以协调或解决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机制。生活于不同地域人们之间的道德文化可能存在相似价值观,也可能存在相背离甚至对立的思想理念,由此形成多姿多彩的亚文化与亚道德现象。西欧民族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显然与中华民族父慈子孝理念存在较大差异,而生活在中东的阿拉伯民族调节男女之间道德关系的保守思想又与西欧民族开放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在民族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道德是民族意志与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代表,具有浓厚的内生性。相对封闭的生存发展状态更是塑造了自秦汉至明清以来中华传统道德关系不同于其他外域民族的文化特质。
道德关系是特定地域人际间文化的重要表现,任何稳定和谐的人际道德关系都需要经历一定时期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积淀才能逐渐形成。社会流动促进了不同地域与民族之间道德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社会流动也为人际间道德关系的培育与维持增添成本与风险,进入陌生地域的人们需要逐渐熟悉当地的道德文化才能更好地融入其中,任何外部传入的道德思想只有经历与当地道德文化的碰撞融合后才能成为调节人际关系的指导规范。道德关系的形成、发展与嬗变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数千年相对较为稳定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道德,形成了具有浓厚乡土气息与人文色彩的人际道德关系。然而,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致使我国社会出现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和民不聊生的困局,在救亡图存的抗争中,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觉醒人士开始对传统社会专制政治制度持强烈抨击立场,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反思。“从清末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产生于欧洲的近代国家所打败。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诸于传统道德或者文化。”[11]新文化运动更是明确地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传统“旧”道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12]以解放思想,建立人际间的新道德关系。他们大声疾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13]他们用饱含感情的犀利文笔揭露和抨击以“三纲五常”与“三从四德”等为代表的封建旧道德的“吃人”本质,主张用新思想新文化重塑新国民,以新道德培育国民的新风尚。
在内忧外患的年代,对内生的传统道德的抨击与否定客观上呼唤更进步的新道德以重构国民间的新道德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我国逐渐走出了一条学习借鉴域外先进思想文化与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的新社会道德关系重构之路。
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社会道德受到一波又一波的价值批判与政治洗礼,传统道德几乎成为腐朽、落后甚至于反动的代名词,成为被批判与否定的对象,由外部传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价值观等日趋受到国人的关注与思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社会道德关系重建的序幕,公而忘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舍己为人、集体利益至上等价值观开始备受公众推崇传扬,实现共产主义成为激励那个时代人们燃烧自己和奉献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推进建国初期社会道德关系重建的主要动力。自建国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道德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成为自己社会的主人,男女平等、人人平等、自由人权、权利与义务对立统一等成为新社会人际间道德关系的核心内涵,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社会道德观规则的制定者与评判者,由外部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社会道德关系的最高指导思想。自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至新中国成立,我国社会新型道德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对传统社会道德关系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先进道德思想汲取的基础上。
与新型社会道德关系形成较为鲜明对比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只有与鲜活的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在与中国社会具体的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促进了我国社会道德关系的第二次质的飞跃,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道德关系的全新建构。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综合的协调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型社会道德关系只有与鲜活的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才会结出灿烂的道德文明鲜花,才会建构人们期待的美丽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我国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社会近现代史上道德关系重构的必由之路,这是一个既注重自身传统优秀文化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又充分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各民族先进道德文化成果之路。
而当中国社会逐渐走上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道路之时,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不断催人反思道德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关系,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思考而产生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在解放人们思想的同时,也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感性的时代思想元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建设实践在理论上升华的具体表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的荣辱观更是体现了中华民族新型道德关系建构中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民族自信。
[1]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
[3]魏长领.道德权利基本内涵探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4]甘绍平.论道德义务的人权基础[J].哲学动态,2010,(6).
[5]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2.
[6]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7.
[7]余涌.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相关性问题[J].哲学研究,2000,(10).
[8]Ada Nesehke-Hentsehke,Tradition und Euas,Die Men sehenreehte und der Rechtsstaat als Frueht des antiken unde christlichen Denkens[M]//.in:Hans-Helmu thGander(Hg.),Menschenrechte.Philosophie und juris tisehe positionen Freiburg/muenchen.2009:28.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10]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N].联合早报,2011-10-04.
[11]李大钊文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04.
[12]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J].新青年,19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