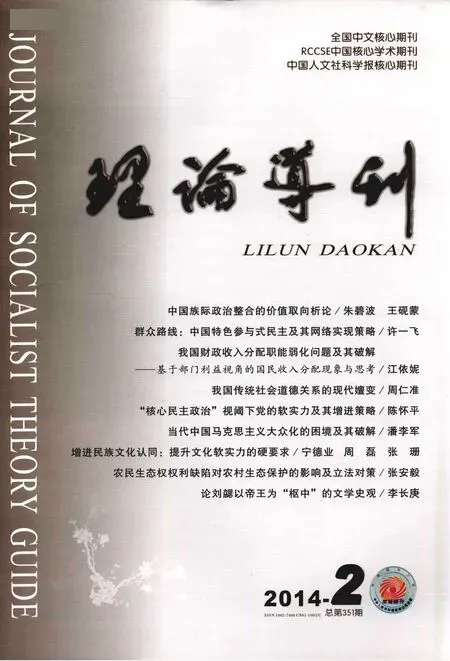论刘勰以帝王为“枢中”的文学史观
李长庚
(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710127;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文史部,西安710061)
一、“环流无倦”是刘勰“通变”文学史观的形象表述
《文心雕龙·时序》篇赞云:“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僾焉如面。”刘勰用“环流无倦”来形容文学的发展状态。《鹖冠子·环流》有:“美恶相饰,命曰复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陆佃注:“言其周流如环。”“环流”有循环往复之意。汉刘向《说苑·杂言》:“孔子观于吕梁,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里。”明郑真《题画》诗云:“万仞苍崖壁立,双溪碧水环流。”“环流”是指回环曲折地流动。单纯从字面意思理解,“环”就是“圆”,“环流”就是“圆周运动”,“不倦”就是不知疲倦,永不停息,“环流无倦”就是描述事物发展运动状态象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和本身自转一样,周而复始、永不停息地做圆周运动。唯物辩证法称事物的这种发展变化规律为“否定之否定”规律。
刘勰用“环流无倦”来描述文学“曲折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发展道路,表达了“通变”的文学观念。《通变》篇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运周”有回环运转之意。《后汉书·律历志下》:“天之动也,一昼一夜而运过周,星从天而西,日违天而东,日之所行与运周,在天成度,在历成日。”[1]把文学的发展轨迹看成是一种“循环相因”的“圆周运动”,但文学的发展并不是简单重复,周而复始,而是“日新其业”。文学无论如何发展演变,如何“参伍因革”,“负气适变”总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通变》)所以,文学发展,既要“变骚”,还须“宗经”。“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刘勰把文学发展描述成为一种“环流无倦”的圆周运动,思想源于周易阴阳观念、通变观念,以及传统的“质文代变”的观点。《史记·平准书》谓:“物盛而衰,时极则返,一质一文,终始之变”。文学的构成因素被“一分为二”为两部分:“文”与“质”,相当于“阴阳”关系,“文质”既对立统一,又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情采》)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阴极而阳生,阳极而阴生”的循环过程,文学发展也是一个“质极而文生,文极而质生”的互相转化的过程。“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时序》)。同时,文学发展也是盛衰交替的过程,《论衡·齐世篇》论述:“文质之法,古今所共,一质一文,一盛一衰,古而有之,非独今也。”[2]南朝文学“踵其事而增其华”,偏向于“新奇、浮艳”,陈子昂反对“彩丽竟繁,兴寄都绝”的齐梁文学,主张“文质并重”,倡导恢复“汉魏风骨”,为“走向盛唐”廓清了道路。陈子昂的文学主张既可以理解为复古,循环,又可理解为创新,变化。《周易·系辞》说:“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一开一合,往来不穷,就是“通变”。“环流无倦”是对文学发展“通变”规律的形象描绘。
二、“枢中所动”与支配和影响文学发展的主导因素
“枢中所动,环流无倦”,是什么因素处在“枢中”之位,其“所动”,即变化造成了文学发展的“环流无倦”呢?枢(樞):门上的转轴,枢中:枢要,中心。刘勰在文中所使用的“枢纽”、“枢要”、“环中”、“关键”等词,与“枢中”意义基本相同,都是指支配左右事物运行变化的中轴。“‘枢纽’是事物运行机制中起关键作用的部位或环节。”[3]
“文变染乎世情”。(《时序》)“世情”对文学发展影响确实较大,但所起作用,发挥之功效,在刘勰看来也不过是文学被“染”而已,不足以占据支配文学发展的“中心”地位,何况刘勰并未在《时序》篇中大篇幅论述“世情和文学”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是在论述晋代文学状况的时候,略作陈述而已:“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时序》)西晋“玄风”盛行,文学的风格从汉魏的慷慨悲歌变为“辞意夷泰”,文学的主题由体物写志变为老庄思想之义疏,刘勰因此发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感慨,而其它“十代”复杂多变的“世情”,究竟怎样“浚染”文学,刘勰并无一一详论,而仅仅是以“原始要终,百世可知”的方式推衍而知。
“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兴废既然系在“时序”之上,“时序”自然应该成为文学发展的决定因素。现代人叙述历史,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为参照物,采用的是“朝代+公历年份”的纪年方式,如:“安史之乱”发生在唐朝,公元755年。古人叙述古代历史,以“帝王更迭”为参照物,采用的纪年是“朝代+帝王年号+年份”的方式。如:安史之乱发生在唐朝,天宝(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二个年号)14年。把“时”理解为朝代顺序,虽然也能讲通,但是朝代的时间跨度太大,不足以标识文学发展的清晰脉络,不足以说明文学崇替、质文代变的根本原因。古人用皇帝的年号纪年,帝王作为“天子”具有记载“天时”的功能。朝代是一姓一族之天下,帝王是一人之天下。以“帝王”做为文学史叙述的时间标识,比朝代远为详细、精确,更能清晰地反映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
结合《时序》篇具体内容看,“序”就是文学有自身发展的顺序,如:“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而“时”,大范围讲是朝代顺序,更详细。具体地说,就是帝王代变之序。文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过程(序),一方面受帝王因素(时)的影响和支配,这就是“兴废系乎时序”的思想实质。帝王因素是支配、影响文学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帝王之变就是刘勰思想中所谓的“枢中所动”。
三、“帝王”占取刘勰所谓“枢中”之位的理由
刘勰在《时序》篇中依次叙述了53位帝王统治下的文学发展概况。其中上古时期的帝王8位,依次为:陶唐、有虞、大禹、成汤、姬文、大王、幽厉、平王。西汉的帝王11位,依次为:高祖、孝惠、文景、孝武、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东汉的帝王10位,依次为: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献帝。三国时期的帝王3位,依次为:武帝、文帝、明帝。西晋的帝王4位,依次为:宣帝、武帝、怀帝、愍帝。东晋的帝王9位,依次为: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恭帝。南朝的帝王8位,依次为: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齐文帝、齐明帝。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国君众多,只能以国家论之,涉及韩魏、燕赵、秦国、齐楚等7国。
如果仅仅着眼于文学随时代的发展,或者政教、世情风俗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刘勰毋须罗列如此数量众多的帝王。历史上一些充当装饰品的傀儡皇帝,寿命短促的“流星”皇帝,无所作为的庸碌皇帝,对文学发展影响微乎其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只字不提,刘勰却一一罗列。如“降及怀愍,缀旒而已”,“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还有一些禁止文学、尚武轻文、醉心权术的帝王,刘勰也如实记录了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如“五蠹六虱,严于秦令”,“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这样一种“流水帐”式不厌其烦的叙述方式,给人一个鲜明的感觉是,其用心处不只局限于叙述文学随时代发展的情况,而同时想要说明文学发展与君主更迭之关系,为文学史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叙述模式。
种种迹象表明,刘勰“秉笔直书,采善贬恶”,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每位帝王对文学、文人的态度、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正如鲁迅先生写日记一样,碰到无事可写的时候,也不忘记上一笔“今日无事”,只有这样,才可以称为“日记”。刘勰如此叙述文学,因为“帝王代变”就是文学的“时钟”、“日历”,遗漏了一个帝王也就遗漏了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文学可以起到美化政治、巩固政权的作用。一些雄才大略的皇帝参透其中玄机,利用文辞粉饰功业,教化百姓,如汉武帝。“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时序》)古代封建社会,文士地位之高低,与帝王好恶息息相关。“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难怪司马迁慨叹:“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汉武帝重视文人辞赋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繁荣文学,而在于维护其统治,但是刘勰完全肯定了他对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对于他礼遇文士,推崇文学的所作所为,刘勰褒赞之情溢于言表。“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盛。”(《时序》)在刘勰看来,辞赋之所以兴盛,汉武帝推崇的功劳首当其冲。刘勰把汉武帝推崇、树立为帝王中重视文学的典范,楷模,将晋明帝比为“当时之汉武”。“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 (《时序》)
刘勰叙述汉武帝时代的文学,没有限于文学本身、完全侧重于汉武帝对文学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从汉武帝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枢中所动”的影响效果。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帝王是整个国家,社会运转的“枢纽”。刘勰在《封禅》篇这样论述:“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封禅》)帝王运用政权养育百姓和贤人,就像天帝运转天枢星一样。周易形象地把君和民的关系比作“乾坤”关系,“坤之道,至柔至顺”,“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易·坤》)臣民之道就是顺应和围绕帝王运转之道。社会风俗、政治教化,这些影响文学演变的因素,均是以“帝王”为中心展开的。
刘勰以帝王为“枢中”的文学史观,与其“神道设教”的文体功用思想密切相关。文学有审美功能,但发挥着“神道设教”的政治教化功能。诗、乐府是言志和写心之作,也具有教化之功用。如《明诗》赞云:“神理共契,政序相参。”“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乐府》)赋,在体物写志的同时,也要有益劝戒。“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刘勰所论之文体,如颂赞、祝盟、铭箴等都有祭祀、礼乐教化功用,诏策、檄移、封禅有帝王行使政治统治功用,章表、奏议、议对具有向皇帝上书言事的功能。许多“文体论”篇次都是论述帝王开篇的。如《诏策》:“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帝王是整个封建社会运行的“枢中”,自然是文学运动变化的“枢中”。政治教化、世情风俗只不过是帝王影响文学的中间环节。
四、帝王因素对文学演进的影响及“帝王代变”与“文学崇替”之关系
帝王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影响”,包括帝王热衷文学创作,引领文学潮流,赏纳礼遇文士、组织文学活动,领导文学集团,编撰文集等。另一类是“间接影响”,帝王通过崇儒、礼乐、讲经、图谶、图籍、兴办学校、科举制度等政治教化的方式影响文学的走向,也可通过自身统治改变“世情”和民风来影响文学。
有些帝王本身就极具文学天赋,才华横溢,成就斐然,可与文士媲美争雄。“据《隋书·经籍志》,南朝诸帝有文集的有宋武帝、文帝、孝武帝、梁武帝、简文帝、元帝、陈后主,其中梁简文帝以下散文更以提倡和创作诗文为务,从存世的作品看,大都具有相当水平。”[4]有些帝王喜好文学,以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引领社会风尚;“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5]裴子野《雕虫论序》云:“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祯祥,及幸燕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6]有些帝王赏纳文人,礼遇文士,聚拢天人才;“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来接待文学之士,汉灵帝开鸿都门来接待辞赋家,魏明帝置崇文观来延揽文士。有些帝王喜爱某种文风,御用文人唯帝王嗜好为从,创作某种风格相近的作品,形成某种创作潮流。如萧刚提倡与宫体诗风的风靡,唐太宗喜好与宫廷诗风的延续。有些帝王通过崇儒、讲经的方式,影响文学的风格和题材,如汉昭帝、宣帝时期举行的“石渠阁”论经,东汉章帝时期举行的“白虎观”讲经,都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些帝王崇尚图谶、图书、聚众讲学、兴办教育,也不同程度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文士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其创作的动机、心态、欲望都是影响文学的主要因素。如果帝王礼遇文士,重视文学,那么文士创作的热情就高,欲望就强,文学相对也比较繁荣(“兴”),例如:南朝帝王对文学的重视与提倡,促成了南朝文学兴盛的局面。相反,如果帝王漠视文学,轻视文人,甚至“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则文学发展会相对处于低谷状态(“废”)。当然,也不排除特殊情况,如“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即便如此,由于帝王不重视,时运不济,文人也不能人尽其才。“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刘师培在《宋齐梁陈文学概略》中曾论述:“宋代文学之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7]如果帝王喜欢文采飞杨的翰藻之文,那么帝王的嗜好必然煽起竞相藻饰的文风,那个时代的文学发展会偏向“崇文”(“文”)。如果帝王注重儒术、经学,“历政讲聚”,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相对偏向于“宗经”、“尚质”,“华实所附,斟酌经辞”(“质”)。文学崇替、质文代变都与帝王之文艺政策具有密切关系。
从刘勰对汉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帝王代变”和“文学崇替”的关系。西汉建国之初,汉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轻视文学和经学,文学发展处于低潮时期(“废”),只有“大风歌、鸿鹄歌”等少数优秀作品。惠帝、文帝、景帝时代重视经术,不重视辞赋,文人得不到重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文学处于质朴无华的时代(“质”)。汉武帝时代,既重视经术,又重视辞赋,重用辞赋作家,所以文学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兴”和“质文并重”)昭帝、宣帝时,又贬低辞赋,崇尚经学(“质”)。哀帝、平帝是时期,文学“降意图籍”,文学随着国力衰落而处于相对衰落时期(“废“)总的来说西汉是崇尚文辞的“尚文”时代,辞赋发达。东汉是注重经学的“重质”时代。
文学发展“质文沿时,崇替在选”。一废一兴,一质一文,“环流无倦”。(一兴一废是对总趋势的描绘,并不意味着“兴”的后面就是“废”)帝王代变,则文化政策、政教世情、文人地位变,文学发展之“时”变,则文学阶段特征也会变,文学演进之“序”变。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文学发展之“环流无倦”皆因帝王更迭之“枢中”所动。
[1][东汉]班固·汉书(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东汉]王充.论衡(下册)[M].大东书局,1934:21.
[3]王少良.文心雕龙·通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25.
[4]曹道衡,沈玉成.中国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9.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四册·齐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