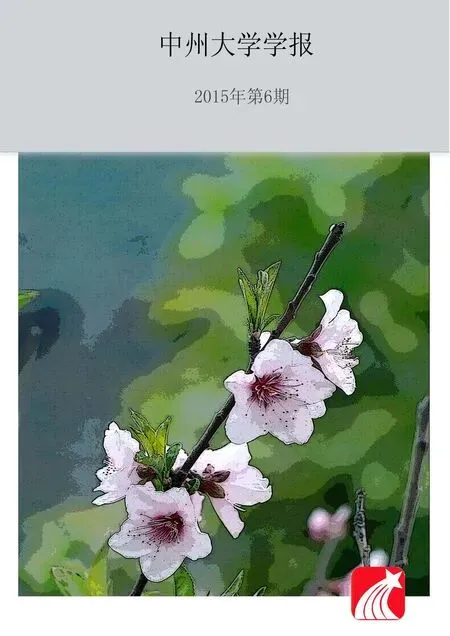“胡子”行状与“流浪汉”身份认同
——萧军的精神肖像
刘 忠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胡子”行状与“流浪汉”身份认同
——萧军的精神肖像
刘 忠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在萧军的精神世界里,“远方”和“流浪”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远方”延伸着萧军的追求空间,“流浪”丰富着他的精神内涵。从东北到上海,从武汉到山西,从延安到成都,又从成都到延安……漫漫跋涉路上,敢做敢为的“胡子”精神始终伴随着他。他渴望一种坦诚的交流,一种生命的恣意。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我们读不出当年朱光潜极力称道的那种纯美的“静穆”之境。这是一个奔放不羁的灵魂,一个永远走在路上的流浪汉。他的豪爽粗犷、重义尚侠,让人不禁想起勇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萧军;胡子行状;流浪汉;身份认同;精神肖像
描述萧军的精神肖像,“远方”和“流浪”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远方”延伸着萧军的追求空间,“流浪”丰富着他的精神内涵。从东北到上海,从武汉到临汾,从延安到成都,又从成都到延安……漫漫跋涉路上,“胡子”行状与“流浪汉”气质始终伴随着他。在他身上,找不到中国诗教“温文尔雅”的传统,他的豪爽粗犷、重义尚侠,让人不禁想起勇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一、阴沉的土地和不屈的灵魂
说起萧军,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35年7月,《八月的乡村》由鲁迅作序并推荐给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小说以“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为背景,描写一支人民革命军抗击日寇的故事,塑造了司令员陈柱、队长铁鹰、战士唐老疙瘩、李七嫂、李三弟等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被誉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鲁迅在序言中给予高度评价:“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部分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1]287胡乔木称赞“《八月的乡村》带给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在神圣的民族战争中,谁是先锋,谁是主力,谁是可能的友军,谁是必然的汉奸,已经画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2]。
《八月的乡村》延续了萧军一贯的创作旨趣。早在1929年,还在东北陆军讲武堂从戎的萧军,就在《盛京时报》副刊上发表处女作《懦——》,愤慨于军阀虐杀无辜百姓的麻木不仁,竟然将曝尸野外的人的头颅当球来踢。虽然只是一篇短文,萧军却把它看作是与“剑术”“拳术”同等重要的又一个武器[3]191。1931年,他在《国民日报》副刊发表散文《暴风雨中的芭蕾》,揭露日寇侵略沈阳犯下的累累罪行。1933年10月,在好友舒群、罗烽、白朗、金人、杨朔、裴馨园等人的资助下,萧军和萧红出版小说散文合集《跋涉》,收入“三郎”(萧军)《桃色的线》《烛心》《孤雏》《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6篇,“悄吟”(萧红)《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5篇。
《跋涉》问世之时,东北文坛充斥着言情、武侠,甚至歌颂“王道乐土”的杂音,萧军一改这种贫血、羸弱文风,以粗犷的笔触表现日伪统治下普通民众的苦难和抗争。《桃色的线》写一个流浪青年在饥饿难耐之际,将自己钟爱的姑娘补缀过的一件绒衣典当出去。《孤雏》情节较为曲折,一开始写穷困潦倒的文学青年在街灯下构思小说,巧遇友人之妻怀抱孩子沿街乞食,友人因在军校替人打抱不平、出手打伤队长遭到除名,并在慷慨陈辞一番之后没了踪影。眼前的一切牵动着文学青年的侠义心肠,他决定以卖文稿所得来接济友人的妻子。孰料结局却让人感到意外,友人妻子留下一函,将照看孩子的事情悉数托付给了文学青年,自己则远走天涯,与丈夫相会去了。《烛心》《下等人》控诉日伪统治者的血腥残暴,表现人们的觉醒和反抗。《跋涉》的反剥削、反压迫主题,不仅鼓舞了东北沦陷区人们的反抗斗争,也确立了萧军小说的主题走向。
《八月的乡村》出版之后,萧军就着手写作《第三代》。《第三代》从日常化生活场景入手,塑造了一批有着“胡子”性格的人物形象,刘元、杨三、海交、半截塔等一群啸聚在东北羊角山的绿林好汉。他们虽然干的是杀富济贫的勾当,却从不骚扰周围的农民,与前来剿匪的军队相比,军队倒更像一群匪徒,海交等人的“土匪”之名不过是旧世界加予他们的蔑称而已。他们有严格的行规,“不准弄女人”,“不准劫掠百姓”,“反抗官府,打击日寇”。在当地人眼里,“胡子”们干的是对抗官府、打击日寇的事情,是农民们摆脱苦难、雪恨复仇的“救星”。不仅刘元、杨三等男人投奔绿林,翠屏这样的农村妇女也选择羊角山的强盗窝作为避难之地。小说很好地表现了胡子的“匪徒——英雄——普通人”的复杂性格和多维人生。
《第三代》不以紧张的情节取胜,而以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触动读者的心灵。小说结构看似松散,实则缜密精细。杨义说:“《第三代》正是聚集粗豪和细致两端,达到艺术上的浑厚境界的,总括萧军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最见艺术功力的是《第三代》,最有社会影响的却是《八月的乡村》了。”[4]546
二、“胡子”行状与“流浪汉”身份认同
与萧军有过接触的人,几乎有着相同的印象:豪爽粗犷,重义尚侠,堪称东北“胡子”。他的性格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人称颂和引起争议并存。读过《鲁迅先生书信集》的人都知道,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两年间,鲁迅收到单独由萧军署名的书信为59封,萧军、萧红联署的6封,共计65封。先生的回信53封,其中,致萧军的33封,二萧并称的19封,单独致萧红的1封。从书信集的整体风格来看,鲁迅给萧军的回信,谈论处世之道的特别多,主要是处理文坛人际关系,真诚而友善,一方面因为萧军初到上海,人地两疏,鲁迅如同父亲一般,关心帮助文学青年;另一方面鲁迅认为萧军虽然豪爽,却失之于粗鲁,怕他吃亏。尽管有过鲁迅先生的叮嘱,但萧军依旧故我,率真得近乎莽撞,鲁迅批评过的许褚、李逵式的“赤膊上阵”行状,在延安和东北都上演过。
萧军一生两次去延安,他独立不羁的性格和文艺界的宗派旧习,使他一直未能从精神上融入延安。1938年3月21日,他第一次去延安是“路过”,准备去五台山打游击,因战事阻隔,路途不通,才住进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巧遇西北战地服务团负责人丁玲、聂绀弩从前线回来向中央汇报工作,也住在招待所。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派秘书和培元前去看望。和培元询问了萧军的行程起居之后,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却说:“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和培元走后,丁玲对萧军说,“毛泽东这人很了不起,你应该见见再走”,萧军并不以为然[5]。直到有一天上午,毛泽东亲自到招待所看望萧军,共进午餐,毛泽东平易近人的态度,让萧军深受感动。在延安的两个星期里,他读到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论鲁迅》,对毛泽东更加尊敬。4月1日,萧军应邀参加陕北公学第二届开学典礼,会后他和毛泽东、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在操场上一起会餐,没有凳子,大家站在桌子周围,大碗喝酒,高声交谈,那种“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场面,非常投合萧军的脾气,使他激动万分。原来延安也有古道热肠,他由衷地感到自己是“同志”中的一员,不再是一个“过客”。就这样,萧军戏剧性地与圣地结缘,成为了“延安人”。
1938年6月,萧军离开延安,流浪到新的驿站——成都。在萧军的一生中,第一次延安之行带给他的是寻找和观望,是一群有着相近气质和不懈追求的共产党人。从他们身上,萧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但是,与丁玲、艾青等知识分子不同,作为精神憩息地,延安仅仅是一个驿站;对于真正的流浪汉来说,心灵的驻地永远在“远方”、在“彼岸”。1940年6月,因不堪忍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迫害,萧军一家再度踏上延安的土地。此番重来,他的心境十分复杂。起初,他尚能沉醉在延安自由的空气里,与画家张汀在兰家坪山脚下放声歌唱。很快,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军事化管理与萧军独来独往、狂放不羁的个性产生抵牾,一颗恣肆的灵魂开始躁动起来。据刘雪苇回忆,一天他从张闻天那里出来,见警卫连的战士和萧军吵架。近前一看,萧军正在甩大衣,要打架。问起原因,萧军说,当他路过时,有战士在山上讽刺他,而且不只一次了,这回他要找那个战士“决斗”。刘雪苇认为,从这件事可以见出萧军的孔武率真本色,仍留恋于“血气之勇”[6]。
渐渐地,萧军也发现自己那一套“胡子”行状与延安整齐划一的等级分配制有着不和谐之处,再次萌生去意。1941年7月下旬,萧军到毛泽东那里去辞行,直言不讳地谈了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间的宗派作风,表示自己要回重庆直接和敌人战斗。后来,在毛泽东的劝说下,萧军勉强留了下来,帮助收集文艺界情况,以供将来制定文艺政策时参考。8月2日,毛泽东复信萧军说:“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5]看得出来,毛泽东对萧军的率性、反叛的性格是非常了解的,对其内心的英雄情结也颇为欣赏。
抗战胜利后,萧军一家来到哈尔滨,在东北局宣传部的资助下,创办《文化报》,自任主编,报纸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发行量攀升至每月七八千份。在这块阵地上,他尽情地宣讲“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不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作为一个‘人’,全应有它的自尊心,不能够容忍任何外力加以侮辱和玷污”[6]。在一个正在树立“革命话语”权威的时代,萧军的启蒙主义主张显得很不合时宜。
1947年7月,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又创办了一份报纸《生活报》,领导人是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主编则是30年代与鲁迅、胡风、萧军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有隙的“国防文学”派剧作家宋之的。《生活报》创刊伊始就在第一版版心位置以醒目标题发表短文《今古王通》,用隋末“妄人”之口,来警告“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己,吓唬读者、迷惑群众”的“今之王通”,矛头直指萧军的启蒙主义言论。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萧军自然不会明白其中的深意,当即还以《风风雨雨话王通》,作为回应。1948年8月26日,苦于抓不到把柄的《生活报》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就《文化报》纪念抗战胜利三周年社论里的一句话大做文章,给萧军戴上了“挑拨中苏民族仇恨”“反对人民的解放战争”的帽子。面对《生活报》的责难,萧军反击说:“什么‘帽子满天飞’主义,随便罗织人罪的主义,这全是封建社会、过去伪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得意手法。”这在他的批判者看来,是无视党的领导,公然与党对抗的行为。1949年5月,先由东北文艺协会做出《关于萧军及〈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后由高岗、林彪领导的东北局做出《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将萧军所犯“错误”定性为“用言论来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很显然,判定萧军“反苏、反共、反人民”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提出的问题却是实质性的——知识分子与“新政权”的关系。新政权正在建立,它要求思想、政治、意志高度统一,萧军式的独立和自由是难以容忍的。这不仅是一个思想取向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文化报事件”之后,东北局“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萧军被组织“安排”到抚顺煤矿去接受“思想改造”。在煤矿,他与矿工们朝夕相处,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
新中国成立后,在彭真的关照下,萧军来到北京,当起了一名文物研究员。50年代“反右”运动中,萧军又和胡风、丁玲、艾青、罗烽等一起成为被批判对象,“他成为一个在故乡的旷野上终日漂泊的幽灵,被家宅里庆祝太平盛世的合唱声驱赶了出来,在社会底层和文化边缘处独自徘徊”[7]。“文革”中,萧军遭到批判、关押、毒打,但与其他文化人不同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个人思考的权利,始终维护人格的尊严。1966年8月23日,200多名红卫兵将老舍、萧军、骆宾基、荀慧生等28位著名人士押到孔庙院内,进行轮番侮辱打骂。萧军晚年回忆说:“当时我真想以死相拼,凭我的体力和武艺,随便夺下一件兵器,就可以打翻10个、8个打手。我死了不要紧,那20多位难友会是什么结局?历史又将如何写这一笔呢?”[8]这次毒打的第二天,不堪侮辱的老舍投湖自尽,而萧军却选择了横眉冷对地活下去。萧军性格中有着特殊的坚韧和顽强,正因如此,当真正的春天来临时,人们发现他还是那样坦荡、达观,锋芒不减。
李健吾谈到萧军时说过一句话,“他有十足的资格做一个流浪人”[9],可谓是知人之言。思想的种子历来难以在不安的灵魂中孕育,在一个动荡的年代,行动显得尤为迫切。萧军渴望一种坦诚的交流,一种生命的恣意,太多的文饰和骄矜不属于他。在他的人生之途中,我们读不出当年朱光潜极力称道的那种纯美的“静穆”之境,“他非要把自己燃烧在里边不可”。这是一个奔放不羁的灵魂,一个永远走在路上的流浪汉。
三、说不完的萧军和萧红
在萧军的一生中,鲁迅、萧红是两个无法忽视的人物。
在鲁迅晚年,与先生交往密切的青年作家中,萧军、萧红这一对从东北流亡上海的夫妇,可谓是获得关爱最多的两位。无论为文还是为人,鲁迅都给予二萧很多帮助。大到指导写作、推荐出版,小到日常生活起居、人际交往,都呵护备至。1936年10月19日,鲁迅辞别人世,他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寄予厚望的两位青年作家,日后的人生道路走得如此坎坷。1942年1月,一代才女萧红瘐死战乱中的香港,给人们留下无边的寂寞。而萧军,这位曾被先生郑重地向埃德加·斯诺推荐,并纳入“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作家”之列的知识分子,更是命运多舛。从延安的“王实味事件”到东北的“文化报事件”,从“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右派到“文革”期间的“牛鬼蛇神”,萧军一直是历次运动被批判的对象和靶子。
在上海的两年时间也许是萧军生命中最值得庆幸的日子。二萧比翼文坛,师事鲁迅,结交文艺界友人:叶紫、黄源、聂绀弩、胡风、巴金、黎烈文、周文、吴朗西、靳以、曹聚仁、傅东华、郑振铎、陈望道、郑伯奇、赵家璧等。萧军尽情地挥洒着个性,分享成功的喜悦,同时也承受着左翼内部矛盾带来的痛苦。为此,萧军还特地给鲁迅写信,请教要不要改掉不拘小节、举止粗鲁的“野气”。先生回信说:“所谓‘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行不同之处,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时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您记得《三国演义》中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10]621萧军当时是否听得进去,不得而知。
鲁迅对萧军的影响是巨大的,萧军对鲁迅的崇敬也是绵长的。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萧军编完《鲁迅先生纪念集》,到鲁迅墓前焚烧刊有纪念特集的《中流》《作家》和《译文》,招致张春桥、马吉蜂在一家小报上撰文讽刺,他当即用自己的拳脚功夫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文革”期间,姚文元利用自己控制的出版社出版《鲁迅杂文书信选》,在《致萧军》一信中将鲁迅指责其父姚蓬子叛变的那段文字删掉,对此,萧军不顾身处逆境,立即去信责问,将姚文元最头痛的文字随信附上,迫使姚文元尊重事实。
张毓茂指出,“萧军先生性格的刚烈,勇敢和暴躁,人所共悉。但他磊落宽厚的胸怀,仁爱深情的体现,却在一片诽谤声中为世人所忽略。其实,他是讲义气、重感情、不计较个人恩怨的人。他一生经受的委屈、诬陷和打击无法计数,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作家中也是罕见的。然而,萧军对于伤害过他的同志和朋友并不耿耿于怀,见了面哈哈一笑了之”[11]319。萧军和丁玲很早就是朋友,在延安,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丁玲曾发言、写文章批判过萧军。“文革”中,“四人帮”抓住鲁迅给萧军信中的一段话大做文章,把丁玲诬为叛徒。萧军知道后,以当事人的身份为鲁迅信中的话做了长长的注释,说明“四人帮”的所作所为“纯属是一种无知或恶意的诬枉之辞”。为此,丁玲非常感动。萧军对误解过、批判过他的人,只要道歉了,都原谅宽恕。胡乔木晚年曾给萧军写过一封信,大意是说:多年来经历了生生死死的考验,如今人都老了,回想起多年前在延安,由于自己的年轻,曾经伤害过你,内心总感到非常的沉痛,向你道歉,请你能原谅。萧军当即复信写道:“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罢!从头提起,只能徒增一些不可补救的懊恼而已。我青年时期,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于人于事拙于处理方式方法,树敌颇多,伤人太重,因此招到任何攻击和打击,决无怨尤之情,正所谓‘种瓜得瓜,种疾藜得疾藜’是也。”[12]新时期,萧军复出,许多人希望他能够续写《我的生涯》这部自传,他表示:仇恨、对立就到父辈这一代中止吧!不写回忆录,主要为一些对立面同志的子孙着想,孩子们是无辜的,不应当承担他们父辈所犯错误的责任。
萧军和萧红的结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1932年夏季的一天,哈尔滨《国际协报》编辑部收到一封署名张乃莹的求救信,信中说:“他与未婚夫一道从北平来哈尔滨,怀了孕又被遗弃,因为欠东兴顺旅馆600多元食宿费而被老板软禁,并准备将她卖入妓院,恳请报社主持正义,救她脱险。”报社副主编裴馨园阅信后,派萧军、方靖远、孟希去旅馆交涉,萧军在二楼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小仓库里发现了萧红,萧红得知眼前的青年正是自己感佩的连载小说《孤雏》的作者时,一见如故,向萧军倾诉自己的不幸身世。闲谈中,萧军看见萧红在几张报纸上胡乱涂抹的诗句和字画,决定要尽一切办法救出这位才女[13]。二萧的相遇注定充满了故事,英雄救美人历来都是充满想象和期待,更何况救的是才女呢!事实证明,两颗年轻的文学心灵的碰撞,激发出难以遏制的创作热情,从1932年两人结婚到1938年分手,尽管两人的婚姻生活时有阴晴,但他们收获了创作的喜悦,出版了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确立了他们在现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关于二萧的结合,有研究者认为,“当初二萧结合时,爱情天平就不对,是偏向萧军一边的……”贾植芳先生说:“这种说法,其实是很难受到事实的检验的。如若按照这个结论,似乎当初萧军根本不应该救萧红出火海,或者换言之,萧军这番义举是大错特错了。似乎当初萧军救萧红并非是出自侠义,而是另有图谋的……”[14]真实的情况包括萧红自己的描述是:一个怀了别人的孩子将要分娩的女人,一个虽有文学潜质却没有发表作品的文学青年。而萧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无经济来源,二无固定的工作,自己都养不活,何以让他做出营救萧红并与之结婚的行动呢?作为二萧共同的朋友,舒群的解释是:虽然两人的结合有偶然因素,但在当时,如欲救出萧红,除了同居结为夫妻之外,别无办法,她一无居所、二无职业、又怀了孕,无法独立生活。
两人结婚之后,萧军冒着严寒,四处工作,养活在家待产的萧红。正是在萧军的鼓励下,萧红在《国际协报》上发表处女作《王阿嫂的死》,迈上了文学之路。也是在萧军的提议下,两人认识鲁迅,并在先生举荐下,他们出版了饮誉文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漂泊的生活因为两人举案齐眉的创作,而有了许多生气。另外,他们还通过师从鲁迅而认识了许多文学界朋友。据许广平回忆,二萧中,鲁迅更看好萧红,“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15]18。不知一向争强好胜的萧军听此评价,该做何感想!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从1932年夏到1938年春,二萧的婚姻之路走到尽头。关于二萧分手的原因,贾植芳曾说:“整整一个甲子以来,我们一直被某种单一方面的叙述左右看。生前,萧红以其‘被受暴虐’的‘屈辱’面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在其客逝香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也一直反复引用萧红生前的‘诉说’加以佐证,然而,人们似乎从来没有听过萧军有关这方面的辩解或说法。”[14]1978年萧军复出,他回顾说:“在我的主导思想是‘恃强’,她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因此,在我是不能具有托尔斯泰那样的‘基督教’式的谦卑,说‘一切都是我不好’,我也不能责备或诬枉已死者,说‘一切都是她不好’。这是有背于一个作为人的起码品质和道德的。”[16]152晚年,萧军曾经跟管桦说:“没别的原因,就是性格不合。她性格温柔安静,需要一个写作环境,一个舒适的小家庭。我性格粗鲁,决心走向抗日战场。”[16]289
二萧分手原因众多,有移情别恋、第三者插足等外因,亦有性格不合、感情危机等内因。从萧红、王德芬的信件和回忆来看,她们对萧军的性格描述较为一致:刚强暴躁,勇于武力,狂放不羁,有书生剑客之气。二萧的结合从一开始就存在角色错位,萧军总是扮演“保护人”和“救世主”的角色,而萧红则扮演着“被保护者”和“被拯救者”角色,这种互补性格在患难之初是合意的,不仅能帮助萧红摆脱困境,而且能够获得一种安全感。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的文学创作进步很快,这多多少少抵消了两人性格方面的摩擦和冲突。但随着萧红在文坛的崛起,两人的裂隙开始显现和扩大。萧红不再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文不名的弱女子了,一跃而为蜚声文坛的知名作家,自信心大增。萧军的轻慢和冷淡让她很不适应,两人的矛盾开始郁积,生性粗犷的萧军对于萧红的敏感、自尊缺乏应有的呵护和关心,致使两人出现沟通上的障碍。这种障碍不仅表现在精神层面,还延及两人的婚恋本身。萧红短促的一生被各种疾病纠缠,体质虚弱,在给萧军的信中,萧红曾感叹说:“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疾病使萧红更加敏感、脆弱,而对于自夸健硕如牛的萧军来说,病痛之苦是难以体会的。在萧红赴日疗养的一段日子里,萧军与一位叫H夫人的女性产生恋情。这次婚外恋对萧红的心灵造成很大伤害,为两人日后的离婚埋下了种子。
在二萧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端木蕻良的出现重新燃起萧红心中的爱情之火。虽然对端木的胆小懦弱萧红是有所了解的,但面对他热烈的爱意,萧红欣然接受了。1938年4月,三人在西安的一所中学碰面,当萧红对萧军说出“三郎,我们永远分开罢”,萧红听到一个“好”字,很快就走了出去……萧军后来回忆,“我们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有任何废话和纠纷地确定下来了”[13]。于是,萧红与端木蕻良返回武汉,过起同居生活。让萧红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爱情的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她虽然从端木那里得到了尊重和赞美,却并没有获得安稳和温暖,而是陷入更深的心灵痛苦和精神伤害。1938年8月,武汉战局吃紧,端木蕻良竟抛下怀孕在身的萧红,独自一人去了重庆。1942年日军空袭香港,端木蕻良抛下病中的萧红不管不问,把照顾萧红的任务托付给像萧军一样有着侠义心肠的骆宾基。
1942年,萧红逝世的消息传到延安,萧军沉痛地写下:“师我、教我者死了!知我、爱我者死了!”思念、痛惜之情溢于言表。晚年,萧军曾对女儿萧耘说:“因为爱她,我可以迁就。我像对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每忆起萧红“披着大衣,流着清鼻涕,时时搓着冻僵的手指,终于把《八月的乡村》复写完了”[17]358的情景,萧军总是感慨万千。
在萧军的性格中,有热情粗犷、豪爽任侠,也有鲁莽轻率、孤寂傲慢。他不是那种徇徇然的纯粹文人,他的血液里一直流淌着豪侠尚义的自我期许。这种融合特定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的心理情结始终左右着他的思维方式和生命状态。他不只是坐而论侠,而是起而行义,洪水中解救萧红、上海租界拳打“狄克”、抗战期间决意奔赴五台山前线打游击等一系列行为,大有书生论剑、慷慨救国的气概。梅志回忆,1955年胡风“反革命事件”中,萧军不顾自己的险恶处境,一次次徘徊在胡风住所东城烧酒胡同一带,想给老友一丝慰安。这些急公好义、解人之难的侠士风范,直到今天仍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
[1]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乔木.八月的乡村[N].时事新报,1936-02-25.
[3]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4]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王德芬.萧军在延安[J].新文学史料,1987(4).
[6]雪苇.记萧军[J].新文学史料,1989(2).
[7]谢泳.勇战风车的独行侠[J].黄河,1999(4).
[8]宋力军,闫鹏.人品文章标青史:百岁诞辰悼萧军[N].锦州日报,2009-06-22.
[9]李健吾.萧军论[N].大公报(香港),1939-03-07.
[10]鲁迅.鲁迅全集:第12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张毓茂.跋涉者:萧军[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12]王德芬.萧军与胡乔木的交往[J].读书周报,1993-12-25.
[13]郝庆军.在生存需求与浪漫爱情之间:对萧军与萧红及端木蕻良关系的几点考证[J].甘肃社会科学,2005(5).
[14]贾植芳.两个倔强的灵魂[J].文史春秋,1999(4).
[15]许广平.追忆萧红[M]//王观泉,编.怀念萧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6]秋石.呼兰河的女儿:献给萧红百年[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
[17]季红真.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Bandits” and “Little Tramp” Identity——Spiritual Portrait of Xiao Jun
LIU Zh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In the spirit world of Xiao Jun, “the distance” and “wandering” have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Far away” extends the pursuit of Xiao Jun, and “wandering” enriches his spiritual connotation. From Northeast to Shanghai, Wuhan to Shanxi, Yan’an to Chengdu, and Chengdu to Yan’an, on the road, “bandits” spirit always accompanies him. He is eager for a frank exchange a kind of life. This is a free soul, a tramp always walking on the road.
Xiao Jun; bandits; tramp; identity; spiritual portrait
2015-10-2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写文学史思潮与上海批评家群体”(11BZW101)
刘忠(1971—),男,河南固始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6.001
I206
A
1008-3715(2015)06-0001-06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