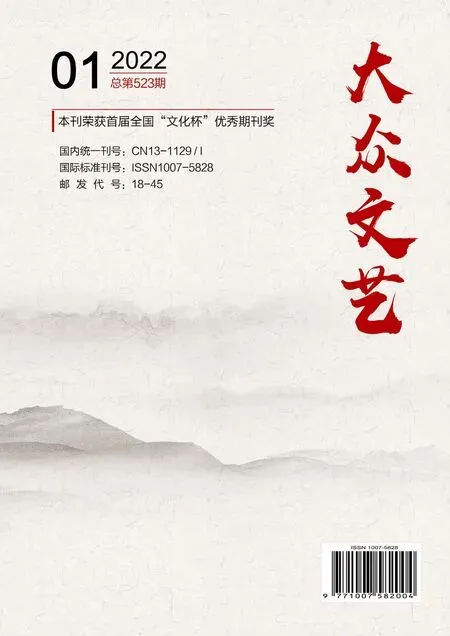鲜卑史及其考古学文化相关问题研究
毛远广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510075)
鲜卑史及其考古学文化相关问题研究
毛远广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510075)
鲜卑族系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族源属东胡部落,兴于大兴安岭山脉。先世是商代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从大兴安岭一带南迁至西刺木伦河流域。曾归附东汉,匈奴西迁后尽有其故地,留在漠北的匈奴10多万户均并入鲜卑,势力逐渐强盛,最终成就代魏之业。笔者关注的重点在于鲜卑起源及早期社会状况、鲜卑与乌桓的关系和鲜卑墓葬及相关研究方面,以期探考鲜卑文化的些许问题。
鲜卑起源 鲜卑与乌桓 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 鲜卑墓葬迁徙
鲜卑是我国古老的北方民族,主要活跃于两汉及魏晋北朝时期。其部署有拓跋、慕容、宇文和段四部,后在东汉晚期形成了“八部”“十姓”,并在十六国时期陆续建立过很多政权,包括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及西燕、吐谷浑和代。对于鲜卑的研究,自近代以降,历史学方面发端于上世纪30年代,以林慧祥的《中国民族史》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为代表。而考古学研究则发轫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赤崛英三和江上波夫对内蒙古包头茂旗百灵庙砂凹地6座鲜卑墓葬的发掘。此后数十年更是收获颇丰,即研究鲜卑名称来源、迁徙路线、早期社会状况等发展脉络被逐步勾画出来。前人研究筚路蓝缕,本文索引多家之言,却也对这一问题只是掠得惊鸿一瞥,暂且抛砖引玉,共议之。
一、鲜卑起源及早期社会状况
(一)所谓骑马民族
说起鲜卑,就不得不提及绵延数千年之久的骑马民族,所谓骑马民族,望文生义,即马背上民族,其存在与发展与亚洲相对地理环境不无关系。从亚洲湿润地带北部向西,东以兴安岭、阴山山脉、南山山脉,南以喜马拉雅、昆仑等山为界,向西延伸至里海、黑海北岸的欧亚内大陆,包括了蒙古、青海、青藏高原,一直到塔里木盆地、吉尔吉斯草原和南俄罗斯草原的干燥地带,深处内部,无法受南上暖流或北下海风之影响,雨量稀缺,满目草原和沙漠景观,而介乎湿润与干燥地带之间的山岳丘陵地区因为有着高山冰雪融化汇成的河流,故养育了以河流为依托的大小绿洲,在古代,被认为是粟特人和高加索人的活跃区域。1而游牧民占据的,主要就是欧亚内大陆的干燥地带和西南亚的干燥地带,这些草原的原住民,或半猎半农,半猎半牧,或半农半牧,逐渐发展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作为游牧民族一部分的匈奴和突厥,他们在长期称霸内陆亚洲的同时也觊觎中原地区充足的人口和财富,但对于中原之地,也仅仅是侵寇和掠夺,“上(汉武帝)乃下诏:‘……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资治通鉴》)而发源于东蒙地区的鲜卑及乌桓,却走着不同于匈奴和突厥的道路,早在新石器时代,他们便从事畜牧和粗放农耕相结合的生计方式,作为东胡之遗种,一方面深受匈奴影响,另一方面匈奴退居漠北时马上临阵倒戈,他们时而同匈奴一起南下入关侵略农耕区,时而作为中原王朝的门户镇守北疆同匈奴作战,这与其经济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我着重探讨一个问题,即在两汉直至魏晋期间,为什么鲜卑与乌桓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民族国家。窃以为原因有三:第一,在牧主农辅的经济结构下,鲜卑、乌桓较之匈奴更具地缘性,各部孤立性和封闭性较强;第二,从兴安岭直至北长城沿线系鲜卑、乌桓居住地,在日益增长人口的压力下,不得不依附于中原王朝,可反被较之先进的文化体系所分化其势力,滋长了各自为阵的倾向;第三,由于特殊的依附关系,致使乌桓、鲜卑一出现统一努力中原政府便立即进行打压(当然,到了西晋晚期,这种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鲜卑之源流
关于鲜卑之名由来,时人多有腓侧,一种言鲜卑最初为“带钩”,或言“衮带头”(郭落带),也有说鲜卑为一种鲜卑语名“郭落”之瑞兽,第三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即鲜卑是为山名,《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注曰:“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即言鲜卑之名由鲜卑山而来,史学界对其地理位置多有猜测,多指为辽河上游一带,《魏书·帝纪·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又言“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苏,简易为化,不畏文字……”略微分析不难看出,稍晚的史书记录竟然更加详备,不但有山名、地理环境概况、生计方式,其方位之说也遵循汉文化五行之说,其祖为黄帝之子昌意,实际上这种莫衷一是的文化依附性正体现了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同时,也能透露出一些信息,即后来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较之于东胡鲜卑,其族属和发展轨迹是有很多区别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鲜卑山与拓跋鲜卑发源地大鲜卑山是否同属一地?1980年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发现的北魏李敞刻石可与《魏书·礼志》和《魏书·乌洛侯传》记载比照,虽然对于嘎仙洞祝文关于拓跋鲜卑起源于南迁史实多有追溯之意,不可尽信,但是至少可以确定拓跋鲜卑曾经在这一带活动过。那么两座相去三千余里的鲜卑山又是为何?一些学者,如马长寿先生认为,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的划分导致了两个鲜卑山的出现,“从汉人的文献记载言,东部鲜卑在前,拓跋鲜卑在后,二者显然有区别。但拓跋鲜卑贵族统一中原后便把鲜卑名称霸为己有,对于鲜卑段氏、慕容氏称为‘白部’或者‘徒何’,对于宇文氏集团称为‘匈奴’”2,所谓东部鲜卑,是相对于拓跋鲜卑而言,是汉魏后形成的概念,确指活动于辽河流域的慕容、段氏部族,而冠以鲜卑称号的拓跋部,于文献中常出现魏晋后,公元2世纪中叶匈奴瓦解,《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盖因匈奴分裂后,其人民东移“诣辽东杂处”(《三国志·魏志·鲜卑传》)。《宋书·索虏传》也言:“匈奴有数百千种,各位名号,索头亦其一也”,马长寿先生在《乌桓与鲜卑》一书中认为“拓跋”一词,可能寓有“鲜卑父胡母(胡,一说指匈奴,也有说东胡之遗民)”之含义。这期间,鲜卑檀石槐建立了一个囊括蒙古草原的部落联盟,使很多游牧民族族称上发生了鲜卑化,因此,笔者认为同其他部族一样,拓跋鲜卑也经过了从“匈奴余种自号鲜卑”(即假称)到檀石槐鲜卑部落联盟之称,再到自觉以鲜卑为族称的阶段。 由此可见,“鲜卑”一词见于史册,当在东汉初。如出自战国人之手《逸周书 ·王会篇》及《山海经 ·海内西经》,甚至西汉初贾谊的《新书·匈奴》篇及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都只提到东胡与乌桓,未见“鲜卑”。而一些更早的史籍,如《国语·晋语》卷八之“鲜卑”(《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作“鲜牟”)、《楚辞·大招篇》提到“小腰秀颈,若鲜卑只”
(三)鲜卑族的社会衍变
鲜卑人兼营农猎牧,其狩猎主要是为了得到虎豹貂等野兽皮毛,然后作为商品交换到中原各地,人称“天下名裘”,《魏书·帝纪·序纪》载:“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农业上,以青稞、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为主,通常在夏季经营农耕,冬季再去打猎,因而各家户有固定居所,住房沿袭匈奴“房车”结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后汉书·乌桓传》,文献亦载吐谷浑“虽有城郭而不居,人民犹以氊庐百子帐为行屋”(《晋书·吐谷浑》)。他们多把头发剃光,只留头顶部分,《宋书·索虏传》言:“索头虏 ,姓拓跋氏”,即为一种索头的习俗,妇女婚时蓄发,将其分开编成发髻,头戴高大冠帽,是为“句决”,饰以黄金和碧石。饮食方面,除了食肉饮奶外,也食用部分粮食。部落管理上,数百数千邑落为一“部”,推举一位“大人”,不世袭,召集部众时,大人将刻有刻纹的信标传往各邑落,部众无一定氏姓,以大人之名为氏姓。到了东汉末年,男系子孙世袭倾向开始出现,但同时存在推举制度。《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注曰:“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这样的记述言母族、妻族对部落权利的影响,反之讲,也同样意味着父子相承的族外婚已经出现。与族外婚相适应的是嫂婚制的出现,即“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在结婚方式上,男子私通将女子带回己处,百日后使媒求婚,然后男子前往女家劳动两年,新居财物由女方供给,这样的以母族、妻族为主导的婚俗被认为是和后妃在政权组成中的居重地位有着直接关系。宗教信仰方面,鲜卑信萨满教,以牛羊为牲,崇敬天地鬼神,其中包含有山川崇拜、自然物崇拜(太阳崇拜,亦有一说为昆仑崇拜,即崇拜天地)以及动物崇拜,鲜卑以驯鹿为贵,也尊诸狼,这与其深厚的匈奴背景有关,葬俗方面,使灵魂上马,以狗为先导,直至守护灵魂至“红山”,北燕冯素弗夫妇墓壁画中绘有狗,亦有殉狗两只,《后汉书·乌桓传》或言:“肥养一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被认为是东胡旧俗,红山即为鲜卑人观念中彼界之地,往生之所。3
毋庸置疑,鲜卑族的社会衍变是在与中原文化交流中完成的,它体现在饮食、信仰、生计、葬俗各个方面,其中较明显变化的是信仰体系的变化,即佛、道之说的传入,早在代北时期鲜卑就有奉道现象,北魏太武帝拓跋珪、道武帝拓跋焘都不同程度的在鲜卑族内扩大了道教的影响力,较之于道教,佛教的传入稍晚,在拓跋鲜卑进驻中原之后,可能初情是为了使鲜卑族更快融入到汉文化体系之中做出的决策,值得商榷的是,虽然在政策上,大部分鲜卑族,特别是鲜卑贵族接受了佛、道之说,但民间信仰上,仍存在萨满教因素的崇拜,北魏太武帝禁止“私养师巫”,孝文帝时再次加强这一政策实施,可见,民间依然对萨满崇拜持亲近态度。
二、鲜卑与乌桓
(一)鲜卑与乌桓的共生关系
乌桓与东部鲜卑最初分布于蒙古草原东南部的西剌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乌桓在南,即老哈河流域,鲜卑在北,即西拉木伦河流域。这一区域可分为三个小区:西拉木伦以南为黄土地带,宜农业;西剌木伦以北,分为东西两区:西边为沙坵地带,宜游牧,东边是森林地带,宜虞猎。4与鲜卑相近的是,乌桓以妇女劳动为主,因为妇女社会地位高于男子,即使是邑落成立后,母权与舅权还是处于较高地位,以保留婚后夫随妻居制、服务婚制和母系氏族复仇制等风俗为体现。《三国志·魏志·乌桓传》称“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其完备的农村公社制度,很可能对鲜卑“部落制”产生了影响。乌桓较于鲜卑汉化时间长、程度深,因而其没有经过奴隶制阶段,从邑落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其民很早便与长城障塞内的汉人错居杂处,这也是为什么乌桓一直以来没有立国的原因之一了。鲜卑和乌桓分化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出现在是檀石槐部落军事联盟前后,檀石槐部落军事联盟成立之时,鲜卑进一步向北方草原扩张,与匈奴融合,而当联盟破裂后,东部鲜卑继乌桓后较早的转向中原发展,而拓跋鲜卑这一变化稍晚发生,这样就可以解释由于拓跋鲜卑较早取得北方的统治权,其自身畜牧习气并未变,因而大肆改农田为牧苑,从而与汉民族产生了较多冲突,直至导致灭亡。
鲜卑与乌桓的共生关系还体现在民族迁徙上,从公元2世纪到6世纪五百年间,乌桓与鲜卑间的移动以及汉族迁徙大致为四个潮流:第一是二世纪草原各族牧民的流动(由于匈奴国家的分裂导致);第二是四世纪汉族的外徙和乌桓、鲜卑的内徙;第三是四、五世纪中原汉人、鲜卑人向北魏代都的迁徙;第四是五、六世纪漠南和代都鲜卑等族向中原的迁徙5。乌桓被曹魏柳城后移民入中原以及苻坚灭燕徙乌桓杂类于北地和冯翊期间,又与东部鲜卑错居杂处,所以乌桓内徙经历了鲜卑化再汉化的过程。《魏书·帝纪·序纪》云:“(始祖神元皇帝)五十八年……其年始祖不豫。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先受卫瓘之货,故欲沮动诸部。因在庭中砍钺斧。诸大人问欲何为,答曰:‘上恨汝曹谗杀太子,今欲尽收诸大人长子杀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乌桓被曹魏征讨后势力大减,虽然在语言、习俗上和鲜卑相同,但这一时期拓跋鲜卑迁至漠南时必与乌桓接触,致使一部分乌桓加入拓跋力微所领导的鲜卑部落联盟。
乌桓人口较之于鲜卑总体少,其集中之地为四郡乌桓,即上谷乌桓九千多落,辽西乌桓五千多落,辽东乌桓一千多落,右北平乌桓八百多落,总计三十多万人,即所谓的幽州乌桓6。幽州乌桓地理位置上更接近于汉地,经济条件较好,常以本土特产与汉贸易,因而在汉与南匈奴敌对时幽州乌桓表现的十分恭顺,他们常追随乌桓都尉去朔方、雁门出击匈奴,直到东汉末年虽然乌桓对汉政府对其利用多有不满,但整体上依然是与汉和睦的,而这一时期由于曹魏的打压,乌桓出现了分散和融合,分散体现在乌桓与北方各少数民族都有婚姻交流,融合体现在大部分乌桓部都作为拓跋鲜卑的外加部落,通过族外婚的形式融入到了鲜卑体系中,因而《魏书·官氏志》言:“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桓”。代北时期的乌桓与鲜卑的共生逐渐转为了融合,乌桓两部铁弗和独孤,史书记载独孤部、铁弗部自称乌桓,又称匈奴,是为两部父匈奴、母乌桓或者父乌桓、母匈奴所致,后一直称自己为乌桓。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说,“作为外家部落的乌桓对拓跋君长的政治介入,构成了代北时期拓跋君位不安定的关键因素”7。从田先生的话也能窥得,正是由于乌桓的母权、舅权风俗通过婚姻缔结方式融入到了拓跋鲜卑体系中,使得后妃对君权造成影响,也直接导致太武帝拓跋珪实行“子贵母死”制度以限制母族和妻族。
(二)余论:护乌桓校尉考和鲜卑的“大人”
“护乌桓校尉”是两汉时期管理和监督乌桓事务的重要官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迁乌桓人于五郡塞外,“始置护乌桓校尉,秋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后汉书·乌桓传》)。护乌桓校尉驻节幽州,王莽时更名为“护乌桓使者”,后乌桓叛乱,护乌桓校尉职权并入“使奴匈中郎将”。东汉光武中兴后“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封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后汉书·乌桓传》)。据《后汉书·百官志》载护乌桓校尉“秩比二千石,主乌桓胡,拥节,长史一人,司马二人,皆六百石”。由此可得,护乌桓校尉首先行监领乌桓内附之众,处理乌桓事务,其次校尉使不得与匈奴交通,以防与匈奴勾结,最后,在东汉时,并兼领鲜卑,掌管乌桓、鲜卑的岁贡、质子和互市之事。“二千石”与“比二千石”考汉制,以俸禄多少为准,如“中二千石”(一百八十斛,一斛十斗)、“二千石”(一百二十斛和“比二千石”(一百斛),较之于郡守、诸侯王相官禄为二千石,故东汉较之西汉,护乌桓校尉较郡守为低了。至魏晋,护乌桓校尉职责又有变化,由于曹操北征乌桓,使其内迁长城以南,乌桓族的战略意义于是变得弥足轻重,《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载:“文帝践柞,曰豫为乌桓校尉,持节,并护鲜卑”,《晋书·唐彬传》载:“太康十年(239年),以唐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右将军”。很明显,魏晋时护乌桓校尉由一个行政监察官授转为兼有监督南迁族和经略东北地的军事主管,也因其享有皇帝钦点“持节”而声威显赫,这一程度上说,东汉持节之校尉又比西汉校尉更具声威。再来看看护乌桓校尉遣军抗击匈奴时的活动,如明帝永平十六年春,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各郡兵及乌桓众,计一万一千骑出平城塞;和帝永元六年(94)冬,新归附的十五部北匈奴人反叛,欲逃回漠北,汉遣乌桓校尉任尚率乌桓等兵,共四万人进讨。以上为编入护乌桓校尉管领的乌桓骑兵,战时由校尉征调,但另有一部分精选队伍调归各郡指挥,称“突骑”,不属护乌桓校尉统领。综上所述,护乌桓鲜卑自两汉至魏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两汉初置、复置的因俗而治的羁縻;2.使持节的军事职能加强;3.魏晋时由中央官职转变为固定地方兼职;4.由于中央政府统治弱化,最终军事职能削弱和消失8。对于研究乌桓、鲜卑与汉政府间关系的学者,护乌桓校尉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根据对一些文献的查阅和解读,且交待一下余见:两汉至魏晋的护乌桓校尉制可以看作是汉中央政府主动意义上汉化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手段,一定程度上戍卫了汉北部边疆,也促成了民族融合,但较之于完全农耕化游牧部族来说,这种“因俗而治”的手段更符合乌桓人的利益,既保留了游牧传统,自身粮食和商品业已得到补充,虽然汉政府和乌桓多有利用对方之嫌(乌桓或随校尉出战匈奴,或联合匈奴侵略汉地,汉政府也利用乌桓铁骑远涉云南平定农民叛乱引起乌桓人不满),但私以为这种利用关系是文化对话的最佳方式,也正是因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之举,才使鲜卑较早接触到了汉文化,为其建立北方政权打下了基础,甚至可以将雁、代地区乌桓、鲜卑族定居壮大看作一次亦农亦牧的鲜卑族早期经略汉地的一次尝试和准备阶段也不为过。当然,后来游牧族在北方坐大也是之前中央政府万万没有想到的。
再及,第一节骑马民族中分析游牧有两种传统:匈奴、突厥传统和乌桓、鲜卑传统,笔者认为正是由于鲜卑亦农亦牧的生计方式和靠近中原的地缘特性,使其在政治诉求上“中国化”(即汉化)近与单单抢掠中原财物,铩羽而归的匈奴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可以解释只有鲜卑是同时期游牧族中唯一称霸中国北方的民族的原因了。
鲜卑族“大人制”在历史上并不是孤例,除同见于乌桓、匈奴和西域诸国外,《魏志·倭人传》也记载了所谓“大人”:“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那么这里的大人又是否具有相同的概念呢?大人一词,常有尊其称的含义,如《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知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另有《汉书 郊祀志》载:“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之迹甚大,类禽兽云。”大人在这里又被异化为时人东去求神人之事所遇的巨大之人,称“大人”,可见,“大人”有实词化的巨大之意,亦有表尊敬的含义。《汉书·五行志》亦载有:“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狄服”,再来看看《山海经·海外东经》对大人的描述:“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磋丘北”,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解释说,“中国东北诸种称大人之号,乃由来久矣!”即大人是对东北游牧民族的一种泛称。到了后汉乃至三国,“大人”专指塞外胡族对其部落首领的称呼,匈奴中以单于为首领,但单于之下,也有大人存在,《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楼誉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这里的大人应该是邑落中的首领,“大人”一词是汉语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称呼,或有“长帅”“大单于”“君长”别称,也对来降的统帅者称“大人”,是中原文化对匈奴部落制的一种理解,即各部落大人组成联盟,推其首领为单于,而值得注意的是大人同单于一样,是世袭的。但乌桓、鲜卑的“大人”与匈奴又有不同,乌桓、鲜卑“大人”多有推举,如檀石槐就因勇健卓绝被推为大人,同样,《三国志·鲜卑传》又记到:“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这些经推戴的大人,在入朝中原王朝时,也被封为“王侯”,赐印绶。檀石槐时期,又将大人制度附以新的含义,他把鲜卑领域分中、东、西三部,各部设许多大人,互相制约,同时受檀石槐之制约,即为一种大人之大人的结构。这种做法也一直延续到拓跋建国之后,《魏书·官氏志》记道:“太祖登国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是年置都统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因而,乌桓、鲜卑的大人是经历了从部落首领到官僚化过渡的过程,实则是受中原文化影响和政治集权的表现。
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大人在不同民族间的用法和含义,比如在汉语中,大人具有多种含义,或实之,或虚之,还被特别用来描述夷狄之巨大人,这些描述都是塞北游牧民族邑落族长的意思的多方转化,乌桓、鲜卑区别于匈奴单于统领各部大人的情况,产生了大人之大人的结构,不难看出部落的集权和“大人”的王侯化(即从魏志所载邑落具声威和德高者的长老到后期凌驾于族人之上的至高统治者形象,最鲜明的表现是大人由推举制转变为世袭制)是受中原王朝的影响,同样,也可以认为各部的大人,是后期拓跋鲜卑官制向中原王朝官制过渡的阶段表现,是北魏官制的萌芽。
三、鲜卑墓葬及相关研究
(一)鲜卑考古学文化
这里所提及的鲜卑,主要是指南迁过程中的鲜卑,其中包括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新中国成立后,对于鲜卑的研究和考古挖掘有着重大发现,一大批遗迹被揭露,主要有三类:其一为辽宁和青海的慕容鲜卑遗迹;其二为从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畔以迄内蒙古河套东部的拓跋鲜卑遗迹;其三为南迁更远的代魏时期分布在山西大同和河南洛阳的遗迹。前两类主要证实了鲜卑诸部迁徙过程中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分化以及汉化程度,体现在从丛葬墓到单葬墓的变化趋势和随葬品的变化,后一类主要说明了虽然北魏封建制度逐步深化,但在文化上依然残存原始风气,如葬式、葬俗方面。具体又如在北票发现的慕容鲜卑墓葬、北燕冯素弗夫妇墓、义县石椁墓;黑龙江发现的早期拓跋鲜卑墓葬、乌兰察布盟墓群;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初期墓葬、北魏平城遗迹等。现总结一些鲜卑墓葬在南迁过程中表现的异同和时代特征,罗列如下:1拓跋鲜卑墓葬异同:公元4世纪之前,墓穴及棺多为前宽后窄的梯形,4世纪以后仅有棺保留了梯形形制,前宽后窄墓穴基本不见; 侈口长腹罐为主要陶器器形,3世纪后出现了长颈壶,5世纪以前随葬品多实用炊器,5世纪以后多为明器; 镂孔双耳铜(铁)鍑和金属牌饰是主要的随葬品,带状装饰物同样较流行,如“郭洛带”,5世纪以前牌饰画面形象多为鹿和马,5世纪以后开始出现野猪、神兽(拓跋鲜卑墓葬常出土有鹿形金属牌饰,学界认为鲜卑神兽即为驯鹿,这与其早期游猎生活密不可分); 4世纪以前拓跋鲜卑墓葬随葬有诸如桦皮器、弓弭、石镞、刀剑等特色器,这与拓跋鲜卑其自身文化原始性和尚武有关。2.慕容鲜卑墓葬异同:墓穴平面为梯形和长方形,是主要的墓葬形制; 敞口舌状唇壶是主要陶器器形,3世纪后瓮成为后期陶器主要器形; 马具和金属牌饰为主要随葬品,特色器为步摇冠和甲骑具装。9
(二)鲜卑的迁徙
鲜卑的迁徙分为慕容鲜卑的扩张(即东部鲜卑迁徙)、拓跋鲜卑南迁和秃发鲜卑兴起,根据对拓跋鲜卑墓葬的发现和分期研究,大致将其迁徙路线描述如下:嘎仙洞→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孟根楚鲁→南杨家营子→苏泗汰→东大井→三道湾→百灵庙→西沟子村(和林格尔)→平城→洛阳10,大致经历公元1世纪至5世纪,各墓形制都为前宽后窄,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西北,都有殉牲存在(以完整马匹和狗的殉牲为主,狗在鲜卑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前文所述使灵魂上马,以狗为先导就证明了其游牧打猎的原始特性)。慕容鲜卑的扩张主要以建立地方政权为表现,有吐谷浑,前燕和后燕,西燕,南燕。秃发鲜卑原属于拓跋鲜卑一支,因其迁至河套地区,被称为河西鲜卑,西迁经黄河西岸至宁夏贺兰山东麓再南下至陕西和甘肃东南,后聚居于青海湖一带,建立了南凉政权,其墓葬形制与拓跋鲜卑多有相似,所以秃发鲜卑墓葬文化是研究早期拓跋鲜卑考古学文化的重要证据。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迁徙并不是相互承继或者单线式的,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并进式的迁徙过程,如在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的墓葬中均发现了侈口长腹罐(拓跋鲜卑墓葬中的典型器,而慕容鲜卑墓葬侈口器在各期交替出现,推测为慕容鲜卑受拓跋鲜卑影响),马纹、鹿纹金属牌饰都为常见器形,慕容鲜卑之步摇冠与拓跋鲜卑郭洛金银带饰似有联系,另有慕容鲜卑冯素弗墓发现的铜提梁锅与拓跋鲜卑铜鍑相似,这说明鲜卑各部的迁徙是存在文化互动和共生关系的。鲜卑迁徙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同样北迁中的汉族流民和鲜卑自身南迁地受汉族影响,拓跋鲜卑入“匈奴故地”(在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可能也接触到了西域文化因素),墓葬数量众多,随葬品增加,汉文化因素大量出现,表现在骨器、殉牲的减少和陶器、牲畜、家禽、牛车等俑器的增多,这说明农业因素成为南迁中的鲜卑族的重要生计方式,再后期,砖室墓和洞室墓逐渐取代了竖穴土坑墓,这些都说明了鲜卑族正在走向从游牧民族向定居农业民族的转变过程,其社会形态也由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
学界常用鲜卑南迁墓葬男女墓葬随葬或葬式的变化试图来说明鲜卑经历着从母权制度残余向父权社会的转变,可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进化论观点真的适用于鲜卑个例的研究吗?鲜卑族从诞生伊始直至北魏时期,一直没有完全脱离母权和舅权对其政治文化的影响,简言之,鲜卑族内部历来有尊母重舅的旧习,所谓从母权至父权社会的进化观点是有些生硬的,至少,从母子合葬和男女合葬墓围绕在单身男子墓中间是看不出来这种进化观点的,社会的演化从来都不是单线,拥有必然性规律的,而是由一些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间共同作用于历史事件中,可能又有人要说,子贵母死制度不正是父权对母权的削弱吗?但是子贵母死制度恰恰证明了母家和妻家对于北魏统治的影响力才使得一些阶段性政策的出现。也有人试图从文化圈理论,即文化传播观点去解释鲜卑族内部的文化互动以及与汉文化的联系,但实际情况是北方各少数民族间,与汉族社会间通过姻亲缔结和迁徙已然出现了杂处一家的现象,例如田余庆教授在《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共生关系》一文中直言,道武帝拓跋珪在进行离散部落制度时,对于独孤部的族属问题十分头疼,因为独孤、铁弗历来有“入匈奴则为匈奴,入乌桓则为乌桓”的观念,其匈奴父、乌桓母或者乌桓父、匈奴母的情况十分普遍,以至于在北魏写史时也含混其词:“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魏书·官氏志》)。可见,对于鲜卑迁徙中与各族文化研究所获考古学资料要谨言慎行,切不能呆板僵化的先入为主。
(三)鲜卑“毁器”葬俗研究
前文列举了鲜卑慕容部与拓跋部的些许墓葬,其中,所谓“毁器”葬俗基本上是贯彻其历史的始终(公元1世纪至公元5世纪间)。其“毁器”葬俗主要集中在陶器、金属牌饰、铜镜和铜(铁)鍑几类随葬品上。首先,从起源上看,毁器葬俗最早出现于史前时期的黄河流域,如青铜时代西团山文化墓葬的“毁器”葬俗,其性质被定义为东北地区原始土著,而后,诺颜乌拉的匈奴墓葬11也发现了“毁器”现象,至于鲜卑以后的高句丽、渤海和女真“毁器”葬俗更加普遍。有学者认为“毁器”葬俗是鲜卑族在各种文化因素下共同作用的结果,更可能是北方民族一贯的丧葬传统,从东胡青铜短剑墓的“毁器”葬俗对比与其有着直接承继关系的鲜卑的毁器葬俗,应该属于一种文化的继承,而是否来自于匈奴,也是一种可能的观点。另外,作为“毁器”的载体,又有着从具有鲜卑族属特征的铜鍑到汉文化因素的铜镜和陶器的变化,“毁器”的覆盖面更加广泛,这种现象既体现了鲜卑与外界的联系密切,也可能证实了“毁器”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主动行为,是一种增强民族认同和自豪感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慕容部与拓跋部在交流过程中,不但有着物质层面的随葬器的交换和影响,其各自的“毁器”葬俗也传入到对方的文化体系中,表现在毁器载体不仅有慕容鲜卑特征的侈口舌状壶,亦有拓跋鲜卑标志性器夹砂敞口长腹罐,这对于鲜卑民族内部归属感和民族自信心也有很大的帮助,就目前来看,慕容鲜卑墓发现的“毁器”特征的随葬品仅有陶器和金牌饰,金牌饰也多集中于王子坟山墓葬中,相较于慕容鲜卑,拓跋鲜卑的“毁器”葬俗多体现在民族特征器物上,造成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可能与慕容鲜卑较早南迁并接触融合了汉文化有关。
从人类学观点看,这种“毁器葬俗”的出现,是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或者衍变的一种形态,即从完整观省美到残缺美的转变,表现为对与人世间相对应的文化不完整性、个人物品通过焚、烧、毁形式转到死亡和终结生命、隔绝生死界限的复杂而神秘的文化内涵,是一种原始禁忌文化模式。应该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大创举。有一部分学者常把多见于鲜卑墓葬中的“毁器”葬俗认为是后来契丹人“毁器”“毁尸”葬俗的渊源,但据实际考古发现来看,至少在鲜卑墓葬中并未发现骨骼因人为的“断尸”而发生残缺现象,恰恰相反,根据鲜卑人的信仰体系,生命源于天地自然,生于土,自然也归于土,非自然死亡或者遭戮之人是不允许进入丛葬墓地的(丛葬葬俗,鲜卑古老葬俗制度,受到一定重视,在拓跋鲜卑早期墓葬中仍有显现,如南杨家营子墓、扎赉诺尔墓群和完工墓,最近几年由于学界多对完工墓文化性质,即是否属于鲜卑墓葬多有疑虑,现搁置疑问,所以单以扎赉诺尔墓为例说明——该墓群有少量丛葬形式,墓中尸骨不超过十具,一般为四具,随葬丰富,且都具有木棺,上下排列,母子合葬改为小孩从葬男子墓,其年代应稍晚,较之南杨家营子,汉文化影响更明显,随葬品种类更繁。)关于鲜卑“毁器”葬俗研究,少有关注,期待更多考古发现和人类学调查为这一问题的方方面面解惑。
尽管早期鲜卑之史料寥寥可数,也存在较多疑虑,但这正是以重现历史为己任的考古学所要做的。本文在辑录一些大家之论据和史书所实载的同时,也较多的运用个人鄙陋言以图窥得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虽是一家之言,冰山一角,却也实是学习之心得,竭尽己力希望做到“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鲜卑之于中国王朝之作用,不言而喻,上承秦汉兴,下启隋唐盛,对于中华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一些本文未能涉及的代魏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盛状虽未能表,但其内涵始终是寓于中华文化之中并与之发扬的。
注释:
1.引自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第一章“骑马民族及其活动舞台”,主要论述了亚洲游牧民族产生的地理环境因素.
2.出自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一书,本书详尽论述了乌桓与鲜卑史及相互影响.
3.本段内关于鲜卑、乌桓社会状况的白话文描述系《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传》原文翻译所得,部分引用原始材料.
4.区域划分观点来自于马长寿《乌桓与鲜卑》.
5.引自马长寿《乌桓与鲜卑》.
6.幽州乌桓,是两汉期间与中央汉政府存在直接互动关系的乌桓部,也是乌桓相对集中的区域,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在“幽州乌桓及其三千突骑反战斗争”部分进行了详解.
7.摘自田余庆《拓跋史探》一书对乌桓的解释.
8.观点引自林幹的《两汉时期“护乌桓校尉”略考》.
9.引自孙危的《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
10.拓跋鲜卑的迁徙路线宿白先生在《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一文中有所涉及,孙危在其基础上,做出了从东北、内蒙古至河南洛阳的迁徙路线,这种路线确定是建立在考古墓葬和遗址分期和分区基础上的.
11.有关诺颜乌拉匈奴墓的资料为《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颜乌拉巨冢》[M],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