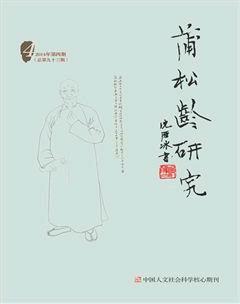斗酒难消磊块愁
刘畅++石玲
摘要: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造了许多“痴男”形象,他们或痴迷于真爱;或痴迷于外物;或痴迷于正义;或痴迷于功名,这些“痴男”的创造并非游戏之笔或宣扬神道,而是寄托了蒲松龄改造黑暗社会的宏大理想,以及“补天无望”的孤愤,既是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投影,更是对社会黑暗的抨击和对真善美的赞扬,有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境蕴。
关键词:聊斋志异;蒲松龄;痴男;孤愤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蒲松龄以虚写实、幻中见真,创造了一个个花妖狐魅世界里的动人故事,其中一个个“痴男”形象颇耐人寻味。
《聊斋志异》毕竟不以“发明神道之不诬”或游戏为主题,而是一部“孤愤之作”。正如蒲松龄自己诗中所云:“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感愤》)他借宋代洪迈的《夷坚志》来喻指自己的《聊斋志异》,说明了自己的创作是为抒发内心不平之孤愤。蒲松龄不仅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情,更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愤懑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蒲松龄身上既体现了传统作家浓厚的民族精神:关注国运民生,有着炽热的责任感和深沉的历史意识;又有时代精神的表现:尊情、求变,追求思想解放。所以这些承载着作者“孤愤”的“痴男”形象是时代精神与民族文化结合的产物,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聊斋志异》中的“痴男”形象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人间自有真情在:《聊斋志异》中的“情痴”
爱情,是人类亘古未变的主题。人们赞美爱情的坚贞、纯洁。蒲松龄更是用一个个“痴男”形象来表达着自己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歌颂。
《聊斋志异》中第一情痴要数《阿宝》中那位大名鼎鼎的孙痴——孙子楚。“粤西孙子楚,名士也。” [1]233 “名士”二字看似简单,实则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孙子楚是当地一位有学问有名声的人。既然是名士,那么孙子楚的“痴”并非“真痴”,作者说其“痴”也是非贬实褒的。孙子楚“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 [1]233,他的“痴”是真的一种表现:他见到妓女就“赪颜彻颈,汗珠珠下滴” [1]233,他的“痴”又是一种诚朴的表现,开篇数句即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性情真诚、诚朴可爱的年轻人形象,为后文浓墨重彩写其痴情作了铺垫。就是这样一个“性迂讷”之人,当爱情来临时表现出的却是一种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执着追求精神。还未谋面,仅阿宝一句戏言就可为她“以斧自断其指”,以至于“大痛彻心,血益倾注,滨死” [1]233。清明节春游,痴心的孙子楚终于见到了所爱的真容,不想回去后竟惘然失魂,“气休休若将澌灭” [1]235,三日卧床不起,魂魄随阿宝去也。中国古代小说中离魂母题早已出现过,但多为女子离魂,男子离魂却是第一次,可见孙子楚其“痴”性之深了。这次离魂虽打动了阿宝,却并未促成婚事。于是,孙子楚在再次见到阿宝时又发生了离魂,“归复病,冥然绝食” [1]236,魂附于鹦鹉又一次飞到阿宝身边。孙子楚的两次离魂终于打动了阿宝,使阿宝不顾父母的反对,抛开门第观念,毅然嫁给了家贫的孙子楚。孙子楚两次离魂所表现出的极端的“痴”,看似荒诞,却发人深省。
古代小说中有很多“离魂”现象,《聊斋志异》中的离魂却极有特色——男子离魂。一个男子为爱而离魂,而且离魂一次又一次。如果说第一次离魂时孙子楚尚保持“人形”,那么第二次离魂时却连“人形”都抛弃了(变成了鹦鹉)。这种不顾形象、不计后果的追求是坚贞的,却也有一丝卑微。在那个只视女子为附庸的社会里,孙子楚打动阿宝的固然有真情,还有一份尊重,一份对女子的尊重。孙子楚的“痴”,是对男尊女卑的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批判。其离魂的“荒诞”行为,是对真爱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蒲松龄通过孙子楚的“痴”,给予女子一个与男子平等的大写的“人”的地位。“痴”,在蒲老笔下是一种精神,一种品格,一种值得赞颂的反封建礼教的力量。
《聊斋志异》中另一位著名的“痴男”是《连城》中的乔大年。他与连城的爱并非产生于外貌的吸引,而是一种惺惺相惜的知己之爱。连城与乔大年以吟诗而互成知己,连城矫父命,赠金助乔生灯火,乔生为重病的连城割下膺肉合药。这种知己之爱,在连城去世时发展到了极致,“生往临吊,一痛而绝”。在地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并最终双双还阳结为连理。蒲松龄在篇末感慨道:“一笑之知,许之以身,世人或议其痴;彼田横五百人,岂尽愚哉!此知希之贵,贤豪所以感结而不能自已也。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才人,仅倾心于峨眉之一笑也。” [1]367连城与乔大年的爱情不以外貌为基础,更不看重金钱、权势,是一种可由生入死、由死入生、生死相从的爱情。就像《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2]1。只是杜柳之爱还停留在外貌的吸引上,还是传统的郎才女貌的故事模式,而连城与乔大年的爱情则是在传统的爱情观中加入了新的元素——知己之爱,这种爱已上升到了心灵层面,而且杜柳的爱情是通过女子的死而复生而最终取得理想的结果的。但在《连城》中,却是男女共同为知己而生死相随。乔大年不惜性命为连城割肉治病,在连城病逝后更是追随她到了阴间。在蒲松龄笔下,女子摆脱了传宗接代的工具地位,有了可以为她而死的知己,蒲松龄给予了女子至高的地位。在《聊斋志异》的世界里,女子与男子的地位是相同的,有的甚至在聪慧、胆识等方面远远超过男子(比如商三官等)。
《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为知己而“痴”的男子,如不在意容貌,尤重相知的贺生(《瑞云》);不以异类而怪之,明知对方是鬼,仍倾心相爱的杨于畏(《连琐》)。这种种“痴狂”的行为共同指向一个崭新的爱情观:心心相印、惺惺相惜的知己之爱。这种爱可以忘记容貌,可以打破生死界线,只要心灵相交,爱就在。
蒲松龄愤懑于理学、礼教对人性的压制,痛心于无辜的牺牲者,所以通过“情痴”们向世人宣告人间自有真情在,鼓励人们抛弃世俗偏见去追求真挚美好的新型爱情。这是蒲松龄对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的鞭挞,是他反礼教、反世俗观念的“孤愤”的表达。endprint
二、真纯诚美的化身:《聊斋志异》中的“物痴”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批痴迷于物的“物痴”——他们对某一事物着迷,难以自拔,以至于置自身的安危福祸于不顾。
《聊斋志异》中最著名的物痴男儿要数书痴郎玉柱了(《书痴》),他痴迷于书:“家苦贫,无物不鬻,惟父藏书,一卷不忍置。” [1]1453如果说这种表现是正常的话,那么他对于《劝学篇》的理解可以说得上是“痴”了。《劝学篇》是宋真宗所作,本是劝读书人读书入仕的。读书为做官,做官后便可从官场上“挣来”荣华富贵。但书痴郎玉柱仅对其作字面理解:“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郎玉柱认为只要读书,这些东西就会“从天而降”。一次,偶然发现了“古人窑粟”,即使“朽败已成粪土”,却更加坚定了他“书中自有千钟粟”的想法。郎玉柱的“痴”是其“真”的表现,他并非将读书当作荣华富贵的敲门砖,并不将书视为提升社会地位的捷径,读书就只为读书而已。即使得到美女颜如玉,仍然读书不辍,即使颜如玉以离去逼其“戒读”时,仍然“觑女不在,则窃卷流览” [1]1455,即使在颜如玉的教授下学会了下棋、音乐,却仍是暂时的“乐而忘读”,仍将书珍之重之。甚至在颜如玉告诫其有灾祸将至,解决的办法便是“举架上书尽散之”时,仍然坚决不肯:“此卿故乡,乃仆性命,何出此言!” [1]1456此时的郎玉柱就是“天真烂漫,机械不存于胸中”了,用吴九成先生的话来说,“这种‘痴是‘不懂或不愿意为自己披上哪怕一点点伪饰的赤诚”。[3]27他爱书,便“痴心”爱之,金钱、美女甚至灾祸都不为所动。
蒲松龄塑造的这个“书痴”形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审视:首先,这是个死读书而食古不化的形象,此时给人的感觉是迂腐而古板;其次,这是个不谙世事而胸无宿物的“呆瓜”,让人觉得可笑又有趣;再次,则是个天真而单纯的“真痴”,“痴”得发人深思,“痴”得让自认聪明的人自惭形秽。[3]25而蒲松龄就是以前两个方面突出强调第三个方面的,即用郎玉柱为人的天真来强调做人的赤诚、坦荡。郎玉柱的天真、赤诚得到的结果是家破人亡。史进士觊觎颜如玉的美貌而不可得,便毁掉了郎玉柱的书也毁掉了颜如玉。书及颜如玉的毁灭对郎玉柱有莫大的警醒作用:一个单纯、善良、几乎不问世事更别说害人的人却不为社会所容许。这使郎玉柱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让他一夜间成熟起来,对世事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开始复仇计划。郎玉柱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了史进士家乡的巡抚,并继续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搜集史进士的各种劣迹,最终抄没了其家为颜如玉报了仇。郎玉柱的变化是蒲松龄对残酷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人本性的揭露。欲做个真纯诚美、胸无城府之人却不为黑暗社会所容,只有虚伪刁滑之徒才能在这样的社会中游刃有余。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 [1]2可见蒲松龄并不赞成郎玉柱的转变,只是用其前后变化作对比,用真纯诚美的毁灭来突出社会的黑暗。在郎玉柱大快人心的复仇背后又有蒲老多少的无奈与惋惜。
“石痴”邢云飞(《石清虚》)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物痴”。他钟情于石头,看到漂亮的玩石便不惜代价将其买下。有一次,为了得到一块自己钟爱的石头竟不惜自减三年阳寿。为了钟爱之物性命都可放到一边,物在其生命中已然超出了玩赏之列,而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了生命的动力和载体。而人与物之间也不再是单向运动,物也具备了人的灵性。邢云飞就得到了一块与之患难与共的“石知音”。在他去世后,石头也自我粉碎报知遇之恩。在篇末蒲松龄这样感慨道:“而卒之石与人相终始,谁谓石无情哉?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非过也!石犹如此,何况于人!” [1]1578在蒲松龄笔下,人与物的关系已然上升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的相交是对人与人的交友之道的映射,痴心于物已变成痴心于知己之交,这是对传统的伯牙子期的知音故事的发展。在《警世通言》中,伯牙与子期的社会地位悬殊,但并不影响他们的相交相知,就像人与书、人与石一样,虽迥异为异类,仍可痴心以待。子期死后,伯牙摔琴绝弦以谢知音,就像郎玉柱虽明知有祸将至,却仍放不下一室的书;就像邢云飞宁可自减三年寿命,也不放弃心爱的石头。蒲松龄将传统的人与人相知通过人与物表现出来,正如学者王琳所说:“从主体人与对象之间的审美关系看,物痴是主体将知遇渴求为核心的友情投射到‘物上,属于将非人的主体人格化,与此理化的至友交心,痴心以待。” [4]24蒲松龄在更高层面上通过人与物的相知进一步宣扬真纯诚美的崭新的交友之道,赞美以心灵相通为基础的、痴心以待的人与人交往的至高境界。
“士为知己者死”,中国人自古看重知音之道,重知音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深邃。这些为外物而不惜性命的“物痴”,正是愿为知己而死的“士”,在他们身上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之道得到继承与发扬。蒲松龄赞美“物痴”是对真纯诚美的品性的呼唤,对古人知音般交友之道的回应,也是对现实的虚伪做作的交友之风的抨击,更是对社会交友秩序的规范。但是,现实中却有太多像转变了的郎玉柱这样的人。作者颂扬知音之道的背后,又有多少对现实无奈的“孤愤”——传统的知音之道正等着后人们去发扬光大。
三、坚守真理的痴性情:《聊斋志异》中的“性痴”
“性痴则其志凝” [1]238,志凝则其坚韧,坚韧则“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性痴就是要坚守真理、不畏强权、至死不悔。蒲松龄赞美性痴,就是赞美这种坚韧不拔的美好品质,反对黑暗的社会现实。
席方平(《席方平》)就是一位坚韧不拔、上下求索、痴心为父伸冤的“痴男”形象。席方平因父含冤而死,所以魂魄赴冥府代父伸冤。无奈由城隍至郡司再至冥府都是贪酷腐败之徒,不但不为其父昭雪,反而对席方平施以笞仆械梏、火床锯解之刑,但席方平坚守真理咬牙挺住各种酷刑而痴心不改。当冥王问“敢再讼乎”时,他毫不犹豫的回答:“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 [1]1342以至连办事的小鬼都被打动了:“此人大孝无辜,锯令稍偏,勿损其心。” [1]1343后来终于在九王的引见下得见二郎神,为父伸冤,使其父冤情得以昭雪。正如蒲松龄在篇末中所说:“忠孝志定,万劫不移,异哉席生,何其伟也!” [1]1348其实,小说写到二郎神为席父伸冤就已经圆满结束了,但蒲松龄却在后面赘述了二郎神对冥王的判词,这就明显是蒲松龄孤愤的发泄了:“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 [1]1346蒲松龄将矛头直指封建官吏,尖锐地揭露酷吏官官相护、鱼肉人民的罪状,《席方平》可说是一篇声讨封建贪官污吏的檄文。席方平愈孝,其性愈痴,就愈反映出背后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蒲松龄赞美性痴,就是赞美被压迫的下层人民的美好品质,更是借此含蓄地披露社会黑暗,抒发孤愤。endprint
另一位痴男向杲(《向杲》)就没有席方平那么幸运地有二郎神相助了,他的报仇是通过自己化虎完成的。有冤无处伸,有仇无处报,生生将人变成了虎,即使变成老虎,报仇的执念也从未变过,也只有将人逼成兽,大仇才能得以报。篇末异史氏曰:“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 [1]833多么尖锐的讽刺!荒诞离奇的故事背后,隐藏着作者一腔热血孤愤:社会公正不存,含冤者申诉无门。但被压迫者的反抗意志丝毫不减,并在坚守真理的“痴”中得到升华。
面对黑暗的现实,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在百折不挠、坚持真理、反抗强暴、不畏牺牲等方面。席方平的申诉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被压迫者抗争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向杲的复仇出于幻想则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含冤者申诉无门的悲惨遭遇,也是被压迫者反抗意志的艺术概括。坚守真理,反抗强暴的传统美德由来已久,从《诗经·魏风·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中下层劳动者反抗意志的觉醒,到《史记·陈涉世家》“死国可乎”,官逼民反,反抗在不断升华,到《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反抗强暴、坚守正义真理,不畏牺牲已发展成为一种自觉意识,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
清代严苛的文化专制和大肆盛行的文字狱,使蒲松龄即使面对满目疮痍的人世,也只能强压满腔的愤懑,以虚写实,幻中见真,用超现实的手法、荒诞之事来透视社会的腐败,启发激励人们勿忘反抗斗争。痴性情背后是蒲松龄自己的反抗意志,蒲松龄将民族传统美德与一腔反抗意识、祈盼社会清明的痴性情一同灌注于荒诞离奇的故事中,其荒诞背后又有多少难以明言的孤愤。
四、一生科举一生泪:《聊斋志异》中的“功名痴”
众所周知,蒲松龄一生科场蹭蹬,晚年才得了个岁贡生之名,可谓一生怀才不遇,受尽科举的毒害,也对科举看得特别透澈。正是因为自己同样怀有一份“痴”,所以蒲松龄笔下的“功名痴”尤见深意。
从隋炀帝创建科举以来,科举为无数士子,特别是寒门之士提供了一条通向成功的捷径。但明清以来,已是强弩之末的科举,其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科举在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环境下已很难发挥其选拔人才的作用,而是成为一种精神毒害剂。王子安(《王子安》)就是一位深受毒害的功名痴,他醉心于功名,成日焦灼不安,所以才会在乡试放榜之前喝得酩酊大醉,在睡梦中被狐仙戏弄了去。在醉梦的狂想中,他中了进士,入了翰林,狂喜之余,一会大呼赏钱,一会大骂“长班”,醒后却只床前一老妻。梦中的繁华与现实的凄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更加突出其痴念之深。而痴迷于金榜题名,日日沉溺于提名的幻想与失利的恐慌中的士人又何止王子安一人!篇末蒲松龄总结了秀才考试前、考试中、考试后的种种癫狂之态: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鸩,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1]438
这一段文字将入试者的不安、焦躁、惶恐、愤怒,失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一场科举,就是封建读书人的一次精神炼狱。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几乎历来都是封建文人唯一的出路,只有科举考试一途才可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但是科举考试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尤其明清以来,日趋僵化的八股制度成为读书人难以摆脱的精神枷锁,再加上封建社会末期社会黑暗、权钱交易盛行,科举考试几乎抛弃了其选拔人才的重任,而成为有钱有权人交易的场所,成为贫士的悬崖。更可悲的是,深陷科举的寒士们少有清醒者,他们一头扎进其中,如痴如醉地追求着功名富贵,从不曾跳出来看一看,才造成了像王子安这样神魂颠倒的痴男,才有秀才考试前后的种种癫狂之态。科举考试因其背后的社会腐败而对封建士子,特别是寒门之士造成了深深的精神毒害。一生科举一生泪。
王子安是痴的,他在梦里都不忘功名,却还有一位更痴的,他死了灵魂还要回来参加考试,他就是叶生(《叶生》)。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 [1]81,但就是难以高中,以至于死后灵魂都要回来参加科举,并考中举人完成生前的夙愿,叶生是痴狂的也是可悲的。在封建社会,考取功名、进入仕途,是读书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叶生的屡试不中,使他的人生价值难以实现,人生的意义遭到质疑,所以死后灵魂也要回来继续考试。叶生的痴狂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他身上又有着时代造成的读书人的悲剧,这悲剧源于社会给予读书人太少的出路,使他们不得不在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上“呕心沥血”。《叶生》与其说是在为叶生鸣不平,不如说是蒲松龄抒发自己挣扎于血泪科场路上的“孤愤”。蒲松龄本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痴男”,他与叶生一样少年得志,且十九岁就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考中秀才。谁知此后蹭蹬科场,终困场屋,直到七十一岁才被援例为岁贡生,七十四岁时四子蒲筠请江南朱湘鳞为他画像,在儿孙劝说下,他穿上了标志着他一生中最高学位的贡生服,并在画像题跋中写道:“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 [5]3472其内心不甘可想而之。蒲松龄看到了科举制度的黑暗,目睹甚至经历了士子们的“痴狂”,但他没有完全否定科举制度,这是个体生命渴求社会认同的传统意识在文人心中作祟的缘故,因为科举取士无疑是封建文人取得社会认可的最好方式,也有可能是唯一方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除了读书以求考取功名外,其他职业只能满足生存之必须,而不能满足他们渴求得到社会认可的心理,所以才有了前赴后继的“痴”人们。
渴求得到社会认同的传统,历来是文人难以逃脱的人生选择。远在春秋时期,《左传》中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司马迁作《史记》也是希望能“成一家之言”,甚至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也是为了“立言”。蒲松龄在七十一岁高龄时仍坚持参加岁贡考试,考取功名以获得社会认同并实现自我价值,这是他一辈子的追求。但现实残酷,梦想终化成泡影,所以蒲松龄只能借《聊斋志异》中一个个虚幻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孤愤”,或许他也做过和王子安一样的梦,他也希望有一日能锦衣还乡,但是“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1]3现实社会中没有人了解自己,没有人认同自己。
蒲松龄是位关注国运民生,有着深厚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笔下的一个个“痴男”,绝非游戏之作或证明“神道之不诬”,这根植于时代精神与丰富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的“痴男”们,寄托了蒲松龄改造黑暗社会的宏大理想,以及“补天”无望的孤愤。但是,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使蒲松龄这点济苍生的愿望都无法明言,更无法实现。所以,他只能将美好愿望化作一个个痴念,诉诸笔端,塑造出一个个“痴男”形象,让他们替自己在魑魅魍魉的世界里完成心愿。蒲松龄自己就是情痴、物痴、功名痴,更是一个性痴,为坚守自己的美好愿望,不惜“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1]3然而,知他者仅在“青林黑塞间”。社会黑暗,注定其痴念难成,仅余一腔孤愤在人间,斗酒难消磊块愁。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吴九成.聊斋美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王琳.谈《聊斋志异》中的“痴”[J].辽宁师专学报,2003,(6).
[5]蒲松龄.蒲松龄全集[M].盛伟,编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朱 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