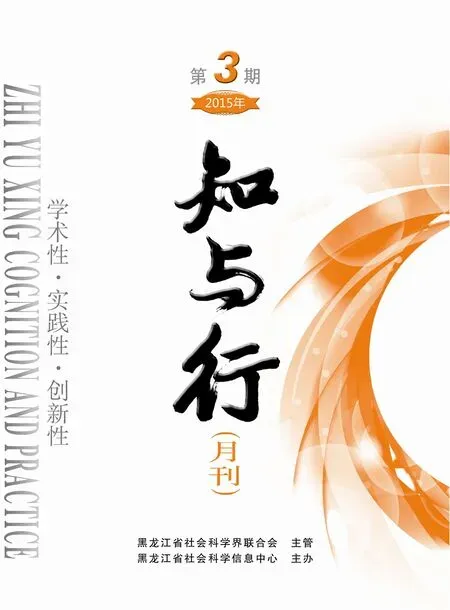关于历史评价中真与善的标准问题
隽鸿飞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哈尔滨 150080)
关于历史评价中真与善的标准问题
隽鸿飞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历史评价中的真与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站在真正的历史性的真实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真正的善的评价。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有意、无意地模糊历史真实的标准,以部分的、个别的真实、客观性取代历史总体的客观与真实,通过遮蔽部分历史真相以在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评价中混淆视听,攻击主流话语。因此,有必要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分析入手,深入阐明在历史认识之中“客观性”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从而明确历史的真实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那种通过遮蔽部分历史真相以获得的所谓的“客观历史”并不是历史性的真。以此为基础,阐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样必须建立在对历史总体性及其发展的进程的理解基础上。因为,只有从历史总体性的视角深入到历史发展进程中,才能阐明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来说,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仅要考虑事件发生时的具体状况,同时要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时段之中才能真正认清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而对于历史人物,同样不能以其自身的个人品性为评价标准,而是必须以其所作所为造成的历史后果为根据。只有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之中,才能充分体现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地位、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历史评价;历史的总体性;历史的真;历史的善
对于事件及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进入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的价值体系逐渐被消解,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彻底消解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均质化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分层已经出现。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同一阶层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明显,并趋于激烈的斗争状态。各个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都从自身的立场出发,从一切可能的方面为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寻求理论的、历史的、道义的支撑。以至于整个的现实存在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为其自身利益辩护的手段或者打击别人的手段和工具。同时,由于在现代中国社会形成过程中社会的均质化,实质上消解了传统的社会精英存在的根基,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沦丧为各个不同的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而,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在当代的中国社会,真的难以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因为无论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甚至在做什么,都会有人提供给你完全相反的意见。更有诸多的“专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向你传播他们的价值判断。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生活?如何确立各种判断、选择的标准?
我们认为,在这纷繁复杂的思想意识冲突的局面之下,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历史的标准。所谓历史的标准,那就是要超越现实的各个阶层、利益集团的具体的利益诉求,或者说,历史地去评价、判断。对于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来说,只有把它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之中,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去审视,才能真正看清楚其本来面目。同时,对于当代的各种利益冲突及其意识形态的表现来说,同样需要历史的视角,即从历史的进程之中阐明其现实的存在状况及其发生的具体进程,从而把握其真实的状况;也只有从历史进程之中阐明其何以如此存在,才能超越具体的、现实利益有限制,看清楚其在现实的发展之中可能呈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态势,从而明确其立场和态度的基点。更为重要的是,只有通过长时段、总体性的历史视角,才能对现实的一切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在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造成的价值冲突之中寻求一个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
一、关于善与恶的问题
在近十几年以来,国内的学术界、思想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为历史翻案。从前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已经形成定式的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重新被以一种截然相反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开始的时候还涉及对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如张灵甫、阎西山等等,后来又出现了关于西门庆、刘文采、黄世仁等一些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的评价问题。最新看到的一篇文章是关于蒋介石的,其标题为“蒋中正——有史以来最悲壮的民族英雄!”如此等等。这种现象直接颠覆了我们多年来接受教育而形成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并不是说我们接受的基本的价值观教育不是没有问题的。但细细想来,这实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关于善恶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个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另一个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所以,在涉及对历史中个人的评价时,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恶、两种善。一种是个人的善恶,另一种是历史的善恶。所谓个人的善恶是比较容易分辨的,诸穷凶极恶之徒、阴险毒辣之辈的恶。但这种善恶乃是小恶,其影响仅于较小的社会活动范围,从时间上来说局限于其个人的一生经历,难以在现实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一定的印迹。从人类历史长时段的视角来说,这样的善恶是不足以引起一个历史学家关注的。特别是通过对这些小善、小恶的分析,能够说明其得以产生的根源仅仅限于某一个人个人的生活,而不是根源于普遍的社会生活时,那更是如此。但是相反,如果说个人的善恶并不是根源于其个人的生活,而是根源于普遍的社会生活,那么这样的善恶就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善恶,而是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正如有人指出的,如果说一个人做恶的根源并不在于其个人生活,而是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那么要批判的就不仅仅是做恶的个人,更要批判的是整个社会生活了。如鲁迅在其小说中描写的华老栓、祥林嫂、阿Q、假洋鬼子,等等。其善恶悲喜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个人,而是属于那个造成他们的那个时代。在谈到历史的时候人们更多讨论的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但如果我们把历史进程中那一切的苦难与人间悲剧都同时呈现出来之后,那么无论是持上述哪一种观点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现实的人的善恶悲喜不过是反映那个现实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意识[das Bewu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u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现实生活的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1]525
因此,我们谈论善恶就不能仅仅限于个体的人,而是必须在历史的意义上去谈,那就必然涉及历史的善恶。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确实是更多地与所谓的英雄人物及其事迹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为了能够真正站在历史的尺度之上,那我们就必须抛弃单独的对个人的品质的评价,即不能根据某一历史人物的个人道德品性去评价他。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他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名自然有其过人之处,无论是善的,或是恶的。如曹操之奸诈、刘备之狡猾、诸葛之过人的智慧、周愉之心胸,更不用说秦皇汉武之雄才大略、唐宗宋祖胸怀宽阔。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特别是从历史长时段的视角来说,其个人的品性如何并不直接关涉到对其作为历史人物的评价。所以,才不会有人因为秦始皇的残暴而否定其一统天下、缔造帝国的历史意义,也不会有人因为汉武帝的金屋藏娇而批评其骄奢,如此等等。因为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之中,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的后果都已经得以充分地显现。相反,越是贴近我们的生活,距离我们越近的历史时段,则越容易混淆是非。所以才会有人因为张春桥的“慷慨激昂”的自我辩护而大加赞叹,为张灵甫被视为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而鸣不平。即使那些为历史翻案的材料对这个历史人物个人品性的描述都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也不应该成为改写历史的证据,因为这一切所涉及的仅仅是个人的品性,而不是历史的善恶问题。换言之,正是他们的优秀品性造就了他们的历史悲剧。因为他们犯的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历史性的错误。因此,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错,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是其所信仰的,但不能因为坚持信仰,就可以由历史的恶成为历史的善。
那么,现今各种为历史翻案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可以有两种:一种不过是借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之名而申张自身的利益诉求;另一种则是以历史的态度寻求历史的真实,要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评价过去的历史。对于前者,不过是现实的阶层、利益集团冲突的一种表现,需要认真进行分析,以明确其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而对于后者,则必须给予尊重,并通过深入的历史分析而明确具体的历史事实,并要在此基础上给予明确的评判。
二、历史中的真与假
对于历史中的真与假的问题,就其根本而言就是要明确历史认识之中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对此,似乎整个史学界并没有异议。无论是现代主义史学,还是后现代主义史学,都承认客观历史事实的存在,只不过在如何获得客观的历史认识、如何表述客观的历史事实方面存在着差异。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但是,今天中国思想领域有关历史事件真与假的争论并未上升到这一高度,而实属于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对此,我们可以结合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认识与评价进行具体分析。
就目前国内思想界有关历史事件真与假的争论来说,主要涉及对近、现代中国历史事实的认识与评价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关于抗日战争中国共双方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有关抗日战争历史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问题,有关抗日战争中国共双方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等等。
对于上述相关问题的争论,首先涉及的是如何理解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即是具有历史客观性的就是真实的,换言之,就是要讨论在什么意义上客观的历史事实能够成为历史性的真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所谓的历史认识并不是历史进程之外的人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进程的认识、理解和把握,而是历史进程中的人对自身存在的认识。因此,任何历史记录总是会受到记录者个人的身份、地位、其自身的利益、眼界等等的影响,不可能是绝对的、客观的,必定会带有其个人特点,不可能完全排除记录者主观的因素,而且只有包含着记录着个人主观因素的记录,这种记录才是真实的。正如马克思所说,“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1]608?这些历史的剧中人物,同时也是自己历史的记录者、言说者。这也就必须导致历史认识中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认识、理解和把握,都不能以单一的历史记录为根据,而必须以一种总体的视角,去审视全部的历史记录,并通过对历史记录的分析、比较和印证,形成对历史事件的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以这样的一种历史认识的方式去面对关于抗日战争历史的各种争论,特别是其中有关的历史事实的争论,就可以发现那种否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各种观点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片面地使用史料,选择性地遮蔽部分的历史真相,以达到自身利益诉求的表达。其二,在运用史料的过程中,缺失了对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的分析。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对抗日战争中有关战役中各方伤亡人员数据的使用。例如,有关平型关大捷中歼灭日军数量的分析中。表现为以日军战报的记录来否认中国的记录。其背后隐含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前提,即共产党会说谎,用以欺骗国人,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日本人不会说谎,因为那是内部的军报,而不是宣传*历史真相(7):平型关大捷的真相[EB/OL],载http://www.xj163.cn/thread-440310-1-1.html。。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其三,片面地以历史记录数据的量作为判断标准,而忽视对事件本身性质的分析。在有关抗日战争中国共双方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上,突出表现在以国民党损失了多少军队、殉国了多少将军,在数量上远远高于中共领导的军队,以此来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观点首先缺失了对当时国共双方的实际状况的历史分析,有意或无意地在否认历史现实状况的前提下做出的判断。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看,平型关大捷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取得了什么样的战果,对于忻口会战的最终影响有多大,而在于其对于其对全民族抗战在精神上的影响。
其次,是关于历史认识中定性与定量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的长时段来说,单纯定量的考察是不足以改变历史认识的性质的。任何历史记载都必然包含着一系列的数据,诸如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大量的经济数据等等可以用数量做记录的内容,并成为理解历史事件真实性的重要依据。但是,数据并不能成为独立确立历史事件的性质。例如,中日学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中,很多中国学者都跟随着日本学者的思路去考证究竟在南京大屠杀的恐怖历史事件中罹难民众的人数问题,并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中被日本学者逼得节节败退。由此,日本右翼学者通过否定中国学者提供的数据进而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及其反人类的性质。这里的问题是,在历史事件的研究中,定量的研究不能取代定性的研究。就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来说,决定对其评介的绝对不是罹难者的数量,而在于这一屠杀事件反映出来日本侵略者反人类的性质。从定性的角度来说,无论是3万还是30万,其性质是一样的,因此不可能、更不可以用单纯的定量的方式来否定历史事件的性质。
再次,任何历史认识都具有当代性,所展示出来的是时代总体性存在的不同方面、不同部分。在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价中所要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历史,而始终包含着现实的利益诉求。因而,任何历史认识,即使是我们所要批判的那种对历史真实有意识的歪曲,同样包含着历史性的真实,是对现实的社会状况的理论反映,反映着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结论
通过上述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目前国内思想领域有关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核心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是目前各个不同的阶层、利益集团用以反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而申张自身利益诉求的表现。因而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就必须结合当前具体的社会历史状况进行分析,而不能单纯停留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本身的讨论。更不能以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历史事实来批判目前的历史虚无主义,否则同样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换言之,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绝不应当仅仅被视为单纯的意识形态斗争,而是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的镜子。必须通过揭示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存在基础,真正阐明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根源,从而通过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变革而才能消除历史虚无主义。这才是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根本任务。
第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必须进一步引向深入,从而深入到对历史真实的理论研究领域,进而推动马克思历史理论领域的变革。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是以现代史学对历史客观性追求为目标的,即将历史学家置身于具体的历史进程之外,去寻求所谓客观的历史事实。这种理解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把历史学家置身于历史进程之外去寻求所谓的历史客观性,而忽视了现实的人本身也是属于这一进程本身的。历史记述者自身的主观性同样是属于客观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必须明确历史的客观事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我们认为,科学史学所说的客观性并不等于历史真实。因为历史并不是死的事实的堆积,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活动,无论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还是对历史事件的记述,还是今天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都是现实的人的历史性的活动。脱离开对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分析,无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真实。
第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对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理解基础之上的。因此,必须明确任何的历史认识与历史评价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人对其自身存在的认识,并不存在着一个独立于历史进程之外去理解和把握历史的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关注现实的历史进程及其问题是每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1]56,只有真实地理解和把握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才能真正使理论走出抽象的封闭体系,以理性的批判精神直面现实的社会生活,并通过对现实社会积弊批判而推动社会的完善与变革,以实现人类的解放。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的辩证统一。因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认识历史本身,而在于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而实现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把握,认清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历史性,从而为寻求现实社会的变革探寻可能的方向与道路。这是马克思历史理论家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崔家善〕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3-0000-04
[作者简介]隽鸿飞(1970-),男,黑龙江兰西人,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13B018)
[收稿日期]2015-10-06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