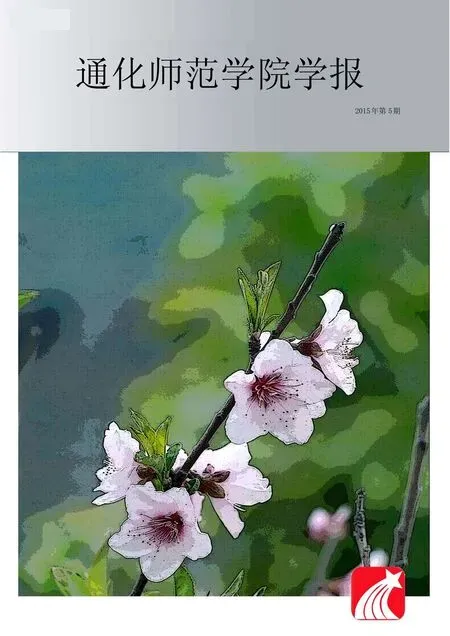设计史文献与研究集成引进的文化意义
——从《包豪斯》一书的出版引发的文化价值审思
连冕
(中国美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系,浙江 杭州 310000)
设计史文献与研究集成引进的文化意义
——从《包豪斯》一书的出版引发的文化价值审思
连冕
(中国美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系,浙江 杭州 310000)
中国社会及学界对于德国“包豪斯”学派的研究已进入反思阶段,大型迻译文献集成的出现,成为此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但由于设计史研究天生的孱弱,以及其他学科对于艺术学关注的缺失,导致引进过程中出现不少磕绊,尤其在教育、文化、市场和社群4个层面,仍然存在众多需要直面和解决的问题。正因如此,只有积极作为,从尊重历史和提升交流的角度,方能更好地借鉴全球优秀物质或非物质文化资源与成果,并为推进中国的设计、文化产业新建设做出贡献。
包豪斯;历史;设计;文化;交流
一
近期,由总部位于德国波茨坦的著名图书出版公司h.f.Ullmann,与供职于“德绍包豪斯基金会”(BauhausDessauFoundation)的让妮娜·菲德勒(JeannineFiedler)、彼得·费尔阿本德(PeterFeierabend)精心编纂的,为纪念“包豪斯”建校90周年而策划,以多语种刊行的现代设计史研究专书暨大型历史图片集《包豪斯》(Bauhaus),终于在前后耗时约2年的烦复筹备后,由浙江某出版社与中国美术学院包豪斯研究院及上海某大学文学研究院、英语学院联袂引进出版。
该书原著,作为一段时间以来,研究“包豪斯学校”及其教育、实践、发展、影响的最紧要集体创作与综合文献汇编成果,甫一流布,即在与之牵涉的各行业内外,形成了相当的支持声浪,继而引发大量关注。中国设计理论、设计史学界,在是书于2006年左右面市时便已知悉,并在随后几年,开始逐步绍介。2009年底至2010年初,作为纪念“包豪斯”创校91载,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率先倡议,并成功主办的大型回顾式文献巡展“包豪斯道路”上,[1]核心的几组呈现素材,乃源自其内。
追溯此书7年来的出版历程,可以说中国研究界结缘极早,引证颇夥,也收获甚众。从更深层的角度论,其之所以在“包豪斯”的母国孕育出雏形、弥散成“气候”,恐怕还是围绕着对“包豪斯”基本谜团的“破解”而展开。意即,就已在全球蔓延了约一个半世纪——甚至有的研究者称是两个世纪的 “现代工艺美术及设计运动”而言,“包豪斯”作为其关键的见证者、亲历者、扮演者,于寰球视野中,或跨行业领域内,既充当了启蒙者、开拓者和继承者的耀目角色,同样还兼具了相当的神秘性、失语性与障碍性。
仅就中国,及普遍意义上的华语学界的现状来讲,“包豪斯”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重新在台湾、香港经“欧风美雨”的洗礼而苏醒,并于80年代正式从纸面传播跳出,曲折进入大陆沿海及京畿地区的实际教学、操持层面至今,我们对“包豪斯”,仍处于极度困惑和迷茫的状态。以致有论者郑重指出,因之而生的那类片面的理解,实际就是一种“‘误读’的过程”及在“建立自己的适合价值体系”最终诉求下的“自觉误读”[2]。不过,《包豪斯》的一纸风行,也说明了,其各色误读的“果实”,并非仅仅见于赤县的地土。
于是,“神秘感”由兹而生:行业内的一部分“复古者”“附庸者”,将其视为攫夺“话语”的“法宝”,通过“奉上高台、精心祭祀”的荒疏且诡异的手法,将之转化为一种新的“愚众利刃”;或者,因远隔重洋、年深日久的时空错位关系,另一部分从业者,倒乐于对其或盲目崇拜、或消极挪用,“诪张为幻”式地进入一种“被催眠”的“恶性重构”情景。而《包豪斯》一书,借助头尾近90篇的研究专论,与尽其所能的历史勾勒,配合前后约650页,约有千幅的文、图穿插“叙述手段”,以及多达四五十位供稿人,真正意义上的跨界协作,第一次向世人较为充分地呈现了一幅档案与现实并置的、百科全书般的“全景图”,描摹出一幅宏观与细节并举、流年史诗般的“具象画”。继而,更为敲碎那种或主观、或失序的“巫语”,提供了一套着实好用,且应手、灵便的理论武器。
但,非是说,我们对“包豪斯”约14年的“校史”及其身后半个多世纪的播迁,做到了了如指掌。相反,这,目前看来称得上是现代设计启蒙核心之一的“无声的教员”,间接透过不断缀补在一起的历史材料,所喃喃传授出的、人类生存史上曾有过的艰辛拓荒,仍伴着飞速试错的时代的叫嚣高音,从未间断地,或被浪掷、或遭屏绝。
而当下,大量的社会实践,尚未能彻底超越现代设计起步阶段所布置下的种种可能。哪怕所谓“新乡土”化的、“新殖民”化的、“新女性”化的、“新人文”化的和“新职业”化的“顶尖”成果,也无非是在受过“包豪斯”等的教育、熏陶、调护、滋养后,一些不伦不类地改装得变了形的,故意的漠视与肆意的傲慢。那么,《包豪斯》一书的努力,正是让“沉默者”“被扭曲者”说话,不论是真实地自述,还是全力趋近“本事”的他述。
最令人感慨的地方还包括,作为一本汇编图文集,除了专业出版物一贯以来所必备的 “大事记”(chronology)、“文献”(bibliography)、“术语表”(glossary)和“主题索引”(index)等版块外,是书还编制了一份较为详实的 “产销图录”(merchandisingappendix)以及收载了一篇对“包豪斯”学校曾举办过的展览的简论。尽管,表层上说,尤其是前者,好似在提供商品收藏清单,功利地寄望热心者们按图索骥。但,依我们的理解,这还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尝试——即将直观的,却也曾经是“孤独无援”的作品,系统地陈列出来。既完成了一个纸面预展的指南目的,也实现了一次抛弃空洞颂赞与狡黠利诱后的,对无名之物的,建立于自觉敬畏伟岸宇宙和人类“大设计”行为之上的,非浅薄“民粹”般的公正直视。
自然,以上表述,我们仍站在出版物的角度,而其前提,是“包豪斯”早已为人类历史反复印证的优秀特质。但,作为研究者,尼采关于“历史之滥用”的告诫,也不断提醒我们:“包豪斯”既不应成为一种“伪装的神学”而令“我们仍活在中世纪”,[3]64也绝非溜滑光鲜得宛若矫情的“水晶”。国外学界、实践界,据观察,最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其因过度倾心于“大师”和“学校”,这两个教育的“形而上”极端概念,而致使在短暂的授业与冗长的传播期中,一概未见“产出”足堪往复剖析与评述的后辈——即“学生”。作为文献与研究集成专书,《包豪斯》显然也无法最终解决这个难题。毕竟如此一部在资本与权力运作面前,只能自感孱弱的纸册的重点,还是如何透过人的理性智慧,而令历史归位。
但,于其内容组织之下,编者更凸显了这样一类逻辑:即通过“主题”“作品”和“理论”三大环节,阐释出那种“胜利的缺憾”和“可能的冀盼”。其内,包纳了“事件逻辑发展的”线性“旨趣”,更触及到了“日常生活”的吉光片羽,继而谨慎地将“制成品”与“人物”“基础课”“工作坊”几个专论方向结合,以之作为全书中心,末了再配搭上“理论”化的展望式总括。那么,仅仅从如此一套“目录”上,我们便不难发现,它业已坚定放弃了对所谓“名家”和“名作”的急切追逐,人本精神与庶众情怀倒更显得溢于言表。这,正巧妙地回应了目前西方世界不时出现的,“‘包豪斯’是‘后现代’之后的设计绊脚石”的苛责,因之也就真正做到了,敬执之下不回护,奉慕之下不委曲。
可见,我们曾议及的,中国社会对“包豪斯”的“接受史”和“四个阶段”,[4]32-35在外域,也仍“似曾相识”地上演着。只是,我国学界的任务更为艰巨,毕竟于历史螺旋升华的“循环”里,大家仍处于某种意义上的,现代认识论和精神、气质属性的“下层”。
二
也恰是基于此种逻辑,针对这部《包豪斯》中文版专书,我们还有几点值得再做申说的内容。
其一,作为教育的关键工具。书籍之于教育,具有明白的功能。但,目前我国的设计界,对于阅读、收集、利用书本信息,仍延续了某种被扭曲了的艺术创作“思维”,即极端漠视。从设计专业特点看,的确存在着“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理论”的,两类植根于不同的生产、社会活动经验的知识总结方向。不过,其最核心的成果表达,仍是书册。只是,眼下“设计”的种种失范,致使从业者固执于“公共关系”的“身体”经营,注目得不多的字面材料,仍无外乎紧密系绕着“厚黑的政治学”与“寡廉鲜耻的经济学”。可惜,这后两者终将无法同气、牵系,而胜任作为一根真正有尊严的设计师的硬挺脊梁。
当然,我们也非是要简单推崇某种“包豪斯”般的“社会乌托邦”。透过该书,恰恰厘清了一个问题,即该“学派”中的大小成员、学员,他们经历过的种种社会、时代所赋予的苦难,我们往往在赞颂其最后的“成功”之余,竟又无情地漠视了。继而对他们,也是对我们自己,造成了不少次令人扼腕痛心的再伤害。或许还可以这么说,此种“苦难”经验所塑成的,才是我们这门学科的现代“元知识”。而仍显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设计者”,对之,却也一贯自信满满地情愿选择弃置不顾。
那么,“书籍的学问”比之“社会的学问”,更有其沉重感。它提供了一种,只要你并非装模作样地为了购回摆设,而是真心投入阅读时,便能领悟到的,灌注了世事曾经的沧桑与生活过度的丰裕的复杂情愫:是什么让我们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又是什么令我们快意自由、诚恳奋进?一旦着落于现实的教学,不论面对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的读者,如《包豪斯》这样的研究集成所能给予的,已不再是粗浅的普及功能,反倒是一束束刺透了隐喻着人类共同挫折、受难和亘古长存的宏大历史重云的启迪光柱。揭示它,又正是教育工作者,所一生难以须臾逃脱的使命。
就《包豪斯》所引发的讨论看,我国迄今在近、现代设计研究领域,可能除了建筑界,并未见出版过堪称理想的、高水准文献与研究集成专书。更勿论,特别地从“包豪斯”的“学案史”的角度进行爬梳,即延续“包豪斯道路”巡展已涉及到的主题,进一步汇编“包豪斯”在华夏大地上种种可能的“叶与花”。藉此,我们也认为,“设计”的第一属性固然表现在“通过造物、解决问题”之上,但以“积淀”为特点的历史研究所能做的,便是要将由此创制出的、关于“第二自然”的高明成果,及时地进行学理化的归纳与整编。其根本目标,并不是为了张狂地吹嘘过往、指导现实和规划将来,倒是为了眼前与日后,提供更加可能的镜鉴与鞭策。
其二,作为文化的核心载体。设计本身就是文化、文明的关键组成部分,自英国拉斯金、莫里斯等人开始,从历史学的现代意义上,便已得到过确证。反之,我们也不应粗陋地认为,古代就一定漠视“设计”。抑或,自以为是地推导出,所谓“旧时只有‘工艺’,没有‘设计’”的高论。工艺与设计,在不少的关联行业内,基本等价。而这,也不断为甚至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工程等理工、科学门类所坐实。意即,作为宏观文化的一员,其自当具备意涵、感情、思想等等必须要件。故此,设计作品与设计师,通过结构与双手,同样投射出为其所已然内化了的文明养分。而《包豪斯》该书,便赋予了我们如此的,于不同精神对象及其实体造物之间,来回穿行、跳跃的多彩选择,继而也足以攻讦那些由“误读的迷雾”而生的,认知、行为上的极端与片面。
例如,早年,佩夫斯纳为从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这一段现代设计的演变所做的学术贡献,便是通过将两者视作不同时代的文化符号,进行了全新的历史性连通,继而成功勾画了日后将对世事产生深远影响的“设计之物”的“前世与今生”。然而,因为中国设计实践界的“不学”,也因为中国研究界,对曾经存在过的、真正有价值的社会“生产”的反应彻底“滞后”,我们几乎是在集体盲目的情况下,否定了莫斯利、格罗皮乌斯等人,于欧洲根源文化中的苦苦求索——即现代设计从发端的那一瞬起,就已不是等着“灵光乍现”的政、商掮客们,所能讨巧地琢磨出来的;它们倒更是从残酷而别辨的藤蔓上,是推溯向更久远智识的枝干上,逐渐得到培植、滋养而茁壮长成的。
更准确地说,“包豪斯”的教学,包括基础课程,只要仔细阅读、悉心体悟,便能轻松看到,无一不是对上承古典文明、下启文艺复兴的“中世纪”,尤其是“哥特”时期,手工技艺及其训练的研究与挪用、简化与现代化。当然,此点,最直接的线索,就是《包豪斯》一书中不少该校执教者对 “中世纪”作品的分析草图。或许可以这么理解,此类国外研究集成的引进,或许非能直接作用于当前中国主、客观的 “设计进程”上,但却可以从激励的层面,起到某种特殊效能——即直观地道出了“外域伟人”的“起家”,绝不是得自飘渺的“神示”,并更客观地指出,疲于为“现代价值”奔命的国人,在日后的“膜拜”,或即“身份认同”的方向,是自己那本不该遭致如此鄙夷的辉煌“造物史”。
其三,作为市场的解毒药石。《包豪斯》一书,纵然仍有不少缺憾,但对于目下言行偏颇、乖戾的我国设计界,仍不啻为一张分量颇重的医方。如前所述,上世纪70年代末,研究界、实践界便已踏上了“包豪斯”的“再引进”之路,可期间的努力,只能说是散点。东方本不是“西方”的“沃野”,以致到了90年代末,不少赶上设计行业兴盛浪潮的出版机构和那些热心的出品人,在国内外苦无资源的状况下,仍仅能翻译一些片语只言,聊以充作应付市场所需的权且之计。所以,即使仅就这个层面论,《包豪斯》中文版的成功也是必定的。不过,我们不应如井蛙观天,骄傲于些许非原创的,单单表现在推广上的“业绩”。因为,对于物与“非物”的种种,西国远邦虽不尽然有多么重大得难以逾越的领先,但我们总归落后。事实上,国外研究集成引进之成功,更重要的将要表现在提示了新的,一如福柯所言的“知识考古”的可能:“档案的这种从未完结的,从未被完整地获得的发现,形成了属于话语的形成的描述,实证性的分析,陈述范围测定的总的范围”;“(而考古学)这个词并不促使人们去寻找起始,也不把分析同挖掘或者地质探测相联系。它确指一种在已说出的东西存在的层次上,探究描述的一般主题”。[5]147
在亟需了解国外发展动态的情势催逼下,事实上,若真能做到对西方“学统”这一“一般主题”微观且细腻的探掘,将比之简单引进两三部名人文集、当代图册,更令国人“说话、办事有底气”。毕竟,我们透过那样的系统研究,已可以碰触到西方之所以实现超越的根本因由。当然,还可借此,除一除我们从业者身上那类源于草莽的野气,真正意识到历史循环的大规律和大法则,改一改那类“成王败寇”式的、源于蛮荒的性子,为更美善的新世界,多积蓄些绝非蠢动的能量。也就是说,透过《包豪斯》所能窥见的,不再仅是那些似乎已详悉的一切,我们倒是更要向过往、更要向未来确实拓进。
比如,除了“包豪斯”在现代设计领域的直接努力外,《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曾有所载记的,自1747年由英格兰诞生雏形,到1774年影响美国的基督教“震颤教派”(The Shakers),在强调教徒于村庄中共同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制作相应日用器具,相信男女平等并自愿禁欲之余,[6]1603还曾主导过历时约200年、包罗万象的乡村集体设计、加工和营造活动。若能近距离观察他们手下的“制成品”,大到宗教建筑,小到匙、杯、盘、碗,自能察觉其中所荡漾着的,静谧、鲜活且感人心脾的,宗教与世俗充分调和的高贵雅意。尤其是在其设计观念,或隐秘、或张扬的表达上,实在也可谓玄妙绝伦,称得上于碌碌忙忙之际,竟早已默默超越“包豪斯”的“启蒙者”拉斯金、莫里斯等辈,不知凡几了。而关于该“教派”的造物,目前美国已有成体系的研究问世,该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在纽约开办的“装饰艺术、设计与文化研究生院”(BGC),更曾于2008年5月至6月间,策划过名为“遁世:‘震颤教派’的设计”主题展。[7]
我国大陆地区,由丁光训、金鲁贤主教主编的《基督教大辞典》内,亦专为该教派开列词条,议及除了“奉行独身禁欲”,“试图仅靠源源不断的皈依者来壮大自己”外,“神秘而节制的礼拜式、经济上依赖农业和手工业的原则、对社会的排斥以及狂热地遏制会员个性发展的做法,对于生活在迅速变化的工业社会的人来说,几乎无吸引力”等,均是其逐步衰弱的因由。比照而言,这,又与后人对“包豪斯”精神式微的评价,何其雷同。不过,该条目在总结此教派其他著称的特点时,还认为:他们“勤劳友善、不在服装和装饰上标新立异,主张和平主义和在实用物品方面表现出创造性。他们所使用的家具的朴素美得到高度赞扬,他们的创造性体现在一些非凡的发明上,其中有圆锯、洗衣机、金属笔尖、晒衣夹等”。[8]815-816这些,又都是不自知地从“设计-造物史”的角度,做出了中肯的记述。
可惜,至今,国内除上述基督教体系的初步成果外,甚少有人成功地专门议及①,更遑论能从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伪专家”“渎神者”口中,听到些什么“史学史”“设计理论”上精微的妙论了。换言之,目前,只一册《包豪斯》,再好,也远远不足。面对热衷追逐明星、喜好复制的华人市场,我们所希冀的,反倒是该书能够真正起到“行气”和“发散”的功能。
其四,作为大众的业余文化滋养。当前,随着社会分工,于“芯片-互联网”等“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持续发酵中日益步入精细,设计界也早已明确出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分野。而在高等教育这类环境里,硬要强化初级的“实践与理论并重”的模式,已愈发显得如置身“前现代”般徒劳。事实是,透过《包豪斯》,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现今我国大学里所谓的“设计理论与实践”训练,早该在初、高中,甚至是小学教育中逐步解决、完成。大学教育,包括大多数高等职业教育,不该再指导如何利用几款现成软件进行低端的操作,不该再指导如何轻松地阅读设计史、设计审美等“常识”类作品。即便目下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尚未能实现如此愿景,我们大多数明智的教育者,也当要鼓励青年,多用、善用社会资源,获得自我学习、实现终身学习的各种积极心态与良好习惯。
于是,作为大型设计史文献与研究集成,其自然不该被定义为一部初级“手册”。但,《包豪斯》的优秀之处,还表现在能借由其独特的布设,为非专业读者提供必要的翻查快乐,继而吸引他们展开个性化的“钻探”。这,正是在为时下流行的“民间研究”,为值得鼓励的“泛研究”,提供新的“信息索引”可能,也就是为早该缩小的“业余”与“专业”间的知识鸿沟,提供了更加现实的扶助。不过,就出版、编辑的角度看,此中译本的出现,却也反映了非设计理论、设计史专业的译者,对必要知识的极度匮乏与轻蔑。当然,更重要的是,若说设计消费的盛行,已实现了现代西方审美情趣无远弗届与“扁平化”,那么,现代设计、艺术作品,及其精神、意识的普及,连带各国本土、在地化的,造物、工艺智慧和思想的深入人心,却仍极端地乏善可陈。
我们的设计界,在“阿堵物”面前,必须自问,是否早已缺乏耐心,不愿支持、培育可靠、真诚、谦逊的文化中介者。我们的翻译界,在“孔方兄”的脚下,也当自问,是否也已放弃努力,不愿钻研、深究除了“鹦鹉学舌”之外的过硬功夫。必须留心,在“使用”与“被使用”处于两难抉择之时,往往是那些傲慢不已的所谓“专业者”率先倒下,并最终为坚强、执着的“非专业”民众,所彻底唾弃与替代。《包豪斯》的引进经验,也给日后势必将更繁难的历史、理论工作提了个醒:即在过度注重油滑的“策略”与“方法”之余,我们是否还敢于“提问”、勇于“求知”,并最终能够胜在“得解”。
前述四点,是一个循环,从教育到文化、由市场到大众,在工具与载体的信息传递中,于药石和滋养的效力承继内,我们更可将如此的书册,看作是一部小小的“知识博物学”与“精神进化史”。而当云卷云舒之际,你我所诚意渴求的,无非不过是透过造化的曙光,瞥见人类文明于玄黄天地之中尚能引以为傲的,那些真的经得起洪荒宇宙检验的大道、名工与圣器。
[1]杭间,靳埭强.包豪斯道路:历史、遗泽、世界和中国[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
[2]杭间.中国设计与包豪斯——误读与自觉误读[J].艺术设计研究,2011(2):79.
[3][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M].陈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连冕.时代与精神:“包豪斯”之于中国的两个基本问题[C]//许江.包豪斯与东方:中国制造与创新设计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
[5][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英]萨默斯等.朗文当代英文大辞典(英英·英汉双解)[Z].朱原,等,译.北京、香港:商务印书馆、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2004.
[7]http://www.bgc.bard.edu/gallery/gallery-at-bgc/past-exhibitions/ past-exhibitions-shaker-design.html.
[8]丁光训,金鲁贤等.基督教大辞典[Z].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章永林)
G05
A
1008—7974(2015)03—0085—05
2014-12-01
连冕,中国香港人,博士,副教授。
10.13877/j.cnki.cn22-1284.2015.05.019
——包豪斯的遗产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