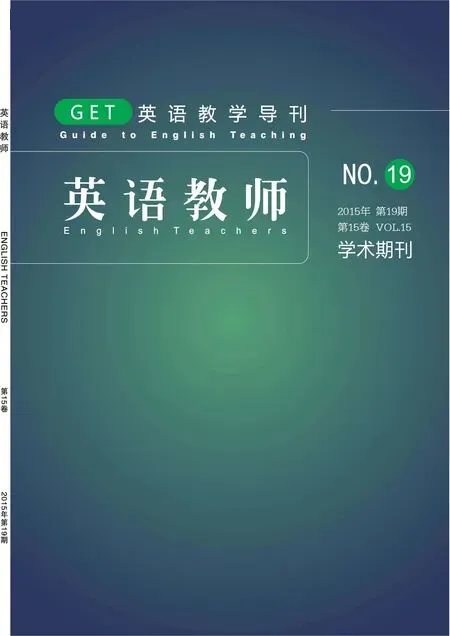《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评析
郑意长
《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评析
郑意长
明代戏剧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是中国古代戏曲,尤其是昆曲的一朵奇葩。问世400多年来,《牡丹亭》的译介与传播经久不衰。通过研究《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情况,评析其在此过程中的得失利弊,以便于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昆曲及中国戏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牡丹亭》;英语世界;译介;传播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宣布中国昆曲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而《牡丹亭》则被公认为最能体现昆曲独特美学特色的代表性剧目。但海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及观众是不是如我们熟知《哈姆雷特》一样,谙熟《牡丹亭》呢?《牡丹亭》是汤显祖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古代戏曲的瑰宝。自问世以来,其英译与传播经久不衰。故事主要讲述了杜丽娘和柳梦梅两人生死聚散的浪漫爱情故事,奇幻与现实相结合,鲜明而又超前的主体性精神诉求,深厚的抒情气息,典雅的曲文文本,都体现出《牡丹亭》强烈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强大的艺术魅力。白先勇认为《牡丹亭》上承《西厢记》下启《红楼梦》,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峰”(付小悦 2005)。本文将对享有如此盛名的《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情况进行述评与研究。
一、《牡丹亭》的译介
《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日语、德语的译介相比,起步较晚。但由于英语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强势地位,《牡丹亭》的英译成果却源源不断、蒸蒸日上。现从英美译者与中国译者两个视角对主要译作进行评析:
(一)英美译者的译介
1939年,哈罗德·阿克顿(H.Acton)编译了《牡丹亭·春香闹学》,在序言中对《牡丹亭》的情节梗概进行了介绍,并视之为中国明代的文学代表作之一,载于《天下月刊》第8卷4月号,由此开创了《牡丹亭》的英译历程。
1972年,纽约的树丛出版公司(Grove Press,INC.)出版了美国汉学家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选译的《牡丹亭》,即《闺塾》《惊梦》《写真》《闹殇》四出。该译本曾再版多次,并一度作为教材在英语国家传播。1980年,印第安那大学出版了白之的全译本。白之的译作不但具有汉学家的学术品位和艺术鉴赏力,还体现了他的翻译观:尽量保持译文表达的张力和在英语世界的可接受度(acceptability)。例如,“添眉翠,摇佩珠,绣屏中生成士女园。莲步鲤庭趋,儒门旧家数。”的翻译为:
Brows limned black with emerald sheen,
Pendants swaying at waist,
Pictured beauty steps as from broidered screen.
Lotus feet in tripping measure
Set long ago as mark of reverence
By the son of the master,Confucius himself,
Scion of scholar's line I now appear.
(Birch 2002:42)
总体来说,白之的译本措辞流畅且语用地道。为了传递原作的文化内涵,他将原作中的人名、曲牌名等都采取了意译。对于《牡丹亭》中的唱词和诗体部分,他则以自由诗体进行翻译。译者对文化信息量丰富的词句虽然采取直译法,但辅以注释作为信息补偿(compensation)。这样译本既保证了较高的准确性和文学性,又使英语世界的读者获得了极大的来自异域的美学享受,对于《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6年,美国W·W·诺顿出版公司出版了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牡丹亭》选译本。宇文所安选译了《牡丹亭》中极具浪漫主义情调的《惊梦》《玩真》《幽媾》以及汤显祖的《作者题词》,并将其编入《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宇文所安一方面对于原文中可能造成英美读者阅读障碍的文化信息类语码进行了大幅归化处理;另一方面,又艺术性地传递了来自中国的异域情调和汉语的表意魅力。例如,为了有效译介《牡丹亭》的诗词唱腔,他采用参差各异的英语表达形式来完成英汉不同语言美学体系的跨越。宇文所安的选译本在编入《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出版后,与白之译本一样,曾长期在英语世界被用作大学教材,这进一步提升了《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
(二)中国译者的译介
1960年,《中国文学》第1期刊发了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夫妇选译的《牡丹亭》。译者挑选了《标目》《闺塾》《惊梦》《寻梦》《写真》《诘病》《闹殇》《拾画》《幽媾》《回生》《婚走》,共计十一出曲作进行翻译。该译本虽未能展现出《牡丹亭》的全部精华,但与此前的阿克顿(H.Acton)译本相比已在英译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域外传播重视的不断提高,愈来愈多的国内译者积极参与到《牡丹亭》的英译事业中。1994年,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光前的英语全译本,这是中国译者的首个全译本。与白之(CyrilBirch)的译本相比,张译本虽然在译入语的地道性与流畅性上略逊一筹,但张译运用无韵体(blank verse)来翻译剧中的唱词和诗句部分,所以在传达《牡丹亭》的音韵和节奏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例如,“先祖昌黎公有云:‘不患有司之不明,只患文章之不精;不患有司之不公,只患经书之不通。'”的翻译为:
(Han):My ancestor Han Yu once wrote:
“Don't blame the officials for their stupidity,
But lay the blame on your poorly written articles;
Don't blame the officials for their partiality,
But lay the blame on your poor mastery of the books.”
(张光前 1994:26)
200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汪榕培的《牡丹亭》全译本,并且该译本被收入同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大中华文库》(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汪榕培的翻译原则是“传神达意”,例如,“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的翻译为:
When I'm awakened by the orioles'songs
And find the springtime beauty all around,
I stand in deep thought on the courtyard ground.
(汪榕培 2000:97)
一方面,译者对剧中大量负载文化信息的语码进行了隐性或归化处理,并竭力用英语进行二度创作,把原文的散体宾白尽量译成通畅的英文,以实现原著与译著对等的美学效果;另一方面,对于可译度较低的唱词和诗句,译者则以抑扬格为基调,采用了多种韵式,侧重于追求原有意象的传递。
2009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许渊冲、许明翻译的《牡丹亭》。与之前某些译本不同的是,该译本是汉英对照的舞台本,译者选译了《牡丹亭》中的《闺塾》《肃苑》《惊梦》《慈戒》《寻梦》《魂游》《幽媾》《欢挠》等22出曲作。例如,“甄妃洛浦,嫡派来西蜀,封大郡南安杜母。”的翻译为:
Descendent of Princess Zhen by riverside,
My family did in the west reside,
Having left Mount Eyebrows,
I'm the first Lady of Nan'an now.
(许渊冲、许明 2009)
总体而言,译文不仅仅拘泥于表层意思,还传递出其深层意蕴;不但表达出原文的言内之意,还努力再现其言外之意。另外,译者还创造性地再现了原文的节奏感和音韵美,充分体现了许渊冲所奉行的“三美”原则,译文生动流畅,艺术性及表演性较强,使该剧的舞台表演又多了一个英文版本的选择。
二、《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舞台传播
《牡丹亭》在海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舞台传播频次并不太多,且发轫较晚。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密切,《牡丹亭》才得以呈现在英语世界的观众面前,现选取颇具代表性的三个案例进行评析:
(一)“颠覆性”的《牡丹亭》
1998年美国导演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ars)依据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的英文译本执导了《牡丹亭》并成功进行了首演,1999年该剧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完成了最后一次演出。塞勒斯的《牡丹亭》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颠覆性,汤显祖的原著被前卫性地进行了解构和再创作。杜丽娘由东方文化中典型的多愁善感的美女突变为情欲炽烈且自恋严重的少女,原作写意象征的手法被断然摒弃。剧情变得相对单薄枯燥,节奏也较原作迟缓,主体架构也因之略显沉重,观众感受到了明显的后现代审美压抑。这种后现代主义的颠覆在学界及戏剧界引起较大争议,但它毕竟开启了《牡丹亭》在英语世界舞台上的传播历程。
(二)“民俗化”的《牡丹亭》
1999年,美籍华人陈士争的《牡丹亭》在纽约首演。他排演的《牡丹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民俗化”(folkishness),为了展现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俗民风,陈士争从舞美设计到道具服装一律使用来自中国的物品。观众在舞台上见到了一座虚实结合的江南园林,亭台轩榭、假山湖石、金丝雀笼、日常起居、丧葬礼仪等一一再现,异域风情(exotic style)跃然入目,这在视觉上就很快征服了英美观众。
可是,很多学者和戏剧文化界人士都难以认同陈士争“民俗化”的《牡丹亭》,认为该剧没有尊重中国传统舞台艺术的美学传统,只是简单拼接了各种艺术形式,构成了一个中国民俗的集市,使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作品流于浅层的符号化再现,进而变成了艺术形式上的感官刺激。但陈士争的《牡丹亭》毕竟是第一个以“全本”的形式向英语世界舞台进行的传播,这让英美观众有机会全面认知中国的戏剧瑰宝,其积极意义是不应被抹杀的。
(三)“青春版”的《牡丹亭》
2004年,白先勇倾力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开始了其世界之旅,先后在旧金山、洛杉矶、伦敦等英语世界的文化重镇进行巡演。白先勇在改编剧本时,力求使古老的昆曲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因此,他在舞美设计方面着力凸显东方特有的写意手法,舞台灯光也被赋予了复杂信息的含蓄传递功能,剧本节奏由原来的内敛舒缓改为饱含青春气息的律动,“体现出《牡丹亭》较为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多重艺术魅力”(袁行霈 1999:134)。
该剧在英美各地的巡演大获成功,老中青观众皆被吸引,学术界及戏剧界的专家也极为推崇,反响十分热烈。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让英美观众较为深入地认识了中国昆曲,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欣赏与研究兴趣,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知,一些英美院校甚至在此后聘请中国专家开设了昆曲或戏曲课程。
结束语
以上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及剧作者或传播者对《牡丹亭》的翻译和推广,虽然在译介或传播的背景、目的、策略等方面各有不同,但都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或观众了解中国戏剧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并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牡丹亭》在海外的文化影响力。从上述译介及舞台传播的案例可见,类似《牡丹亭》的中国经典戏剧在海外进行译介与传播时,语言的转换只是一个方面,适度地保留和传递原有的文化意象及审美体系才能充分体现其语言及文化的丰厚内涵,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我国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
引用文献
付小悦.2015.看我们后院的牡丹有多美——青春版
《牡丹亭》北大演出之际访白先勇[N].光明日报,2015-04-08.
汤显祖.1994.牡丹亭[M].张光前,译.北京: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汤显祖.2000.牡丹亭[M].汪榕培,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汤显祖.2009.牡丹亭[M].许渊冲,许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袁行霈.1999.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34.
Birch,Cyril(trans).2002.The Peony Pavilion[M].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42.
作者信息:300222,天津,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