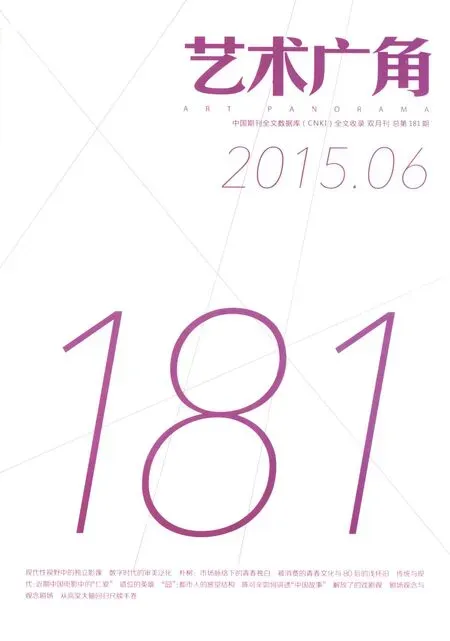被消费的青春文化与80后的浅怀旧
关建华
被消费的青春文化与80后的浅怀旧
关建华
关建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近几年,华语电影界刮起了一股怀旧之风,以大学青春成长故事为题材的小清新怀旧电影成了黑马,不断斩获令人瞩目的票房成绩。其中,台湾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以下简称《那些年》)在内地上映第二日起,便迅速超过同档期的两部超级大片——《金陵十三钗》与《龙门飞甲》,成为了单日排片量全国第一、观影人次全国第一的“双冠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投资4000万,获得了约7.19亿元的票房;2014年上映的《同桌的你》,票房冲破4.5亿,位列2014年国产电影票房第四位。这几部与同时期类似的《小时代》《中国合伙人》以及近期上映的《匆匆那年》等青春电影,共同构筑了“青春怀旧”的文化景观,顺应了小清新的大众文化欣赏趋势,以小投资获得高票房,形成了近年来中国商业电影浪潮中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在全民怀旧的浪潮中,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此类青春电影受追捧的背后,有着系统的商业策略和大众文化的支撑。影片卸下了沉重的历史负担,淡化青春的叛逆,省略了成长中人性的挖掘,转而通过修补青春镜像、营造感伤情绪来获得大众共鸣,拉大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营造怀旧的伤感,充分利用了消费时代中的快餐式心理,凭借“浅怀旧”的方式,在温暖与伤感中进行了一次集体的青春缅怀。
一、青春影片的流变
电影诞生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青年题材一直是创作者非常热衷的,在英、美、日、韩等国,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春电影体系,但是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青春电影并没有形成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完整的发展体系,被人指出“青春电影是在场的缺席者”。当然,华语电影中并不缺乏青年人的角色,只是受国内环境的影响,青春影片依附在时代背景上,其发展偏向于政治化、功用化和成人化,无法表达出青春影片应有的声音。
建国后到文革结束的近三十年里,“影像艺术更多展现的是革命中的年轻人如何经受考验和历练并最终走向成熟的,而这种成熟其实对应的是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以及在敌对势力面前英勇不屈的战斗信念和实践精神”[1]。如《战火中的青春》《青春之歌》等。这期间的影片展露出青春元素,但个人话语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青春的叙述热情洋溢,个人成长史从属于国家的生成史,凸现为为了至高无上的事业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主题,因而很自然的将个体叙述消融到国家、历史的大叙述之中,形成了共性大于个性的艺术特征”[2]。
文革结束后,国内政治环境逐渐宽松,随着改革开放和文艺新政策的推行,电影对于青春的表达也逐渐自由和多样化,如第三代导演谢晋的《青春》,第四代导演的《青春祭》《红衣少女》,以及第五代导演的大胆尝试。随着第六代导演的崛起,华语青春电影进入到了更加开放和多元的阶段。早期的第六代电影“顽强地保留了青春反抗性、意识形态异性和边缘性色彩……其青春反抗性还是发自真诚的,更绝无戏剧性”[3]。王小帅《冬春的日子》讲述了青春私密体验和心灵成长;张元《北京杂种》包含了摇滚、性、暴力、毒品,暗含了对主流价值的排斥,但也显示了青春成长中的迷茫与苍白,以外在的对抗暗合青春成长的规律。另外贾樟柯的《小武》、何建军的《邮差》等,都以冷峻的镜头描写了青春的迷茫甚至病态,挖掘了青年内心的隐秘与惶恐。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越来越成为影片生产所考虑的因素,虽有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站台》《任逍遥》,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等影片,继续讲述特殊历史和社会环境中青年人成长的创伤、思想的碰撞,也有部分知青题材,如《美人草》《高考1977》等讲述特定历史的特定人群,但存在于第六代导演早期作品中的明显的意识形态对抗性趋于缓和,时代背景也逐渐模糊,“青春果断走进了纷扰的社会大环境,成长的创痛不再是个体的专利,而是人人皆有,青春的温情和无奈交织而行,导演意图表达的是青春可堪回首的珍贵和不复再来的遗憾”[4]。
随着新生代创作群体的出现以及商业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速,青春电影表现出日益向青春消费方向发展。更年轻一代的导演没有经历过革命与文革,对历史的记忆也相对模糊,剧本创作主体以70后甚至80后为主。这时期的青春电影,往往在网络小说走红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小说风格轻松幽默或温暖感伤,电影风格偏向于小清新,相对符合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这批人生活在经济社会的背景下,历史与国家的责任意识逐渐淡化,自我意识又消弭在商业社会的大潮中,个体的时代精神创伤被模式化复制到每个青年人身上,构成了集体的青春记忆。这时期的青春影片更贴近当下,贴近世俗,更具有商业意识,“从不同的层次和方面来展现新时代日趋时尚化的生活”[5]。从李芳芳的《80后》,到11度青春的网络电影系列之《老男孩》,再到近两年的《致青春》《小时代》《同桌的你》,青春的话语权正逐渐从精英分子转移到青年大众手中,逐渐被80后和90后夺取。但影片多以都市为背景,充斥着年代标签,缺少青春的奋斗与心灵的挣扎描写,变成了物质和文化消费的载体。
综上来说,中国式青春电影虽然是“在场的缺席者”,但仍有着模糊可辨的轨迹,“大体走过了一条从‘青春万岁’到‘青春残酷’再到‘青春消费’的道路”[6]。
二、80后怀旧的文化背景
“似乎在一夜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先是怀旧。他们唱着‘老男孩’,感叹消逝在记忆里穿着海魂衫皮凉鞋的夏天,怀念看过的连环画,还有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再是叹老。一群在父母看来还是小孩的80后,在比自己更小的小孩面前大叹‘老了’‘心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7]这成了80后人群的普遍写照。70后作家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中说到“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面对70后发出的“这么早就开始回忆”的感慨,80后出生的人普遍患上了“初老症”,被称为“还没长大就老了”的一代。我国对青年人的定义是14岁到28岁,而80后出生的人最小的是24岁,最大的也才34岁,这批处在青春尾巴上或刚刚迈出青年阶段的人群,纷纷回忆自己的青春,过早陷入集体的早衰,这背后的动因并不能仅仅归结为“矫情”,而是有着深刻的生存环境烙印,也是被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所导引。
躲过了文革,迎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出生的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百年来,中国人终于有了一片安稳的天空,没有压迫,没有战争,没有政治的紧张。处在经济转型的年代之初,政治环境逐渐宽松,社会又没有形成强烈的商业竞争气息,人心没有那么浮躁,文化领域涌现了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现象,处于众生喧哗的、追求理想的年代。虽然80年代被定义为“反叛”与“彷徨”[8],但反叛与彷徨的社会氛围,对于正在儿童期的80后来说,并没留下多大印象。所以,80后与过去百年间的中国人比较,拥有完整的童年。在80后的青春初期,社会成员间还有基本的尊重与道德束缚,人与人的交流还依赖见面和信件等,虽然清贫但没有温饱的压力,虽然不富裕但没有巨大的贫富落差。“但是当这些年轻人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这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所有的善恶美丑,不但错过了工作包分配,而且没赶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同时却赶上了大学扩招,研究生满大街的尴尬局面,基本的生活尊严都不能保证。”[9]社会发展到今天,80后大多成家立业,处于黄金年龄的这群人要生儿育女、赡养老人,又要面对房贷保险、生存竞争,诸多的生存风险容易让人焦虑、踟蹰,造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返贫”。在寂寞的精神沙漠中,梦想成了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只能回首遥望无法返回的记忆绿洲。另外,在公共资源越来越倾向于少数群体,官二代、富二代在集体竞争中依赖特殊身份青云直上的背景下,80后大多数能够与现实抗衡的只有单纯的校园青春回忆。就连这种回忆,在近两年的青春影片中也都被植入了“毕业即失恋”的情节,没有逃脱“屌丝”被“高富帅”挖墙脚的悲剧。回忆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在这种巨大落差的影响下,回忆就显得意味深长。
青春是“终将逝去的”,但历经其中的我们却没有察觉到。“我走的时候还不懂得怜惜曾经拥有的事物,我们随便把一堵院墙推倒,砍掉那些树,拆毁圈棚和炉灶,我们想它没用处了……我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10]当年我们年少轻狂轻装前行,如今因现实的无望而回忆青春时,发现我们留下的只有模糊的面孔、青涩的感情和散落的时代标签。当回忆走向了虚无,我们愈发需要重建青春。而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让这一切有了再现的可能,通过传媒建构的文字与影像复制失去的青春,成为了曾经生活过的“今生今世的证据”。同时80后玩过的“老物件”也随着怀旧的文化倾向悄然走红,与文字和影像一起成为怀旧的载体。当文化遇到了消费,消费便开始引导甚至挟持文化的发展方向。青春怀旧就这样附加在经济之中,逐渐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并迅速弥漫开来。
三、当下影片重构的伪青春镜像
在消费文化挟持下的青春怀旧,体现的更多是商品价值而非文化价值。商业青春电影追求的高票房要求影片更加吸引观影大众,契合当下关注热点,符合观众心理预期,营造青春记忆的真切体现。《那些年》《致青春》与《同桌的你》正是在商业元素与文化怀旧的双重驱使下的“特定时代和社会的青春痕迹,不仅成为导演凭借个性的叙述方式再创造出被‘伪饰’的‘青春’,而且还以怀旧形式重构了观众的‘青春镜像’”[11]。
首先,三部影片都充斥着年代标签。青春的回忆弥漫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绪,而回忆青春的最好方式,无疑是场景的再现。同时,相对于文字、语言,影像更具有直观感,能迅速将观众带入特定的年代。所以,三部影片中充斥着特定年代的标签:遍地狼藉的宿舍是男生的大本营,氤氲着雾气的公用洗漱间与滴着水的发梢是女生的集体记忆,日本小电影是青春荷尔蒙发泄的对象物,逃课睡觉、考试作弊是青春的必修课,收音机,海魂衫,校园民谣……三部影片都是借用年代标签这种“记忆载体”让人产生“这段生活似曾相识”的感觉,相同的拍摄手法难免给人强烈的“代入感”,影片借助一闪而过的“记忆载体”弥补新晋导演叙事能力的不足。但是,青春的标签承载的记忆是被过滤的青春印象,只应是故事的点缀,并非青春的主体。影片中,无处不见的标签与浪漫的故事被故意缝合在一起,标签变成记忆主体,故事反而需借用标签才能界定年代,凸显了这些影片故事叙述的薄弱。
其次,三部影片里重构的青春镜像是伪饰的记忆。一方面,制造青春与现实的落差,伪饰青春的美好。“怀旧首先是一种心理现象,表现为美化‘故乡’、夸大‘过往’人和事的优点而忽略其不足的心理历程,并呈现出想象胜于实际的特征。”[12]当下青春影片也明显地将故事割裂为两个阶段——校园青春期和社会青春期,以制造两个阶段的落差,来暗示回忆的理由。《那些年》中,柯景腾与沈佳宜共同走过了残酷的高中生活,并在大学初期开始了恋爱,本以为故事会向着圆满方向发展,但结果是柯景腾以及追求沈佳宜的所有朋友都未能和她走到一起,最后在沈佳宜的婚礼上,柯景腾以别样的方式赢得了青春之爱,但这样的爱总有种失落的倔强。《致青春》中,将校园的浪漫与社会的无情缝合在一起,郑微执着追求的爱情在毕业后被现实打败,阮莞追求的爱情最后用生命做代价,陈孝正追求的成功踩在无爱的婚姻上,张开诗人的豪情化作混饭吃的工具。《同桌的你》则完全综合了前两部影片的模式,从高中的单纯发展到大学的浪漫,再到毕业、出国、分手,将青春回忆与残酷现实缝合一起,营造梦想与现实的落差。虽然影片最后男主人公林一面对周小栀的婚礼那刻,给我们上演了虚实两重结局,一是幻想中的逃婚与私奔,一是现实中的接受与祝福,梦醒后周小栀终究还是嫁给了别人。那样一场虚幻的私奔给了人青春逆袭的激情,却也留给此刻无尽的失落。回忆总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但这种不满被导演片面化地解读为“初恋嫁作他人妇”与“工作的失败”,将前期的喜剧与后期的悲剧缝合在一起,故意制造未完成的青春缺憾,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观众浅层次的回忆,从而让怀旧成了名正言顺的潮流。另一方面影片修补了一份教科书式青春,用回忆来弥补青春留下的遗憾。影片里的青春涉及到成长过程中所能经历的一切元素——友情、爱情、学业,以及发生在这三者之间的所有故事。学霸也好,痞子也好,默默无闻的班级路人甲也好,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但又并非真实,而是一场彻底的虚构,“这种影像化的‘青春’也恰是被‘伪饰’或被过滤的‘青春’”[13],伪饰了一段包罗万象的典型的青春,符合了当下青年寻找存在感与认同感的心理诉求。但“怀旧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而现代社会关于怀旧的文化记忆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感和深度感消失,从浪漫的历史想象物变成现实生活的消费物,甚或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消费寻找怀旧理由”[14]。青春影片也从过去的沉重且反思的主题,逐渐变为纯怀旧的疗伤影片,从片面的深刻过渡为全面的肤浅。
四、消费后的满足与失落
当怀旧情结变为一种怀旧行为,怀旧文化就产生了,这种文化需要表现形式,于是文字、影像、老物件、老品牌、家族记忆、个人感情就都成了文化载体。而文化载体变为商品后,又反向成为消费时尚和怀旧情结,吸引我们消费自己制造出来的怀旧情绪。小虎队重新聚合走上春晚便是全民怀旧的成果,但我们发现今天的小虎队早已是三个老男人,气喘吁吁地跳着十七岁的舞蹈,唱着青涩的忧伤,有种卖弄的尴尬。悄然走红的“国民床单”也让网友纷纷表达怀念之情,一时之间脱销,可买回家后能铺上几天?我们对过往的留恋如此虚伪,仅仅需要一点安慰就能满足心灵的欠缺,然后我们如阿Q捏了小尼姑的脸一样,带着满足转身走进未来的生活。被消费绑架的“青春怀旧”,其文化内涵已被冲淡,《致青春》这类的浅回忆青春影片亦是如此,在温暖中加点感伤,在轻狂后加点失落,在回忆中品味遗憾,在遗憾中感慨成长,赚取几滴眼泪,赢得巨额票房。观影后,观众带着淡淡的忧伤走出影院,只记得几个时代标签和男女主人公未完成的爱情,不用思考,没有沉重,怀旧情结似乎也被解开,似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不用回忆了。
但是,重构青春之后,带来的必然是对青春的解构。怀旧本无可厚非,但将怀旧进行到底就好似给维纳斯安上了胳膊,无论多完美,感觉都不对,毕竟人们怀念的只是那份纯真与青涩氛围,怀念的是彷徨的心理和追梦的无畏。当到处都是怀旧餐厅,满大街的怀旧服饰,打开电视播放的是怀旧栏目,走进影院看的是青春电影,好似时光倒流,却有着浅薄与矫情之态。连续观看几部类型如此统一的商业青春片,犹如重新经历了几次青春,审美疲劳导致情感麻木,丢失了回忆的感动触点,最终习惯了青春的故事,开始嫌其幼稚和无聊,逐渐拒绝回忆。无论如何热爱,耐不住狂轰乱炸,“所谓的‘青春不朽’的神话,终究不过是市场消费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15],而“青春不朽”又被无孔不入的“青春商品”迅速腐蚀、解构。
当青春被解构,所有青春的记忆都以可观、可触的方式呈现,金钱成了购买记忆的手段,回忆不再奢侈与感动,而成为一张苍白的纸。丢失了感动触点的我们,将结结实实地迈上虚无之途,成了无根的精神游魂,在当下生活中麻木地四处游荡。
注释:
[2][3][6]陈旭光:《影像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280、280页。
[5]彦纯钧:《与电影共舞》,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5页。
[7]白龙:《莫让青春染暮气》,《人民日报》,2013年5月14日。
[8]甘阳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9]何禾:《80后“暮气沉沉”不能只怪80后》,http://gb.cri.cn/42071/2013/05/14/2165s4115145. htm。
[10]刘亮程:《今生今世的证据》,见《一个人的村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11][13][15]陈进武:《青春镜像、成长修复与叙事的‘缝合术’——以〈那些年〉和〈致青春〉为中心的考察》,《东岳文丛》,2013年第7期,第120、121、125页。
[12]周平:《解读怀旧文化》,《理论月刊》,2007年第8期。
[14]胡磊:《大众的怀旧情结与文化消费》,《文化月刊(下旬刊)》,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