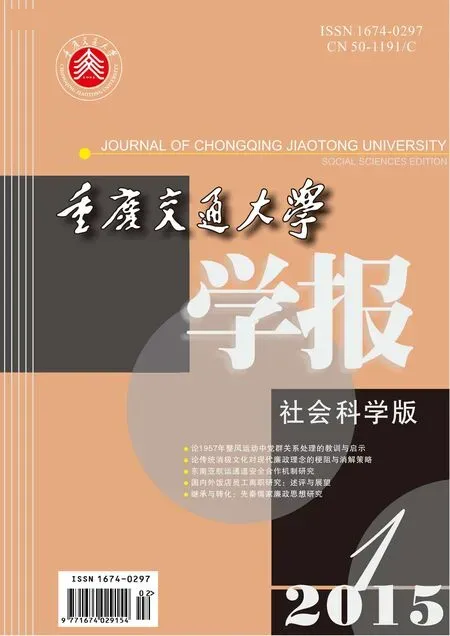从《七色魇》看沈从文40年代的创作心态
高晓瑞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在群星闪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绝对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提到这个自称“乡下人”的文学才子,人们不禁会联想到他笔下那如画如歌的湘西世界和朴素善良的湘西人,这些共同谱就了一曲纯美的牧歌。然而,沈从文经历了他二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后,进入40年代却并未留下多少小说作品,留下的是一些抽象的哲思散文,如《烛虚》集、《七色魇》集,显得晦涩难读。研究者在研究沈从文的时候,常常是把40年代的沈从文一笔带过,仅仅把目光投向他30年代的创作,认为那才是沈从文创作的巅峰,更有甚者还以为越过了30年代的沈从文已经渐渐走向了创作的低谷。我们必须明了的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他创作了多少脍炙人口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能有对自我的认识和思索,即使遭遇很多寂寞、痛苦,仍能清醒地选择自己的人生路途并坚持走下去。40年代的沈从文便是这样在矛盾痛苦焦灼中思索着自己人生道路和文学选择的一位作家,他不仅承受着外界环境的压力,也承受着拷问自我灵魂的纠结。这段时间他的作品难以理解,很大程度上便因为这些是他思考的产物,而非仅仅是故事。钱理群先生曾说:“必须承认:还有相当部分的‘沈从文世界’我们还是陌生的,甚至未知的,远谈不上‘理解’。”[1]所以要谈研究沈从文,他的40年代是不可绕开的一个阶段,而40年代的哲思散文如1949年结集而成的《七色魇》,更是了解沈从文当时精神和心理的一把钥匙,因而我们可以把他那个时期的散文创作与当时的心态结合在一起研究,以期对沈从文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创作因由——无法逃脱的外在痛苦
《七色魇》中大多数的篇目均在云南写成。在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沈从文的到访却并不是因为闲情逸致。1937年的战火致使大量知识分子移居到祖国的大后方,沈从文便是其中一位,而困居在此一呆就是8年。这场战火不仅打断了他一直以来对于民族命运和民族走向的思考,更给他的周围带来了一种政治化的声音,即要求“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来响应全民抗战。这对于一心只想营造纯粹的艺术世界的沈从文来说,必定是一种折磨。“他只想在写作上终其一生,就像泅水者‘扎猛子’一样,而且倔得要命,不顾政治,只钻艺术。”[2]当战争一开始,他便把自己牢牢地隔绝在了政治主流之外,近乎天真地继续营造自己的艺术世界。
凌宇先生曾说,“沈从文的全部历史活动没有展示他参与任何党派和政治集团活动的任何迹象。沈从文正是以这种无党派作家的身份著称于世。”[3]9而沈从文在《七色魇》中的《水云》篇也称,“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4]94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们的选择和行为总是受制于他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这种认识是经过长时期他所处环境熏陶而形成的。并非每个人都能形成对社会人生明确的整体认识,就算形成了也可能有固定和不固定的区别,而沈从文恰恰“是一个对人生有着系统思考的作家,一旦完成对人生的认识,他就固执地抓住不再放手了”[3]102。同样,当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存在的价值在于思考着民族的命运、走向,或者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任务便是专注于文艺创作时,他是无法将自己完全地投入到抗战的创作中的。那种“乡下人”看人论事的独特观念紧紧地印在了他的心上,无论什么样的思想和学说,都不能再系统地占据他的头脑。
对于自我人生观的坚持促成了沈从文无法去顺应政治话语来创作,而那种文人的自负或者说是乡下人带着固执的一种天真,竟促使他向异趣的文学观念发难,如1938年10月他写下《谈朗诵诗》,认为朗诵诗是随意写成的,与真情实感的文艺无关,而散文更适宜于朗诵。这种论调显然与当时需求的民间文艺旨趣不相符。在全民抗战的紧要关头,沈从文主张的抒情性的纯文学和作家远离政治的希求,显然得不到大众的理解和支持。而为了统一各界达成全民抗战的目标,当时的左翼显然是不会放任“与抗战无关”、“反对作家从政”以及沈从文对纯文艺的追求的。对沈从文而言,此时各方的压力扑面而来。
因此从30年代末起,沈从文便面临了一个困境,如果坚持自己的话语权和创作精神,他必定会遭到当时占主流的左翼文人的口诛笔伐;如果俯就当时社会给予创作内容,则又与他一直坚守的文学世界相悖,同时,附和大众话语则意味着失去了自我。双重的压力让他的精神处于紧张矛盾的状态,他深知写附和大众的文章与他的习惯和理想不符,如果强行模仿终会使他的创作生涯走到手足无措的境地,所以他做出了一个选择:要依旧坚持自己的理想写作,表达个人的情绪,贴近自然,倾听来自自然的声音,于广阔的宇宙中思索生命为何。
除了外界环境的压力以外,沈从文还面临了一重困境,就是他习以为常的城乡对立,城乡二重化写作已经不再适合于现实的情况。他意识到,曾经浓墨重彩渲染的素朴的湘西世界已经不复从前的生命活力,如他在《长河》里所表现的湘西平静封闭的生活被打破,保安队长为代表的外来势力与滕长顺发生了厉害的冲突,这些地方原有的“常”被“变”打破,而他一直以来所肯定和赞颂的质朴纯良的人性渐渐被内战所造成的人性、利益上的冲突磨灭。对沈从文而言,这一发现是痛苦的,由现实带来的惟利一面与曾经《边城》中的人性美两相对照,即使是沈从文自己也会发现这个“变”让人痛苦不堪。湘西世界不复从前的美好,而这种变化恰巧是由外来的政治、文化所带来的,沈从文不愿意写政治,却最终发现无法逃离整个社会的大圈,《长河》的写作便可以看作是他向现实尝试的一小步,在文中那种现实与浪漫交替的手法,恰恰表现出他创作时的困苦无奈。
综上所述,40年代的沈从文既无法自愿地融入社会化、政治化的写作,也无法重拾湘西昔日的光辉和温情。理想被现实冲破,而作为作家的沈从文终无法放下自己的那支笔。痛定思痛,超越曾经的“城—乡”视角,“将以前对‘人生形式’的关照提升为对‘生命’存在本身的审视和思考,从他对‘生命’的特殊理解出发,用他那有着特定内涵的‘生命’为价值圭臬,去探照整个中华民族堕落的种种情形及其根源”[5]。这种思考的深度加深了,但这种思考也限制了他创作的范围,因而40年代的沈从文无法再如30年代般创作小说,只有写出大量的散文、随笔来展现这一时期苦闷、紧张、压抑中的思索,这便是我们看到的大量晦涩难懂的哲思散文了。要了解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这些散文是不可绕开的部分。
二、《七色魇》——智者心灵的内部思考
由前所述,我们明白了40年代沈从文无法再创作小说的原因,而他把写作的重心倾向于内心的思考。从创作心态上来看,把对民族现实、社会现实的关注转向对自我的一种关注,对生命何为的一种思考。这种思考映证到文体上,则成了由一种故事的表述到一种思维的表现。《七色魇》中的几个篇章就是他在内心焦虑中思索,然后付诸文字的一种表现。
沈从文这一时期靠沉思后写成的以“魇”命名的文字共6篇:《绿魇》《黑魇》《白魇》《青色魇》《橙魇》《赤魇》。1949年初,作者曾以《七色魇》为书名,把以上6篇加上《水云》,共同组成了一部作品集,只不过未曾付印。顾名思义,《七色魇》以“七色”和“魇”来命名,沈从文曾在《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一文中说:“人的意象,亦复如是。有时平匀敷布于岁月时间上,或由于岁月时间锁作成的暮景上,即成一片虹彩,具有七色,变异倏忽,可以感觉,不易揣摩。生命如泡沤,如露亦如电,惟其如此,转令人于生命一闪光处,发生庄严感应。悲悯之心,油然而生。”[4]279“七色”就如同是“虹”的代言词一样,美丽却不可捉摸,就像是一种超越于现实的理想和追求,象征着沈从文对于生命,或者说成是他理想中所希望达到的境界,而这种美好终究还是与“魇”在做无形的纠葛。“魇”是人的噩梦及噩梦中的呓语,当美好的理想与噩梦相碰撞,对于作者心灵而言必是经历了一番挣扎的。可以这样说,《七色魇》的诞生是作者守住内心各种追求、理想的产物,而这种坚守终与昆明、北京各地的现实所碰撞、打击。“魇”表现了噩梦中的挣扎,七色又展现了渺不可及的梦想,不同的梦想与不同的噩梦相交织,充分体现了40年代的沈从文精神上的紧张和痛苦,以及不断思索造成痛苦的原因和力求排解的心境。
沈从文对于这种内外交加的痛苦情绪,首先选择的是独自融入自然,于自然中冥想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逃避。从童年开始,沈从文就与自然有了解不开的因缘。“他具有亲近大自然的天然爱好,热衷于领略宇宙万物的动静与声色,总是以极其敏感的心灵去体察人生世相。”[6]所以当面临外界的压力时,他会本能地选择逃向自然这个安稳的场所,在自然里沉湎于思考而暂时抛弃痛苦。这正是我们在《七色魇》中经常可以看到的。虽然他身处大后方云南,战争并未离他远去,可是在他的散文集里,我们甚少看到他对于战争惨烈的直接描述,有的顶多是周围人来人往的变迁,连空袭威胁这种危及性命的事在他写来还带了一点艺术的成分,像是在欣赏一场演出,如《白魇》里的暴力描写——“我耳边有发动机在高空搏击空气的声响。这不是一种简单音乐,单纯调子中,实包含有千年来诗人的热狂幻想,与现代技术的准确冷静,再加上战争残忍情感相柔和的复杂矛盾”[4]279。他竟像是“和场面社会都隔绝了”,只身融入自然,淡看周遭一切的变故、死亡、冷暖,在自然中借着那种生命力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在《绿魇》《白魇》《黑魇》里,沈从文曾多次写到那个能让他暂时逃离现实的“自然”,即山上一块四周被草木蒙茸枝叶交错绿荫下的草地,在这里他可以远离战火、人事纷杂而暂时获得一种宁静。这种静带给他的是更深的思索,“只觉得这一片绿色,一组声音,一点无可形容的气味,综合所成为的境界,使我视听诸觉沉浸到这个境界中后,已转成单纯到不可思议”[4]134。在这个地方,他可以与自己对话,与自然中的生物对话,通过这种对人事的排斥,达到对现实的领悟。如他在《绿魇》里和那只细腰大头的黑蚂蚁的对话,他自拟了蚂蚁对自己手爪用处的疑问,顺理成章地引出了自己的想法——沈从文把战争比拟为动物的手爪,因为人的一些“妄想”便想用它来撕碎身边真实或假想的仇敌,毁灭“那个妄想与勤劳的堆积物,以及一部分年青生命”[4]135。点出战争的破坏性,表明了战争是一些所谓“哲人”的妄想所挑起的活动,除了满足他们的欲望外,带给人类的均是灾难、屠杀。而身为一个普通人,沈从文只能用自己的思索来考究战争的真相,他无力改变这种悲剧,所以只能更加沉溺于自然,完全地让自己被“一片绿色”所征服,反映到《七色魇》的创作中,我们则可以发现这段非常时期的创作显示出不少作者自动避世的色彩,文本上趋于自然崇拜,在光与影的变化中呈现作者的思考。
除了沈从文在40年代主动融入自然以躲避压抑外,《七色魇》中另一个特点是他的“对话体”创作手法,这种偏爱独处、喜爱自我对话的风格源于他的孤独感。沈从文一直以来便是个孤独的存在,身为乡下人的那种清醒更让他对周围人事抱有敏感的态度,如他刚刚踏入文坛时曾用笔名休芸芸写下的“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的人海里,更何处去寻同情与爱”[7]。而40年代的沈从文外遭左翼文人的批判,内又无法放弃自己的创作理想,因而压抑异常,甚至连最亲近的妻子也无法理解他的痛苦,如《绿魇》中的“主妇完全不明白我所说的意义,只是莞尔而笑,然而这个笑又像平时是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象征,这时对我却成为一种排斥的力量,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景中”[4]155。沈从文虽是个爱好思索、爱好独处、“用脑子走路”并享受沉思的人[8],但他依旧是个活生生的人,渴望他人的理解和关怀,所以当他在苦闷中无法得到理解时,他会选择用一种方式来自我排解——以自身为本体幻化出两个对象,让他们进行对话,这两个对象代表着沈从文不同的思想,他们的讨论便是沈从文精神内部的斗争,这种“对话体”的文本在《七色魇》中非常常见。如在《水云》篇里面对家庭与“偶然”之间的选择时,他心中的两个声音便开始了对话,一个说着“你这是在逃避一种命定。其实一切都是枉然”,另一个代表理性的声音又说着“我目前的生活很幸福,这就够了”,显示出他在面临情感的外来诱惑时一面想顺应自己的情感,与“偶然”有段美丽的邂逅,并让彼此之间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另一面对于家庭的责任感又让他要满足于现实,守住现实的温暖。两种声音的对话表现出他情感的矛盾纠葛。除去感情,在沈从文独处时思考人生的变迁、人生的追求,甘于清贫或是去追求更多的物质享受时,他依旧用了这种“对话”的方式来变现内心的矛盾。如同巴赫金所讲,“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9]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心理内部的对话恰恰是沈从文作为一个人逐渐完善自己人格、扩充自己智识的一种有效方式,反映到沈从文40年代的创作上,这种复调的手段实际上比他二三十年代单纯的叙述故事更多深度和内涵。
之前谈了沈从文一直以来“贴近自然”的心理和他由孤独转向内省式思考的“对话体”写作,在《七色魇》里还有个特别明显的现象,是沈从文有意地改写了佛经故事,并把它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中。《黑魇》和《青色魇》都讲述了《法苑珠林》中驹那罗王子的故事,王子有一双俊美无双的眼睛,比一切诗歌所赞美的人神眼睛都要美丽动人。可阿育王的妃子真金夫人因为爱上了王子的眼睛,但名分已定,于是由爱生妒、因妒生恨,假借阿育王之手弄瞎了王子的眼睛,最终依靠全城纯洁年轻女子流下的同情与爱的眼泪来清洗王子的眼睛,才让其恢复光明。沈从文在这个故事里借驹那罗王子的口宣扬了“美不常驻,物成有毁”的观点,和他在《水云》里提到的“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一样,与佛经里的“法眼无常相”遥相呼应。沈从文在《青色魇》里具体地解释了这种含义:“凡美好的都不容易长远存在,具体的且比抽象的还更脆弱。美丽的笑容和动人的歌声,反不如星光虹影持久,这两者又不如某种观念信仰持久。英雄的武功和美人的明艳,欲长远存在,必与诗和宗教情感结合,方有希望。”[4]183即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无法保持常态,即使拥有也会失去,然而只要承认这种生命中必有的残缺,对生命抱着虔诚的信仰,才有可能得救。因此在沈从文的故事里,王子能在盲眼时靠着对父母的思念回到国都,是种信仰,驹那罗王子之所以最后能重见光明,恰恰是因为那些虔诚女子的信仰。沈从文在引入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意做了改动,原始故事中王子眼盲是因为前世挑了500只鹿的眼睛,因而今世来补偿,显示了佛教的因果报应,今世因为修塔、造佛像积德,才使得众人为之流泪,因而复明,依然是因果报应说。而沈从文有意省略了这些部分,把王子当成善良无辜的受难者,最值得赞赏的是他在受难后还能原谅那个带给他痛苦的人。王子能做到这一切的原因,在沈从文看来便是那值得珍惜和赞颂的赤子之心。在《青色魇》的末尾,沈从文点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新的信仰,去实证同样明确而单纯的新的共同愿望。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4]190。他不仅是在赞扬故事中的品格,更希望这种童心能被运用到现实中,因为现实社会里多的常常是怨毒、仇恨以及由此而生的憎恨和仇杀。所以可以说被迫来到云南的沈从文虽处于内外压迫下,但他没有一刻停止过对社会、对生命的思考。
当我们重观《七色魇》的时候,不应该把它当作晦涩难懂的“哲思散文”或“抽象散文”而忽略其现实意义。在这些篇章中沈从文寄予了自己一直坚守的创作理念,也成功地实现了关注内容的向内转,更思索出现实的纷争一部分是由于人们缺乏信仰、缺乏童心、缺乏善意造成的,其实此时的沈从文比起文学家更可以被称作一位哲学家。他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4]128。
[1]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48.
[2]贺兴安.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M].成都:成都人民出版社,1992:2.
[3]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5]王友光.穿越城市文明的三次精神还乡——沈从文小说创作心理阐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30-47.
[6]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33.
[7]休芸芸.一封未曾付邮的信[N].晨报:副刊,1924-12-22.
[8]章长城.沈从文浪漫主义思想论[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4(2):69-72.
[9](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