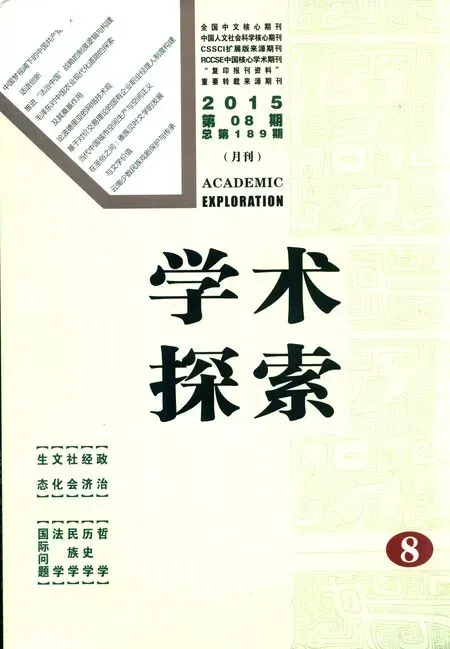《史记》“入山作炭”辨析
柴国生
(中原工学院 哲学与历史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7)
《史记》“入山作炭”辨析
柴国生
(中原工学院 哲学与历史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7)
学界对《史记·外戚世家》“入山作炭”的记载有“入山采煤”和“入山烧炭”两种解释,其考释论证都有其合理性,但相关论据多不确指,至目前仍未形成普遍认可的结论。本文从对两种观点的考释论证的分析出发,结合史料记载和汉代生产实际,对“入山作炭”进行考释分析,认为《史记》“入山作炭”即为“入山采煤”,其“卧岸下”“岸崩”的记载也是正确的。
《史记》;入山作炭;煤炭;木炭
《史记·外戚世家》载:“(窦皇后)弟曰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寒)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1](P1973)这是关于汉代能源生产不多的史料中极具价值的记载,对了解汉代能源生产实际和社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作用。对此事件,《史记》之后,《汉书》《论衡》也有记载。
《汉书·外戚传》载:“窦后兄长君。弟广国,字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脱不死。”[2](P3944)
《论衡》卷二《吉验》载:“窦太后弟名曰广国,年四五岁,家贫,为人所掠卖,其家不知其所在。传卖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卧炭下百余人,炭崩尽压死,广国独得脱。”[3](P94)卷十《刺孟》载:“窦广国与百人俱卧积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广国独济,命当封侯也……命不压,虽岩崩,有广国之命者,犹将脱免。”[3](P468)
比较上述记载,不同之处即在“炭”与“岸”的区别。也正是对“炭”与“岸”的不同考释与理解,学界对“入山作炭”产生了两种不同解释,一是入山烧炭,一是入山采煤。就其分析论证而言,双方都有其合理性,但论据多不能确指,因而,至目前仍未得出学界普遍认可的结论。鉴于此条史料的重要价值,下文拟从对两种观点及其考释论证的分析入手,结合考古发现、传统生产实际和汉代社会发展实际对相关记载进行考释分析,以期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对两种不同观点及其考释论证的分析
(一)关于“入山采煤说”
“入山采煤说”始于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石炭》中自注曰:“《史记·外戚世家》:‘窦少君为其主入山作炭。’《后汉书·党锢传》:‘夏馥入林虑山中,亲突烟炭。’皆此物(石炭)也。”[4](P1838)顾氏对此说并未进行论证。
20世纪50年代,在顾氏的基础上,周蓝田和赵承泽等先后对“入山作炭”进行了考释。
周蓝田1956年在《中国古代人民使用煤炭历史的研究》中指出:“据顾炎武《日知录》的考证,夏馥‘作炭’与窦少君‘作炭’,都是作‘石炭’。汉唐称工场为‘作’。可见所谓‘作炭’,即是开‘煤矿’,到明代仍沿用这个称呼……‘岸’是指当时石底采矿,已进入很大深度,以致一次压死即有百十余人,可证当时煤矿已有相当规模了。”同时指出:“自春秋战国以至晋、唐、宋,一千多年间都有出煤炭的记载,直至今日,宜洛煤矿仍是河南省较大的煤矿。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事实:就是‘宜阳’不仅存在颇大的煤田,而且历代都在开采,因此历史上才加以记载。据此,西汉初窦少君在宜阳作炭的故事应当是可信的史实。”[5]
按:“作”如果做“工场”解,则指手工业工场,那么,采煤的煤矿可称为“作”,烧炭的炭场亦可称为“作”。而周先生关于宜阳历代采煤的考释,以及由此认为“西汉初窦少君在宜阳作炭的故事应当是可信的史实”的推断,是合理的。
赵承泽1957年在《关于西汉用煤的问题》中认为:“《史记》的这条文字虽不明显,然这条记载则确是西汉初年用煤的真正史料。”并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史记》之岸字皆是炭字之讹文”;二是“炭下”和“炭崩”是指“采煤工人住在煤洞子里,因为突然遭遇崩压事故,百余人遂同时遭难”[6]。
按:赵先生认为造成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采煤个人住在煤洞子里”的结论是正确的,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就赵先生的考释过程,不确指之处较多。
首先,立论不能确指。赵氏认为“《史记》之岸字皆是炭字之讹文”,理由是“王充生于司马迁之后仅仅百年,故所见之《史记》依然正确”。如果以此逻辑,班固(32年~92年)与王充(27年~97年)为同时代人,那么,班固所见《史记》当也不误。
其次,对于《史记》与《论衡》“炭”与“岸”的区别,赵先生认为“应是后人读《史记》不明‘炭下’和‘炭崩’的意义,以炭岸形同声近妄改”。《汉书》的记载“亦妄改《史记》者同改”。三书在两千年的流传中,出现讹文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仅以王充“所见之《史记》依然正确”为由,就认为《史记》《汉书》被“妄改”,显然过于牵强。
再次,赵先生得出结论的另一重要依据为“岸下必是山谷或河谷,山谷河谷之间难避风寒,窦少君等百余人绝不能在冷天的晚间露宿在这种地方”。这一点恐怕不尽然。对于窦广国等没有人身自由的奴仆而言,“入山作炭”夜间休息的地方恐怕要服从矿井的所在。如果矿井在“岸下”的山谷或河谷,他们也只能就近选择避风的地方休息。
至20世纪80年代,祁守华、吴晓煜等人在《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中,对赵承泽先生的考释进行了补充,列出了四条理由。[7](P21~24)[16](P251~252)
第一,认为赵承泽关于《史记》中“岸为炭之讹”的考证“是有根据的”。据此认为,“‘卧炭下’即是煤窑工人夜晚(暮)为避寒,而卧于依山开挖的煤洞内休息。而炭崩,则是煤洞坍塌事故,致使一百多人同时被压杀。”
第二,窦广国等人卖身为奴仆,没有人身自由,进山劳动,“暮寒”的情况下只有睡在煤洞中才好避风御寒。并认为:“炭是木炭的看法也不正确。因为木炭不会有崩塌的现象发生,更不会崩塌规模大到‘尽压杀百余人’。只有煤洞崩塌才可能造成一次使百余人同期遇难的事故。”
第三,古代煤窑工人夜晚在煤洞中过夜的现象十分普遍。
第四,河南宜阳地区煤炭蕴藏丰富,煤层出露较为明显,不少地方埋藏较浅,为“入山作炭”提供了有煤可采的条件。
按:与赵承泽先生的考释比较,吴晓煜等人的前两条理由基本是赵承泽先生理由的翻述。如果宜阳地区煤炭蕴藏丰富,为“入山采煤”提供了资源条件,那么,宜阳多山、陵、川的地貌特征,也决定了其在汉代拥有丰富的林木资源,同样具备“入山烧炭”的资源条件。
(二)关于“入山烧炭说”
具有代表性的为容志毅和李欣的考释论证。
容志毅在《中国古代木炭史说略》中认为,“近代学界多据该条文献(《史记》的记载)以证中国用煤之记载始自西汉,误也。”“‘积炭’堆放过高引致崩塌,故不可将‘炭崩’之炭目为石炭。”其理由有三,一是凡挖煤者,所得之煤大都就地堆放,重力使煤堆通常呈上尖下圆的锥形。锥体堆煤不会崩塌致“百人皆死”。而木炭不同,为避免过多吸湿并易于目测炭堆体积,通常将烧制好的木炭码放堆高成正方体或长方体形。因木材各方向之热收缩率不同,木炭堆放过高时,会因其中某些木炭断裂而致整个炭堆倒塌。人若正好处在倒塌的木炭堆下,则不幸便会发生。二是古代作炭,多在深秋为之。当炭烧成并码放堆好时,已是天寒用炭之际,“卧积炭下”,除炭堆吸湿避风外,尚可就近燃炭取暖。三是“作”是由某种过程将一物做成另物。以木做成炭乃正合此意,而挖煤则不可称为“作煤”。由此三条理由,得出“《史记》所云‘作炭’,只能是烧木炭,其余它解均误”。[8]
按:容先生从力学原理出发,认为“力学使然”使煤堆呈锥体堆而不易崩塌,这是科学的。其提出的炭烧好后“为免过多吸湿并易于目测炭堆体积,通常要码放堆高成正方体或长方体形”的观点,也符合生产实际。但是,炭工是否会将木炭堆高至能够压死人的高度,这是需要商榷的。而将“作炭”理解为“由某种过程将一物做成另物”,这与周蓝田关于“作”的解释完全不同。“作”在古代有多种解释。《说文解字》曰:“作,起也。从人从乍。”[9](P165)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作,起也。秦风无衣传曰。作,起也。释言,谷梁传曰。作,为也。鲁颂駉传曰。作,始也。周颂天作传曰。作,生也。其义别而略同。别者所因之文不同。同者其字义一也。有一句中同字而别之者。”[10]因此,“作炭”到底做何解释,是值得商榷的。
李欣在《秦汉社会的木炭生产和消费》中认为,对于此事的记载,《史记》《汉书》文意一致,不可能有“岸”为“炭”之讹,而且木炭坍塌压死人史有其例,如近代张思德之遭遇。汉代在宜阳开洞挖煤,迄今为止没有文献、考古资料的任何证据。秦汉文献也看不到“炭”指代煤的任何记录,所以这里的作炭应是烧制木炭而非挖煤。[11]
按:《史记》《汉书》《论衡》相关记载中“岸”与“炭”的不同,必有误者。但是,在没有新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对史料记载进行考释分析恐难确定相关记载的正误。对于李欣所指“史有其例”的张思德事件,也非木炭坍塌所致。张思德事件在电影《张思德》中有较完整的再现。1944年9月,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冒雨带领战友赶挖炭窑,炭窑因雨突然崩塌被埋牺牲。另一方面,在历史研究中,以当前没有或未发现有史料记载就断言史上没有,也不符合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律。许多被考古发现改变的既有结论的存在,即是明证。而且,宜阳煤炭开采确有悠久历史。对此,周蓝田先生在《中国古代人民使用煤炭历史》一文中进行了较详细地考释,此不赘述。
除上述对两种观点的相关考释外,其他学人多是直接肯定一观点,或进行简单的考释,但基本上未超出上述的理由,不再一一列出。对上述不同的论证稍加分析,不难看出存在几对明显的不同:
一是对“炭”和“岸”的理解。一方认为“岸”非“炭”之误,另一方则认为“岸”为“炭”之误。
二是对“炭崩”的解释。一方认为是煤洞坍塌。相反,另一方则认为是木炭堆坍塌。
三是对“作”的解释。一方认为“作”汉唐时指工场,“作炭”即开“煤矿”。而另一方则认为,“作”是将一物做成另物,以木做成炭正合此意。
综上,尽管上述两方的考释分析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因一些重要论据不确指造成其论证与结论并非无懈可击,特别是对相关记载完全相反的理解与解释,致使目前学界仍未能形成普遍认可的观点。
二、《史记》“入山作炭”为“入山采煤”考
比较《史记》《汉书》《论衡》的记载,没有争议的是“入山”和“百人皆死”的基本事实。
对于“入山”这一事件发生的因由和地点,因丰富的煤炭蕴藏和宜阳“三山六陵一分川”的地貌,决定了汉代宜阳“入山”采煤、烧炭的客观条件都是存在的。因此,在没有新的史料或考古发现来佐证的情况下,仅从史料记载对“岸”与“炭”进行考释分析,显然无法得出让学界普遍认可的结论。因此,要弄清楚是入山烧炭还是采煤的关键,应从史料记载出发,结合当时烧炭与采煤的生产实际来分析造成“尽压杀卧者”这个结果的可能性。这应是弄清“入山”烧炭还是采煤唯一可行的方法。
如果是“入山烧炭”,就生产实际而言,窑址的选择,不仅需要周边有丰富的薪柴资源、充足的水源、足够的石块和黄土(建造炭窑用),而且还要有一定面积较为平坦的场地来堆放木柴和木炭。通常情况下,窑址选好后,炭工往往先“治舍盖屋”搭建临时的棚屋,解决好吃住等生活问题,然后才会筑造炭窑。因为,炭窑的筑造需要一定技术和较长的时间,非常不易。炭窑建好后,如果不是周边的山林采伐殆尽,往往常年使用,不会废弃。对此,西汉王褒《僮约》记载:“持斧入山……焚薪作炭,垒石薄岸。治舍盖屋,书削代牍。日暮欲归,当送干薪二三束。”[12]王褒要求奴仆进山烧炭,要修岸堤、治舍盖屋。治舍盖屋自然是为了居住,而修岸堤则应是蓄水供日常生活和烧炭之用,这也是入山烧炭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传统烧炭,一窑通常需4~5人,一周左右的烧制时间,出炭在1000斤左右。[13](P14~25)为提高产量,通常采用多个炭窑轮流烧制的方式。那么,百余人的炭场,应筑造30个以上的炭窑,这就需要有足够大的平坦场地来布置炭窑、存放薪柴和木炭。炭工房舍的建造位置自然应靠近炭窑,靠近水源(便于生活),且在相对较高的地方(避免被雨雪山洪倒灌或冲毁)。因此,不应出现百余人“暮卧岸下”的情况。
如果是“入山采煤”,则刚好与烧炭相反,工人往往在矿井附近开挖窑洞居住,或者睡在煤洞中。在巩义铁生沟位于北庄村的东北部和西北部的汉代采矿场遗迹中,除了有圆形和方形的矿井外,还发现有当时采矿者寄居的窑洞,窑洞开挖在矿井附近的耐火土层上,洞顶呈弧形,周壁垂直,有镢痕进深(残)2.1米,顶高2.2米,宽1.4米,距现在地表深1.5米,洞内还发现有铁锤等采矿工具。[14](P5)这样如果出现“岸崩”的地质灾害,一次压死百余人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就汉代的采煤技术而言,不仅需要较多的人力,而且采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一处煤井采掘一段时间后,往往因排水、通风等问题导致无法继续开采,需要另换一处,自然会留下较多的煤洞。这些废弃的煤洞很容易被采煤者利用作为临时的避风休息场所,而古代煤炭工人夜睡煤洞确是普遍的现象。而这些煤洞出现坍塌“压杀”采煤者的可能性则更大。因此,《史记》的“入山作炭”,如果是采煤,出现“岸崩”,即煤洞坍塌或依山而挖的“窑洞”坍塌,“尽压杀”“百余人”的情况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造成积炭崩塌“尽压杀卧者”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也是弄清是“入山采煤”还是“入山烧炭”的关键。从汉代有限的生产能力来看,百余人采煤或烧炭,“积炭”崩塌致“百人皆死”的可能性基本是不存在的。就烧炭而言,炭条的完整程度是评价其质量的重要指标。而木炭沿纤维横向之抗压强度,仅及纵向抗压强度的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15](P703)木炭堆放过高时,会造成木炭承压而断裂,影响到木炭的质量。因此,炭堆不会堆得太高,自然不可能出现木炭堆崩塌压杀百余人的情况。即便是堆得较高,因为木炭质地疏松、硬度较低,倒塌之后压在人身上也容易脱险,更何况是百余人。因此,木炭倒塌一次造成“尽压杀”“百余人”的情况,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如果是采煤,一方面,煤的堆放如容志毅所言,呈自然的锥体不易坍塌;另一方面,当时有限的生产能力,也不至形成足以压死百余人的大煤堆。按当时的生产能力,百余人生产一天的产量应在10000~20000斤(5~10吨)的煤炭,[16](P252)一个月的产量为150~300吨。如果按300吨计算,煤的散密度(又称堆密度)为0.5~0.75g/cm3,体积最大为400~600m3,按照堆高1米计算,则煤堆的面积为400~600m2,相当于一个至一个半篮球场大。这样的一堆煤即使崩塌也不可能压死“百余人”。这样,就可以排除“积炭”崩塌压死“百余人”的可能。
综上,造成“百人皆死”的结果,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睡在煤洞,二是依山挖洞居住,发生“岸崩”而“压杀百人”。如此,《史记》“入山作炭”的记载是采煤无疑,其“卧岸下”“岸崩”的记载当也不误。
三、“入山采煤说”成立的社会基础
煤炭的规模化采用,必然有与之相应的技术条件和社会需求。汉代煤炭燃用、开采技术的进步,以及在一些煤炭产地周边社会生产、生活等领域较为广泛的利用,为煤炭的规模化开采奠定了应有的社会基础。
就煤炭燃用技术而言,汉代已经掌握了原煤直接燃用和型煤加工技术,并实现了原煤和型煤的规模利用。1988年在汉魏洛阳古城东汉砖瓦窑遗址的发掘中,发现“火膛内存有厚达0.6米的煤渣堆积,从残存煤渣来看,这些燃煤事先并未加工成煤饼”“似直接使用散煤,这种做法显然与大规模使用煤作燃料是相适应的。”[17]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巩义(原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中,发现有大量的原煤块、煤饼,“原煤和煤饼在各个炼炉附近都有发现”,出土的许多煤饼的形状不规则,“煤块一般长度为6~13厘米之间”“多数经过火烧,有些未烧透。有的外边灼成白色。”[14](P18~19)相较而言,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出土的煤饼已是按规格批量制作的模制型煤。这些煤饼集中于窑5的火池内,内掺有黏土,呈圆柱形,直径18~19厘米,厚7~8厘米,有的上面凸鼓;火池内用砖架设六条风道,煤饼架于风道之上,近门处通风较好的已全部燃烧成渣,而靠里边的下部仅燃烧了表层,煤饼内掺有黏土。[18]批量模制煤饼的制作和使用,反映出汉代型煤加工技术和煤炭燃用技术的成熟。至此,除烧焦技术外,我国先民已基本掌握了传统煤炭的主要燃用技术。
煤炭的社会需求,与燃用技术的进步是互为促进的。汉代煤炭日臻成熟的燃用技术,促进了煤炭在社会生活、手工业生产等领域的利用。日常生活方面,1938年在辽宁抚顺发现的汉代玄菟郡居住遗址,煤炭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取暖、做饭的燃料。[7](P21)1955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的汉代生活遗址中,发现有煤和煤渣,表明“至少在东汉末年我国人民已经知道用煤作为燃料了”。[19]
手工业方面,煤炭在高耗能的冶铸、烧窑等领域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利用。冶铸方面,在巩义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从发现的大量煤饼、原煤块、煤渣的出土位置推测,“煤饼主要用于圆形和长方形的排炉和反射炉”“原煤块主要用于海绵铁炉”“无比雄辩地证明了我国在西汉时期以煤冶铁的事实”。[14](P18~19)此外,1979年洛阳市博物馆在黄河北岸洛阳市吉利工区的一座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发掘中,发现有直口卷缘、直腹、圜底的炼铁坩埚,并附着熔炼后残剩的铁块、煤块和炼渣、煤渣,“说明当时是直接用煤作为冶铸铁的加热燃料”“为西汉时期冶铸铁直接以煤为加热燃料提供了重要的实证”。[20]河南之外,山东章丘地区汉代也已燃煤冶铁。1954年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东平陵故城遗址的城址中心,发现一处春秋以来到秦汉间冶铁作坊遗址,内有炉址、煤渣、铁砂、铁块以及铁器残片等物,[21]反映出当时可能已用煤炭冶铁。
烧窑方面,煤炭利用更为广泛。古荥镇冶铁遗址中发现的煤饼无疑是当时用来烧烘范、烧制砖瓦和鼓风管等陶器的燃料。[18]此外,在巩义铁生沟冶铁遗址的许多陶窑中,发现有“煤灰”和“原煤块”,说明这处冶铁遗址还“兼营陶业”,而且“使用了煤作燃料”。[22](P27~28)1985年在洛阳市老城东北2公里处发掘的两座东汉后期的砖瓦窑遗址,堆积物中发现有“煤渣炭灰”,窑炉底部砌有砖箅,用矩形条砖交错排列,每排砖与砖之间互不衔接,“缝隙处留有煤燃烧后的煤渣和炭屑”,说明这里当年烧窑所用的燃料是原煤。[22](P30)1988年在汉魏洛阳古城东汉砖瓦窑遗址发掘中,已发掘的3座东汉窑址“结构相近,且无一不是以煤作为燃料。在火膛中皆发现有大量的煤渣堆积,而且在窑址附近的同时期灰坑堆积中也都发现有许多煤渣。这表明此窑址群有可能都是以煤为燃料的……而且用煤量甚大”。[17]此外,河南偃师翟镇乡东汉时期窑址,[23]汉河南县(治所在今洛阳市西郊)瀍河东岸的汉代陶窑遗址等,[22](P27~28)都已用煤作为烧窑的燃料,反映出汉代洛阳及周边地区已较为普遍地使用煤炭作为烧窑燃料。
从这些遗址的分布及燃煤情况来看,基本集中在汉代以洛阳为治所的河南郡(尹)及周边地区,遗址的密集程度和煤炭利用的普遍程度为全国所仅见,而且用煤冶铁、烧窑等手工业生产绝非短期行为,消耗量自然也不会小,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利用,反映出汉代一些地区对高品质的煤炭已经有了较大的社会需求。
相应的采掘技术,是满足汉代煤炭较大社会需求的重要前提。能够反映汉代煤炭的采掘技术,目前所见仅东汉末年《魏都赋》“墨井盐池,玄滋素液”的记载,对此,张载注曰:“邺西、高陵西、伯阳城西有石墨井,井深八丈。”[24](P267~268)据考证,曹操藏于冰井台的“数十万斤”煤炭,即产自今河南河北相邻处安阳、磁县、峰峰一带的产煤区。[16](P257)这与张载的记述基本是一致的,说明汉代已经掌握了煤炭的井下开采技术。而曹操“藏石墨数十万斤”[25]的规模,反映出的可能的开采能力,与《史记》百余人“入山作炭”反映出的可能的开采规模基本相符。另一方面,古代煤炭开采的掘井、支护、通风、排水、提升、照明等关键技术在先秦时期已有较好发展。1974年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掘,清晰地展示出春秋战国时期的采矿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有了较合理的巷道布置,较完善的提升系统、排水系统、通风系统,以及相当高的支护技术。[16](P245)根据传统时代技术发展的连锁性等相关规律,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这些铜矿开采技术,被应用于煤矿等技术相近的采矿活动中是完全可能的。
汉代煤炭日臻成熟的燃用技术,一定深度的井下采掘技术,较大的社会需求,为百余人规模采煤活动的存在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社会基础。
结 语
《史记》《汉书》《论衡》“入山作炭”相关记载的不同,使学界对“入山作炭”产生了“入山采煤”与“入山烧炭”两种不同的理解。然而,从“尽压杀”“百余人”的事件结果出发,结合当时的生产实际,对入山采煤与入山烧炭所造成结果的可能性进行分析,不难看出,窦广国等人夜睡煤洞或依山挖洞而居是因“岸崩”造成“尽压杀”“百余人”的、仅有的两种可能,这也符合当时入山采煤的生产实际。因此,《史记》等“入山作炭”的记载为“入山采煤”无疑,“卧岸下”与“岸崩”的记载也当不误。从考古发现反映出的汉代洛阳及周边地区的规模化燃煤情况,以及汉代煤炭开采燃用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综合来看,宜阳存在“百余人”的采煤队伍是与汉代社会发展和生产实际相符的。
[1]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黄晖撰.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全校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周蓝田.中国古代人民使用煤炭历史的研究[J].北京矿业学院学报,1956,(2).
[6]赵承泽.关于西汉用煤的问题[N].光明日报,1957.
[7]《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编写组.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
[8]容志毅.中国古代木炭史说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9](汉)许慎.说文解字[M].(宋)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影印,2004.
[10](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李欣.秦汉社会的木炭生产和消费[J].史学集刊,2012,(5).
[12](清)严可均辑.全汉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臧连明,等,编.《土窑烧炭》[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59.
[1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15]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16]李进尧,吴晓煜,等.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发现的东汉烧煤瓦窑遗址[J].考古,1997,(2).
[18]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78,(2).
[19]黄展岳.一九五五年春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6,(4).
[2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发现西汉冶铁工匠墓葬[J].考古与文物,1982,(3).
[21]杨惠卿,等.山东师范学院同学赴东平陵城进行考古实习[J].考古通讯,1955,(4).
[22]祁守华.中国古代煤炭开采利用轶闻趣事[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6.
[23]王春斌.战国及秦汉之际陶窑初步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1,(5).
[24]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5](晋)陆云.陆士龙集[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Making Charcoal in Mountains”in Records of History:Making Charcoal or Mining Coal?
CHAI Guo-sheng
(Philosophy and History Research Center,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450007,Henan,China)
In the academic circle,there are two different explanations about“making charcoal in mountains”in The Biography of Emperors'Female-side Relatives of Records of History.One is mining coal in mountains,and the other is making charcoal in mountains.Both of the textual researches and argumentations are reasonable,but the related grounds of argument are indefinite,and the conclusion has not been agreed.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accounts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in Han Dynasty,the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ysis of the two views,and conclude that the“making charcoal in mountains”in Records of History is mining coal in mountains.And records on the landslide are correct too.
Records of History;making charcoal in mountains;coal;charcoal
K05
:A
:1006-723X(2015)08-0134-06
〔责任编辑:李 官〕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0AZS005)
柴国生,男,中原工学院哲学与历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能源史、科技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