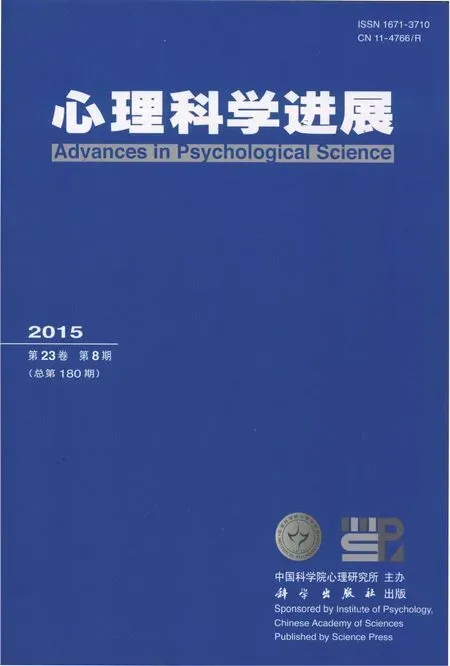情绪性时间知觉:具身化视角*
贾丽娜 王丽丽 臧学莲 冯文锋 张志杰
(1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育系,无锡 214122)(2淮阴师范学院心理学系,淮安 223300)(3慕尼黑大学心理学系,慕尼黑 80802)(4苏州大学心理学系,苏州 215123)(5河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石家庄 050091)
1 引言
个体的主观时间往往受内外因素(强度、情绪和运动等)的影响呈现扭曲(Eagleman,2008)。尽管各种因素导致的时间扭曲涉及不同的加工过程,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调整计时以适应所生存的环境(Droit-Volet &Gil,2009)。这一点在情绪性时间知觉方面尤为典型:个体在具有生命威胁的情景中(如车祸)往往感觉时间变慢。主观时间的调整有利于个体快速做出决定和行为反应,如反击和逃离(Droit-Volet &Gil,2009)。
近20年,情绪对时间知觉的调节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Droit-Volet &Gil,2009;Droit-Volet &Meck,2007)。对于决定情绪性时间调整的因素,研究者们则观点不一。早期研究认为情绪的基本维度——唤醒度(低-高)和愉悦度(负性-正性)——是影响时间判断的主要因素(Angrilli,Cherubini,Pavese,&Manfredini,1997)。例如,有研究发现唤醒度和愉悦度的交互作用产生了不同的主观时距的扭曲:对高唤醒度图片刺激,负性图片的时距被高估,而正性图片的时长被低估;相比而言,在低唤醒度图片的条件下,对负性图片的时距判断呈现低估,正性图片则呈现高估(Angrilli et al.,1997)。研究者认为具有相同唤醒度和愉悦度的情绪刺激会产生类似的时间扭曲,如所有负性高唤醒度刺激的时距估计都将呈现主观延长。然而随后一些研究却发现与此结论相矛盾的结果,并揭示情绪性刺激(如危险性信号)引起的特定行动准备和反应(如逃跑)是决定主观时间的关键因素,而不是刺激的情绪维度(Gil &Droit-Volet,2011;Shi,Jia,&Müller,2012),这表明特定躯体状态和行动体验即具身化(embodiment)在情绪性时间知觉中具有重要作用(Effron,Niedenthal,Gil,&Droit-Volet,2006;Nather,Bueno,Bigand,&Droit-Volet,2011;Wittmann,van Wassenhove,Craig,&Paulus,2010)。实际上,以上研究的分歧反映了不同认知框架下情绪概念观点(维度情绪观和具身情绪观)之间的争论。
传统认知观点认为,认知“始于感觉刺激的输入、终止于运动反应的输出、封闭于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内在过程”(叶浩生,2011),即大脑与身体和环境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在此认知框架下,维度情绪观(dimensional emotion view)认为情绪由所评测的唤醒度和愉悦度构成,这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决定情绪的知觉和行为功能(Russell,1980;Smith &Ellsworth,1985)。神经成像研究显示,对不同情绪(高兴、悲伤、生气、害怕和恶心)的加工既激活了有关情绪维度的神经区域,也激活了与其内容相关的特定脑区(Vytal &Hamann,2010)。这一研究表明对情绪的理解不能简单地基于情绪维度,也应考虑其特定内容。
相对于传统认知观点,具身认知观强调身体在感觉-运动过程中的枢纽作用,认为认知包括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身体物理状态以及大脑特定通道系统中的知觉、行动和自我内省的体验(Niedenthal,Barsalou,Winkielman,Krauth-Gruber,&Ric,2005),这表明认知、身体和环境是一体的(Clark,1999;Engel,Maye,Kurthen,&Konig,2013;叶浩生,2010,2011,2014)。在具身化认知的理论框架下,具身化情绪的观点(embodied emotion view)强调对情绪的感受包括知觉、身体状态及其与周围环境交互作用产生的反应(Niedenthal,2007)。与该观点一致,研究发现感知情绪往往包括行为模拟和(潜在)行为应对等具身化表现。行为模拟的核心是个体对观察对象有关动作特征的行为体验,如个体注视别人的情绪性面部表情时不由自主地进行模仿(Levenson,Ekman,&Friesen,1990);行为应对主要指的是,个体根据以往经验和知识对具有特定运动含义的对象产生的(潜在)行为反应,直接体现人类进化和适应环境的结果。例如,在Alexopoulos和Ric(2007)的研究中,快速呈现的悲伤词或高兴词消失后,要求被试做接近动作(屈折胳膊)或逃避动作(伸展胳膊)。结果显示高兴词之后的接近动作快于逃避动作,悲伤词则反之。研究者认为对情绪词的感知自动激活了与其对应的行为倾向:高兴词激活了接近运动的准备,而悲伤词激活了对逃避行为的准备。因此,当实验中要求的动作与情绪词引起的行为倾向一致时,被试的反应时较短。
在具身认知观和具身化情绪观及有关研究证据的基础上,近期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情绪、具身化和时间知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具身化涉及身体与外部刺激交互作用产生行为反应的过程,这一体验可以引起或者促进对情绪刺激的感受(Adelmann &Zajonc,1989)。例如,观察者对别人的行为进行模拟时产生了与自己行动时类似的唤醒度(Garbarini et al.,2014)。根据时钟计时模型(Wearden,1991),唤醒度调节计时机制中时间信息的累积进而影响主观时距。有研究认为具身化通过影响唤醒度调节时间知觉(Effron et al.,2006)。另一方面,具身化对时间知觉的作用,在需要行为反应的情绪性情境(如生气、害怕和危险等)中得到突出体现。例如,上文提到的威胁性场景中,观察者为了生存需要快速逃离,行为反应的紧急性使主观时间变长。这一典型例子说明了情绪、行动和时间知觉之间的连接关系。
总之,情绪的具身化和时间知觉的有关研究不仅为理解情绪概念的构造提供了参考,也可以为探索时间信息加工的规律提供借鉴。本文归纳和分析了情绪的具身化对时间知觉调节的研究,阐述了相关的理论解释,并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2 情绪的具身化和时间知觉:研究证据
2.1 具身化因素的实验操纵
在刺激材料方面,研究者采用标准化情绪刺激(如从国际情绪性图片系统、面部行动编码系统和国际情绪性数字化声音系统选取)、身体姿势图片、电影片段和运动刺激等探讨情绪性时间知觉(Droit-Volet &Gil,2009;Nather et al.,2011;Wittmann et al.,2010)。其中对具身化的实验操纵主要分为两类。第一,操纵刺激的具身特征,包括刺激是否具有行动含义、刺激的运动量多少、刺激运动速度的快慢和对刺激的运动熟悉与否等。例如,在Gil和Droit-Volet(2011)的研究中,要求被试对情绪性面孔表情的图片进行时距估计。其中,恶心和生气的面孔都会引起高唤醒度和不愉快的体验,但不同的是,恶心的反应主要拒绝品尝一些不利于健康的东西,不具有采取行动的含义(Rozin &Fallon,1987);而生气则将引起反击或离开的行为准备。情绪维度观认为相同唤醒度和愉悦度的刺激将产生一致的时距判断,由此推测被试对生气和恶心图片的时距估计应该没有差异。然而,根据具身化情绪观点,情绪刺激引起的行为反应会影响时间知觉。据此,对生气图片的时距估计相对中性图片将呈现扭曲,而恶心图片的时距判断不会受到影响。该实验结果与具身化情绪观一致,揭示了具身化对情绪性时间知觉的重要作用。第二,操纵观察者的身体物理状态(自由行动和限制行动)、身体意识状态(对身体的关注程度)以及身体与外部环境的交互性。例如,在呈现情绪性面孔表情刺激或运动背景中,对实验组被试身体的(潜在)行动反应部位给予抑制,如要求被试手部或嘴部持有无关物体以阻碍其行动;控制组中被试身体的相应部位可以自由行动。如果实验组对刺激的时距估计不同于控制组,则说明行动(具身化)与时间判断的密切关系。实验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Effron et al.,2006;Jia,2013)。
有关研究主要揭示了行为模拟和(潜在)行为应对这两种具身化体现在情绪性时间知觉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模拟的作用受身体的物理状态、模拟目标的熟悉性、目标的运动量及其速度特性等因素的影响并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潜在)行为应对往往通过情绪刺激的运动含义、情绪的愉悦度、身体与环境的相关性、身体的物理状态和意识状态等因素的操纵反映其在时间判断中的调节作用。这些因素通过激活相应的动机系统影响(潜在)行为应对:趋向性系统和防御性系统(Lang,Bradley,&Cuthbert,1997)。防御性系统伴随退缩、逃跑和攻击等行为反应;趋向性系统会导致摄食、交配和养育等行为反应(Bradley,Codispoti,Cuthbert,&Lang,2001)。与防御性系统有关的行为反应将产生对时距判断的高估,而趋向性动机的行为反应往往导致时距低估。此外,视觉引导的避免碰撞(visual-guided collision avoidance)是一种直接反映(潜在)行为应对的范式。研究发现婴儿对接近运动(接近观察者的运动)产生逃避行为(Ball &Tronick,1971)。神经成像的动物研究表明,与物体的离开运动(离开观察者的运动)相比,个体的特定神经元对物体的接近运动产生偏好反应,并通过其它神经元传送到运动系统,引起逃跑行为(Fotowat &Gabbiani,2011)。实验室中的接近运动和离开运动是在电脑屏幕中间放大(looming刺激)或缩小(receding刺激)二维阴影产生的。对接近运动的时距判断通常长于离开运动和静止条件,这很可能是由于接近运动需要观察者快速的行为应对(如反击或逃离)所致。
2.2 模拟和时间知觉
Effron等人(2006)的研究采用时间二分法检验了情绪性面孔表情的时距估计。为了揭示具身化的作用,他们把被试分为两组:控制组的被试可以自由模仿面孔表情,实验组则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用嘴夹着一支笔以抑制模仿行为。实验指导语中没有给予被试模拟表情的要求。结果发现,控制组的被试对情绪性表情图片的时距估计呈现高估,实验组则没有。研究者认为,控制组的个体对情绪表情进行了模拟,这种心理模拟提高了个体的唤醒度水平,进而加快了时间信息加工速度,导致主观时距的延长。当身体模拟行为受到抑制,时间的延长效应就会消失。这表明了身体的物理状态在情绪表情时间判断中的关键作用。
在另一项研究中(Mondillon,Niedenthal,Gil,&Droit-Volet,2007),法国被试判断生气面孔表情(法国和中国面孔各一半)的时距长短。结果显示,被试只高估了与其同一国家的面孔表情时距,而对另一个国家面孔表情的时距判断未呈现扭曲。两种国家人的生气表情都是负性高唤醒度的刺激,被试对其时距估计的结果却不同,说明了法国被试只对自己国家人的生气表情产生了模拟,他们可能不熟悉中国人生气时表情肌肉的状态,因而没有激活对其进行同情性模拟的动机,这表明对模拟目标的熟悉性是影响模拟的重要因素。目标的熟悉性对模拟的影响也反映在性别因素上(Chambon,Droit-Volet,&Niedenthal,2008)。在研究中,年轻被试对老年面孔图片的时距估计短于年轻面孔图片,但这一效应仅发生在被试性别和面孔图片中人的性别相同的条件下。这表明被试的潜在模拟受性别限制,因其不能充分确认异性老年人的行为特征,从而无法模拟与异性有关的身体运动特征(如缓慢的走路)。这一点在 Effron等人(2006)和Mondillon等人(2007)的研究中被忽视,他们的研究只采用了女性被试和女性表情图片。
最近有研究发现,图片中具有不同运动量含义的舞蹈姿势会导致被试产生不一样的主观时间:被试感觉具有较多运动含义图片的时距长于较少运动含义的图片(Nather et al.,2011;Yamamoto&Miura,2012)。研究者认为,被试可能对具有更多运动含义的刺激产生了更多努力和高唤醒度的模拟,主观上认为需要更长的时间。Orgs,Bestmann,Schuur和 Haggard(2011)的研究揭示,被试从连续呈现的姿势图片中所体验到的运动姿势变化的速度扭曲了主观时距(速度与主观时距成反比)。另外,语言中所暗示的运动特征也会促使个体产生对语义的体验进而影响时间估计(Zhang,Jia,&Ren,2014)。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对汉语快速词(如“奔跑”)的时距判断长于慢速词(如“蹒跚”)。这可能是因为被试对不同词语暗示的速度进行了相应的体验,影响了时间信息加工的速度。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认知的内容是身体的,即身体在活动中的不同体验为语言提供了内容(叶浩生,2010)。
综上所述,相对于唤醒度,模拟在时间判断中起更为根本的作用。身体的物理状态、模拟目标的熟悉性、模拟对象的运动量和模拟对象的速度特性都会影响时间判断。需要注意的是,愉悦度不会影响模拟在时间判断中的作用,正性、负性和中性的刺激都可以促使模拟引起时间效应(Chambon et al.,2008;Zhang et al.,2014)。例如,在 Effron等人(2006)的研究中,被试对高兴和生气面孔都产生了行为模拟,进而高估了时距。Nather等人(2011)的研究采用的刺激愉悦度为中性,也发现了被试的潜在模拟和相应的时间扭曲。
以后研究可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1)可以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系统地检验行为模拟、唤醒度和时间扭曲程度的相关性。Effron等人(2006)和 Nather等人(2011)推断具身化通过调节唤醒度影响时间知觉,但缺少直接的证据。因此,揭示具身化情绪的调节机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时间具身加工的过程。2)可以探讨行为模拟对时间知觉的调节是否具有广泛性。有关研究集中检验了情绪本身的时间估计,忽略了情绪模拟的跨通道时间效应。
2.3 (潜在)行为应对和时间知觉
情绪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个体对外部危险性事件做出快速的反应以求得生存(行为应对),这是具身化的重要体现之一。有关的实验研究探讨了行为应对在时距估计和时间顺序判断中的调节作用。
检验行为应对在时间知觉中作用的直接方式是设置运动背景。研究者大都采用二维图像来模拟视觉引导的避免碰撞范式。研究发现,被试对接近运动的时距判断长于离开运动和静止的物体(van Wassenhove,Wittmann,Craig,&Paulus,2011;Wittmann et al.,2010)。例如,在 Wittmann等人(2010)的研究中,每次试验连续呈现 5个圆形,依次是:3个标准圆、1个目标圆(其大小大于、等于或小于标准圆)和1个标准圆。其中,目标圆大于标准圆时形成looming刺激,反之则是receding刺激。目标圆的时距是变化的,标准圆时距保持不变。被试判断目标时距短于还是长于其它标准时距。该研究表明 looming刺激相对于 receding和控制条件延长了主观时距。looming刺激作为接近运动的实验模拟是与自我相关的具有潜在危险的信号,主观时间的延长有利于个体快速做出反击或逃跑的行为反应。然而,looming刺激引起的高唤醒度或其自身的物理特征(视网膜上的成像由小变大)也可能伴随自我相关引起的行为应对在时间判断中起作用。
为此,一项新研究试图将潜在行为应对从其它因素中分离出来(Jia,2013)。该研究设定了真实的小球单摆运动以形成感觉-运动背景。触觉时距刺激在单摆运动中呈现。被试注视小球运动的同时判断触觉时距的长短。在其中一实验中要求被试把手放在单摆运动最低点的正下方,使得被试与小球的交互作用在接近运动和离开运动条件等价,结果显示估计的触觉时距在两种条件下类似,且都长于静止条件。该实验表明自我相关性的重要作用,且排除了刺激物理特征效应(在接近运动条件下小球在视网膜上的成像由小变大导致时距延长),因为离开运动(小球的成像由大变小)产生了与接近运动类似的时距延长。为了进一步将唤醒度从潜在行为应对作用中分离,接下来的实验设定了两种接近运动:在一个条件下,分别在被试双手的掌心里放两个很轻的物体,以抑制身体与小球的交互作用(限制行动);另一条件中被试双手的掌心为空(自由行动)。结果表明,当被试的双手放有物体时,触觉时距的延长效应消失了。情绪评定显示,两种接近运动下的唤醒度没有差异。因此,该研究更直接地表明了潜在行为应对在时间估计中的关键作用,而不是唤醒度和刺激物理特征效应,同时也说明周围运动背景与自我的相关性和观察者身体的行动状态(自由行动和限制行动)影响潜在行为的状态。该研究与Wittmann等人(2010)研究探讨了运动发生时的时间估计,而视觉-运动有关脑区实际上在运动前已被激活(Wise,1985)。有研究证实被试在等待运动时倾向于高估呈现的视觉时距(Hagura,Kanai,Orgs,&Haggard,2012)。
最近研究发现,情绪刺激的运动含义和愉悦度影响动机系统的激活和方向性,进而操纵潜在行为应对的时间效应(Gable &Poole,2012;Gil &Droit-Volet,2011;Shi et al.,2012)。例如,Shi等人(2012)检验了恶心和威胁性情绪图片对随后的非情绪性触觉时间估计的调节,发现威胁性的图片延长了触觉时距估计,而恶心图片则没有。该研究表明只有具有运动含义的刺激(如威胁性刺激)才可能激活防御性系统,进而影响时间判断。Gil和 Droit-Volet(2011) 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结果。然而,与负性情绪相关的防御性反应导致的时间延长不同,正性情绪激活的趋向性反应缩短了主观时间。在另一项研究中(Gable &Poole,2012),被试对正性的高趋向动机(诱人的甜点)、低趋向动机(鲜花)和中性(几何形状)图片的时距进行估计。数据显示,对高趋向动机的图片时距估计短于其它两者。研究者认为,主观时距的缩短延长了对美味食物的潜在趋向,增加被试得到食物的欲望。
此外,研究还发现对身体状态的意识会影响情绪性时距的估计(Pollatos,Laubrock,&Wittmann,2014)。实验中,被试对情绪性电影片段(害怕和有趣)进行回溯式的时距判断。根据指导语将被试分为两组:告知一组被试在呈现电影片段时注意身体状态的变化,而另一组被试注意电影中细节以回答影片结束后的几项问题。实验结束时,被试需要回顾每段电影片段的持续时间。研究表明,对身体状态的注意增强了情绪性时距扭曲。
大部分研究关注具身化在时距判断中的作用。实际上,情绪还可以引导注意转移到更明显的刺激上(如有趣的或危险的)(Mather &Sutherland,2011)。目前主要有两项研究探讨了情绪引起的潜在行为应对在非情绪性时间顺序判断中的调节作用(Jia,Shi,Zang,&Müller,2013;van Damme,Gallace,Spence,Crombez,&Moseley,2009)。在van Damme等人(2009)的研究中,被试对分别在左手边和右手边的一对触觉刺激或听觉刺激做时间顺序判断:左边还是右边刺激先出现。在呈现目标刺激之前,一张情绪性图片(身体威胁、普通威胁和中性)作为线索信息出现在屏幕的左下方或者右下方。结果显示,与普通威胁性图片和中性图片相比,在触觉时间顺序判断中,身体威胁图片促进了与其同一侧的触觉信号加工;而听觉时间判断没有受此类图片的调节。van Damme等人(2009)指出,相对于听觉通道,身体威胁性图片与触觉(与身体感觉有关的通道)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 van Damme等人(2009)的研究中,情绪刺激和时间顺序判断的任务都具有空间性,尚不清楚特定情绪导致的通道注意偏见是基于空间位置还是与通道有关。另外,他们采用通道内时间顺序判断,由此产生的关于身体威胁与触觉通道更为密切的推断具有间接性。为了进一步证实情绪的潜在行为应对在时间顺序加工中的作用,最近研究检验了非空间线索的情绪信息如何调节听觉-触觉时间顺序判断(Jia et al.,2013)。实验中,在屏幕中央呈现情绪图片,听觉和触觉刺激分别出现在被试左右手位置的一边。被试看图片的同时判断左边还是右边的刺激先出现。研究表明,具有靠近身体含义的图片(如张口的毒蛇)促进了触觉时间信息的加工,而与身体无关的危险刺激(如失事的飞机)则没有产生调节作用。与 van Damme的研究相比,该研究直接表明了刺激与身体的相关性在引起潜在行为及其对时间判断的调节中起重要作用。
总之,研究表明,个体的身体与环境/刺激的相关性、个体身体的物理状态、情绪的运动含义、情绪的愉悦度和对身体状态的注意都可能影响情绪动机及其产生的(潜在)行为应对。行为应对在时间估计中的重要影响有效揭示了认知、身体和环境的一体性。未来研究可以采用3D、虚拟现实或真实的运动背景,从行为和神经机制两方面揭示运动和时间知觉连接的生理基础。相对于情绪性图片和对运动的二维模拟,真实性运动刺激可以增加相关脑区的激活强度(Wittmann et al.,2010)。此外,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探索对行为应对技巧的短时训练能否提高时间知觉的判断力,进而改善行动策略。
3 具身化调节情绪时间知觉的机制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直接关于具身化调节时间加工的理论模型,研究者们往往通过时间加工模型和有关时间加工的情绪观点解释具身化的调节机制。时间知觉的研究者假定人类有一个内部时钟(internal clock)加工时间信息(Wearden,1991)。内部时钟包括三个信息加工阶段:时钟、记忆和决策。其中,时钟阶段包括起搏器、开关和累积器,开关位于起搏器和累积器之间。当计时信号开始时,起搏器以一定的速率发放时间脉冲,开关关闭使得脉冲从起搏器传送到累积器。当计时信号结束时,开关打开,停止了脉冲的累积。累积器中脉冲的数量决定时距的长短。唤醒度可以加速或减慢起搏器来调节时间加工(Treisman,1963)。基于具身化在情绪性时间知觉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者推断具身化促使唤醒度影响时钟速率,速率的变化导致了主观时间的扭曲(Chambon et al.,2008;Effron et al.,2006;Nather et al.,2011)。例如,Nather等人(2011)认为,更多运动含义的刺激导致了更高的唤醒度,高唤醒度加速了内部时钟中起搏器的速度。然而,具身化通过唤醒度调节起搏器-累积器机制的观点缺乏直接的神经生理支持。
独立于时间信息加工理论,近期提出的意识模型(awareness model)强调身体内部状态的变化调节时间信息的加工(Craig,2009a)。该模型认为前脑岛皮层(anterior insula cortex)可以统一身体内平衡感觉的元表征,这些表征随时间产生银幕电影般的自我镜头。呈现情绪刺激时表征速度加快,从而增加了情绪时刻的表征数量,表征数量越多主观时间就越长。身体内部对自我的表征是具身化的体现。因此,该模型认为身体状态和情绪意识共同导致主观时间的扭曲。在Wittmann等人(2010)的研究中,负责认知控制和意识的脑区(前脑岛和前扣带皮层)在运动(looming和receding刺激)情境中得到激活,且岛页皮质被确认负责表征身体生理条件,这为身体内部平衡感觉的表征提供了神经支持(Craig,2009b)。然而,对于looming和 receding条件产生的不同时距效应,Wittmann等人却没有给予充分的生理证据:在 receding条件下,负责趋向动机的有关脑区得到激活,而looming刺激却没有激活防御动机的有关脑区。也有其它研究试图用该理论解释实验结果(Zhang et al.,2014)。例如,Zhang 等人(2014)的研究认为,快速词相对慢速词含有更多的活动量,被试为产生相应地模拟体验加快了身体状态变化的速度,这样更多的自我表征填充了时间片段。值得注意的是,意识模型没有说明表征时间信息的直接机制,而只指明了身体内部状态的表征速度和时间加工的关系。
Eagleman和 Pariyadath(2009)提出编码效率假设(coding efficiency hypothesis),认为主观时距是编码效率的结果,时间体验是表征刺激时花费能量多少的指标。该理论认为,明显性或权重大的刺激(如尺寸较大的、运动的和新颖的)导致的主观时距延长是由于这些刺激的加工效率得到提高。该理论没有直接提及情绪性时间加工,但情绪性刺激(尤其需要潜在行动)显然属于权重大的刺激。有少量与情绪有关的研究利用该理论进行解释(Hagura et al.,2012;Wittmann &van Wassenhove,2009;Zhang et al.,2014)。例如,Hagura等人(2012)利用该理论解释运动准备(和唤醒度)导致的视觉时距扭曲。他们发现运动准备增强了视觉信息探测成绩,由此时间的延长很可能来自于运动准备时视觉信息加工能力的变化。换句话说,具身化可能增强了能量的支出,更多的能量提高了信息加工效率,导致更多的时间信息得以编码,进而延长了主观时间。
以上三种模型之间并不相互排斥,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他们对于情绪和具身化效应的解释都与加工速度有关。时钟模型中起搏器速率的加快、意识模型中情绪时刻元表征的加快和编码效率中信息加工速度的改善,都涉及加工速度的提高增加了时间信息的数量。
4 小结
本综述从情绪性模拟和潜在行为应对两个角度总结和分析了情绪的具身化对时间知觉的调节,表明时间信息在感觉-运动回路中进行加工,支持了具身认知观点。当然,这并不否认唤醒度和/或愉悦度对情绪性时间判断的影响,而是强调具身化在其中起关键性作用。情绪维度和具身化可以共同解释不同的时间扭曲(Maniadakis,Wittmann,Droit-Volet,&Choe,2014;Wittmann &van Wassenhove,2009)。关于具身化和时间知觉的一些问题仍需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首先,近期几项行为研究发现视觉情绪的具身化影响了非情绪性触觉时间判断,认为这是由于具身化引起视觉-触觉的功能性连接所致(Jia et al.,2013;Shi et al.,2012;van Damme et al.,2009)。然而,根据具身化认知观点,具身化是对特定通道的感觉-运动系统的重新体验(Niedenthal,2007)。例如,当我们看到威胁性动物(如狗)时,产生的情绪体验会储存在视觉-运动有关的系统里。之后遇到相同情景时,将再次激活有关的视觉、情绪和运动系统(Pineda,2009)。既然具身化体验在特定通道中进行表征,视觉的具身化对触觉感知的调节可能由于某种神经连接的存在。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揭示负责交叉通道连接的相关脑区。实际上,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视觉情绪刺激自身的时间估计,对其它通道及具身化跨通道调节的研究很少,在这方面更多的实验证据(如听觉-触觉和视觉-听觉等交互作用)有助于发现有关的连接机制。此外,具身化的跨通道调节可以为探索时间信息在多通道还是单一通道的时钟机制中进行加工(时间知觉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提供借鉴(Bueti,2011)。
其次,关于具身化调节时间加工的心理机制存在分歧,现有理论缺乏充足的实验证据。在时钟框架内,具身化促使唤醒度调节时钟速率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者试图把具身化和时钟加工机制联系起来,并没有神经学证据的支持。意识模型指出身体内部状态与时间加工之间的关系,并没说明时间加工的机制和生理基础,编码速率假设也有类似不足。为了完善和发展情绪和具身化调节时间加工的理论和机制,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1)研究者可以采用神经成像技术揭示具身化和时钟机制的连接,身体内部状态和时间加工的连接以及编码效率和运动有关机制连接的神经基础;2)现有研究集中关注情绪的具身化对时间认知的影响,反过来时间感知的长短对情绪和具身化的调节也值得探讨,这将有利于更深入地揭示时间加工和具身化的共同机制;3)大部分研究使用单一的时间估计方法(主要是时间二分法)和短时距(<1 s)。为了更好的了解具身化在时间加工中的作用和动态变化,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多元时间估计法和多范围时距。有研究发现情绪对时间知觉的作用只限于几秒之内(如2 s~4 s)(Angrilli et al.,1997)。这可能因为在情绪加工的晚期,其它加工过程如情绪管理取代了情绪效应。具身化与时间知觉关系的动态关系研究也会为有关理论的完善提供证据和参考。
此外,具身化强度与个体的同情心及理解辨认能力有关(Banissy &Ward,2007;Chambon et al.,2008;Decety &Jackson,2004)。以后研究可以进一步确认哪些社会性因素操纵具身化、情绪和时间知觉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神经成像技术进一步揭示辨认情绪含义及行为决策(具身化)的脑区。
叶浩生.(2010).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心理科学进展,18(5),705–710.
叶浩生.(2011).有关具身认知思潮的理论心理学思考.心理学报,43(5),589–598.
叶浩生.(2014).“具身”涵义的理论辨析.心理学报,46(7),1032–1042.
Adelmann,P.K.,&Zajonc,R.B.(1989).Facial efferenc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nnual Review Psychology,40,249–280.
Alexopoulos,T.,&Ric,F.(2007).The evaluation-behavior link:Direct and beyond valenc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43(6),1010–1016.
Angrilli,A.,Cherubini,P.,Pavese,A.,&Manfredini,S.(1997).The influence of affective factors on time perception.Perception &Psychophysics,59(6),972–982.
Ball,W.,&Tronick,E.(1971).Infant responses to impending collision:Optical and real.Science,171(3973),818–820.
Banissy,M.J.,&Ward,J.(2007).Mirror-touch synesthesia is linked with empathy.Nature Neuroscience,10(7),815–816.
Bradley,M.M.,Codispoti,M.,Cuthbert,B.N.,&Lang,P.J.(2001).Emotion and motivation I:Defensive and appetitive reactions in picture processing.Emotion,1(3),276–298.
Bueti,D.(2011).The sensory representation of time.Frontiers in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5,34.
Chambon,M.,Droit-Volet,S.,&Niedenthal,P.M.(2008).The effect of embodying the elderly on time percep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44(3),672–678.
Clark,A.(1999).An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3(9),345–351.
Craig,A.D.(2009a).Emotional moments across time:A possible neural basis for time perception in the anterior insula.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Series B,Biological Sciences,364(1525),1933–1942.
Craig,A.D.(2009b).How do you feel --now? The anterior insula and human awareness.Nature Review Neuroscience,10(1),59–70.
Decety,J.,&Jackson,P.L.(2004).The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human empathy.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views,3(2),71–100.
Droit-Volet,S.,&Gil,S.(2009).The time-emotion paradox.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Series B,Biological Sciences,364(1525),1943–1953.
Droit-Volet,S.,&Meck,W.H.(2007).How emotions colour our perception of time.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11(12),504–513.
Eagleman,D.M.(2008).Human time perception and its illusions.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18(2),131–136.
Eagleman,D.M.,&Pariyadath,V.(2009).Is subjective duration a signature of coding efficiency?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Series B,Biological Sciences,364(1525),1841–1851.
Effron,D.A.,Niedenthal,P.M.,Gil,S.,&Droit-Volet,S.(2006).Embodied temporal perception of emotion.Emotion,6(1),1–9.
Engel,A.K.,Maye,A.,Kurthen,M.,&Konig,P.(2013).Where's the action? The pragmatic turn in cognitive science.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17(5),202–209.
Fotowat,H.,&Gabbiani,F.(2011).Collision detection as a model for sensory-motor integration.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34,1–19.
Gable,P.A.,&Poole,B.D.(2012).Time flies when you're having approach-motivated fun:Effects of motivational intensity on time perception.Psychological Science,23(8),879–886.
Garbarini,F.,Fornia,L.,Fossataro,C.,Pia,L.,Gindri,P.,&Berti,A.(2014).Embodiment of others' hands elicits arousal responses similar to one's own hands.Current Biology,24(16),738–739.
Gil,S.,&Droit-Volet,S.(2011).How do emotional facial expressions influence our perception of time? In S.Masmoudi,D.Y.Dai,&A.Naceur(Eds.),Attention,representation,and human performance:Integration of cognition,emotion,and motivation(pp.61–74).New York:Psychology Press.
Hagura,N.,Kanai,R.,Orgs,G.,&Haggard,P.(2012).Ready steady slow:Action preparation slows the subjective passage of time.Proceedings of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 The Royal Society,279(1746),4399–4406.
Jia,L.(2013).Crossmodal emotional modulation of time perception(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Jia,L.,Shi,Z.H.,Zang,X.L.,&Müller,H.J.(2013).Concurrent emotional pictures modulate temporal order judgments of spatially separated audio-tactile stimuli.Brain Research,1537,156–163.
Lang,P.J.,Bradley,M.M.,&Cuthbert,B.N.(1997).Motivated attention:Affect,activation,and action.In P.J.Lang,R.F.Simons &M.T.Balaban(Eds.),Attention and orienting:Sensory and motivational processes(pp.97–135).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
Levenson,R.W.,Ekman,P.,&Friesen,W.V.(1990).Voluntary facial action generates emotion-specific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ctivity.Psychophysiology,27(4),363–384.
Maniadakis,M.,Wittmann,M.,Droit-Volet,S.,&Choe,Y.(2014).Toward embodied artificial cognition:TIME is on my side.Frontiers in Neurorobotics,8,25.
Mather,M.,&Sutherland,M.R.(2011).Arousal-biased competition in perception and memory.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6(2),114–133.
Mondillon,L.,Niedenthal,P.M.,Gil,S.,&Droit-Volet,S.(2007).Imitation of in-group versus out-group members'facial expressions of anger:A test with a time perception task.Social Neuroscience,2(3-4),223–237.
Nather,F.C.,Bueno,J.L.O.,Bigand,E.,&Droit-Volet,S.(2011).Time changes with the embodiment of Another’s body posture.PLoS ONE,6(5),e19818.
Niedenthal,P.M.,Barsalou,L.W.,Winkielman,P.,Krauth-Gruber,S.,&Ric,F.(2005).Embodiment in attitudes,social perception,and emotion.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9(3),184–211.
Niedenthal,P.M.(2007).Embodying emotion.Science,316(5827),1002–1005.
Orgs,G.,Bestmann,S.,Schuur,F.,&Haggard,P.(2011).From body form to biological motion:The apparent velocity of human movement biases subjective time.Psychological Science,22(6),712–717.
Pineda,J.A.(2009).Mirror neuron system:The role of mirroring processes in social cognition.New York,USA:Humana Press.
Pollatos,O.,Laubrock,J.,&Wittmann,M.(2014).Interoceptive focus shapes the experience of time.PLoS ONE,9(1),e86934.
Rozin,P.,&Fallon,A.E.(1987).A perspective on disgust.Psychological Review,94(1),23–41.
Russell,J.A.(1980).A 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39,1161–1178.
Shi,Z.H.,Jia,L.,&Müller,H.J.(2012).Modulation of tactile duration judgments by emotional pictures.Frontiers in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6,24.
Smith,C.A.,&Ellsworth,P.C.(1985).Patterns of cognitive appraisal in emo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48(4),813–838.
Treisman,M.(1963).Tempor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indifference interval:Implications for a model of the'internal clock'.Psychological Monographs:General and Applied,77(13),1–31.
van Damme,S.,Gallace,A.,Spence,C.,Crombez,G.,&Moseley,G.L.(2009).Does the sight of physical threat induce a tactile processing bias?:Modality-specific attentional facilitation induced by viewing threatening pictures.Brain Research,1253,100–106.
van Wassenhove,V.,Wittmann,M.,Craig,A.D.,&Paulus,M.P.(2011).Psychological and neural mechanisms of subjective time dilation.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5,56.
Vytal,K.,&Hamann,S.(2010).Neuroimaging support for discrete neural correlates of basic emotions:A voxel-based meta-analysis.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22(12),2864–2885.
Wearden,J.H.(1991).Do humans possess an internal clock with scalar timing properties?Learning and Motivation,22(1–2),59–83.
Wise,S.P.(1985).The primate premotor cortex:Past,present,and preparatory.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8,1–19.
Wittmann,M.,&van Wassenhove,V.(2009).The experience of time:Neural mechanisms and the interplay of emotion,cognition and embodiment.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Series B,Biological Sciences,364(1525),1809–1813.
Wittmann,M.,van Wassenhove,V.,Craig,A.D.,&Paulus,M.P.(2010).The neural substrates of subjective time dilation.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4,2.
Yamamoto,K.,&Miura,K.(2012).Time dilation caused by static images with implied motion.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223(2),311–319.
Zhang,Z.,Jia,L.,&Ren,W.(2014).Time changes with feeling of speed:An embodied perspective.Frontiers in Neurorobotics,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