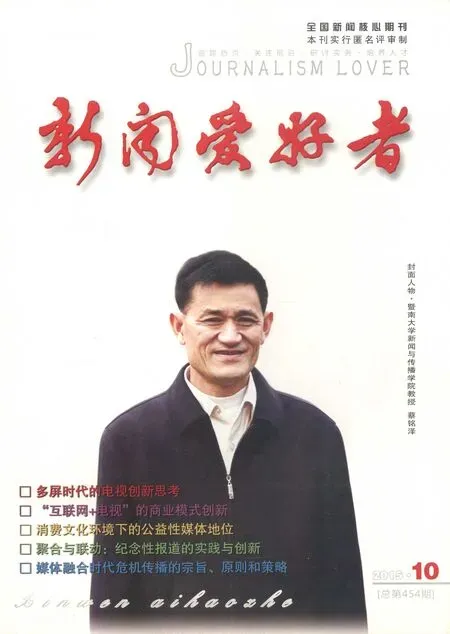历史就在你的脚下——读台湾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李 彬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这个《新闻与文化书谭》专栏,不知不觉就要结束了,如何收束,最后一篇谈什么,自然颇费心思,正当举棋不定时,友人惠赠一套四册“王鼎钧回忆录”,同专栏开篇所谈一套四册《范敬宜文集》在新闻与文化的意味上一脉相通,以此作结也可谓首尾呼应了。
王鼎钧,山东兰陵人,也就是《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之兰陵,1925 年生于耕读世家,少年时参加抗日游击队,后以流亡学生辗转于安徽、河南、陕西。 国共内战中当过国民党的宪兵与解放军的俘虏,1949 年流亡台湾,先后供职军方《扫荡报》、“中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晚年定居纽约。 在台湾新闻界与文化界,王鼎钧以散文著称,1992 年至2009 年,他陆续撰写了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以一种细腻的回忆、敏锐的感受、生动的书写,展现了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风云,从抗战到内战,从大陆到台湾,“融人生经历、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显示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这部宛若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的私人历史,大到风云变幻,小到家长里短,不管状人写物,还是剖事析理,无不娓娓道来,文笔自然、清新、生动,读来如饮醇醪,陶然忘机。 如此新闻与文化的书写,对普通读者了解社会、认识人生固然多有裨益,而新闻记者更是值得一读。 因为,既可从中体悟知人论世的功夫,换一种“陌生化”视角理解身处的时代与社会, 从而更懂得 “现实中国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又可学得或悟得“文章不著一字空”的门道,避免党八股的陈词滥调、洋八股的莫名其妙。
四部曲分为两大板块, 前三部是在大陆的人生回顾,第四部是在台湾的文学追忆,而一脉相通的则是天长地久的故国情怀, 如同那位同样流寓海外经年的新闻人与文化人赵浩生所起回忆录的书名 《八十年来家国》。 若将四部曲比作交响乐的四个乐章,那么作为主体与精华的前三部又像奏鸣曲式的三部曲——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 乡绅世家,大户门楣,作者显然属于中国革命触及的主要社会基础,当年战火纷飞的年代,确曾遭逢离乱,家破人亡。 而基于阶级背景以及主动被动的选择, 自己又始终依附于“蒋家王朝”,到台湾后还从事了多年反共的“文宣工作”。 于是,虽然作者力求超越阶级与时代的局限,站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审视一切, 并达到难能可贵的境界, 但八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地山河的败亡心结,毕竟还是挥之不去,回忆录不妨说也在追寻历史深处的答案。 这一追寻,便构成四部曲四个乐章的主题与乐思——共产党为什么胜而国民党为什么败。而前三个乐章又在急管繁弦、步步推演中,使这一主题与乐思不断深化,日益丰满,直至人间正道是沧桑的高潮。 其中,第一部《昨天的云》是呈示部,娓娓谈及故土风物之际,也将这一主题与乐思表露出来。 第二部《怒目少年》是展开部,讲述流亡故事,回顾抗战往事,又对主题与乐思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第三部《关山夺路》是再现部,通过国共内战,反思江山易色,更使这一主题与乐思鲜明昭彰。
呈示部——《昨天的云》。
在这部回忆录中, 王鼎钧除了絮絮讲述吾乡——临沂兰陵的风土人情,吾家——王氏家族的各色人物,寄寓了一腔对故乡、故人、故土的眷恋,更着重写了少年读书与随父参加游击队的种种亲历亲闻, 正是在这两部分中, 集中呈现了兴亡主题——共产党何由兴,国民党何由亡。 第四章“荆石老师千古”中,王鼎钧浓墨重彩地写到一位家乡的“意见领袖”——卓尔不凡的大老师王思璞 (荆石),从回忆录中描绘的言谈举止上, 读者似乎历历在目地看到一位革命者或先进知识分子的身影。 私立兰陵小学成立后,这位大老师除了音乐,什么都教——国文、历史、美术等。 通过教学,他把许多新事物引进家乡,如引进注音符号,引进话剧,引进木刻,引进荷马、安徒生、希腊神话、《阿Q 正传》。 最让作者印象深刻的是他专门记述的一笔:“我必须记下来, 他老人家引进了马克思……”在少年王鼎钧的听闻中,大老师三读《资本论》,赞成社会主义,欢迎共产党。 虽然大老师没有对他亲口谈过这些话题, 但老师的一言一行却让他铭记终生,难以忘怀:
我只知道大老师同情——甚至尊重——穷苦而又肯奋斗的人。
有一个人, 算来和大老师同辈, 半夜起来磨豆腐,天明上街卖豆腐,他儿子在小学读书,成绩极优。当他的太太沿街叫卖热豆腐的时候, 那些大户人家深以辱没王家姓氏为憾, 唯有大老师, 若在街头相遇,必定上前喊一声三嫂子。 这一声三嫂子出自大老师之口,给他们全家的安慰激励是无法形容的。
那时, 兰陵的清寒人家有些是敝族的佃户或佣工,他们的孩子和“东家”的孩子一同读书,那些少爷小姐把阶级观念带进了学校。 在那种环境里,连某些老师也受到习染,走在路上穷学生向他敬礼的时候,他忘了还礼。 我们的大老师不是这个样子,大老师的儿子侄女也不是这个样子。[1]
王鼎钧上小学的时候,国共已经分裂,江西开始“剿共”,大老师言谈绝不涉及国文之外。但他猜测,大老师的得意门生、入室弟子,想来也许有些“异闻”吧:
一个不可抹杀的事实是,七七事变发生,兰陵人奋起抗战,国共竞赛,各显神通,大老师最欣赏最器重最用心调教的学生全在红旗下排了队……这些人都做了建造“人民共和国”的良工巧匠……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2]
王鼎钧的故乡在鲁南沂蒙, 这一带民国年间匪患猖獗,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就发生在这里。 军旅作家李存葆在散文名篇《沂蒙匪事》中记述了当年一系列令人发指的土匪暴行。 抗战爆发后, 土匪消失了,因为有的投靠日寇,为虎作伥,有的变成游击队,奋起反抗,而游击队又分属国共两家。 王鼎钧父子参加的是兰陵王氏家族组织的一支游击队。 在这部分回忆中,他记述了许多活灵活现的抗日故事。 如当地流传着三句话:日本鬼子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 下面一段细节,相信读者更是过目难忘,那时王鼎钧已是一名小游击队员:
在队上,我的顶头上司是毓肇叔,他说:“别的事不要你干,你在村子里到处走走看看,看到什么事情马上告诉我。 ”
村子里还能有什么事情? 这村庄已经是游击队的了,老百姓不过是布景和附件。
还是看到一些事。 大早晨,一个老太太,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提着一罐清水,瓦罐很小很小。 早晨是家家户户挑水的时候,老太太没力气,只能站在井口央求别人顺便替她提上小小一罐水来,瓦罐太小,看上去好像老太太在打油。
虽然瓦罐很小,老太太的步履仍然有些艰难,我就上前一步把水接过来替她提着。 她端详我,“以前没见过你,你是八路军吧? ”
不知怎么,我受到很大的刺激,内心震动。 连这么一件小事也得八路军才做得出来, 十二支队还能混得下去吗?[3]
展开部——《怒目少年》。
王鼎钧的最高学历是初中, 回忆录第二部讲述了抗日烽火中这段流亡学生的经历, 类似经历在那代人身上很常见。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教授李瞻,比王鼎钧小一岁, 也是山东人, 抗战中就同属一所中学。 业师方汉奇先生与李瞻同庚,原名方汉迁,当年流落南方上小学时,迁字被方言念成“jian”,于是执意改名“汉奇”。 年逾九旬的暨南大学新闻学教授梁洪浩先生,2015 年农历新年时, 还在公子陪同下,历时十几天,重走当年流亡路,想来也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一种纪念。 从这部《怒目少年》中,既可体味歌曲《松花江上》那般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悲痛境遇,“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也能点点滴滴感悟未来中国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
据说有种“国粉”,力挺国军,贬抑共军,国军威武雄壮,共军游而不击(这也是当年汉奸汪精卫的说辞),等等。 其实,兄弟阋墙,外御其侮,面临日寇的凶暴入侵,无论国军还是共军,无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无愧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如果非得“评功摆好”,那么全面抗战爆发的初期,国府国军自然位居首要,因为是国家政权所在,并掌握着绝大多数资源,国府投降就等于中国投降,国军败亡无异于中国败亡。 而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越打越强的八路军、 新四军则日益显示中流砥柱的地位,你打你的阵地线、我打我的游击战,以及敌后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更是成为主战场, 抗击着60%的日军和95%的伪军。 一篇《中共缘何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文章就此对比道:第一,共产党全心全意抗战,而国民党三心二意抗战;第二,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而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第三,共产党灵活机动作战, 而国民党单纯防御作战;第四,共产党坚信自己的力量,而国民党寄希望于外部力量。[4]剑桥大学教授、《剑桥战争史》的主编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也从军事上谈了类似看法:
南方周末:你觉得抗战中,中国哪一仗打得比较漂亮?
方德万:每一仗都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死了太多人……一定要说有,那应该是毛泽东。蒋介石和日本人都认为,他们之间的战争应该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结果在中国战场上,他们都失败了。 但毛泽东说,中国不具备打现代战争的条件……要打就用我的办法打。
南方周末: 他的原话是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方德万:对。 所以后来亚洲、南美……很多独立运动领导人都看毛泽东的书。 他们认为他教会他们用前现代的办法跟现代化敌人打仗。 毛说,我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跟你打,我打的是“人民战争”。 毛还有一个好经验:要么不打,打一定要打胜。 因为你越胜利老百姓越支持你。 你老打败仗,哪怕这个败仗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老百姓也会越来越不相信你。[5]
在王鼎钧的笔下, 到了抗战后期, 国军日渐疲软,军纪荡然,而共军日益强大,民心所向。 1944 年,苏联红军已经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彻底击溃围困列宁格勒的德寇, 解放了克里米亚和罗马尼亚,英美盟军也已在诺曼底登陆,罗马、巴黎相继光复,太平洋上,美军以“跳岛战术”正一步步逼近日本本土。 而当年4 月,日本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困兽犹斗发起一号作战,国军仅在河南一地就“三十七天内连失三十八城”,蒋介石的“天子门生”汤恩伯指挥五个集团军,一遇日寇,溃不成军,整个豫湘桂也是一溃千里,丢盔卸甲。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在《光明日报》撰文说,1944 年4 月的豫湘桂大溃败,“是正面战场的最大败笔”“把中国军队多年来的奋斗、牺牲和国际声誉丢失众多,并且对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不良影响”[6](最突出的一例就是1943 年的开罗会议邀请蒋介石,而1945 年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雅尔塔会议只剩美苏英)。 之所以如此,除了军事方面的问题, 包括众所周知的国军派系林立、士气低落,每战往往拥兵自保、作壁上观(台儿庄激战中汤恩伯主力迟迟不肯回援, 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军长率部孤守危城47 天等都是典型), 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政治的衰败腐朽, 如新闻史上的著名报道所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王鼎钧流亡途中,经过河南的所见所闻, 也活灵活现地提供了这方面的真实图景。 如抗战后期,河南有240 多种摊派,汤恩伯所部“纪律之坏,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民间甚至流传着“宁愿日军烧杀,不愿汤军驻扎”。 他目睹的下面两例也足为旁证:
一中到了城固以后,师生公演京戏筹措经费,阻挡无票的军人入场,有一个军官恼羞成怒,开枪打死一个学生。 这一枪,把唱“盗御马”的打成演“棠棣之花”的(《棠棣之花》为郭沫若抗战时期创作的历史剧——引者注),把看“三国演义”的打成看“大众哲学”的(《大众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代表作——引者注),把到西安兰州升学的打成到延安升学的。[7]
我在公路旁看团管区押送壮丁, 他们用绳子把壮丁一个一个捆起来,连成一串,路上同时大便,同时小便,当然也同时睡觉,同时起床。 当然吃不饱,所以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么瘦,当然不盥洗,所以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脏。 谁生了病当然也没有医药,一旦轻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8]
后面一例, 让人想到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新潮》,里面也写到抗战期间他代表国府巡视, 途中看到大队壮丁被绳捆索绑的凄惨景象。 如此征召的士兵能有多大战斗力,就也不难想象了。 诸如此类的所见所闻既触目惊心,也使敏感细腻的少年王鼎钧陷入深思。 当他所在中学从皖北迁到关中时,一位新来的主任在课上,又让他歪打正着一窥共产主义的门径,从而引起他更多“离经叛道”的思考。 这位主任讲的内容多半是批评共产主义,而恰恰是这种“共产主义批判”,反而触发了许多学生的好奇心,包括王鼎钧:
共产党处处讲“阶级”,主任说中国没有阶级,只有“阶层”。 这个说法吓人一跳,阶级好比楼梯,下面的一层还可以伸出头来透口气,阶层简直是水成岩,上面盖得严丝合缝,不见天日,想用阶层代替阶级,弄巧成拙啊![9]
再现部——《关山夺路》。
解放战争是王鼎钧回忆录第三部的背景, 更是少不了痛定思痛的反省:好端端的江山怎么就丢了?不起眼的共军怎么就赢了? 对此,他写下一句颇为深刻的话:国民党走的是“领袖路线”,共产党走的是“群众路线”[10]。换言之,蒋介石奉行“精英路线”,毛泽东奉行“群众路线”:“一位美国记者当年在采访过中国后说,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官员,多是留学生、富贵人家的后人。 他们高高在上,说外语,敬耶稣,缺少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不了解基层人民的苦难。 他们的那些政策,多是空洞的口号,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他们的治国理念来自西方,与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 ”[11]
抗战胜利后,王鼎钧参加了国民党宪兵,在宝鸡受训时看到班长每天动手动脚打新兵, 而且骂骂咧咧的:“打一下,骂一声活老百姓,打一下,骂一声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 ”[12]而今回想起来,王鼎钧深有感触:
兵士来自民间,带着民间的习性和身段,也许和军事训练的目标相悖,但是你不该因此侮辱老百姓,不该借此丑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卑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
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八路军走出解放区,蹲在收复区农家的灶门, 亲亲热热叫声老大娘老大爷:“八路军把鬼子打退了,蒋介石要下山来摘桃子……”
以我亲身体会,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百姓为耻。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得到老百姓支持。 一九四九年,那时国民政府已吞下一切苦果,我到台湾卖文为生,下笔东拉西扯,不知轻重。 我给具有军方背景的《扫荡报》副刊写了一篇文章,直陈军中不可把“老百姓”当作骂人的话使用。[13]
按说国民党军打骂百姓,欺压民众,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若非看到王鼎钧的记述,怎么也想不到“老百姓”居然成为国军骂人的话。而一首解放初期创作并传唱至今的红歌, 一张口则唱道:“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14]
一般印象中,国民党败在军事上,蒋介石哪是毛泽东的对手,而美国学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在权威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一书中, 对国共双方的所作所为做了深入翔实的学术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国共之争是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的全面较量,国民党的失败也是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的全面失败。 拿文化来说,《回延安》一文提到的国民党宪兵学校校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典型。 前者的歌词体例,仿照民国的国歌,佶屈聱牙,节奏呆板,共同特点或缺点是:“你得读过许多文言文, 才看得懂, 即使读过许多文言文, 也听不懂。 ”[15]不信,就闭上眼,试一试:“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克励尔学,务博尔知,唯勤唯敏,唯职之宜”——几人能够听得懂。 作为对比,王鼎钧不由得慨叹道:“就在我们嗡嗡作声、不知所云的时候,黄河北岸中共士兵朗朗上口的是:人民的军队爱人民! 一听就会,触类旁通。 ”[16]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1949 年4 月23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蒋介石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黯然飘落,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停播“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而播出大江歌罢掉头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一听之下,高下立判: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着全国的解放!
人民的军队爱人民,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共军响遏行云的嘹亮歌声, 也将王鼎钧前三部回忆录的主题乐思推向了大江东去的高潮。 随后第四部《文学江湖》,就像尘埃落定的一声叹息,一曲余音袅袅的尾声:
九十年代我在纽约,一位观察家告诉我,反共的人共有五类:有仇的,有病的,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和莫名其妙的。这是真知灼见。我想反共是这五种人的组合互动,可能一个有病的排斥一个有理想的,可能一个有仇的指挥一个有病的, 也可能一个有野心的出卖一个莫名其妙的。 高踞他们之上,有一位总指挥,他可能有仇、有病、有理想,也有野心……[17]
他还提到20 世纪50 年代的一次座谈会,更让今人感到拨云见日,醍醐灌顶。 当时他问一位台湾教授,怎样才能写好反共小说, 教授的回答令他始而大惑不解,终至叹服先见之明:“现在”写反共小说写不好,“将来”由大陆作家来写,才写得好。 当时谁能想到大陆作家写“反共”作品,而且写得好。 当然,“反共”既有反对的反,包括“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也有反思的反。而不管什么反,怎么反,如今看来,反得最“好”即最具颠覆性毁灭性的,无疑来自大陆而非台湾。
前些年,厦门大学某位教授发表演讲,声称解放战争中震惊全国的“沈崇事件”,原是共产党导演的美人计, 美国大兵强奸的北大学生沈崇实为共产党“特工”云云,一时网上风传。 有人还将其编入所谓“年度最佳演讲”, 在湖北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 其实,这套说辞恰恰是当年国民党特务为了掩盖真相、转移视听炮制的谣言,当即就被戳穿,为天下笑,而今“专家学者出版社”又当秘闻传播,不也正好证明王鼎钧叹服的那位台湾教授确有“先见之明”①。
王鼎钧回忆录中除了鲜活生动、 比比皆是的历史细节,难能可贵的还在于知人论世的情怀与境界。虽然他的出身与一生,使他难以摆脱“党国”的政治意识形态, 但在自身自家遭逢如许离乱辛酸的情况下,还能超越或力求超越阶级与时代的藩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诚可谓达人知命也。 他在《关山夺路》的后记里动情地呼吁道:
五十年代台湾的反共文学,“文革”结束后大陆的伤痕文学,都太执着个人的生活经验,都不很精彩。可敬可爱的同行们! 请听我一句话:读者不是我们诉苦伸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是来替我们承受压力。 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啦啦队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弱势团体任意摆布的时代也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血泪化成的明珠……[18]
他的回忆录特别是前三部, 就是用心捧出的明珠,“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给人启迪,令人温暖, 读来就像文史大家朱东润先生那部暖人暖心的自传。
从王鼎钧的痛定思痛, 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张光直。 张光直(1931—2001),祖籍台湾,享有国际声望的考古学家,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台湾“中研院”院士、副院长。 张光直早年为左翼青年,深受参加革命的长兄张光正(何标)影响。 在《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一书里,他写了一些有似王鼎钧的故事,如哥哥为什么参加革命:
在我上小学搬家到手帕胡同前后, 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搬到我们家里来住, 这人就是徐木生。 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圆圆的脸,一身笔挺的日本大学生黑制服。 徐木生说话声音很大,充满自信,见了我和哥哥便叫,少爷! 少爷! 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事的时候便向我和哥哥宣传马列主义。 我哥哥确由一个 “少年” 转变成为一个马列主义的革命者,大致是受了徐木生的影响。1945 年,哥哥出走,进入河北平山晋察冀边区, 同时也走上了人生另一条大道。 在80 年代,我们重会以后,有一次我问哥哥:(是)“什么让你下决心加入共产党的? ”他的回答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我加入共产党的第一个目的是,好让徐木生不再叫我少爷!! ”[19]
1982 年, 张光直创作了三篇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主人公都是“我”当年的青年导师,也是新中国的功臣。 “我”本以为,革命成功后,他们会图画凌烟阁,没想到后来下场却都很凄惨,更没想到的是,他们居然无怨无悔。 在《杨老师》一篇中,杨老师的儿子对父辈的追求与坚守很不理解,去信给“我”,认为父亲执迷不悟,一辈子白活了。 于是,“我”就写了如下的回信,这封信的光明正大,也使形形色色、明里暗里的“反共”之士,顿显格局褊狭、境界晦暗:
五千年来的中国,不早不晚偏偏要在我们的年代自黑暗开始走向光明。 四十年代的一首歌唱得好:兄弟们,向太阳! 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快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 我们这几代的人是最幸运的了,我们这几代的人也是最不幸的了。 我们的幸运是因为只有我们才有那走“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的千载一时的机会。 可是那五千年来的黑暗有强韧的生存力量, 不是一瞬间的光华便可以将它消灭的。 要走那万丈光芒的路是漫长的、崎岖的、曲折的,我们跌倒的机会也比别人都多。 这样说来,你和你的父亲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和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不知下去多少代的儿女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 你的父亲战斗过了,下面要看你的了。[20]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2012 年在给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演讲《历史就在你的脚下》中,最后饱含深情地谈到张光直和他的小说《杨老师》:
张先生不是文学家,但他的文学作品,让我非常感动。 最近,我又读了一遍,不是当文学读,而是当历史读。 它让我想起我的北京,想起我执教28 年的北京大学,想起我生活其中的上一个世纪。
这100 年只是刚刚翻过的一页,宛如昨日。 它不仅对我们的父辈是轰轰烈烈,对张先生是魂牵梦绕,对我也是挥之不去。
记忆的碎片纷至沓来,有如大树飘零。
历史就在你的脚下。[21]
注 释:
①2015 年第1 期《纵横》刊发《我对沈崇的一次访谈》,作者为香港文物收藏家许礼平,《新华文摘》2015 年第6 期予以转发,也算为此画上盖棺论定的句号。 原刊“编者按”写道:2014 年12 月16 日,沈峻在北京病逝,享年88 岁。沈峻原名沈崇,是68 年前“沈崇事件”当事人……本文作者依据该事件实物资料,采访沈崇本人,撰成此文,对该事件作出澄清,以飨读者。
[1]王鼎钧.昨天的云:回忆录四部曲之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54.
[2]王鼎钧.昨天的云:回忆录四部曲之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55.
[3]王鼎钧.昨天的云:回忆录四部曲之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75-176.
[4]王立华.中共缘何成为抗战中流砥柱[N].环球时报,2015-04-11.
[5]石岩.“二战”是罗斯福发明的,中国人叫“抗战” 《剑桥战争史》主编谈中国抗战[N].南方周末,2015-04-09.
[6]钱乘旦.世界大格局中的二战东方战场[N].光明日报,2015-08-15.
[7]王鼎钧.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73.
[8]王鼎钧.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86.
[9]王鼎钧.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68.
[10]王鼎钧.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93.
[11]陈延武.万水朝东:中国政党制度全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53.
[12]王鼎钧.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2.
[13]王鼎钧.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2.
[14]王鼎钧.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86.
[15]王鼎钧.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41.
[16]王鼎钧.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42.
[17]王鼎钧.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91.
[18]王鼎钧.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72.
[19]张光直.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7.
[20]张光直.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81-83.
[21]李零.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