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人大机构经费拨款的影响因素——基于1994-2007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庄文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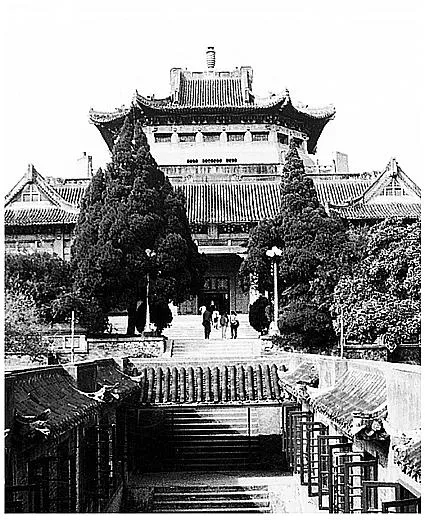
中国地方人大机构经费拨款的影响因素
——基于1994-2007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庄文嘉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人大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的地区性和功能性不均衡。根据1994至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所建立的动态模型以及系统广义矩(System GMM)估计方法考察各地人均人大经费拨款的影响因素发现,政治竞争、经济增长、行政国家重构与维持社会稳定四种理性共同塑造着地方人大的发展轨迹。多重理性的同时存在也决定了各地方对待人大机构的工具性态度,这也是地方人大发展呈现出地区性和功能性不均衡的根源。
关键词:地方人大; 经费拨款; 面板数据; 动态模型; 系统广义矩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动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90年代推动“依法治国”运动均为中国地方人大的壮大提供了重要的契机(Cho,2006:592-609)。但是,由于全国人大领导人坚持“地方的事情地方管”(O’Brien & Luehrmann,1998:91-108),所以30多年来各级地方人大主要靠自己解决人员编制和机构经费等问题。结果,地方人大的机构建设呈现出高度的地区间不均衡(O’Brien,2009:131-141)。那么,为何在整体政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且缺乏来自中央实质性支持的情况下,有的地方人大能成为先锋并快速发展起来,有的则跟随先锋者的步伐缓慢发展,还有的却在人大建设问题上成为懈怠者呢*有关地方人大发展的三种类型:先锋者(Pioneer)、追随者(Bandwagoner)和懈怠者(inactive),来自于韩国学者赵英男的类型学划分,具体见Young Nam Cho.LocalPeople’sCongressesinChina:DevelopmentandTransi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56~160.?我们如何解释这些地方人大机构建设的差异呢?换言之,哪些因素影响着地方人大的机构建设?
对此,既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学者主要强调经济转型对地方人大发展的影响(Chen,1999:229; Pei,1998:68-82;Xia,2000:148)。因为中央希望加速法制建设来配合市场转型,所以鼓励地方人大进行超前立法,在中央立法空白领域进行创新(O’Brien,2009:131-141)。不过,中国经济发展采取的是发展主义模式,这一路径决定了地方人大的壮大不会带来过多的冲突与对抗,而是带来增进权力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决策理性化的共识性政治(consensual politics)(Xia,2000:148、171)。与第一派学者所强调的工具性色彩相区别,第二派学者则倾向于将地方人大改革看作是行政国家重构过程的一部分(Burns,1999; Yang,2004)。卜约翰认为,预算工作委员会等机构的成立,使得人大作为一个工具性机构的能力得到增强;从行政改革的角度看,这会促进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分化和决策过程常规化(Burns,1999:580-594)。杨大利也指出,人大作为横向问责机构的强化,体现的是中国政府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治理结构而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为现代监管型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Yang,2004:22)。除了经济理性和行政理性的影响,第三批学者强调地方人大发展是作为改革者提升政权弹性与适应能力的构成部分(包瑞嘉,2004:4-10; Nathan,2003:6-17)。例如,1995年中央推动地方人大常委会主席团提名候选人与人大代表提名的候选人竞争,产生了一批更加优秀的地方官员,使得执政党和老百姓都从中受益(Manion,2008:607-630)。类似的,有的地方人大代表参与预算民主恳谈,也增进了精英团体和老百姓的协商,帮助地方政府更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He & Thøgersen,2010:675-692)。所以整体上看,地方人大的发展并不会约束国家权力,而是巩固国家权力(Sun,2010:833-866)。
综上所述,经济转型、行政理性化和政权的自我调整与适应,都对地方人大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这三种因素背后,既有中央的鼓励和推动,也有地方的异见和工具性态度。由于这些复杂因素同时存在,我们很难打开黑箱并清晰地分离出不同维度和层面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判断地方人大发展的影响因素时要小心谨慎地解读。本文基于上述梳理的三种视角建立假设,并且利用1994-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各种假设进行检验。通过计量分析,发现政治竞争、发展主义理性、官僚理性和维稳理性等多重因素同时塑造着地方人大的机构发展。在政治层面,经济增长潜力较弱的地方倾向于推动人大改革以将其作为替代性的政绩。在经济层面,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地方党政愿意投入更多资源予人大机构以提升立法能力,但是也因担心人大监督和过多制度约束破坏投资环境而存在顾虑。在行政层面,税收最大化的目标激励地方加强制度建设,从而扩大和巩固财源。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民族自治、劳动力市场化和流动人口等因素都迫使地方党政加大对地方人大的资源投入以改善治理能力。
本文认为,正是因为多重理性同时存在,使得地方人大的发展不仅呈现出高度的地区间不平衡,也表现出明显的功能性不均衡。在缺乏自上而下推动的情况下,地方人大通过嵌入既有的地方政治权力结构而非寻求自主性,虽然赢得了机构能力的提升,却也牺牲了部分功能。但是,地方人大发展绝不同于其他官僚机构的扩权或行政性改革,其制度性地位决定了地方人大发展是与中国的政治变迁和民众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的。从政治现代化和制度化的角度看,地方人大的长期发展不仅能够约束政府权力的运作,也会为社会主体的参与提供新的舞台,使得决策过程更加制度化、多元化和开放化。也正因为如此,加强地方人大机构建设和促进地方人大各项功能的均衡发展,应当成为下一步政治改革的重要部分。
二、 模型、方法与数据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因变量的选取和操作化。本文将不同省份的人均地方人大经费拨款作为因变量。经费拨款反映的是各地方对人大机构建设的资源投入,资源投入的提升会从整体上促进不同功能的发挥。一般而言,地方人大通过两种办法扩大资源投入:一种是依靠地方人大常委会领导出面去申请增加个别编制和经费,另一种是人大机构进行内部改革。由于国家编制受到严格控制,前者很难大幅度地改变预算拨款,所以要想有实质性的提升,地方人大必须提出充分的理由来赢得地方权威的支持,例如为提升立法能力而增设工作委员会*对X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的访谈,2012年1月3日。。这类改革往往会带来编制和经费的大幅度提升,也从客观上推动了人大某些功能的提升。因此,比较人大机构经费拨款不仅更具可行性,也可以更简单清晰地看到不同地区人大机构建设的差异。虽然不同层级的人大经费由同级财政提供,但是省际差异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省际比较也抹去了一省之内的地区差异,这是本文的一大局限。不过,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结构性因素而非行动者因素对人大机构建设的影响,省际差异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一问题。而且,有关人大经费的系统连贯的数据,官方也只提供到省一级。。考虑到各省行政区划大小存在很大差异,在因变量操作化中,本文采用人均人大经费拨款(即各省人大经费的财政拨款数分别除以各省常住人口)作为测量指标。
对于经济增长因素,本文同时考察经济发达程度、经济增长潜力和地方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所带来的影响。按照上述学者们对市场转型和经济绩效的假设,本文认为经济发达地区相对于不发达地区更有意愿去推动人大建设,因为建章立制有助于地方政府控制快速市场化所带来的混乱与失序(Cho,2006:599)。基于此,本文假设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地方人大经费拨款有积极的影响。但是,经济增长潜力较弱的地方可能更有动力在经济绩效之外寻求政绩,这时发展地方人大可能成为一个替代选择。而为吸引外资或避免外资抽逃,外资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可能会采取“逐底竞争”的策略,为避免过多权力机构的制约而抑制地方人大的机构发展。因此,本文假设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占地方生产总值比重这两个变量都会对地方人大经费拨款有负面影响。
对于行政理性因素,本文考察征税能力和自产国家特征的影响。市场化改革导致原有国家财政的主要支柱来源——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下降,此时需要有新的机制来为国家预算提供税收(Wong,1991:691-715)。按照这一逻辑,推动加快建章立制的速度和改善立法能力应该有助于改善各级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出于这样的考虑,税收征收能力较弱的地区可能更有动力去推动人大立法以将财源制度化。所以,本文假设征税能力较弱的地方会加快立法机构建设以便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扩大税收来源。而各种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预算内加上预算外收入)的比例,则成为测量征税能力的指标。但是,如果财税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部门,那么国家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此时自然不会有太强的意愿去发展代议机关。由于我们没办法彻底从财政收入中分离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各自的贡献*在地方层面,要在财税贡献中对不同经济类型进行分离十分困难。因为从1994年到2007年,官方统计口径多次发生变化,所以无法找到系统连贯的数据。而有关全国层面的分离办法,可见马骏:《走向税收国家: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所以本文采用间接测量方式,将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贡献的比重作为测量自产国家特征的指标*“自产国家特征”,在此特指国有经济部门对政府财税贡献的多寡;贡献越大,自产特征越明显。有关这个概念在中国财政领域的应用,见马骏:《走向税收国家: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研究》。。比重越低,国家面对社会的自主性越弱,则更可能推动代议机构的发展以增进与市场化经济主体的讨价还价能力。
对于政权回应性和适应能力因素,本文考察了少数民族自治、劳动力市场化和流动人口等因素的影响。首先,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中央鼓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提升代议性以改善地方治理(O’Brien & Luehrmann,1998:91-108)。为了检验这一因素的影响,本文将有民族自治地方的20个省份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各省常住人口的比例作为测量少数民族规模的指标。比例越高的地区可能会分配更多财政资源于人大机构。其次,如果说地方人大的壮大反映的是国家为适应市场转型而做出的自我调整,那么,90年代末以来的国企改制和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化应该会促使地方政府加快人大建设以推动制度化进程*有关90年代国企改制与职工下岗对劳动立法的影响问题,见岳经纶:《中国劳动政策: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所以本文将非国有或集体单位的城镇劳动力占城镇劳动力比重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检验其对地方人大机构建设是否存在积极影响。最后,伴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的是流动人口骤增,尤其是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务工与居住,给输入地的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Solinger,1999)。基于此,本文假设,外来人口密集的地区可能更倾向于发展代议机构以化解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挑战。而对外来人口规模的测量,采取的指标是户籍人口占地方常住总人口的比例;比例越低,表明外来人口规模越大。
最后,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地方财力的影响,本文用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以上年为基数)作为衡量通胀率的指标,而用人均预算内支出作为测量地方财力的指标*该指标是将预算内支出除以地方常住人口。之所以选取预算内支出,一是因为地方人大经费都纳入同级预算,二是因为支出更能反映真实财力。,并在下列所有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本文使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等官方出版物。表1罗列了上述所有解释变量和因变量的基本数据。
根据1994年预算法,每年政府预算都会参考上一预算年度的情况制定,所以因变量会受到自身滞后一期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来进行计量分析。而且,本文采用的因变量是人大经费的财政拨款数,考虑到各级预算是在每年年初制定,所以将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影响都滞后一期,即假设上一年的各种因素影响了下一年的预算拨款,更符合实际情况。具体模型为(水平方程):
其中下标i代表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截面单位,t代表从1994年到2007年的14个年份,因变量yi,t为人均人大经费拨款,yi,t-1为滞后一期因变量。xit-1为滞后一期的严格外生的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wit-1为滞后一期的前置解释变量,vi是各省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由于假设上述因素是地方人大发展的推动力,那么承认这些因素会受到过往的随机扰动项的影响可能更为合理。所以,除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预算支出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本文将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占地方生产总值比重、税收收入比重、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业产值贡献率、少数民族规模、非国有或集体部门劳动力规模和户籍人口规模都定义为前置变量。为了消除随机扰动项对前置变量的影响,可以将这些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其自身的工具变量。滞后一期因变量亦同。而且,所有倾斜分布的变量都取其自然对数以使分布趋近正态。另外,为了消除固定效应vi的影响,可以对水平方程进行差分转换,得到(差分方程):

表1 变量列表
但是差分转换会损失掉一部分样本信息,所以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generalizedmethodofmoments,简称system-GMM)而非一阶差分广义矩(firstdifference-GMM)估计方法,将水平方程的信息作为补充,从而改善估计效率(Roodman,2009:86-136)。为了避免水平方程中使用的一阶差分工具变量受到固定效应的影响,而且一期滞后项可能与随机扰动项相关,再者工具变量数量要小于观测样本量,所以本文只在差分方程中采用变量的二期滞后作为工具变量*有关具体设置的解释,可见ElitzaMileva.“UsingArellano-BondDynamicPanelGMMEstimatorsinStata”,Workingpaper(2007),http://www.fordham.edu/economics/mcleod/Elitz-UsingArellano%E2%80%93BondGMMEstimators.pdf.。
三、 计量结果与讨论
从表2可以看到,滞后因变量和大部分解释变量的结果都是非常稳健的,而且在四个模型中的估算结果都是保持一致。从中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些重要发现。首先,人大经费拨款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上年预算拨款显著地影响着下一年度的拨款。这与现实一致,反映了地方人大在90年代以来的稳步发展。
其次,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原有三个假设都得到验证。经济发展推动地方政府加快制度化建设,也给地方人大发展带来了机遇。而经济增长潜力弱的地区,更倾向于在经济绩效之外寻求替代性的政绩。此时,对地方人大进行改革或者通过发展地方人大以促进地方制度创新,便可能为这些地方的官员带来更高的边际回报。而外资依赖性约束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人大的意愿。因为过多刚性的制度约束和来自新权力机构的制约可能会破坏地方官员所谓的投资环境,在制度建设上“逐底竞争”,更符合这些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逻辑。在总模型中,即便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三个解释变量的结果依然稳健。

表2 地方人大经费拨款的影响因素 (1994-2007)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符号“+”、“*” 、“**”、 “***”分别代表10%、5%、1%和0.1%的显著性水平;AR(1)和AR(2)检验表明差分误差在一阶以上不存在序列相关。
在行政理性模型中,征税能力假设得到验证。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对地方人大的发展有显著的负影响。征税能力弱的地区会积极促进立法,以便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扩大和巩固财源。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汲取能力较弱的地区为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而寻求制度建设。这一负面影响的存在也从侧面佐证了马骏(2011:26-27)的混合型财政国家理论。税收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未必会形成西方向财政国家转型那样的“无代表不纳税”压力,因为这些税收很多是来自于国有部门而非私人部分。如果考虑经济贡献而非税收贡献,那么私人部门的逐步壮大又是否会推动中国代议机关的发展呢?从统计结果看,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业贡献率对人大经费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这一指标本身只测量了工业领域,而不是整体经济结构的国有程度;而且除了国有和集体企业,还有大量的国有控股经济成分被这一指标列入市场化部分。不过,在总模型中,该变量的显著程度有所提升,而且显示了正面的影响。另外,劳动力市场化因素也间接测量了经济市场化程度,这一变量在总模型中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所以,如果能更准确和全面地测量市场化程度,应该可以看到其对人大机构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政权弹性模型中,户籍人口规模有着非常显著的负影响。这反映了流动人口因素对地方代议机构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在总模型中,户籍人口规模的统计显著性消失,很可能由于经济发达程度和工业的国有化程度挖空了这一因素的解释力,因为流动人口输入地往往是广东、上海等经济发达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不过,控制其他因素后,少数民族规模和劳动力市场化反而有显著的正影响。这表明少数民族自治因素会对地方人大发展带来积极推动力。
四、 结论
中国地方人大机构建设背后,同时存在经济增长、政治竞争、行政理性化和维持社会稳定等多重理性。因此人大机构发展也带有很强的工具性特征。从经济层面看,地方党政将人大机构作为立法工具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同时也担心人大制衡和过多制度性约束会破坏投资环境。从政治层面看,在经济绩效带来的边际回报递减的情况下,地方党政也可能将改革地方人大作为政绩来寻求晋升。从行政层面看,税收最大化是推动人大机构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由于国家对非国有经济力量的依赖性不强,所以并没有太强的意愿去与后者进行制度性的讨价还价。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发展地方人大机构也成为国家面对市场转型与社会变迁而进行自我调整与适应的重要机制。出于促进民族自治的考虑,中央领导人鼓励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人大向下负责,这一点也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响应。而90年代以来的劳动力市场化和大规模的地区间人口流动,也迫使地方加强代议机关的建设以增强回应性,进而改善治理能力。多重理性同时存在既导致各地人大的机构建设状况参差不齐,也约束了其功能的均衡发展。各地方党政往往各取所需,在最大化地方人大的立法功能的同时,最小化因人大监督所带来的制约,而对来自社会的压力也是有选择性地给予回应。
对于这种情况,中央也进退两难。一方面,如欧博文等学者所说,中央不希望人大系统过度集权而影响整体的分权安排(O’Brien & Luehrmann,1998:91-108),所以不会像其他改革那样采取直接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推动措施。另一方面,人大系统内部对于应该人大应该官僚化(bureaucratizing)还是亲民化(popularizing)也存在很大分歧(O’Brien & Li,1993/1994:20-31)。所以,那些得以快速发展的地方人大,靠的绝不仅仅是市场化和法制化所带来的契机,更多的是需要其领导人去积极嵌入地方政治权力结构和靠近权力中心(Xia,2000:185-214)。应当说,地方人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效仿了80年代全国人大的扩权经验,即争取政治嵌入性而非自主性来换取机构建设和影响力的提升(O’Brien,1994:80-107)。通过牺牲自主性和某些功能的缓慢发展,不少地方人大成功跻身原本拥挤的决策过程。在重大决策做出之时,地方人大至少“在场”而不至于被边缘化和象征化。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90年代以来中央的多次制度性调整,也都给地方人大的发展带来实质性推动。从制度化角度来看,中央的这些制度调整和地方的人大机构建设,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O’Brien,2009:131-141)。伴随着地方人大作为工具性机构得到增强的,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制度化、权力主体的结构性分化和决策过程的常规化(Burns,1999:586)。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越来越多的制度性约束。更重要的是,地方人大作为权力机构的崛起,也为民众和社会团体参与地方决策提供了新的舞台(Cho,2009:125)。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维权人士、国有企业领导、村委会干部、乡镇企业老板参与地方人大换届选举(He,2010:311-333)。这说明,地方人大的壮大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民众的政治生活。从这个角度看,地方人大机构发展绝不仅仅是一项行政性改革,更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乃至民主化进程的重要部分。因此,进一步加强人大机构建设和促进各项功能的均衡发展,便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参考文献:
[1]包瑞嘉(2004).中国的“温和威权主义”改革之路.二十一世纪(香港),6.
[2]马骏(2011).走向税收国家: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
[3]John P.Burn(1999).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50:National Political Reform,ChinaQuarterly,159.
[4]Young Nam Cho(2006).The 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Chinese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ChinaQuarterly,187.
[5]Young Nam Cho(2009).LocalPeople’sCongressesinChina:DevelopmentandTransitio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Baogang He& Stig Thøgersen(2010).Giving the People a Voice? Experiments with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in China.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19(66).
[7]Junzhi He(2010).Independent Candidates in China’s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A Typology.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19(64).
[8]Laura M.Luehrmann(1998).Institutionalizing Chinese Legislatures:Trade-Offs between Autonomy and Capacity.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23(1).
[9]Melanie Manion(2008).When Communist Party Candidates Can Lose,Who Wins? Assessing the Role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the Selection of Leaders in China.ChinaQuarterly,195.
[10] Andrew J.Nathan (2003).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ournalofDemocracy,14(1).
[11] Kevin J.O’Brien& Lianjiang Li(1993/1994).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 Question of ‘Deputy Quality’.ChinaInformation,8(3).
[12] Kevin J.O’Brien& Laura M.Luehrmann(1998).Institutionalizing Chinese Legislatures:Trade-Offs between Autonomy and Capacity.LegislativeStudiesQuarterly,23(1).
[13] Minxin Pei(1998).Is China Democratizing?ForeignAffairs,77(1).
[14] D.Roodman(2009).How to Do Xtabond2:An Introduction to Difference and System GMM in Stata.StataJournal,9(1).
[15] Dorothy Solinger(1999).ContestingCitizenshipinUrbanChina:PeasantMigrants,theState,andtheLogicoftheMarke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6] Ying Sun(2010).Constraining or Entrenching the Party-State? The Role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PRC China.HongKongLawJournal,40(3).
[17] Christine P.W.Wong(1991).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an Era of Fiscal Decline-the Paradox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Post-Mao China.ChinaQuarterly,128.
[18] Ming Xia(1997).Informational Efficiency,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stitutional Linkages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TheJournalofLegislativeStudies,3(3).
[19] Ming Xia(2000).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Power Players in Chinese Politics:A Network Explanation.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9(24).
[20] DaliYang(2004).RemakingtheChineseLeviathan:MarketTransitionandthePoliticsofGovernancein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地址:庄文嘉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Email:wjzhuangsysu@163.com。
■责任编辑:叶娟丽
◆
Determinants of Budgetary Provisions on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 Dynamic Panel Data Analysis of 1994-2007
ZhuangWenjia(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Since 1990s,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 have experienced an uneven development in both regional and functional dimensions.Without any radically political reform at the national level or substantial suppor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why did some local congresses successfully institutionalize themselves and even wield assertive influence on local decision-making,while the others failed to achieve either goals? Using a panel database ranging from 1994 to 2007,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budgetary provisions on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multi-rationalities of local authorities,including political,developmental,bureaucratic and social rationalities.Without strong top-down support from the central authority,local congresses had to make trade-offs between political autonomy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The logics of administrative instrumentalism and political embeddedness tightly shaped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local congresses.
Key words:Local People’s Congress; budgetary provisions; panel data; dynamic model; system-GMM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3000-31610136);中山大学青年教师起步资助计划(13000-3110140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青年项目(GD14YGL08)
DOI:10.14086/j.cnki.wujss.2015.0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