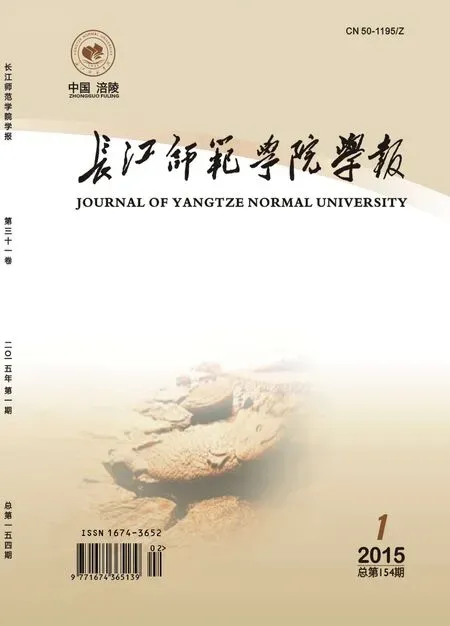罗家伦与文学革命
罗家伦与文学革命
冯夏根1,胡旭华2
(1.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31;2.广东药学院人文社科部,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在文学革命中,罗家伦以人本主义文学观为指导,对传统旧文学和文言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旧文学的特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文学的涵义及存在的危机和解决办法等诸多理论问题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并且积极地参与白话小说和新诗的创作,因此他不愧为文学革命的健将。
[关键词]罗家伦;文学革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5)01-0059-05
[收稿日期]2014-11-10
[作者简介]冯夏根,男,安徽安庆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胡旭华,女,湖南常德人,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学人的社会主义观”(14YJA710010)。
罗家伦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在推进“文学革命”的阵营中,也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可是,学界对此长期缺乏相应的研究。实际上,无论是从批判旧的文学观念,提倡白话文,还是从探索新文学理论、注重新文学创作等方面来看,罗家伦都不愧为“文学革命”中的一员健将。
一、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首先是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始的。1919年3月,曾留学英国的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在其《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一文中批驳白话文,主张文言文,认为“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其文认为白话文的提倡者把文字当成文学,主张“言文合一”,实在是不懂文学的概念。他说:“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而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非为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1]由于胡先骕此文出自所谓学贯中西的留洋教授之口,颇得守旧派的赞赏。见此情景,罗家伦奋起反击,发表了《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的长文,系统地阐发了白话文学的主张。
罗家伦指出,文学与文字不同。但文学应以语言为根据,文学随语言而变更,语言亦随文学而进化。文学革命的宗旨只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0字,即文学是要用国语来做的,才会成“真文学”;国语有了文学的性质以后才是“真国语”,并不是说“国语就是文学,文学就是国语”。因此,“文学的界说与语言的界说不同,所以文言合一的话是我们不承认的。”他指出,胡先骕强调的所谓结构、照应、点缀等只是文学的细枝末节,文学最重要的是要有“最好的思想”“感情”“想象”“体性”“普通”等特质,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并且只有用白话这种形式才能最好地表现出来。“因为我们人生日日所用的都是白话,我们日日所流露的所发生的种种感情,都是先从日用的白话里表现出来的。所以用白话来做文学,格外亲切,格外可以表现得出,批评得真。”相反,文言文模式僵化,形式单一,不能灵活地表现人类的情感和生活。因此,罗家伦强调:“我以为白话文是最能有想象、感情、体性,以表现和批评人生的,最能传布最好的思想而无阻碍的。”[2]在这里,罗家伦从文学与人生的紧密关系来阐述白话文必然代替文言文的必然性,这是一种进化的、历史主义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揭示了文学的时代性特点,当时是驳斥守旧派攻击白话文的有力武器。
白话文的“白”究竟是什么涵义?罗家伦指出,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国内有两种误解:其一,白话文学只是“引车卖浆”(平民百姓)的话,所以不屑道也。守旧派即持这种观点。其二,白话文学虽为“引车卖浆”的话,
但是为“通俗教育”起见,不妨一道。这种认识在赞成白话文学的人中也大量存在。对于第一种误解,他指出:其一,白话的“白”,是“说白”的“白”。既然“文人学士”的说白可以入文学,那么“引车卖浆”者的说白又何尝不可以入文学呢?只看文学家用的时候,各得其当好了。其二,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的本质必须洁白,决不是旧套的文言的质地,把几个“之乎者也”换成“的呢呵吗”就可以冒充的。其三,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也就是说,白话只须清楚地说过去,决不能堆砌晦涩的词句令人不懂。总之,“以白话文学来表现批评人生,传布各种思想,真可以无微不到”。针对第二种误解,罗家伦指出,“白话文学自有白话文学本身的价值,巨大的作用,……我们做白话文学,是要去做‘人的文学’,做人类知识的全部分的解放,断不为了他们所谓的‘通俗教育’才来如此。”[2]显然,在他看来,白话文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超越“文学革命”,使白话成为传播思想、解放思想的工具,成为完成和实现人的解放的工具,进而达到改造中国社会,带动整个中国文化形态发生变革的最高目标。应该说,这种认识道出了白话文运动的深远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白话能不能为诗?白话诗能不能胜过文言诗?这是当时守旧派等人最大的疑问。胡先骕认为诗尚典雅,而白话尚平实,所以白话不可以为诗。如果一定要用白话写诗,必然导致毫无诗意可言。对此,罗家伦指出诗的本质与文学一样,也是用来表现和批评人生的,只不过诗特别注重想象、情感和音韵。“无论什么诗,只是有思想能表现批评得(的)人生好,而有那几种特质,就是好诗。”因此,文言可以为诗,白话也可以为诗。既然“白话可以把人生表现批评得真切,而且声韵亦近自然;白话诗可以比文言诗好,亦无了疑义。”[3]虽然白话诗尚处在草创阶段,还不够完备,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白话不能作诗及白话诗永不及文言诗的结论。他还指出,西方近代新诗的特色有五:重精神而不重形式;用当代的语言;绝对的简单明了;绝对的诚实;音节出乎天籁。有了前三条,可以表现批评人生的格外亲切。而后两条则说明白话诗绝不是随随便便、信笔所致就能写出来的,而是要以高度的凝练和深切的人生体验为基础的。
此外,罗家伦还驳斥了胡先骕的白话不能运用艺术、白话容易变迁、不便保存古籍、白话是为了避难就易等攻击白话文的论点。他认为,白话里不但可以运用艺术,而且运用艺术的难度要高于文言文。白话文与保存古籍是两回事,文学是为人生而有的,不是为考古而有的。所谓白话是避难就易的论点,是完全不了解白话文的价值和意义的奇谈怪论。罗氏还指出,我们应当承认人生的价值,承认时代的价值。“我们在这个时代,就当做这个时代的人,说这个时代的话;何必想去做几百千年前的死人?”[2]
在反对白话文运动的人当中,林纡之流只会使用影射和漫骂的手段,于学理上则不值一驳。而以胡先骕、吴宓等为主的学衡派则是留学归来的,他们的学术素养远非那些守旧的封建保守派可比。驳倒胡先骕等人对白话文的质疑,对于推进白话文运动的顺利开展非常必要。因此,罗家伦对于胡文的驳斥在当时确有推进“文学革命”的意义。
自从“文学革命”发动以后,白话文言之争就成为新旧文学争论的焦点。因为语言作为文学的表现形式,对文学的内容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因为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们认识到了白话对于旧文学的内容具有巨大的冲击作用,他们才不顾守旧派的反对而大力提倡。“文学革命”的实践证明,从文学的文体变革再到文学内容的全面变革是五四新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提倡白话文决不仅限于文学史的意义,白话文不仅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还改进了中国人的语言思维方式,促进了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并引起了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这种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因此,罗家伦对白话文的大力提倡,对守旧派的奋力批驳,虽然从思想方法上来说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正是这种深刻的片面性为白话文迅速战胜文言文,为推进“文学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二、坚持人本主义的文学观
人本主义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潮之一。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把否定束缚人性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视为运动的重要目标,把人的解放视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观念。陈独秀倡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3]青年观,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4],胡适大力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5],周作人则提出人的文学,“从新要发见(现)‘人’,去‘辟人荒’”[6]等等,无一不是把人的解放置于最高的地位。这种思想潮流反映在文学领域便是以表现人的价值、尊严、个性和创造精神为内容、以人的生活为本位、肯定人在文学领域里的中心地位的人本主义文学观,并构成了“文学革命”的核心命题。这种文学观同样体现在罗家
伦对文学的认识中。
首先,罗家伦以人本主义立场对传统文学观进行了抨击。一般而言,中国传统文学观主要有两种:第一是文以载道、代圣人立言的文学观,它使文学成为封建制度的附属品,成为维护封建旧秩序、旧礼教的工具。第二是把文学当作游戏消遣工具的文学观,在五四时期集中体现在所谓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及一些黑幕小说中。对于这两种害人不浅的文学观,他都予以了抨击。他指出,国语文学的精神就是“人生化”的精神,所以“凡是‘非人’的,妨害人生的东西,都应当放在排斥之列。但是最没有人性,缚束人生最厉害的,就是旧文学了!”[7]他抨击中国旧文学大都“只是摆出道学先生的面孔,代圣人立言”,因而“是见人生而远避的”,是“供少数人的玩具的”[8]。所以,对于这种不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旧文学应当尽早摒弃。他还发表了《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抨击所谓黑幕派、滥调四六派和笔记派的游戏消遣的工具文学观。他指出,黑幕派小说的杜撰者是欺世骗钱,“莫不借了‘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招牌,来实行他们骗取金钱教人为恶的主义”;滥调四六派危害青年,应当予以取缔;笔记派毫无思想,应当加以改良。他认为小说的第一责任就是要改良社会,而且要写出“人类的天性”来,“把读者引上善路去”[9],这正是人本主义立场的体现。
其次,罗家伦以人本主义为指针,对中西文学进行了对比,深刻批评了中国旧文学脱离人性的弊病。他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洋文学注重表现和批评人生,重视人类普遍的思想与美感,而中国旧文学大都浮泛混沌,往往只讲字面上的雕琢,缺乏实际的内容;西洋文学“多半从主观而外,还能以客观的观察,唤起人类的同情”,而在中国旧文学中则限于个人的生活,不注重人类共同的感想;西洋文学家肯说老实话,事事能求其真;中国旧文学往往矫揉做作,远离真实的人生,“‘假’字真是中国文学的第一个特征”;西洋文学是极力发挥个人情绪,极有趣味的,是平民的,而中国旧文学则是“同古人一个鼻子眼出气的”,是代圣人立言的工具,是贵族的,只剩下了进博物馆的价值[8]。罗家伦对西洋文学的高度推崇和对中国旧文学的极度贬斥是以人的文学为标准,虽有一定的绝对化和片面化,但在替新文学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五四时期,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最后,罗家伦对人的文学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世界的进化,是从‘神的时代’,进到‘物的时代’;从‘物的时代’,进到‘人的时代’。”自19世纪末叶以后,“‘人’的潮流,所向披靡”,而中国“新文学的勃兴,乃是人生觉悟后应乎时势所万不能免的”,所以人的文学自然成为时代的主流。那么,什么是人的文学所说的“人”呢?他赞同周作人的观点:一方面,人具有与动物类似的本能和天性,这些天性应当予以满足,所以,“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另一方面,人又有高于动物本性的特点,人性应当不断地向真、善、美的境界发展,所以,“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这种对人的看法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和人性的优美崇高,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他接着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主要区别便在于著者的态度,即是以人的生活为是,还是以非人的生活为是这一点上。他还指出了提倡人的文学的思想意义,认为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是不可分的,“思想革命是文学革命的精神,文学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工具,二者都是去满足‘人的生活’的。”[7]因此,“文学革命”的最终目的在于以文学实现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这一切都必须以人的解放为先决条件,所以提倡人的文学是势所必然。
由此可见,在文学观上罗家伦深受五四时期人的解放观念的影响,自觉地、积极地倡导人的文学,表现了人本主义的思想立场。从五四时期历史发展的要求来说,其人本主义的文学观值得肯定。
三、大胆探索新文学理论
在“文学革命”中,对文学理论贡献最大的首推胡适和鲁迅两兄弟(即周树人、周作人,以下简称周氏兄弟)。胡适不仅倡导白话文的形式变革,而且发表了一系列对文学革新和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文章,为“文学革命”指明了方向。周氏兄弟则进一步丰富了新文学的内容和思想。鲁迅创作的小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理论都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学的创作。在新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罗家伦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第一,尝试界定文学概念。对于国人高谈“文学革命”,而对什么是文学却不甚明了的现象,其深感不满。他说:“中国人论事做事,只从枝叶上着想,永不从这件事的体用上着想,所以愈谈愈远,愈不中用。……我们倡文学革命的,就是要推翻这些积弊,从根本上还出一个究竟来。”[2]由于痛感我国自古以来所谓文学的含义模糊混乱,因而他对于“什么是文学”这个最基本的命题做了探讨。在对中西文学史上的文学家对文学的界定进行
了一番归纳和分析之后,他提出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他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集此众长,能使人类普遍心理,都觉得它是极明瞭,极有趣的东西”[8]。这一界定虽不够凝练和精确,但肯定了“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的本质,大体阐发了文学的内涵,抓住了文学的基本特征,相对于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模糊不清的文学概念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还应该看到,罗家伦对文学的这种趋向于人生化的认识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们的普遍认识。如周作人谈文学,最终也归结到“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6],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也提出要表现“平易”“抒情”“新鲜”“立诚”的社会生活[10]。可见,罗家伦对文学的界定反映了五四时期呼唤人、发现人的时代特色,具有极大的进步性。
第二,初步论述了中国旧文学的特质。文学既具有表现人类生活和社会变迁的时代性特征,又具有表现民族生命特质的民族性特征。罗家伦以文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为标准,以批判的眼光,将中国旧文学的特质归纳为五个方面。其一是充满了忧乱伤离的情绪。他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历代丧乱太多,以致影响文人的情绪所致。其二是颓废。虽然中国文学里也有一些慷慨激昂的作品,但颓废的成分太多,尤以汉魏六朝为最。颓废表现一种腐烂和朽蚀,所以是中国文学里的毒素。其三是形式主义。中国文人好讲形式,不讲内容,“于是其作品一变而为字面主义”。中国的诗、词、赋“工整是工整极了,却常常弄到有躯壳而无精神”,这是中国文学的重大缺陷。其四是山林主义。中国文人对自然只知一味地歌颂崇拜,“其最高的意境就是与自然相融合,为自然所吸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愿为自然之主宰”。其五是个人主义。中国文学往往只注重“陶冶个人的性灵,发抒个人的感情,表现一种‘林泉生活’的闲情逸志,绝少团体生活的兴趣”[11]。他指出,中国文学的这些特质,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起来,未尝没有独到之处,但从文学的时代性看起来,则表现出很多的缺陷。因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只有表现时代、表现人生、表现人类共同生活的文学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所以,对于中国旧文学的这些缺陷,应当尽力克服。
第三,阐述了新文学的创作理论。罗家伦指出,从内容上来说,国语文学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展开。消极的方面是破坏旧文学,抨击旧文学压抑人性、妨碍人生的一面,以便为新文学的建立开辟道路。积极的方面是建设新文学,提倡运用新材料,另辟蹊径,以建设适应人的生活的新文学。从形式上来说,要避免中国旧文学中形式主义、颓废主义、山林主义、个人主义及悲观主义的弊病。创作新文学,必须有高尚的理想和积极的态度,必须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必须以文学“增进大众的幸福,发扬人类的文化”[12]为己任。从时代性上来说,新文学的创作要抓住时代精神。没有时代精神的文学,就是没有生命和灵魂。对于古代的文学,不但不必模仿其形式,而且也不必模仿其内容。“我们生于现在的时代,就应该创造一种现在的文学”。从方法论上来说,新文学的创作者其一要扩大自己的经验;其二要研究外国的文学;其三要有科学的训练。经验不丰富,作品便枯燥、偏窄、拘泥。要创造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创造的人自己“看得多,听得多,经验得多,体会得多,取精用宏,才能有好的成就”。对于外国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应该大力研究和介绍。因为“不但外国文学中有许多作品可以供我们借鉴,供我们观摩,而且有许多方法供我们采取,许多词句供我们吸收。使我们看了,能得新的领悟,新的启示。”科学的训练更是必不可少。“我们生在科学的时代,我们的文学作品决没有不受科学陶镕而可以成功之理。”[11]这些论述对于新文学的创作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第四,指出了新文学存在的危机及解决的办法。就在国人为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和新文学运动顺利发展而欢欣鼓舞之际,罗家伦却清醒地看到了白话文学存在的危机。“这种危机不在乎旧派外来的攻击,而在乎自己本身的毛病。”其主要表现为:在新文学中处处受到中国旧思想的影响,形式主义严重。“现在新文学出品之中,思想精密,壁垒森严的固也不少。但是就大多数而论,其中轻佻、谩骂、武断、笼统、空泛、不合逻辑,……哪一点不是中国旧思想的流露,其所不同之处,不过是以文言的形式,换了白话的形式。”对于这种危机,若不加以指出批评,“其将来的流弊有不可言状者。”新文学的创作者在思想上缺乏科学精神的洗礼。“中国人好笼统的议论,而不好分析的研究,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唯其如此,所以容易犯轻信、武断和断章取义的毛病。他感慨道:“思想上不经一番精密科学的洗礼,而专以附和和强拉类似东方的思想自重,哪能盼望真正的新文学出现呢?”要解决这两大危机,除要抓紧介绍西洋的文明外,最要紧的就是要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人,“排除一切客气,保守气,把思想上清清白白地用科学方法洗刷一番。排除一切自来盘踞的东方思想,专门研究西洋的学问”[7]。应当承
认,在新文学初创时期,他能从中国人思维方式缺陷的高度指出新文学存在的危机,其认识确有独到之处。
虽然罗家伦对于新文学理论的探索总体看来还比较粗糙浅显,但就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而言,它毕竟构成了新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基础。在当时西方文学理论尚未大量引进,国人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消除传统旧文学的消极影响的历史背景下,其文学理论尝试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此外,罗家伦也积地极参与新文学的创作,他和傅斯年、俞平伯、叶绍钧、朱自清等《新潮》杂志同人堪称新文学创作的轻骑兵。在新诗创作方面,他认为:“余尝谓诗必有诗意、诗情、诗境三者乃成。盖无意则空,无情则死,无境则低,……至于韵脚,不过便歌咏耳!未可以前人之声带,缚今人之心灵也。”又说:“余于诗毫无所长,惟常求写景必真,写情不伪,虚构之词,无病之吟,窃非所取。”[13]他发表了《雪》《除夕入香山》《天安门前的冬夜》以及《往东车站送楚僧赴法》等新诗。其诗力求反映现实生活,用语平实,色彩冷峻,基调低沉,有的揭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如《雪》;有的揭示青年孤寂、忧郁的心灵,如《天安门前的冬夜》《除夕入香山》等,这在早期创作的新诗作品中具有一定的特色。他还发表了小说《是爱情还是痛苦》,通过描写一位大学生迫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戕害,不能与自己相爱的恋人结合,而被迫与一个自己不爱的女子生活在一起的人生悲剧,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摧残,张扬了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意识。
综上所述,在“文学革命”中,罗家伦以五四时代青年特有的激情,热情洋溢地投入到新文学的宣传、阐释和创作之中。他以人本主义的文学观为指导,对传统旧文学和文言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树起了新文学的鲜明旗帜;他对新文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都进行了大胆的、初步的探讨,为新文学理论的发展及完善铺就了道路;他积极地参与新文学的创作,其白话小说和新诗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中也颇具特色。其对新文学的贡献,黄季陆认为:“罗家伦先生是五四时代文学改革运动的健将,是新文艺的创导人,也是新思想的启迪者”。林语堂也评价说:“罗家伦先生是我国新潮时代文学革命的两位佼佼者之一”“是中国新思想的领袖,对推展中国新文学,有很大的功劳,在中国文学革命上,他是一位青年斗士”[14]。这些评价虽有过誉的成分,但的确也真实地反映出罗家伦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上)[J].东方杂志,1919(3).
[2]罗家伦.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J].新潮,1919(5).
[3]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
[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5]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18(3).
[6]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1918(3).
[7]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J].新潮,1920(5).
[8]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J].新潮,1919(2).
[9]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J].新潮,1919(1).
[10]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7(2).
[11]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民族与语言文字[M]//罗家伦文存(第2册).[中国台湾]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6:275-281.
[12]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文学的维护与培养[M]//罗家伦文存(补编).[中国台湾]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17-21.
[13]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西北行吟》自序[M]//罗家伦文存(第10册).[中国台湾]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235.
[14]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学术界同声哀悼[M]//罗家伦文存(第12册).[中国台湾]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584.
[责任编辑:黄志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