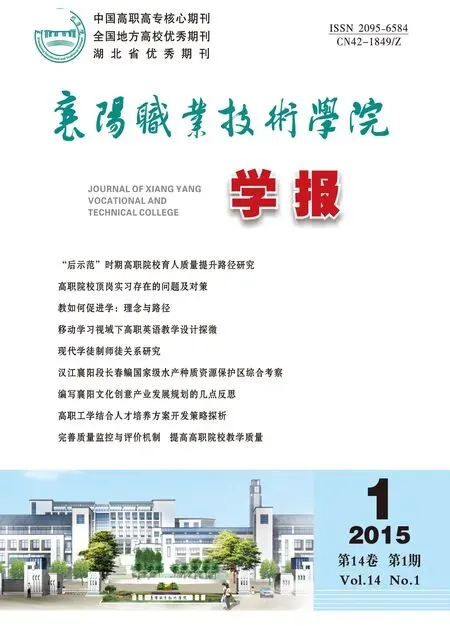论汉画像的喜剧性精神
陈效毅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6)
“河出图,洛出书”,中国文化自古就有重视图画的传统,汉字本身就是抽象化的图像。就汉代文化而言,既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史典籍,还有着广阔无比的汉画像石和汉画像砖的记载,历代史书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故事,但汉画像记载的不仅有胡汉战争国家大事,还有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展现出了汉代人恢宏大气的审美想象空间和文化内蕴。可以说,对于现世生活的喜爱,是汉画像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一,而展现出的是汉代人集体无意识的喜剧性心理。
楚文化中的巫色彩,奇幻瑰丽的想象和浪漫情怀与汉代天人同构的思想相结合,大一统的儒家礼乐宗法文化在审美的角度上和浪漫奇幻的巫文化相结合,体现出的正是不同于后代的汉文化。在汉画像这种图像记录的历史画卷中,用象征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天人合一、天人相谐的文化内蕴为基础,表现了人们追求成仙的思想,展示出的是楚人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一种直面生活苦难、直面死亡恐惧的乐观精神。在汉代棺椁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宇宙观,是以现世人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所以,生活的描写与记录,必然也就成为了汉画像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而对于如何表现汉代人当时的生活内容,记录下彼时彼刻,则有着丰富多样的形式。无论是对于死后世界的描摹,还是对于宴饮庖厨的记录,亦或是刻画了男女之间亲密的秘戏图,都反映出了汉代人生活的场景。固然汉画像是死亡的艺术,它所服务的对象与丧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这也恰恰证明了人们面对死亡时的心情,因为对现世生活的喜爱,对生离死别的痛苦,所以才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祭奠故人,缅怀曾经,抚慰生者的心灵。汉代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下,必然有着时代的烙印,黄老道家、儒家以及佛教思想无疑是在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每种思想展现在汉画像中,都是可以看出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喜剧性心理和对现世生活的喜爱之情。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后,百废待兴。汉初的统治者接受秦朝灭亡的教训,采用黄老道家的思想治理国家,道家的审美观念也便体现在了艺术创作中。道家思想对汉画像的影响已有很多论说,不必再次重复,需要探讨的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下体现出的汉代人积极进取的心理和喜剧精神。最为明显体现出的是汉画像中的仙人世界。先秦黄老、老庄思想中已经参杂了阴阳五行、神仙方术,汉代人的生死观,也便有了很大的改变。道家有摄生、养生,最后达到长生乃至升仙不死的美好结局。传说中操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住在昆仑山上,曾与人间之王周穆王宴饮唱和;后羿的妻子嫦娥也曾有盗服长生之药的故事。汉代人的思维体系中,仙人就是超越时空保留肉身永存的人。仙字,拆解开来就是人在山中。可以看得出,道家纵然讲究顺应天道,与天相谐,但面对生死之时,却可以充分利用“道”的规律,求得生命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颇有人定胜天的思维。固然长生也是要遵守天道,顺应天时才能养生,但是生命长度的改变本就是对于命的修正,对于上天既定时间的改变。从中可以体会出汉代人对生的眷顾。当然,面对死亡,每个人都是恐惧的,但中国人之所以能够积极地追求长生不死,有养生的传统,有着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可以说和道家思想是有着关联的。[2]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黄老道家不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在民间的影响依然是很大的。它与鬼神迷信进一步的结合,至东汉道教产生,创造了丰富的神话世界,反映在汉画像中,与儒家礼乐宗法文明相融合,展现出的是更多的人的色彩,其思想中心不似西方宗教,以上帝为中心。它以现世人为服务的中心,炼丹、采耳,以及在汉画像中大量的西王母东王公的形象,都是对活着的人的精神慰藉。就汉画像中的秘戏图而言,除了有着表现汉代人日常生活的热爱之情,是否可以看作是道家房中术修炼的一种表现呢?固然未必有着准确的答案,但现实生活的内容题材,世俗化的转化,让人们看到了汉代人面对死亡时所抱有的积极精神。而在汉画像中对于死后世界的描摹,对于升仙不死的向往,都是当时人们内心喜剧性结局的表达。女娲伏羲交尾图(见图1)有着生殖崇拜的象征意义,寓意着天地万物阴阳交感,化育万物,繁衍子孙,生生不已。这样对于生命美好的渴求,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但刻画在石头上,埋葬在洞穴中,以生的希望掩埋死的痛楚,这正是人们利用想象的虚幻世界来给死亡这样一个悲痛故事的喜剧性结局。汉画像中有很多表现现实生活的,宴饮庖厨、豪华宫殿、锦衣玉食以及人们的天伦之乐,这些是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但这些想象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热爱人生,享受生活,这些就是美的,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展现,汉代人将对死后彼岸世界的忧愁转化为了对此岸世界的留恋,都是在用美好的喜剧性结局来遮蔽死亡悲剧性的结果。道教中的很多神仙也都是人的形象,这就直接体现了这一点。汉代人广阔的心胸,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法天象地的思维模式,都给了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现世世俗功利的环境。也许是汉代人对于世俗的喜爱而改造了道家思想,成为了为人服务的道教,亦或是因为道家哲学思想体系给了汉代人积极乐观的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汉画像中,道家思维所展现出的汉代人积极乐观的喜剧性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图1 伏羲女娲交尾图
儒家思想在汉代追求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在董仲舒改造儒学后被汉武帝尊为汉代国家的指导思想,独尊儒术成了后世的主题,这自然会表现在汉画像中,就其中儒家观念所体现出的进取精神与喜剧性的审美心理,是所要讨论的重点。儒家以礼治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哲学在艺术表现上就是主题的选择和刻画。武梁祠中的鲁义姑姊、秋胡戏妻、荆轲刺秦王等,展现的是儒家道德的忠孝节义的思想。孔子在听《韶》时,有着尽善尽美的标准,可见作为儒家审美而言,美善是不一样的,只有美的形式没有善的内容是不行的。所以汉画像中的这些儒家礼义故事,不能仅仅就其艺术表现来评价其艺术价值,所反映的思想道德内容,也是十分重要的。《无盐丑女钟离春》的故事更是直接地传达了这一标准。当然,作为汉画像的表现内容,还有很多英雄故事。胡汉战争,传达的主题却是人们对国家的忠贞,对外来侵略者的痛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精神目标的达成,本身就是一种完满的喜剧性结局,主人公以身殉道,以达到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目的。[3]这种积极追求的心态,通过艺术化的形式体现出来,彰显出汉代人广阔的胸襟和包容宇宙的精神风貌。汉画像中有一副《孔子见老子》图(见图2),儒家是讲究尊师重道的,但这幅图,一者有着儒家伦理的象征,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否也可以看出是作为汉代国家指导思想的传承延续呢?道家哲学是更加深沉更具哲理性的学说体系,儒家哲学可以说是对其一种阐释,但学术的传承,与人生生命的轮回,也是有着生生不息的寓意的。汉画像是死亡的艺术,但是在生命的终结点,用这样一种形式来继续承载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是对生命的礼赞,在死气沉沉的墓穴中灌注了勃勃生机。天人同形同构的哲学体系,法天象地的艺术创作理念,让人感受到的是汉代人磅礴大气、包容宇内的精神气度,上至神仙世界,下至地府幽冥,也无不是遵从着人世间的礼仪规范和等级制度。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但汉代人用艺术的表现方式来规定了世间万物的秩序。人们想象的虚幻世界,以人世间的一切为基础,就算是神灵有着动物的头,也是要有着人的身体,人是其他生灵进化的最终形态。人世间的社会秩序,是和天相应的,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而身为天子的皇帝也是对应着天空中的紫薇星。汉代人对于生活的向往,对于宇宙的自信,也在汉画像中一展无遗。汉代昂扬向上的精神、积极进取的心态,反映在了儒家哲学上,通过汉画像这样一种图象的艺术表现出来,是让人可以充分感受到的。天地人三才,人居其一,这种自信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精神状态,必然也是由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喜剧精神所带来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给每个人所带来的这种自信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面对死亡时,死后的世界,依然是人们能够去预料的,是人们所熟悉的,灵魂最终的归宿是和现实世界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似性的,为人们所掌握的,这样一种内心安慰,遮蔽起死亡带给人的恐惧阴影。人们因未知而恐惧,有了认知,面对死亡时,也就不再那么恐惧了。所以在汉画像中,以如此的表现方式,体现出了汉民族坚韧、旷达的乐观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图2 孔子见老子图
儒释道三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塑造是根深蒂固的。佛教早在汉代时便传入了中国,作为宗教,对汉代人的生死观,必然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佛教期许世人的生死轮回,给了普通人生的希望,这在汉画像中是能看的出的。但任何外来文化的进入,无疑都是要被中华文化改造后才能被接受,佛教也是如此,从观音菩萨形象的演变就能看出。佛教教义本身也是在中国本土生成了很多宗派,如华严宗、禅宗等。以佛教中的莲花形象为例,在汉画像中有很多的莲花纹,这些展现出了汉代人对于宇宙的一种认识,徐州地区也出土过鱼戏莲花纹的画像石,整个世界是一朵莲花,四周的鱼儿可以看出是水。[1]当然,这和实际情况相比,虽然是不正确的,但有着合理的相似度。鱼作为生殖的象征之一,在死亡的墓地中,定然是表达了对生命的渴望,但这其中寄寓着的是乐观的心态,抚慰着伤痛的人们。在汉画像中,出土过半身菩萨像,可以看出的是,佛,作为一种通彻宇宙天地不为人世红尘所困扰的这样一种存在,成为了中国人观念中的神仙。佛教的众多内容是中国传统信仰结合在一起,汉化的过程虽然复杂,但汉代人改造世界的决心是能看得出来的。佛教更重要的意义应该是在于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面貌以及对死后彼岸世界的归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减少了对于未知的恐惧和对现世生活的痛苦感受,它不仅安慰了对于人类死亡的困境心态,也给了生者活下去以祈求美好未来的希望。这无疑是符合中国人喜剧性心理的。就像后世《窦娥冤》中描绘的那样,生前受人冤杀,死后也有美好的结局,沉冤得雪。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应该可以说是因果的思想。这种因果循环理论,给了中国人美好未来的期盼,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需求,所以,窦娥才会有最后的喜剧,而人的生命也是由因果所确定。这种喜剧性的心理模式,让人不由得摆脱了悲剧的命运,获得了审美上的自由。
汉画像中有着大量的升仙图、宴饮庖厨图、乐舞百戏图和狩猎图,这些都是最直接地展现出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是艺术创作生活化的体现。汉画像艺术之所以有着大量生活化的展现,可以说和中国人民族心理的喜剧性有关。中西方艺术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在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审美心理。中国人是喜欢喜剧的,即使是悲苦的故事,也一定是要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即使是沉冤不得报,最后也要有一个神奇般的结局来了结一切恩怨。如果说悲剧有着净化的作用,那么喜剧则是成年人的童话。西方文化喜欢悲剧,因为悲剧的净化作用,时刻提醒人们悲苦的生活,宣泄内心不健康的心理情绪,使得审美情感得到净化,审美体验获得“医药”的效果。宗教,恩格斯说它是人们心灵的鸦片,寄托人们内心的苦难,而艺术则是通过形象化的创造,时刻提醒着沉湎于宗教中的人们,生活中的悲苦依然存在,可以说是有情皆孽,无人不冤。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早在上古时代就已逐渐地完成了去魅的过程,《易经》的传承,就可以看到,它将西方人眼中的上帝褪去了人格化的外衣,形成了我们中华文明中那个至高至上的“道”。道就是如来,就是上帝,是那个来了也没来,无所不在的上帝。在这样的文化审美下,人们对于生活中的苦难便在集体无意识中获得了依靠自我力量顺应天道的思想,中国人不需要用悲剧这种艺术来时刻提醒自己生活中的危险,他需要的是自我的救赎,是人文伦理上的升华,所以喜剧也就在这样一个民族中获得了更高的地位,整个民族的心理也是喜剧性的。正所谓苦难辉煌,成就中国梦的是人民自己的勤劳勇敢,即使是文化中的算命看相测算风水,这其中也包含了无比伟大的天文星象学,有着复杂深刻的道理和数学建构模型,比起神学来说,更加具有科学性。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有求仙的传统了,他不同于神,仙是以肉体之身存留于世间的自由的人。中国人是全世界唯一讲求长寿的,房中术、炼丹术等,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喜爱。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是从死的一面来看世间红尘,中国和希腊文明是从生的一面看待,但是中国人更加积极追求长生,追求永恒的快乐,这样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体现在审美上,便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喜剧精神。在西方艺术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延宕的哈姆雷特王子,他们有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这样的悲剧大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诗学》主要论述的也是悲剧的伟大意义,(他对于喜剧的论述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从《诗学》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他对于悲剧至高无上的艺术地位的阐述。可见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在这一点上,是有着根本的不同。
所以,在面对死亡时,汉代人如何克服这样一种悲剧的情怀,也便成了其艺术创作的重要命题。[1]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过:“人若纯然是天使,就不会恐惧死亡;如果人纯然是动物,就不懂得死亡。但人既非天使又非动物,天地万物之间,人与其他生命不同,人即是生理性的肉体,有拥有自我意识,因文化而生成符号性的自我,因而命中注定要直面死亡,恐惧死亡。有了自我意识,人的存在困境和悖论本性就尖锐地凸显出来,一方面人是君临万物的灵长,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是文化体系的符号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人最终是被造物,是必有一死的高等动物。如此彻底的二元性分裂,是人独有的荒诞命运,人拼命利用种种文化规范和关系,去营造某种神化工程,以求出类拔萃,力争不朽。这种人类内心的困顿,展现在艺术创作上,汉画像的喜剧性展现和对生活的描摹,也就是理所应当、顺其自然了。
在获得了这种心灵上的安慰后,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才能将自身的审美情感倾入其中,获得审美自由。在汉画像艺术创作过程中,汉代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各种文化所呈现出的审美因素,也是无不带有喜剧性的心理,传达出的是生活中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情怀。
[1]朱存明.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