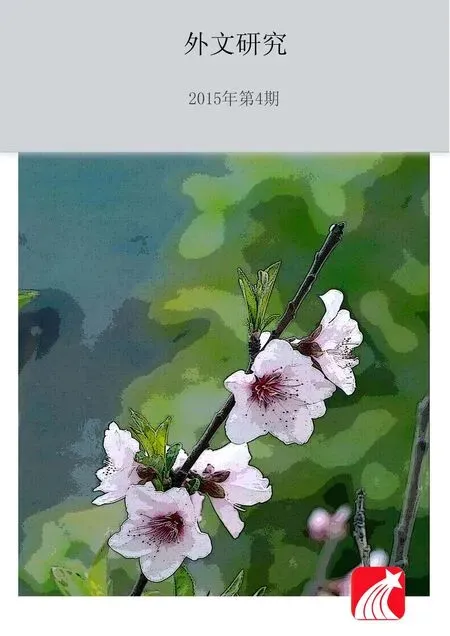布伊尔新著《“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述评
南京农业大学 丁夏林
布伊尔新著《“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述评
南京农业大学 丁夏林
自从“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一说法1868年诞生以来,美国涌现出了一大批小说家,为世人所瞩目。在劳伦斯·布伊尔的笔下,这些题材繁复、风格各异的作品都是“伟大的美国小说”主题的一个个变奏曲。他论述了老故事的重述如何成就了经典,以及“美国梦”的沉浮如何与美国的南北种族分歧一样造就了像马克·吐温、福克纳和莫里森那些巨匠的伟业。此外,虽然包括德里罗、品钦在内的悲观主义者在书写着美国的社区如何变得“不可能”,这一切都同样见证了“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为何生生不息。
劳伦斯·布伊尔;伟大的美国小说;美国梦;南北种族分歧;社区的解体
一、 导言
2014年2月,美国哈佛大学的贝尔科纳普出版社推出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新著《“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TheDreamoftheGreatAmericanNovel)。布伊尔是哈佛大学英文系资深教授,可谓博学多才、著作等身。这位艾默生及超验主义研究专家最近十几年来撰写了多本关于环境及生态保护方面的学术专著,如《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与美国文化的形成》(TheEnvironmentalImagination:Thoreau,NatureWritingandtheFormationofAmericanCulture)、《为危机重重的世界而写作:美国及境外的文学、文化与环境》(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inUSandBeyond)、《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TheFutureofEnvironmentalCriticism:EnvironmentalCrisisandLiteraryImagination)等,为生态文学批评注入了活力。而新鲜出炉的该书学术视野宏阔、论述精深,集学术专著与“美国小说史”于一身,为“十年磨一剑”之作,引发了无限阅读快感,给许多美国研究学者、美国文学专家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带来了一顿美味的文化大餐。
二、内容述评
除前言和尾声外,全书包括5大部分,共计13章。在“前言”中,他梳理了“伟大的美国小说”(Great American Novel)之概念的来龙去脉,对全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单介绍,并试图将专业术语降低至最大限度,以便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它并不是一本关于几本美国小说的独立论文集;它关乎如何想象这些小说在更广大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公共政策语境中形成,而即便后来者重新定义它们,离开它们的话这些“独特”的成就无法取得,也无法理解。这些语境不局限于美国内部,而延伸至全世界,因为作为“国族想象”(national imaginary)的载体及定义者,它们总是在与他人(非美国人)的对话中获得能量。关于该概念具有多大的“美国性”,他认为,除了对文化合法性的焦虑以外,它起码有4个因素。其一,超大的地盘;其二,美国宪法内含的模糊性,即关于地方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关系问题;其三,个人主义的影响,即国家的故事主要在于有代表性的个人故事,尤其是必须与各种社会限制做斗争的个人的故事;其四,从“美国革命”以来所继承的关于美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共和国民主制度的试验,总是在试图兑现其《独立宣言》中的承诺。至于为什么现在仍然热衷于讨论它?作者认为,一方面,如今的文学批评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都不能够从一个国家的内部去理解。另一方面,在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盛行之时,美国的凝聚力却正江河日下。吊诡的是,正当“美国世纪”渐行渐远,美国甚至存在分崩离析的危险之时,人们却更热衷于讨论它,因为争吵不休的美国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开始引发该梦想的驱动力之一。正如美国学者科希(Adam Kirsh)所言,“也许这些书的内驱力,以及驱使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他们的动力,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的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情怀,而它不断地被现实所粉碎”。*A.Kirsh.2015.Why are we obsessed with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N].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01-18.
在第一章“诞生、盛行及貌似的衰退”中,作者指出,“伟大的美国小说”出自美国小说家福莱斯特(John W.de Forest)之手。他在1868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呼吁通过描述“美国经历的普通情感及行为”,在一幅容纳国家生活的全部地区和文化范围的画卷中捕捉“美国灵魂”,并取得欧洲文学巨匠萨克雷、特鲁姆普和巴尔扎克的气势。其实,对这样的作品的召唤起源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但关于什么能够构成“国家小说”(national novel)还是众说纷纭。就像《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接受史所证明,内战前夕交通和通信的高度发达反而造成了“想象社区”式的国家的分裂。该文章在美学上也是一个风向标,因为1850年之前不到5%的美国小说被称为“小说”(novel),更常用的名称为“故事”(tale)。虽然引起了许多怀疑,但是这个美梦已经成为美国文学报道的口头禅。1860至1920年间,人们热衷谈论何种小说可以贴上这个标签,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它是一次性事件,还是几个事件(复数)?局限于某一个地区及某个地方的作品够格吗?必须限于美国问题或者美国场景吗?必须是客观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吗?必须指望作者来自某个特殊背景吗?对其性别、族裔甚至国籍有什么规定?这些问题都没有定论,因为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美国》三部曲(USA:The42ndParallel, 1919,TheBigMoney)和斯泰恩(Gertrude Stein)的《美国人的成长》(TheMakingofAmericans)都没有达标。连声誉卓著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直至20世纪70年代都一直受到冷落,被认为与社会学而不是文学有关,其粗糙美学及种族画像被沦为笑柄。
在第二章中,布伊尔讲述了该梦如何浴火重生。例如,20世纪30至60年代初期,共有7位美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5位为小说家。20世纪中叶之前,美国文学评论的职业化使霍桑、梅尔维尔、马可·吐温、亨利·詹姆斯、海明威及福克纳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而《美国文艺复兴》的作者麦西逊(F.O.Matthiessen)将20世纪中期的美国文学复兴归功于5位文学巨匠:艾默生、梭罗、霍桑、 梅尔维尔和惠特曼。网络上关于他们及其作品的讨论证明对于21世纪的读者和作者来说,该梦想仍是饶有兴趣的话题。布伊尔寄希望予厄普代克和莫里森,认为虽然其作品(如《兔子四部曲》和《爱女》)的风格迥异,所想象的国家以及作者与美国中产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都不同,但他们都是有力的竞争者,说明该概念的涵盖面很广。在这些作品中,家庭成为演绎“被压抑之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的场所,而小女儿被亲生母亲杀害的创伤记忆在主题关注和叙事策略方面可谓一箭双雕。当然,将两部小说进行横向比较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可运用的叙事策略很多,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将某一部小说视为该梦想的备选必然需要考察许多叙事模式,即将“国家性”(nationness)浓缩于文学文本中的比喻和窍门不胜枚举,因而单独讨论某个文本的意义不大。
第三章“半推半就的杰作:霍桑《红字》的沉浮”论证了为什么《红字》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如此独特的地位。它使作者名声鹊起,并永远红得发紫,成为詹姆斯之前欧美文学评论界公认的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家。自1985年以来,它在3大洲催生了4本小说、4个剧本、3个歌剧、2个音乐剧、3部电影及2个舞蹈剧。至今,红色的“A”字继续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母题,影响了对性工作者及性罪犯的脸谱化刻画以及右翼人士对避孕的反应,甚至成为2012年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拉姆尼(Mitt Romney)倡导的健康保险法的代名词。其实,该小说是对个人自我实现与社区稳定之间的张力的一次透视,通过19世纪的视角查看17世纪的清教伦理观,并以“欧洲-大西洋”之离散视角影响了一大批欧美小说的创作。其中包括英国作家艾略特的《亚当·贝德》和马可·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它与续篇的纽带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可被视为一个标杆。
接下来的3章构成该书的第三部分,名叫“美国的希冀”。其中第四章扫描了从富兰克林到文学现代主义的开端的各种“成功”故事。原来,小说是欧洲的发明,乃17世纪晚期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物。席勒1794年出版的《审美教育书简》就谈到一个完全成熟的文化应当体现于充分实现的个人生活故事中。接下来便出现“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雏形。而美国的《富兰克林的自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讲述了一个普通印刷厂学徒工如何通过智慧、能力、魅力成为一个富裕商人、博学者、政治家及外交家。当然,这个神话既成为样板,又成为靶子,因为像豪威尔斯的《塞拉斯·提珀拉姆的发迹》中的主人公在事业失败后其道德水准才上升,而伦敦的《马丁·伊登》中的主人公事业成功后反而投海自杀。相反,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成长小说渐渐兴旺,如詹姆斯的《贵妇人画像》和凯瑟的《云雀之歌》。当然,对成长与财富的关联描绘得最透彻和最系统的要算沃顿的《乡土风俗》了。其对“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之脚本的重述为后人(如德莱赛、菲茨杰拉德、福克纳、贝娄及罗斯)指明了方向。
在第五章“迟到的上升期”中,他发现1925年是美国小说的丰收年。这一年涌现了《教授的房子》、《阿罗思密斯》及《曼哈顿中转站》等佳作,但最著名的当推《美国悲剧》和《了不起的盖茨比》。至此,一个年轻男子从卑微无名到社会巅峰的奋斗过程最终得到经典式呈现。它们都描写一个一字不识的中西部白人男孩向往东部的高雅休闲生活,却被富有、漂亮但可望不可及、浅薄的年轻女子所欺骗,与其说享受往上爬还不如说是获取美学陶醉的过程。其奋斗目标都来自大众媒体。就影响而言,《了不起的盖茨比》大大超过《美国悲剧》,但德莱赛对“族裔现代主义”(ethnic modernism)的贡献更大,因为怀特的《土生子》几乎复制了成长性挣扎叙事与示范性少数派经历相匹配的叙事模式。如果说《土生子》那种自然主义色彩浓厚的现实主义强化了30年代特有的社会讽刺效果和心理刻画强度,那么贝娄的《奥吉的冒险》则重新发明了自然主义,使通常只是民俗学凝视的对象的故事人物成为它的叙述者,并拥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探究精神。其结果是一种狂欢式的杂糅。它与另外一部非裔小说《看不见的人》存在异曲同工之妙。
在下面的“连字符的美国中的成长叙事”一章中,他阐述了为什么《看不见的人》对“伟大的美国小说”发起了冲击。在此,我们必须提到历史背景和国际政治语境,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及日本的基础设施受到重创。它们的文化影响力也衰败不堪,而美国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美国英语、美国电影、美国音乐、美国快餐及美国书籍一下子称霸世界。《看不见的人》正好出版于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将学校种族隔离政策判为违宪的年份。其主人公的匿名暗示其无限的可塑性及默默无闻的地位。虽然他既聪明又雄心勃勃,但却被一个个挫折及诱惑击败。就叙事层面而言,它偏离了先前非裔小说的“社会学方法”(the sociological approach),呈现爵士乐演奏特有的即兴式变化,使思想和情感得以充分宣泄。其语言从正式转到口语化,再转到正式文体。这与怀特和菲茨杰拉德那种内敛叙事风格相去甚远。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揭露了作为“人类和社会可能性”的象征的“黑人”(the Negro)其实受到的“制度化的非人待遇”暴露了美国“民主大蓝图”的缺陷。尽管与《哈克菲历险记》不同,但两本小说都揭露了“文明”的弱点。不过《看不见的人》在亚马逊网站上得分相当高——4.3分,其对带连字符的美国性(即对黑人性与美国人之间的博弈)的探讨最为深刻。同样,罗斯的“美国三部曲”(《美国牧歌》、《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及《人性的污秽》)都以美国梦的是是非非为主题,说明美国小说的族裔转向(the ethnic turn)初露端倪。
第四部分由4个章节构成,名叫“关于分歧的罗曼史”。其阐释对象为《汤姆叔叔的小屋》、《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押沙龙,押沙龙!》、《飘》及《爱女》等。美国的文化分歧主要包括地区性、种族性或族裔性,涉及旧世界与新世界、东部与西部、北方与南方、白人与红种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等。作为北方的评论家,斯托夫人对南方奴隶制的抨击以及对非裔美国人的同情式描绘难免受到当时白人废奴主义者头脑中关于种族的偏见及无知的影响,而作为南方白人的福克纳和作为白种人和“前南方人”(ex-southerner)的吐温既想摆脱地区性文化记忆的牵引,又得承认其影响,但他们对肤色的理解程度各不相同。莫里森作为非裔北方人,对在南北方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文化来说是个局外人,但她明白白人是其主要的国内读者群。由于上述作家的叙事声音庞杂又交叉,所以国族想象的不确定性在于如何在不牺牲某些人群的完整性的情况下将这些地区或人群熔铸成一个声音。
在第七章中,作为“改变了世界”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道出了各种下层人物的心声,如工人、俄罗斯农奴及被大国奴役的非西方人。该作品不仅直面当时最烫手的道德及政治困境,而且囊括比其他小说更多的区域,从东北部、中西部、南部至西南边境。其叙述者试图在大部分南方白人认为非白人不是“人”的情况下满怀同情地理解他们,并在家庭与工作场所分离的情况下试图以女人的视角理解男人的世界。此外,它还从作者的中产阶级立场试图理解社会阶梯两端的情况,并与非新教福音派进行诚恳的对话。
在第八章中,他论述为什么《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超过《汤姆叔叔的小屋》,成为“全世界通行的大学教材”。前者的节奏更明快,种族化习语更明显,少了豪华修辞和神学超自然主义,代之以滑稽和怪异,描述了更广泛的难忘人物。作者对密西西比流域及其河边小镇了如指掌,而且一反一个世纪以来由一个斯文的叙述者主导的叙事路径,让一个乡巴佬的儿子发出自己“本土”的声音。哈克成为美国文学中最难忘的叙述者,吐温被称为喜剧讽刺大师。吐温的书被门肯(H.L.Mencken)称为这些州已经见到的最伟大的想象性作品,海明威也声称所有的现代美国文学都来自《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Buell 2014: 261)
第九章名叫“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米歇尔的《飘》与南北方的文学跨种族主义”。虽然福克纳是 “文学怪客”,但他的巨人地位不可动摇。以其为代表人物的南方文艺复兴表明南方的“农业性”(agrarian)与北方的工业性不同,表明美国“将永远是一个白人的国家”。内战后美国北方工业和技术的勃兴、“对西部的征服”、美西战争及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使联邦与地方各州的关系发生急剧变化,而《押沙龙,押沙龙!》在男性自恋主义面纱下揭示了跨种族的相互共存性,但白人家庭、白人社区及其是否可以维持本身的纯洁性仍旧是一个问号。比较而言,《飘》的篇幅更长、更厚重,但其魅力主要归功于电影改编。若说前者将旧秩序的神话戏剧化,那么后者则满足于沉醉于过去的替代性快感。
下面一章将《爱女》视为一个高峰及预兆,并认为其最可能成为当之无愧的“伟大的美国小说”。故事发生在1873至1874年,以主人公赛思的创伤记忆为轴心揭露奴隶制的罪恶。该书对先前美国小说的借鉴很多,旨在挖掘被湮没的历史真相,通过人物或者社区与其物质环境的互动,重新描绘关于北方与南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分歧的罗曼史。虽然她旨在“教育黑人”,但其读者群大大超出预期,成为了畅销书作家。故事的伦理主线很清晰:赛思和前奴隶们必须忘记历史才能生存,而可悲的是,到了故事的末尾,整个社区都忘记了她,连3个主要人物也都忘记了历史。
全书的最后一部分为“不可居住的社区”,主要探讨了《白鲸》、《美国》、《愤怒的葡萄》及《万有引力之虹》。其共同点在于美国民主在危机中如何运行。为了了解美国民主为何失败,我们必须看看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国的民主》和库伯(J.F.Cooper)的《美国民主》。后者发现美国的《独立宣言》不成立,因为人不是生来平等的,而托克维尔也担心“民主的暴政”(the tyranny of democracy)。可是,他更伟大的发现是“民众的顺从”(mass acquiescence),即当一般人的生活条件改善后,个人就迷失于“民众”之中,将权利交给民选代表,使商业寡头与一般工人的距离不断增大。这些现象在上述文本中充分显露。
在第十一章“《白鲸》:从默默无闻到‘伟大的美国小说’”中,作者展示该小说如何催生了一个工业。其规模相当于内战前美国的捕鲸业,渗透至大众文化的每个毛孔。它的内容庞杂,其中心是一个“搜寻—摧毁”(search and destroy)的使命,不仅描述美国如日中天的捕鲸业,对宇宙的终极意义进行形而上学式探究,而且对哲学系统或世界宗教的相对益处进行质问,夹杂着对跨物种的生态关系、美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寓言以及全球人类危机的深层次思考。它对既有合法性但没有实现普世性的人权既抱有希望又充满讽刺的态度说明,人们在继续做“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因为做这个梦表示“最好的还在后头”。
下面一章为“关于20世纪社会分崩离析的‘伟大的美国小说’:帕索斯的《美国》还是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就篇幅、范围、人物和事物群体而言,前者共达1200页,为最扎实也最政治化的作品。1936年,作者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但是,场面虽然宏大,但人却没有未来;众多的人物成长了,但是其孩子们没有成长。后者描绘的人物的下场同样悲惨:一家从俄克拉荷马州前往加州寻找出路的农民,历尽千辛到达了目的地,却看到另外一个更加残酷的种植业。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具有元小说意味的故事,它们意在揭示人类主体性在强大的、日益渗透的技术文明影响下都烟消云散了。
最后一章为“20世纪晚期的极繁主义: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及其影响”。二战后美国大学里“创造性写作计划”(creative writing program)的兴起使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项目相得益彰,以至于20世纪晚期许多美国作家作为学生、教师、访问学者或者表演者加入到作家队伍。罗斯和德里罗等都是驻校作家,而品钦在美国康内尔大学物理系读本科时参加的写作班使其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万有引力之虹》气势磅礴,知识面宽广,地理及历史跨度极大。因其涵义的精密及多层次、叙事架构的划时代意义及其影响的持续力,它被称为“二战以来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它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历史性寓言,暗射“欧洲殖民化”(Eurolonization)的必然后果,即美国最后对欧洲的反殖民行为。它对亨利·罗斯(Henry Luce)所谓的“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构成一种讽刺。它暗合21世纪之交美国文学研究的反例外论及后民族主义思潮趋势,揭示美国从种族灭绝式征服到天定使命,再到新帝国主义的过渡历程中所经历的一切。
三、 结语
在世人面前,美国的美国研究专家(Americanists)往往将“美国例外论”挂在嘴边,津津乐道地谈论美国如何凭它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教育优先以及技术至上在世界之林傲然独立,不愧其“山巅之城”的称号。当十几年前苏联解体后,美国人更是抛出了如保守知识分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丧失了一以贯之的自我批评精神。就小说创作而言,它与其大国地位基本相称,但谈不上鹤立鸡群。至于美国人为何热衷谈论“伟大的美国小说”,也许美国学者斯久尔特(Cheryl Strayed)说得对:人们对“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执迷也许证明了更大的真理,即不可能存在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对此,布伊尔教授表示认可。在简短的“尾声”中,布伊尔认为,一方面,“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可能即将销声匿迹,因为随着美国的世界影响力日益降低,加上国内“成熟”的国家官僚机构的复杂性、法律先例以及其他历史性包袱,该梦想只是一个“残余势力”而已。可另一方面,他认为该梦想残而不死,无论人们怎么评说。由于拒绝承认美国是一个实在的、永久的物体的想法一开始就存在,美国小说家才如此起劲地抓住这个话题(美国的力量和威望正日益下降)而进行创作,正如罗斯、品钦等所做的那样。而种族分裂、亚文化分歧的多样性将继续驱使作家对该梦想实践的主导性比喻进行重访和更新。最后,布伊尔勾勒出3种前景。其一,只要美国继续成为外人向往的移民之地,只要纽约市继续成为英语世界最大的出版中心,“美国”及“美国经历”将继续成为作家们的创作题材,虽然创作基地可能移至美国境外。其二,小说将继续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被写成及被阅读,而数字化可能有益于小说创作。即使更多的人将转向有声读物和电子书,评论家也将在网上比在图书馆里花费更多的时间。其三,30年后小说的式样及评价机制将面目全非。人们目前也无法预测,但科幻小说有望一枝独秀,因为甚至关于美国命运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是面向未来的。由此可见,“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将生生不灭,虽然这个美梦的内容将不断发生改变。为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Buell, L.2014.TheDreamoftheGreatAmericanNovel[M].Cambridge/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rsh, A.2015.Why are we obsessed with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N].NewYorkTimesBookReview01-18.
(责任编辑 李巧慧)
通讯地址:210095 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十届全国英语专业院长/系主任高级论坛会议通知
第十届全国英语专业院长/系主任高级论坛定于2016年4月14日至16日在古都河南开封举行,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河南大学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外语界》、《外国语》、《外文研究》等期刊协办。
本届论坛将邀请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各分委会专家、代表性高校外语学科负责人分别做主旨报告、专题报告和教学实践交流,并安排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学成果展示与交流活动,邀请全体代表进行实地观摩、交流与探讨。热忱欢迎全国各高校外语学院院长、英语系主任出席会议,为英语类专业的“十三五”发展出谋划策!
会议地点:河南开封中州国际饭店(河南省开封市大梁路121号)
电话:0371-22218888
会议费用:会务费为300元/人。会务组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报名方式:参会代表请登录http://events.sflep.com在线报名,报名截止时间是4月5日,会议邀请码为2016YZ。
主办: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河南大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代章)协办:《外语界》、《外国语》、《外文研究》
该文的写作受到2013年国家留学基金公派访问学者项目的资助。
I712
A
2095-5723(2015)04-0096-06
2015-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