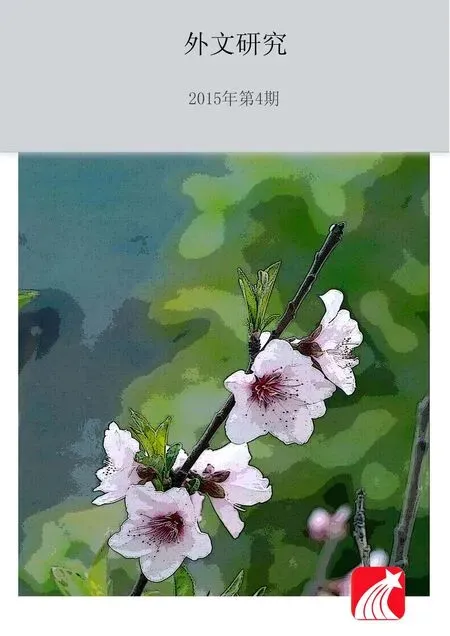《红星照耀中国》译创过程中的读者意识研究
东华理工大学 陈 勇 廖华英
《红星照耀中国》译创过程中的读者意识研究
东华理工大学 陈 勇 廖华英
埃德加·斯诺谙熟中美两种社会与文化,其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译”、“创”结合,在译创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两种文化的优势,在借用西方文明来解读红色中国文化的同时,又充分保留中国特色的语言与文化,在“异域风情”和“读者习惯的风格”之间保持了平衡,体现了强烈的读者意识,从而为欧美读者所接受。
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读者意识;译创
一、引言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又译《西行漫记》,以下简称《红星》)一书,是第一本由外国记者用地道的英文撰写的、最早将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说明的重要著作。该书英文版分别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1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和美国兰登书屋出版发行,后又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至今仍然是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教科书,是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权威著作。斯蒂尔曾评论说,正如《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认识普通中国人一样,《红星》使西方人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Steele 1966: 19)。从某种意义上说,斯诺为一代甚至数代美国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
斯诺是如何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的呢?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又为何能为欧美读者所接受呢?除了拙文《〈红星照耀中国〉的对外传播途径与影响研究》中提到的独特的传播途径的贡献外,斯诺在译创过程中所体现的读者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斯诺研究在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之后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升温,90年代以后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渐从回忆性、纪念性文章转向对斯诺本人生平、其主要作品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但纵观所有这些研究,对斯诺的读者意识却鲜有涉及。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以《红星》一书的译创过程为出发点,从欧美话语体系的建构和译创过程中的翻译现象来说明其强烈的读者意识,并指出其读者意识对今天所提倡的中国典籍外译具有的启示性作用。
二、《红星照耀中国》的译创痕迹
《红星》一书的成书过程极其独特,主要内容与其说是斯诺创作的,还不如说是“译创”的。斯诺力图完整准确地传达受访者的意思,使英文内容贴近原话,因此通过保留汉语中特有的表达方式来再现受访者的风貌,展现读者所关注的异域文化,满足欧美读者了解神秘东方的诉求,并解答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种种疑问。斯诺本人(1979: 7)曾在《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中写道:“从字面上讲起来,这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而在正式访问毛泽东时,斯诺亦写道:“坐在我旁边的是吴亮平,……,在我对毛泽东进行正式访问时担任译员。我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下来,然后又译成中文,由毛泽东改正。……靠着吴先生的帮助,这些访问记再译成了英文,经过了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斯诺 2005: 138)有一定汉语基础的斯诺,在译员们的协助下,通过“译”向读者展示了富有红区特色的社会与文化,因此深受读者欢迎。同时,作为训练有素的新闻记者,斯诺了解读者,并通过“创”在作品中融入了一套欧美读者熟悉的话语体系,使其译创作品欧美读者阅读起来也没有明显的障碍。《红星》一书因此留下了深深的“译”与“创”的痕迹,亦译亦创,读者意识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创——欧美话语体系的建构与读者意识
斯诺是美国人,同时也是训练有素的新闻记者,了解西方读者的心理及诉求,因此在译创过程中,他用西方文明来解读红色中国的文化现象,用欧美读者熟悉的语言文化现象来描述其所见所闻。
一方面,斯诺大量采用英语中的典故来描述其在红区的所见所闻,为读者扫清语言文化上的阅读障碍,适应欧美读者的阅读心理。以“罗宾汉”为例,斯诺在书中3次用到该典故来描述红军战士。罗宾汉是英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据说生活在查理一世(Richard Ⅰ)统治时期(1189-1199),住在诺丁汉附近的舍伍德森林中,和同伴们一起劫富济贫。没有证据表明罗宾汉确有其人,但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后来还有很多关于他冒险经历的电影,其故事和形象流传甚广(Crowther 2007: 1324)。而斯诺在记叙长征的经历时写道:“Their Robin Hood policies were noised ahead of them, and often the oppressed peasantry sent groups to urge them to detour and liberate their districts”(斯诺 2005: 323),描写了红军长征途中“没收”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并分配给穷人的“罗宾汉式”的事迹;红军将领刘志丹也被称为现代罗宾汉,“Liu was a modern Robin Hood, with the mountaineer’s hatred of rich men(斯诺 2005: 337)”;在描述一名药剂师兼理发师的红军战士时,斯诺这样写道:“So off they had gone to become red, red Robin Hood”(斯诺 2005: 589)。斯诺用欧美读者熟悉的罗宾汉这一典故成功地刻画了为穷人而战斗的红军战士形象,为读者扫清了认知上的障碍。斯诺本人进入红区时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冒险的决心也通过典故生动地表现了出来,“It was a farewell to my last link with ‘White’ world for many weeks to come.I had crossed the Red Rubicon”(斯诺 2005: 51)。“Rubicon” 是指意大利北部小河卢比孔河,曾为高卢与罗马共和国的界河,公元前49年凯撒大帝越过此河进军罗马,与罗马执政庞培决战,“cross the Rubicon” 因此而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跨过了就没有回头路)”之意。借用这一典故,斯诺将自己孤身一人深入未知之红区的悲壮心情展露无遗。
另一方面,斯诺也擅长用简化的模型来代替复杂的外国现实,从而得到读者的认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尤其如此。在与毛泽东初次见面时,斯诺是这样描述的:“a gaunt, rather Lincolnesque figure, above average height for a Chinese”(斯诺 2005: 107),“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这一简化的描述,让欧美读者一下联想到林肯的形象,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受爱戴的总统之一,林肯永远为世人铭记,通过这一联想,毛泽东的形象跃然纸上;在毛泽东的自述中,还有这样一句,“I had first heard of America in an article which told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contained a sentence like this: ‘After eight years of difficult war, Washington won victory and built up his nation’”(斯诺 2005: 201),而后来的历史发展戏剧性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样经过八年抗战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再经过第二次国内战争,终于像华盛顿一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成为开国元勋;而“Patriot” 一词在书中的多次出现,不能不让读者想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爱国者(Duffus 1938: BR3)。类似这样的简化模型,书中多次出现。斯诺第一次见到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时,将其描述为“ old Santa Claus Hsu T’eh-li”,两者形象异常匹配;对于朱德夫人,斯诺写道:“a big-boned peasant girl, who is an excellent shot and an expert rider, an Amazon who has led a partisan brigade of her own”(斯诺 2005: 749),将她与古希腊女战士亚马逊联系起来,形象一下清晰了;当描述刘志丹受冤屈含恨离开时(斯诺 2005: 343),一个 “Achilles-like”的表达简直就是点睛之笔,作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因与统帅阿伽门农争吵而生气退出帐篷,与刘志丹的这一幕何其相似;而对于红军剧社的演员,其艰苦的物质条件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让斯诺印象深刻,于是借用古希腊悲剧诗人泰斯庇斯(Thespis)来描述他们的形象,“From the standpoint of material comforts they were unquestionably the most miserably rewarded thespians on earth, yet I hadn’t seen any who looked happier”(斯诺 2005: 175);同样快乐充满希望的还有“红小鬼”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向季邦莫属:“The Beau Brummell of the Vanguards, he had inherited a Sam Browne belt from somebody...with his usual quota of dignity, clicked his heels together, gave me the most Prussian-like salute I had seen in the Red districts” (斯诺 2005: 555), 短短几句话包含了3个欧美读者熟悉的表达“Beau Brummell”、“Sam Browne belt”、“ Prussian-like salute”。第一个指的是英国著名的花花公子博布鲁梅尔(1778-1840),因其时髦服装和举止而闻名,后来人们干脆用他的名字来指代花花公子;第二个指的是军人们用的武装带,最早由驻印度英军一个叫Sam Browne的军官发明,一战期间美军开始大量使用,因此也用其名字来指代;第三个则指标准的普鲁士军礼,典型的幽默表达。这些欧美文化负载词的使用将红小鬼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印象深刻。斯诺渴望与美国人沟通,因而采用了一个个美国人的形象或欧美人熟悉的形象来描述中国共产党人(Hamilton 1988: 87),从而达到了为欧美读者接受的效果。
斯诺亦借用《圣经》和基督教原型来确保语言文化的归化。在描述红军所进行的正义之战时,斯诺多次用到“Crusade”一词,该词原本指11-13世纪间欧洲基督教国家反对穆斯林国家争夺圣地的几次军事入侵,被基督教称为神圣战争,后泛指为推进某项事业而进行的运动等。“Credo”一词也多次出现,本指基督教使徒信经,在书中用于描述红军战士的坚定信念。斯诺还把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比作“gospel”(布道,传播福音),并多次提到红军中有基督教信仰者,或曾经在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接受过教育,或曾在卫理公会医院工作过,而共产党保护了他们的信仰自由,表现出了宗教的宽容(斯诺 2005: 589)。而红军所唱的歌曲里面,相当一部分都是配着基督教赞美诗的调子唱的(斯诺 2005: 475)。斯诺在书写中也多次借用《圣经》原型。在写“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时,斯诺直接使用了《圣经》开篇第一章“创世记”的标题 “Genesis”;在谈到一位铁匠学徒如何加入红军时,斯诺写道:“When the Reds arrived in his district, he had dropped bellows, pans, and apprenticeship, ...hurried off to enlist” (斯诺 2005: 97);徐海东加入红军也是类似的模式:“And yet he still gave the impression of a peasant youth, who had but recently stepped out of the rice fields, rolled down his trouser legs, and joined a passing ‘free company’ of warriors” (斯诺 2005: 497)。这样的描写无疑让读者想到《圣经》马太福音书中的一幕,“As he walked by the Sea of Galilee, he saw two brothers, ...And he said to them, ‘Follow me, and I will make you fish for people.’ Immediately they left their nets and followed him(Jesus Calls the First Disciples)”。难怪美国中西部颇具影响力的《密尔沃基新闻报》曾刊载评论指出:“人们不难发现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朴实的基督徒的信仰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Hamilton 1988: 88)。
斯诺还采用了对比修辞来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以期与读者产生共鸣。为让读者理解红军长征这一历史壮举,斯诺借用了欧美读者熟悉的模型来描述,他认为在过去3个多世纪中除了土尔扈特部落的大迁徙之外,在亚洲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而与此相比,公元前218年汉尼拔远征军征战意大利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就像一场假日远足, “Hannibal’s march over the Alps looked like a holiday excursion beside it” (斯诺 2005: 331),以此说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勇艰巨与举世无双。斯诺甚至用拿破仑当年从莫斯科的大溃败来做反面例证,当时拿破仑的军队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与长征中红军的战略撤退、高涨的士气和必胜的信心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斯诺对红军长征的英勇行为的描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任太平洋关系学会秘书长的爱德华·C·卡特(1938: 111)曾在《太平洋事务》上撰文评论:“(斯诺)对长征的描述使(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笔下的英雄形同巧克力士兵”;而红军沿途所宣传的“自由、平等、民主”(liberty, equality, and democracy)理念,不能不让读者想到美国独立宣言中的“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理念;红军剧社为唤醒千万中国农民起来为“人民当家作主”(fight for “the reign of the people”)而斗争,也不能不让读者想到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名句“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斯诺甚至把红军剧社的演出场面和美国纽约的“肖托夸教育集会”进行了比较,“It would be hard to imagine a more democratic gathering—something like old-time Chautauqua”(斯诺 2005: 167)。“Chautauqua”本指纽约东南部的肖托夸湖,每年夏天,这里会举行肖托夸教育集会,包括讲座、音乐会等,盛行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1920年代中期结束,是最具美国特色的活动之一。用这个美国人特别熟悉的活动来描述红军剧社的演出盛况,让读者倍感亲切。而另一个颇具美国特色的表达“underground railway”也被用来形容共产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线。该典故出自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当时的废奴主义者通过组织“地下铁道”,通过隐蔽的方式,经由秘密的路线和食宿站,协助奴隶逃出南方获得自由。对红军而言,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下,也只有通过秘密地下交通线将人员和物资运进送出,两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借用西方文明的精华来描述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斯诺有意识且成功地拉近了前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四、译——斯诺译创中的翻译现象
中西语言与文化迥异的事实给翻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就需要译者采用适当的策略和技巧将源文化中涉及语言文化特色的内容传达给译语读者。斯诺是美国人,既熟知欧美文化,又熟悉中国社会与文化,其较强的读者意识使其在描述红区的过程中大量采用了音译加直译、文内注解、文外加注等手段,立足于中国现实与红色中国的真实风貌,结合自己对事物的独特认识视角和亲身体会,完整准确地传达了红区文化的真谛,保留了汉语特有表达方式和汉语言原貌及其映射的民族思维与心理模式,向欧美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红区文明画卷。斯诺从自身外国新闻记者的身份出发,自信这是一个读者想要知道的故事(斯诺 2005: 179)。一方面要满足欧美读者的期待从而获得读者的认同,一方面要表述“真实的中国”和“一个与条约港口城市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纠正西方话语中的“负面中国形象”,调和着“异域风貌”与“欧美读者习惯的风格”,努力达成一种平衡。这种方式既保留了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让欧美读者品味到了原汁原味的红色中国文化,又让欧美读者顺利跨越文化差异,消除曲解,使得红色中国与外界之间的多层次对话得以顺利展开。
斯诺译创中的这种翻译现象在《红星》一书中比比皆是。毕竟中国文化主题与西方文化传统之间多有不一致或相冲突的地方,这时,斯诺多采用音译加直译的方式进行处理,对于重要的语言文化现象则加上文内注解或文外加注的方式进一步阐释,一方面保留了汉语的发音,另一方面又将英文解释融入到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中,充分体现了斯诺的读者意识。以陕北的窑房为例,Yao-fang, or “cave houses”, as the Chinese call them, but they were no caves in the Western sense.Cool in summer, warm in winter, they were easily built and easily cleaned (斯诺 2005: 43), 窑洞在陕北随处可见,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习惯,典型的中国乡土文化,但与西方人所谓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作者在此进行了解释,既保留了汉语的“原汁原味”,又准确传递了信息,满足了读者阅读的需要;“瞎子”的翻译亦是如此,Hsia-tzu, or “blind man”, as the Chinese call total illiterate (斯诺 2005: 473),音译加直译,但这是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表达,因此加以解释,让欧美读者明白这个“瞎子”并非字面意义的瞎子;“民团”也是个比较复杂的概念, White bandits were in the Kuomintang’s terminology called “mint’uan”, or “people’s corps”, just as Red bandits were in Soviet terminology called “yu-chi-tui”, “roving band”—Red partisans.In an effort to combat peasant uprisings, themint’uanforces had increasingly been organized by the Kuomintang(斯诺 2005: 59),民团的直译是 “people’s corps”,是国民党组织起来镇压农民起义、保护地主豪绅利益的,在老百姓眼里,就是“白匪”,跟土匪没两样,完全与“人民的”概念相悖,而国民党又称红军游击队为“赤匪”,因此作者使用音译加直译再加文内解释的方式对这一特殊复杂的现象进行了阐释,力图使读者准确理解这一概念;文中对“妈的马鸿逵”(Ma-tiMaHung-kuei, meant you could defile Ma’s mother and it would be too good for him)(斯诺 2005: 531)、“兵谏”(Ping-chien—“military persuasion”—a recognized tactic in Chinese political maneuver)(斯诺 2005: 665)的处理均是如此。
但有时为保持行文流畅,对于一些重要的表达,斯诺采取了音译加直译再加文外注解的方式。以“亩”、“里”、“担”等中国特色计量单位为例,毛泽东在讲述其家庭状况时用到了这些表达,在音译之后,在页底加注,用欧美人熟悉的单位予以表达,如fifteenmou: about 2.5 acres, or one hectare;tan: one tan is a picul, or 133 1/3 pounds; eightli: two and two-thirds miles, one Chineseliis about a third of a mile (斯诺 2005: 187)。采用这种方式翻译的多是涉及社会文化类的颇具中国特色的表达,如“老百姓”,音译“Lao-pai-hsing”,保留源语读音,在底注中直译并解释为“Literally ‘old hundred names’, is the colloquial Chinese expression for the country people”(斯诺 2005: 45);再如“哥老会”,音译“KeLaoHui”,直译“The Elder Brother Society”,再解释为“an ancient secret organization which fought the Manchus and was useful to Sun Yat-sen.In structure it strikingly resembled the cell system adop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ground”(斯诺 2005: 87);“磕头”,音译“K’ou-t’ou”,直译“to knock head”,解释为“to strike one’s head to the floor or earth was expected of son to father and subject to emperor, in token of filial obedience”(斯诺 2005: 191);“土豪”, 音译“T’u-hao”,直译“Local Rascals”,解释为“was the Reds’ term for landowners who also derived a large part of their income from lending money and buying and selling mortgages”(斯诺 2005: 365); “水浒传”, 音译“ShuiHuChuan”,直译“The Water Margin”,解释为“a celebrated Chinese romance of the 16thcentury.Pearl Buck has translated it under the titleAllMenAreBrothers”(斯诺 2005: 65),而提到赛珍珠的译本,欧美读者更是熟悉。赛珍珠的《大地》是1931年和1932年的全美畅销书,赛珍珠本人也因此声名大噪,当1933年其《水浒传》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时,亦很受欢迎,《水浒传》因此而为众多欧美读者所了解。通过采用赛珍珠译本的方式,斯诺为读者架起了一座从已知到未知的桥梁。有些表达由于含义丰富,不能音译,则直接用直译加注的方式,如“观音土”,直译为“Goddess-of-Mercy earth”,再解释为“balls of mud and straw eaten to appease hunger, and often resulting in death”(斯诺 2005: 127);“吃大户”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和表达,直译为“Let’s eat at the Big House”,进一步解释为“‘Eat Rice Without Charge’ movement, that is, at the landlord’s granary”(斯诺 2005: 197)。此外,像乾隆、梁启超、袁世凯、胡适、陈独秀等书中提到的名人也都采用这种方式加以翻译,以扫除读者的阅读障碍,为理解主要内容做好铺垫。
音译加直译或意译的方式在《红星》一书中也是一种常见的处理方式。像红匪(Hung-Fei, Red Bandit)、铁老虎(T’iehLao-hu, the Iron Tiger)、人民抗日剧社(Jen-minK’ang-JihChu-She, People’s Anti-Japanese Dramatic Society)、日本鬼(Jih-Pen-Kuei, the Japanese Devils)、路条(lu-t’iao, road passes)、长征(Ch’angCheng, the Long March)、贫民会(P’in-MinHui, Poor People’s Society)、儿童团(Erh-T’ungT’uan, the Children’s Brigades)、识字课本(Shih-tzu“know characters” texts)、战士(chanshih, fighters or warriors)、堡垒(pao-lei, the hilltop machine-gun nests)、同志(t’ungchih, comrade)、汉奸(Han-chien, an archtrator)、洋房(yang-fang, foreign houses)等,通过音译加直译或意译的方式,既体现了红区的本土韵味,又适应了欧美读者的阅读口味和习惯,既保留了东方元素,又采用了西式表达方式,真实形象地描述了红色中国的情况。
五、结语
从保留东方元素和选择最佳西式表达方式来看,读者意识在斯诺译创《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也是该书经久不衰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作为一名美国记者,斯诺精通自己的语言与文化,而在中国长达8年的生活也让斯诺结识了众多的中国社会人士,尤其是以宋庆龄、鲁迅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在他们的影响下,加上其本人在中国的亲眼所见,斯诺对中国社会非常了解,由此而产生了对中国的同情,并希望中国社会能发生变化,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对红色中国的严密封锁和单方面的歪曲报道及污蔑,更加坚定了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探究竟、寻找故事的另外一面的决心。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斯诺踏上了去陕北红区的“冒险”之旅。而在红区4个月的亲眼所见与亲身体会令斯诺兴奋异常,同时也使他冷静地认识到应该及时把红区的真实状况告诉全世界。因此,为达到上述目的,斯诺不仅用西方文明的精华来阐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红色中国,同时又把在红色中国的所见所闻原汁原味地呈现给好奇的读者,读者意识得到了自始至终的贯彻。当前的翻译研究愈加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愈加强调这种跨文化传播的最终效果,希望本项研究对上述问题有一定启示。
Carter, E.C.1938.RedStarOverChinaby Edgar Snow [J].PacificAffairs(1): 110-113.
Crowther, J.2007.牛津英美文化词典[Z].黄梅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Duffus, R.L.1938.A remarkable survey ofTheRedintheMapofChina[N].NewYorkTimesBookReview01-09.
Hamilton, J.M.1988.EdgarSnow:ABiography[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teele, A.T.1966.TheAmericanPeopleandChina[M].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埃德加·斯诺.1979.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埃德加·斯诺.2005.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清平)
通讯地址:330013 江西省南昌市 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红星照耀中国》与红色文化传播研究”(14WX319)成果之一。
H059
A
2095-5723(2015)04-0059-06
2015-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