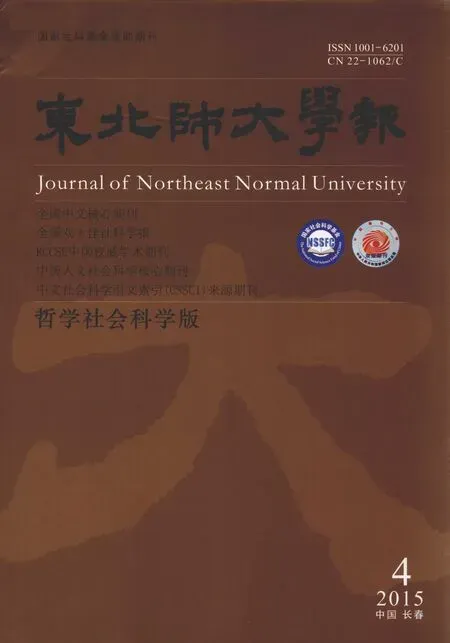“回到”与“遗忘”:论德勒兹对马克思的深层继承关系
张 岩 磊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回到”与“遗忘”:论德勒兹对马克思的深层继承关系
张 岩 磊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德勒兹一方面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另一方面又提出要“遗忘”马克思。“回到”与“遗忘”间的张力体现出的正是德勒兹对马克思深层次的继承。尽管德勒兹的精神分裂分析最终仍然类似于德里达的延异,使马克思所开启的社会批判边缘化、碎片化,但是德勒兹的思想涌动着的依然是改变现实的“激愤”。因而无论就文本还是社会实践,我们都能在德勒兹身上看到马克思的身影。也许正是因为“遗忘”掉那些已经固化的教条式的公式,才能避免我们把传统哲学根深蒂固的同一性诉求重又强加给马克思,才能真正回到那个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马克思。
回到;遗忘;德勒兹;马克思;继承
一定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与马克思的关系往往能够最为有力地彰显马克思在现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中的活力和作用,也能够给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有益的启示。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德里达。德里达在回应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时创造出“马克思的幽灵”这样一个概念性人物,借以彰显自己对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的继承。而较之德里达,德勒兹与马克思的关系可能更为引人入胜。实际上,德勒兹与马克思的关系也直接影响了德里达。就德勒兹的思想谱系而言,考察他与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尼采、柏格森,甚至是与福柯之间的关系是较为方便的,德勒兹本人就有直接解读他们的著作。但是当论及马克思之于德勒兹,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就文本说,德勒兹较少直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就德勒兹的理论实践看,尽管他从来没有加入过法国共产党,但是德勒兹终其一生都没有否定过马克思,他始终赞扬马克思,即便是在68革命失败之后——在Jean-Marie Benoist于1970年出版《马克思已经死亡了》之时,德勒兹也公开倡导“我们应该回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1]。德勒兹晚期曾明确地说,“我认为瓜塔里和我,我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1]。并且在德勒兹即将离世之前,他准备写一本题为《马克思的伟大》的书,谈谈对马克思“对这个时代的激愤”以及他不断挑战的勇气[1]。以至于詹姆逊认为,“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杰出思想家中,德勒兹是在自己的哲学中赋予马克思至关重要地位的唯一一位,他后期的著述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和马克思思想的碰撞。”[2]
但是德勒兹并非一味教条化地赞同马克思,尤其是不赞同当时法国的左派马克思主义。在68革命失败之后,德勒兹很少直接参与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刻意保持一种边缘状态。针对当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偏离,德勒兹(和加塔利)也曾明确表示,他们的问题从来不是要回到马克思,而是要遗忘,包括遗忘马克思,将他淹没到细小的碎片之中[1]。由此,彰显出德勒兹和马克思关系的复杂:马克思的幽灵始终萦绕着德勒兹,但德勒兹又着意与之保持差异。我们的问题是,就德勒兹的思想体系而言,究竟该如何理解这既回到又遗忘的矛盾的说法,或者说,德勒兹是如何继承马克思的呢?
一、“回到”与“遗忘”
德勒兹一方面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另一方面又提出要“遗忘”马克思。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马克思,“回到”和“遗忘”虽然是德勒兹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但并非是态度的转变,并非是对立性的非此即彼的“回到”还是“遗忘”的问题,而是既“回到”又“遗忘”的辩证性的问题。实际上这种看似矛盾的两种态度始终胶着地或者说思辨地体现在德勒兹之于马克思的态度中。我们认为,对于理解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问题不在于强调“回到”和“遗忘”之间的分裂,而是要凸显“回到”和“遗忘”间的张力,要弄清楚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德勒兹,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继承了马克思。
按照伊莎贝拉·伽霍尔的解释:“对马克思的怀念与对马克思的‘遗忘’发生了冲突,但这种冲突却并无矛盾。这种遗忘所逃避的是一个名称和某些概念:即从对一般性概念的讨论中退出,从对劳动的政治—理论的界定中退出,同时却仍保持着马克思自身的精神。”[1]这不禁让人想到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说的,“……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勒兹和德里达对于马克思的态度有着惊人的相似。遗忘掉那些已经被“教条化”的所谓思想,遗忘掉那些已经与时代不符的种种教条化、公式化的判断,但是要切近马克思的那种批判一切进而改变现实的“激愤”和力量。无论对于德里达还是德勒兹都是这样:不能没有马克思那种生命不已批判不已的精神。事实上,马克思始终作为德勒兹隐而不显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背景。统观德勒兹的思想脉络,他试图把马克思作为隐而不显的要素,把诸如“生产”、“历史”还有“劳动”等概念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和柏格森的“绵延”、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等思想,重新揉在一起,生成新的思想,就像“面包师”一样。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德勒兹的“差异本体论”、“精神分裂分析”、“欲望生产理论”以及他的政治哲学意味上的“游牧学”。引用伊莎贝拉·伽霍尔的说法,“德勒兹与马克思的关系或可概括为,拥有共同‘经典’主题,但却在如何装点这一主题上分道扬镳。”[1]
“经典”的主题就是批判资本主义,这一点毋庸置疑。到今天马克思已经故去131年(以作者投稿时间计算)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远远没有走出他所批判的视野。可以说,但凡存在着剥削、压迫、人强加于人的屈辱,我们就需要马克思的幽灵——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德勒兹甚至有着比马克思还要强烈的“激愤”,但是他又总是呈现出某种置身事外的姿态:德勒兹总是保持着与这个时代之间的距离。或许正如那场“玫瑰革命”一样,游行示威表达的都是些愤世嫉俗的不满,过度的情绪化反而消解了所谓革命自身的力量。德勒兹本人的哲学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太多的政治隐喻,太多的文学色彩和诗化的文风不但使他的思想奇谲晦涩,也使得他的思想多元化、分流化甚至碎片化,以致难以把捉。对于德勒兹来说,革命总是某种意义上的革新,但这种革新却总是以捕获和重新编码结束,德勒兹更倾向于解码,倾向于解放的“流”。不过德勒兹激愤的情感希冀的却是一种温和的变革。这或许是因为德勒兹对于资本主义的新理解以及他对于革命自身的悲观态度。在德勒兹看来,资本主义的各种“流”一定意义上释放了“欲望”的生产,但是强势的资本逻辑敉平了欲望的自身差异性重又捕获“欲望”,从而将“欲望—生产”异化为“生产—欲望”,最终“生产—欲望”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公理”。德勒兹担心对资本主义的对抗最终会被资本的逻辑重新捕获,因而与直接地暴力对抗不同,他试图另辟蹊径,他选择了一种通过创造概念介入现实进而改变现实的进路。“言论与信息传播可能已经腐败。它们已经完全被金钱所腐蚀,这并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必然的结果。……重要的也许是创造一些非信息传播的细胞质液泡,一些断路器,以便避开控制。”[4]
此处,“创造一些非信息传播的细胞质液泡”,德勒兹意指创造新的概念,他把创造概念视为哲学介入世界进而改变世界的方式。这也是在他和加塔利合著的最后一本著作《什么是哲学?》中所着力阐发的主题,“哲学就是创造概念”。而“创造概念”意味着人的全新的自我觉解和自我生成。德勒兹力图把对抗资本主义的战场从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空间转移到“人心惟危”的“褶皱”空间。“褶皱”是德勒兹创造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德勒兹那里,“褶皱”是不能被同一性逻辑甚至是思辨的方法“扬弃”掉的无限场域,在这里,“我”与“他者”产生共振,思想的内部与外部产生共振,由此生成的偶然性的“差异”从必然性的逻辑之网中突围、逃逸出来,因而获得既成的合法性。在这样的意义上,德勒兹完成了对传统“主体”的消解,令他的主体“无器官身体”一开始就具有“去自我化”的倾向,通过思想的绝对速度使“自我”与“他者”区分的界线消弭。德勒兹试图在最微观的单子层面改变人心所向,进而令已然具有确定性的变化了的观念像“根茎”一样扩散开来,扎根、生长。
综上所述,或许“回到”和“遗忘”这样冲突性的表述已经折射出德勒兹和马克思之间复杂的姻亲或者说生成性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德勒兹概念的体系或者说高原群使他能够在一种本体论的层面上思考问题,令他的思想富有生产性、冲击性的力量,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说,他更多的是在隐喻的水平上来使用它,这反而消解掉了或者说弱化了直接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因此,德勒兹的思想虽然更具有解释力但其思想切入现实的“力”远远不及马克思的“实质伦理学”那样有“力”,而后者带来的往往是更为直接地、切实地改变世界的力量。
下面我们就他们较为重要的思想内容进一步着重考察一下马克思和德勒兹之间的差异,这差异或许一方面能让我们更好地梳理德勒兹和马克思更为深层的生成关系,另一方面也能够彰显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思想活力,从而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描述现实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带来有益的启示。
二、“无产者”与“游牧民”
要厘清德勒兹和马克思的内在生成关系,我们不妨借助德勒兹的方法,即我们要先“生成”德勒兹,然后以德勒兹的感知方式、理解方式和概念方式来解读马克思。那么,我们首先来勾勒一下马克思的“概念性人物”。
因为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概念性人物是哲学家的‘异语同义词’,而哲学家的名字不过是其概念性人物的化名而已。……概念性人物是哲学的表述行为的真正施行者。”[5]根椐这种“异语同义词”的说法,无论是就文本还是就实际的革命实践说,马克思的概念性人物毫无疑问应该是“无产者”。而作为一个第三人称,“无产者”或许是最为特殊的概念性人物。这是一个总体性的作为单数的复数形象:它本身是由独立的作为单数的无产者组成,但是共同的理想和政治目标则使得这个团体以凝聚性的“集体”的单数形象——无产阶级出现。这样的一个概念性人物,作为马克思哲学的表述行为的真正施行者或者说实践者,更为深层的特殊性在于: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性人物,“他”(她)不再停留在抽象的书斋式的论证里或者哲学体系的“睡帽里”,在某种意义上“他”(她)无疑代表着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但是在现实中真切笃实地把这种精神实现——外化出来,并且绝不故步自封于某种既成的体系或者权力。如果说马克思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那么这当然是因为“无产者”这一概念性人物第一次真正具有了把理论变为现实的力量。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个著名的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57甚至在更早些的时候,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提出口号,“让哲学成为世界的哲学,让世界成为哲学的世界。”[6]121改变世界的并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作为概念性人物的“无产者”,“无产者”蕴含并释放概念的能量。
无论基于对马克思的继承还是回应,与“无产者”这样的概念性人物相对待的,在德勒兹(和加塔利)那里是“游牧民”。游牧民源自于诺摩斯(nomos)这一概念,与逻各斯相对立。早在《差异与重复》中,德勒兹就已经从诺摩斯和逻各斯(logos)之间的对立中开始了一种游牧分配的定义,力图打破逻各斯的体系化和僵化的倾向。而在《千高原》中诺摩斯被进一步阐发。“诺摩斯”是“游牧”排列要素的方式,说到底,是对人、思想或空间本身的配置方式。与逻各斯相对,这种方式不依赖于一个组织或持久的结构,它表明某些要素的一种自由分配,而不是这些要素的结构化的组织。“这个希腊词诺摩斯一般被译成法则(law)。……德勒兹用作为分配的诺摩斯来反对另一个希腊词逻各斯。”[7]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游牧民”是在历史中相对于城邦结构而出现的另一个传统。而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游牧”代表着与同一性的逻各斯不同的根茎主义。需要指出的是,“游牧民”不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描述和再现,而是一种方向、一种可能。由于公理化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捕获装置,游牧民首先得生成自身然后才能进行对资本主义的抗拒、对抗,因而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游牧民是属于未来的民族。
所以,同为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德勒兹的“游牧民”迥异于马克思的“无产者”。“无产者”是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具体存在着的与“资产者”相对立的现实的革命力量。“无产者”变革现实世界的方式就是主动而直接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272伴随“无产者”这一概念形象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内在性平面。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作为一种不断克服其自身局限(比如说经济危机)的内在体系。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会相应地加大,最终资本主义无法再容纳这一矛盾,从而导致自身最终的灭亡。根椐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经济决定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历史必然。
而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至少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适用。“与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拒斥一道,似乎没有什么比德勒兹和加塔利的阶级斗争的贬值更远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念。在他们的观点中,阶级斗争本身不是革命的,因为实际上只有一个阶级……包括工厂工人,他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仅仅是资本的化身。”[8]161因而,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的逻辑运作,通过公理化这样的捕获装置,使资本主义的同一性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无论是工人、管理者、商人甚至是公务员、政客,无不被资本捕获,而跟随着资本的公理化系统,其中并没有工人与资本家的生死对立,而是某种抽象的同一性逻辑同所有人相对立。
德勒兹(和加塔利)寄希望于“游牧民”来对抗资本的同一性逻辑。“游牧民”结域—解域—再结域的流动特点使其对资本主义公理的解码成为可能。“游牧民”解域的方向是四散的、无中心的,它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蕴含着一种线性的进化论式的历史观。而他们认为:“经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事情”[8]156。他们按照颠倒的因果关系、分歧点和起点来构想历史,而不是按照被开启了新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所强调的一种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来构想历史。基于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是作为偶然的分歧点(bifurcation-point)而出现:资本主义实际上从‘自由’劳动和流动财产的结合中产生,这一事实改变了一切。但是它同样本可能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于其他地方。然而它一旦出现,历史就变成普遍的,而且资本积累的动力赋予它一定的线性。”[8]155
综合上述分析,相对于现实层面的“无产者”来说,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民”更多侧重的是一种符号系统或者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理想的概念系统,它旨在阐发不同于马克思“线性”历史的另一条可能性的历史方向。不过,德勒兹(和加塔利)直接使用了马克思的许多概念,如生产、剩余价值等,但是他们赋予这些概念以不同于马克思的更能适应当代资本主义因而更具解释力的新内涵。比如,他们在经济和欲望的双重层面上使用生产这一概念,他们把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的逻辑视为一种同一性的捕获装置。因此,为了寻求人的存在层面上的自由,他们求助于诺摩斯。正如在《千高原》“12.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这一部分中展示的,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这种游牧式的生存是唯一可以逃离资本主义公理之网所构建的捕获装置的生存方式。对他们来说,内在的差异是唯一可以与同一性抗衡的现实力量,因而游牧民的内在动力机制是差异机器或者说是欲望机器,在这样的意义上,作为概念性人物,游牧者本身又是“精神分裂者”。精神分裂者自身就是个多元体,每一个精神分裂者自身就是复数的,他(们)拒绝服从,拒绝服从资本以及资本和技术的合谋,更拒绝被资本捕获的国家机构——他们拒绝内在的或者外在同一性的权力意志,而追求一种绝对的永恒的自由。德勒兹(和加塔利)所理解的自由是一种类似于根茎的逃逸系统,是各种流的溢出,当“流”受到阻碍时会激发相应的战争机器。但是德勒兹的战争机器并不是毁灭者,而是一种制衡权力的力量,因此游牧民寻求的不是革命性的颠覆而是权力的平衡以及这种权力的平衡带来的“平滑空间”(自由)。不难发现,无论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解,还是对马克思的核心概念,德勒兹(和加塔利)都基于他们所谓“回到”和“遗忘”的思辨态度予以了实质性的继承。
三、“社会—人性论”与“欲望—人性论”
按照已故哲学家高清海先生的说法,哲学的奥秘在于人,人如何理解自身就怎样理解哲学。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性自觉或许是理解哲学家具体理论主张的更为基础性的内在性平面。基于人性自觉这一内在性平面的考察,我们或许更容易洞见德勒兹与马克思的差异以及德勒兹对马克思内在的继承关系。
我们知道,西方传统哲学把理性理解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因此我们认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人性论是“理性—人性论”。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更是把这种“理性—人性论”发展到极致。对于黑格尔来说,“理性不仅仅是人性的内在规定而且是世界宇宙历史的内在规定。”[9]6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相对于黑格尔,马克思已经有了对人性的新的体认。对于马克思来说,人性并非一种抽象的先验的、超历史的规定性,而是基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之上的“生成”——“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根据孙利天教授的看法,马克思对于人性的这种新的自觉,可以看作是开启了我们今天各种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起点。对于马克思来说,那种对于人性的纯粹理性或者纯粹德性的理解,并不能作为人性自觉的基础,无论是人的理性能力还是道德能力,终究是在历史的特定时代中才能形成、才能存在。孙利天教授进一步认为,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看法,后来引向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只有通过改变世界、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才能达到。所以对人性的自觉,不再是一个纯粹理性能力的实现,也不再是纯粹德性的培育和发展,而是社会批判[9]9。在这样的意义上,孙利天教授把马克思的人性论叫做“社会—人性论”。
马克思的“社会—人性论”所开启的新的社会批判理论,不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影响一直延伸到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如福柯、德里达等,当然也包括德勒兹。在反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人性论方面,德勒兹和德里达、福柯是一致的。按照德勒兹,基于同一性传统的人性论正是由德里达称作“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那种东西决定的。“逻各斯”意味着理性,意味着合法化。把“理性”视为人的规定性,以一种独断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霸权式口吻做出这一不容商议的决断无疑是非法的。而对于德勒兹也包括福柯来说,理性只是人的欲望之流中的一种。不过,德勒兹(和加塔利)与福柯、德里达等其他后现代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是在本体论的维度上开展对于人性的反思,这使得他们并非像德里达那样陷于批判和拆解的惯性。德勒兹是一位寻求基础的建构主义者。依照他(和加塔利)的哲学表述,把人理解为“欲望—机器”。“欲望”在他们那里具有了本体论层面的意义,欲望是理解人自身乃至世界的内在性平面。因此基于人性论或者说基于对人性的自觉这样一个内在性平面,我们可以把德勒兹的人性论称作“欲望—人性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之后,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于人性理解的空间。通过弗洛伊德对于人的意识的划分,人们意识到原来“理性”只是人性的冰山一角,其背后是幽深难解的“欲望”深渊。但是由于弗洛伊德把人的欲望(多)归于“力比多”(一),他始终试图把欲望纳入到理性的统摄之下,因此,弗洛伊德仍然是在传统理性范式下来定义人,他仍然秉承着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的人性论观点。拉康则力图从“多”出发,在根基处反对弗洛伊德,他与福柯一样,并不认为精神分裂就是病态,拉康甚至明确指出,“人的所谓人格本来是分裂”。当然,福柯在这个基础上走得更远。但是在总体上,就弗洛伊德和拉康也包括福柯而言,他们实际上是用“欲望”来扩展人们对于人性的理解。只不过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无意识领域是“延异”了的理性。拉康和福柯则是在分析欲望的基础上消解掉人性。
德勒兹(和加塔利)综合了弗洛伊德、拉康以及福柯的理论主张,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欲望—人性论”并非旨在消解人性,而是试图通过其自身差异的欲望理论尽可能地扩展人性生成的所谓平滑空间。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来说,德勒兹的“欲望—人性论”继承了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的理解,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欲望”作为人性的本体与人性的社会性、历史生成性并不冲突,因为作为本体的“欲望”在德勒兹那里并不是一个超验之物,它既是官能性的存在又是经验得以发生的内在性平面。因而德勒兹的欲望是先验的经验主义的产物。德勒兹的唯物主义立场决定了他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态度,也直接决定了他对欲望的不同理解。所以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在精神分析那里作为根本性的力比多仅仅是一种流,它在一个集合中与其他流一起成为欲望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个在欲望的集合中享有特权的基础设施,也不是一种可以被转化或升华为其他流的能量。
因而,“欲望”不是多种“流”汇集而成的多元体,而是生成多种欲望“流”的本体,但是作为“欲望”的本体本身不是一个像“绝对精神”一样的超验之物,它是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多元体。根椐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多元体概念,欲望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源初之点,它是一个“根茎”式的多元体。我们可以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在马克思的社会人性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莱布尼兹的单子论。这一点从他们对于“根茎”的解释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10]。“根茎”正是对人、对社会的创造性描述。“根茎”中的“点”即是个体意义上的人,那么人与人之间必定是连接和异质性的关系,而且,根椐人的社会属性,人必定要和他人发生连接。只有承认并尊重人与人之间绝对的差异性,甚至是人之生成的内在差异性,人才能摆脱来自抽象同一性的“一”的统摄和异化。并且“根茎”的特点也反映出德勒兹(和加塔利)深层次的“革命理论”,差异性的欲望在受到阻碍的情况下并非一味地逃逸或规避控制,而是会激发出反抗或革命的力量和行为。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勾勒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人性论”。通过对人性的新理解,德勒兹继承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精神并在微观政治(即根茎—游牧这一思维模式)的层面上弥补了利奥塔批评的所谓“宏大叙事”的解释空白。这也意味着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杂糅了弗洛伊德、拉康和福柯的思想之后,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生成。一定意义上,这是对于马克思社会人性论的完善和丰富[11]。
综合上文,无论是通过其概念性人物还是人性自觉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回到”与“遗忘”间的张力所体现的正是德勒兹对马克思深层次的继承关系。尽管德勒兹的精神分裂分析最终仍然类似于德里达的延异,使马克思所开启的社会批判边缘化、碎片化,但是德勒兹的思想涌动着的依然是改变现实的“激愤”。因而无论是哲学气质还是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我们都能在德勒兹身上看到马克思的身影。尽管德勒兹曾公开反对辩证法,但从他对马克思的态度上又能看出他的思想方法带有深刻的思辨性。德勒兹给予我们的启示或许是,正是因为“遗忘”掉那些已经固化的教条式的公式,才能避免我们把传统哲学根深蒂固的同一性诉求重又强加给马克思,才能真正回到那个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马克思。
[1] [法]伊莎贝拉·伽霍尔.德勒兹、马克思与革命:如何理解“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内涵[J].夏莹,译,江海学刊,2010(5):22-26.
[2] [美]詹姆逊.德勒兹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二元论[J/OL].邱瑾,译.http://dzl.ias.fudan.edu.cn/MasterArticle.aspx?ID=4806.
[3]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4]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M].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1.
[5] [法]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M].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287-288.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Gilles Deleuze.TheDeleuzeDictionary,ed[M].Adrian Par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185.
[8] Graham Jones,Jon Roffe.Deleuze’sPhilosophicalLineage,ed[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
[9] 孙利天,张岩磊.哲学的人性自觉及其意义[J].长白学刊,2011(1).
[10] [法]德勒兹,加塔利.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7-14.
[11] 舒心心,穆艳杰.试析马克思视野下“完整的人”及其理论意义[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58-63.
“Return to” and “Forgetting”——the Deep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s of Deleuze to Marx
ZHANG Yan-lei
(School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Deleuze proposed “return to” Marx on one hand,and on the other hand,he proposed “forget” Marx.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tension between “return to” and “forget” reflects the deep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s of Deleuze to Marx.Although Deleuze’s schizophrenia analysis is still similar to Derrida’s differance,which made the social criticism initiated by Marx marginalized and fragmented,Deleuze’s thought surges the “indignance” of changing the reality.Therefore,regardless of the text or social practice,we can see the shadow of Marx from Deleuze.Perhaps it’s because we forget the formulas who have been cured and dogmatic,that we can avoid imposing the identity of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n Marx again,that we can truly return to Marx who discovered the new world by criticizing the old one.
Return to;Forgetting;Deleuze;Marx;Inheritance
2014-11-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6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QN14013)。
张岩磊(1981-),男,山东滨州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讲师,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B1;B089.1
A
1001-6201(2015)04-0077-06
[责任编辑:秦卫波]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