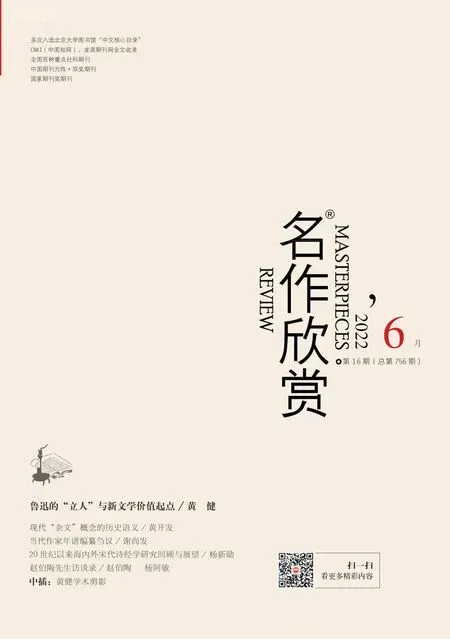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
北京 邵燕君
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
北京 邵燕君
媒介革命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如何使印刷时代的文学星光继续在网络时代闪耀,如何将“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连通,将粉丝们的爱与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爱连通,让文学的精灵在我们的守望中重生——这是时代对我们这些当代文学研究者提出的特殊挑战,也是知识分子无可推脱的责任担当。
媒介革命 网络时代 文学传统
网文观察与新媒体(六) 主持人:邵燕君
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都与媒介转型有关。一篇是我本人于3月7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TEDX Peking University“顿悟时刻”发表的演讲,该活动是在国际TED大会精神“值得分享的理念(Ideas Worth Spreading)”指导下建立的,旨在通过邀请各领域具有杰出成就的嘉宾分享关于科技、娱乐、文化等多方面的思想感悟。另两篇是在“新媒体理论与实践”课堂上关于“网络时代:我的部落化生活”讨论的发言稿中遴选出来的。我们各自从切身经历出发,挖掘在千年一遇的媒介变革中,自己在研究方式、认知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发生的深刻转变,以期与同样处于转型阵痛期的朋友们交流。为了传达现场感,文章尽量保持口语化。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作为一个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我要经常在各种场合回答朋友们一个特别原始的问题:你们是不是专门看小说的?我的回答是:没错,看小说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我们没有朋友们想象的那么幸福。我们不是专门看小说,而是专业看小说。我们必须在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创作中把握潮流脉象,必须在一个作品刚刚诞生之际判断其良莠优劣。我们不但要看一个作品写什么,还要看它怎么写,更要看它为什么写。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是一个社会的梦幻空间,那么,文学批评者的工作就有点像释梦师。我们要在作者有意识的书写背后,读出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在貌似肤浅的流行背后,读出人们深层的怕与爱;通过文学潮流的兴衰把握时代精神的走向。这是当代文学研究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一个迷人的地方是它的介入性。我们的解读和判断能多少影响到作家的写作、读者的阅读,乃至文学史的选择。我想这就够了,通过一种专业性的工作,你不但可以更有效地认识你所身处的世界,并且还有可能,哪怕是那么一点点,改变你将要身处的世界。
正是抱着这样的热情和希望,我在留校工作的第一年就和几位同仁成立了“北大评刊”论坛,并且以论坛为核心开设了选修课。那是2004年,那时网络文学已经度过了萌芽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但其燎原之势远远没有烧到主流文坛,主流文坛依然是文学期刊一统天下。我们选择了十种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期刊,逐期阅读,逐篇点评,在网站上发表评论。评刊的工作坚持了六年,影响越来越大,当时文坛上几乎无人不知北大有这么个论坛,有一群人在傻傻地读文学期刊。然而,这个工作越做下去我的内心越是惶恐。因为,对期刊了解越深我的失望也越深,这些号称支撑中国主流文坛的作品,离我心目中的当代文学距离太远。在我的定义里,当代文学最根本的属性是它的当下性,优秀的当代作品必须传达出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焦虑和希望,负载这个时代最丰富饱满的信息和元气,并且找到一种最契合这个时代的文学形式。这种“当下性”其实就是“时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文学经典在它诞生的时代都是“当代文学”,经典的超越性是穿透了那个时代,而不是逃离了那个时代。还是那句老话:不熟知一个时代的气息如何勾画一个时代的灵魂?而我们的期刊文学却常常是自说自话,它甚至不是一个遗世独立的象牙塔,而只是一个与时代脱节的小圈子。更让人悲观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不在作家而在体制,那个曾经让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期刊和专业/业余作家体制,由于市场化转型的失败、片面追求“纯文学”理念等多重原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功能障碍乃至坏死,大量的读者和业余作者流失,特别是年轻人大量流失,伴随着圈子化的是老龄化和边缘化。这样的土壤怎么能产生真正的当代文学?而能产生当代文学的土壤又在哪里?我在失望中一步步陷入绝望。这是我的绝望时刻。
于是,我把目光转向了网络文学。那是2010年前后。这时的网络文学经过十余年的飞速发展已经非常强大,读者接近两亿,作者号称百万。“盛大文学”已经成了网络文学的“航空母舰”,发出“谁更能代表主流文学”的挑战。按照业内人士的估计,此时网络文学与期刊文学的实力对比,大概是作者百倍之,读者千倍之。不仅如此,网络文学在十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生产—分享—评论”体系,形成多姿多彩的粉丝部落文化,这一切都对运转了六十年的主流文学体制和延续了近百年的“新文学”传统发出挑战。然而,对这一切,无论是主流文坛还是主流学术界,都几乎是漠然的。傲慢与偏见让我们视而不见。所以,当我停办当时已成为品牌的“北大评刊”论坛,转向网络文学研究时,很多人惊讶、不解,甚至认为是一种背叛。我也说不清我为什么要研究网络文学,让我跳下去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如果说有什么希望,就是我相信文学不会死,如果它已经不在我熟悉的地方了,那就一定在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生长。
第一次在北大开网络文学的研究课程确实是一场学术冒险。因为,对于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所有选课的学生都比我这个老师懂得多。他们懂,但是他们不敢说。在他们的阅读经验里,读网络小说一直是一件不务正业的事,特别是上了中文系,在经典的威压下,更是上不得台面。我对学生们说:“让我们先把所有的金科玉律都放在一边,回到一个朴素读者的本心。”我们说,“北大是常维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我们不必刻意维新,但要敢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当年胡适等“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就是把引车卖浆者流读的白话小说列为正典,20世纪80年代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们一边读卡夫卡一边读金庸,老师们是在学生们的引领下才开始研究金庸小说的,之后才有金庸的经典化。我们要用我们的胆识和学识来守护本心,对于那些曾经陪伴过你、温暖过你、激励过你的作品,要心存感激。如果你觉得它们有价值,就要去捍卫这价值。不管有多少权威称它们是垃圾,你都要敢于质疑,这些权威背后的“天经地义”是从哪里来的?“从来如此,便对吗?”
在我的鼓励和怂恿下,学生们拿出了他们深藏的最爱。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惊喜。老实说,这四年来不是我在给他们开课,是他们在给我开课,至少是我们在共同学习。作为老师不是不惭愧的,学生们安慰我说:“老师,我们的课堂才是真正web3.0时代的,用户自己生产内容!”他们让我真正理解了一个词:有爱——这是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所有粉丝文化的核心概念。和他们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因为我相信,爱在哪里,文学就在哪里。
进入网络阅读后,我也有了我自己的最爱,并且把它们与儿子分享了,他当时正上小学。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金庸和网络小说是我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借助那些故事和人物,我们聊做人,聊处世,聊底线,聊情怀,聊什么叫兄弟,聊什么是真爱。每当有人问我网络小说有没有正能量时,我就会说我儿子就是看网络小说长大的。也经常有学者问我,现在的网络小说中有没有接近金庸的水准的?我的回答是有的已经超过了。类型小说本身就是要不停地升级换代,现在网文中最优秀的作品不但在文学的精彩方面不输于金庸,而且更具有丰满的当下性。他们对制度的反思、对文明道路的思考,都是以中国当下的处境为出发点的,这是阅读金庸小说不能替代的。并且网络的互动性是报刊所不能及的,每一个优秀作家身边都聚集了一圈精英粉丝,这些粉丝里有不少也是各行各业的精英,“网络性”使网络文学必然在某种意义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也是当年史诗、神话的生产方式。当然,这样优秀的作品在浩如烟海的网络小说中堪称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小说都是供人YY(意淫)的。但我们也不能低估这些YY(意淫)小说的功能。网络文学发展的这些年,不但中国正处于道德恐慌期,全世界都处于“启蒙的绝境”的精神危机之中,人们不得不回到“黑暗森林”,重新探索生活的法则。网络文学的种种“类型文”不但分门别类地满足着人们的心理需求,形成了一套“全民疗伤机制”,并且在“爽”的基础上重建道德底线。这些道德很朴素,很原始,一点也不高大上,却是在欲望深处升起来的,特别靠得住,是重建“主流价值观”的基础。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挖掘、总结的。
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迷惑。最重要的迷惑有两个。首先,虽然我们一直强调要入场研究,要创建一套独立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和批评话语,但我们如何摆脱经典文学体系内的雅俗秩序?网络文学就是通俗文学的网络延续吗?第二,我们鼓励以“学者粉丝”的身份进行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如何确定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我们要告别精英情怀吗?这两个迷惑直到我读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时才有豁然开朗之感。
被誉为“先知”的麦克卢汉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具有“哥白尼式革命”意义的媒介理论。它提醒我们跳出哺育我们长大的印刷文明的局限,从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大局观”审视人与媒介的关系。从媒介革命的角度出发,网络文学真正颠覆的不是雅俗秩序,而是构造雅俗秩序的印刷文明自身。未来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的其实是“纸质文学”而不是网络文学,因为网络是电子文明的主流媒介,今天以印刷形式存在的各种文学都将进入网络移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文学的重心在“网络”而非“文学”——并非“文学”不重要,而是我们今天能想到的和想象不到的“文学性”,都要从“网络性”中重新生长出来。如果我们把“文学性”比喻成精灵,它从竹简、从绢帛、从手抄本、从印刷书籍,以及从网络屏幕中钻出来,面目肯定是不一样的。所谓“内容一经媒介必然发生变化”,这正是麦克卢汉那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的核心要义。
麦克卢汉理论给我的更重要的启示是,他认为,在媒介变革之际,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新媒介打击彻底降临之前,引渡旧媒介的文明成果。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常使人误解他在欢呼印刷文明的崩解。恰恰相反,他一再警戒媒介变革可能带来的文明中断。如16世纪古登堡印刷技术兴起时,当时注重口头传统的经院哲学家没有自觉应对印刷文明的挑战,很快被扫出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印刷术的爆炸和扩张,令很多文化领域陷于贫乏。在媒介革命来临之际,要使人类文明得到良性继承,需要深通旧媒介“语法”的文化精英们以艺术家的警觉去了解新媒介的“语法”,从而获得引渡文明的能力。
麦克卢汉的启示让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真正使命,这是我的“顿悟时刻”。我们研究网络文学不是为了割裂文学传统,恰恰是为了延续文学传统,而我们的入场式研究可以是一种引导式的介入。当然,在网络时代任何精英的引导都必须是自下而上式的而不是自上而下式的。我们必须从“象牙塔”进入“控制塔”,按照网络文学场域自身的逻辑去影响网络文学的发展。只有这样,精英批评的“引导”才是真正有效的。
2014年对于网络文学发展而言是十分关键的一年,经过十几年的爆发,网络文学的发展格局在这一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声势浩大的“净网”行动和同样声势浩大的“资本”行动,让网络文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至此,网络文学才真正从某种意义上的“化外之地”成为了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学场”。在这里,至少有三种核心力量在博弈——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网络文学“自主力量”,同时还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就是媒介革命的力量。如果说,媒介革命的力量曾是网络文学发展的内在 “核动力”,随着媒介革命的深入,ACG(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电子游戏Game)产业文化的兴起,以文字为载体的网络文学还是最受大众和资本“宠爱”的文艺样式吗?在“有钱”的挤压下,“有爱”的“粉丝文化”会受到什么影响?原生的“网文机制”又会受到什么影响?如果网络文学要被纳入“主流化”的进程,这个“主流化”和网络文学自身的“部落化”又构成什么样的关系?随着媒介革命的深入,网络文学需要重新定位。网络文学能否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寻找到自己的新位置,承担起新使命,不仅影响着自身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需要以之为“孵化器”的其他文艺形式的发展。
在网络文学场域的三方博弈中,我们学院研究者要坚定不移地站在网络文学“自主力量”这一方。当务之急是总结研究网络文学发展十几年来的重要成果(包括优秀作品、生产机制、粉丝社群文化等),特别是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经典性的作品,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和批评话语,并在一个广阔的文学史视野脉络里,确立网络文学的价值意义。在这一批评体系主导下推出的“精英榜”必然有别于商业机制主导的“商业榜”,同时也必然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主导的“官方榜”。
总之,媒介革命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如何使印刷时代的文学星光继续在网络时代闪耀,如何将“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连通,将粉丝们的爱与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爱连通,让文学的精灵在我们的守望中重生——这是时代对我们这些当代文学研究者提出的特殊挑战,也是知识分子无可推脱的责任担当。
作 者: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生产机制研究和文学前沿研究,2009年开始由文学期刊研究转向网络文学研究,2011年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网络文学研究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