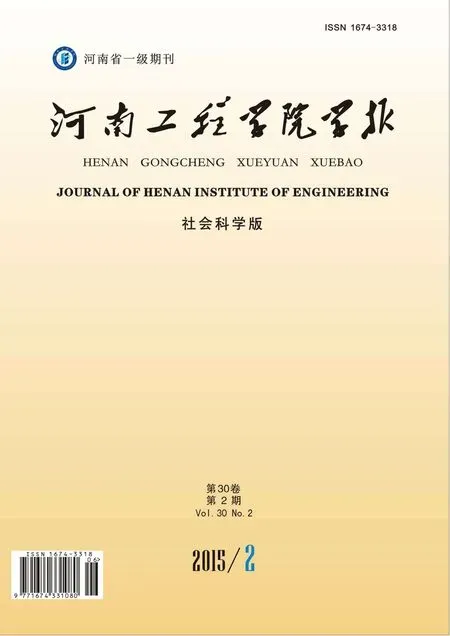论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
欧阳爱辉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湖南衡阳 421001)
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指刑事诉讼中,在网络环境下以非法手段取得之证据不得采纳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根据。①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当涵盖民事诉讼领域,但笔者在这里仍持通说,将其限定于刑事诉讼范畴。对国内学界相关理论观点争论,具体可参见张立平的《中国民事诉讼不宜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对传统社会刑事诉讼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最重要的证据法规则,它能有效防止国家公权力滥用并妥善保护被追诉人正当权益。但当人类社会全面迈入信息时代以后,网络和各类数字化虚拟信息逐渐替代传统工具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学习的最主要媒介。而通常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着重点往往更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传统证据,它未必能充分适应数字虚拟化的网络环境。故在这种情况下,与时俱进建构一种同信息时代相吻合的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显然迫切需要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一、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的必要性
较之通常意义的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言,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顾名思义主要关注对网络环境中的非法证据进行否定。其建构之所以成为一种必要,无疑同信息社会网络环境普遍出现息息相关。
第一,信息社会的网络证据运用日益广泛。在以计算机和有线、无线互联网络为主要表征的高科技信息社会,人体感觉器官无法直接与之发生接触的虚拟电子数据信息俨然已经成了社会交往的最根本性媒介。譬如网络购物会出现大量电子购物信息,网络通信会留下众多电子信息,即便仅仅是最简单的浏览网络页面,也会产生难以计量的虚拟网页浏览信息……证据作为能证明某事物真实情况的事实或者材料,[1]由于信息社会交往中用来佐证真实性的事实、材料很大程度上是由网络虚拟电子数据构成,所以各类案件内的证据有很多都是由网络证据构成。有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更是顺应时代要求将电子数据列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所以网络证据作用便愈发重要和关键。
第二,网络证据很难根据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可采性评断。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从其雏形“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追根溯源,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2]它要排斥的非法证据主要包括两种——非法实物证据和非法言词证据。但一项二百多年前就已确立的证据法规则要尽善尽美地适应21世纪信息社会的司法,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毕竟二百多年前的“实物”和“言词”与今天信息社会中某些比比皆是的电子数据信息难以画等号。譬如传统意义的“实物”往往指实体有形可以被人的感觉器官触摸的物品,这样一来虚拟财产就不能被视作“实物”;传统意义的“言词”往往指人们口头直接交谈或者借助纸质媒体、电话、传真等方式展现的信息,可此类界定模式便令虚拟的网络交流(微信、QQ等)无法纳入“言词”范畴。而这些虚拟电子数据既然不能被分门别类归纳到“实物”和“言词”中,就势必意味着它们无法被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容,令网络证据可采性评断彻头彻尾沦为一句空话。
二、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建构设计
从前述可知,在信息社会网络证据运用日渐广泛,并且网络证据很难借助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展开其可采性评断。“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3]既然社会自身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为了能在有效查明刑事案件规制犯罪的同时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适应新时代需要打造与信息社会相对应的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然非常重要。具体而言,笔者认为,这种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可从以下几个环节着手:
(一)确立基本指导原则
基本指导原则是贯穿某特定活动始终需遵照的基本性依据。对建构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说,其基本指导原则理当为保护网络空间自由权。Internet作为一个开放共享、快捷便利的人际交往虚拟空间,它最大的正面价值便是充分彰显个体自由,但若完全放任自由,又会像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那般一发不可收拾。所以网络空间立法就如同市场经济要求以自由经济为基础、国家必要干预为辅助一样,必须以维护网络自由为主体、国家进行必要管制为保障。放置到网络环境非法证据排除上,也即强调排除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可采性是出于对网络空间自由权的保护,以确保网络交往自由。换言之,在网络非法证据排除上,应时刻强调网络空间自由权的保护。倘若某些非法取证行为严重损害网络空间自由权,就要受到排斥;若某些非法取证行为对网络空间自由权(网络隐私权、网络通信自由权等)损伤并非特别严重,它的存在是以牺牲个别网络空间自由权(网络隐私权、网络通信自由权等)来维护更大层面的社会整体利益,则可适度容忍,不必排斥。
(二)设定排除范围
遵循当前各国设立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流模式,其证据排除范围大多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两大类。考虑到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有别于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最大区别仅是数字虚拟环境与传统现实环境的差异,故要建构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可大体照搬传统模式——即将证据排除范围设定为网络言词证据和网络实物证据两大块儿。其中,网络言词证据主要指借助BBS、微信、微博、QQ、陌陌、电子邮箱等各类互联网平台或通信工具彼此进行虚拟交往所产生的虚拟化表述信息;网络实物证据则主要指在网络空间交往中彼此间涉及的虚拟财产(游戏道具、装备、虚拟货币等),各类同虚拟财产相关的重要信息(如银行账号、密码、网上注册身份信息、网上登记出入境信息等),以及与网络交往直接相关但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实体物品(如在网上达成交易而在现实中交付的豪车等)。假设获取这些证据的方式违法,造成了较大网络空间自由权损害,它们就可列为非法网络言词证据或非法网络实物证据。
(三)明确网络非法证据排除的提出主体
究竟谁有资格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这对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同样意义重大。毕竟若无人提出需进行排除或提出的主体太狭窄,都将不利于网络空间自由权保护,破坏司法公正。但反过来,提出的主体过于宽泛也会阻碍刑事诉讼高效进行。笔者认为,若以违法方式获取的网络证据被法官采信,就难免会给刑事诉讼相关当事人造成不利影响,故在提起主体上,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方(包括公诉机关、被告追诉人、被害人或自诉案件原告等在内)都应享有提起权。法官作为审理案件的第三方,倘若发现了网络证据合法性问题,也可据职权提起。此番做法,还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1)》第四章第八节的内容保持了一致性,无疑具备相关实践操作价值。
(四)规划网络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
在网络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流程上,鉴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6—58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1)》第四章第八节已经就传统非法证据排除具体操作程序作了较详尽的规定,而网络非法证据与传统非法证据更多是证据表现形态的不同,所以在网络非法证据排除具体程序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传统经验,直接适用传统非法证据排除具体操作程序。
(五)设置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
对非法证据排除具体程序,考虑到与传统非法证据排除的共性,可以照搬传统规则。但在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上,因网络证据是虚拟电子化形态,比传统证据要复杂,故其要求与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所不同。
首先,就证明责任来说,尽管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7条已经指出“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且公诉机关力量要远远强于被追诉方,但是鉴于网络证据不像传统证据那般真实存在和一目了然,特殊情况下亦要将部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追诉方。例如,当网络电子数据很多,以元数据或操作系统伪影等非直观形态出现时,检察机关根本没有这么多精力去完全注意到,[4]那么证明责任就应适当转移给被追诉方。此外,若是刑事自诉案件,考虑到双方都处在平等对抗中,就宜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要求各自承担相应证明责任。①有必要指出的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限定范围学界一直存在多种观点。有的认为,应仅包括国家公权力机关非法取证;有的则认为,普通私个体非法取证同样应囊括其中。由于公权力主体和普通私个体非法取证都将造成对相关人员合法权益之侵害,故笔者赞同后者观点。对于前后两种不同观点,可分别参见杨缨:《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犯罪研究》2005年第1期;秦宗文:《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获取的证据——兼对证据合法性的批评》,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7期。
其次,就证明标准来说,作为举证责任应达到的证明程度,它必须强调可行性和经济性。在美国刑事诉讼过程内,即要求所谓“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1)》第99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召开庭前会议……”据此不难推断我国要求排除非法证据也是对证据收集合法性存有疑虑。故在证明标准上,若被追诉人等提出的证据达到了有理由怀疑非法取证存在的程度,即可认定符合证明标准;而被有理由怀疑实施了非法取证方(不论是国家公权力主体还是普通私个体),提出的证据必须达到了确实充分证明收集完全合法的程度,才可被认定符合证明标准。毕竟被有理由怀疑实施非法取证方对自己的取证手段更容易举证,且在中国语境内他们大多为国家公权力主体,对其适用较高证明标准也是合适的。[6]
(六)明确除外范畴
世间所有事物都须依照具体情形实施个案微观特殊分析,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也不例外。当设定基本指导原则、排除范围、提出主体和具体程序等重要制度后,立法还应对某些特殊情形下可适度容忍、不采用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排除的除外范畴进行规范。毕竟这也是与其基本指导原则相吻合的,因为要保护网络空间自由权就决不能仅瞄准非法取证本身,更需从宏观层面实施全方位平衡考量。从网络交往特殊性出发并参照西方发达国家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成功实践,笔者认为,应排除的主要有下列几类:
其一是善意的网络非法取证。即公权力机关或其他私个体主观上是善意地收集网络证据,并没有故意违反法律。尽管此类证据最终被定性为非法证据,但依旧具备可采性。譬如侦查人员误认为开展网络监听已经办理了严格审批手续,而实质上相关手续因他人原因导致存有瑕疵,届时通过网络监听获取之证据虽然非法,但仍有可采性。
其二是对方事后表示同意的网络非法取证。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揭示了从强制化到契约化的过程,[7]倘若公权力机关或其他私个体借助特殊软件截获他人电子邮箱中的信息事先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但事后相关人员对此等行为表示同意或者主动作了与截获信息一致的陈述,则该证据同样具备可采性。虽然公权力机关或其他私个体事先行为违法,可事后相关人员表示了同意或者自愿对被截获的信息作了阐述,也即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身权利(“同意”意味着其放弃了网络隐私权等权益)或这种证据获取有必然性(“自愿阐述”表示即便没有事先的非法取证,我们依旧可获得该证据)。不过,此刻必须确保相关人员是发自内心之真实意愿。假如他们的同意是受到了公权力机关或其他私个体威逼利诱所致,则仍要排除证据可采性。
其三是基于公共安全紧急需要的网络非法取证。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指导原则是保护网络空间自由权,但这种自由权决非某一单独或少数个体的权益,它同时也覆盖了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假设某些特殊紧急情况下,公权力机关或其他私个体来不及办理严格审批手续,而犯罪行为人正利用网络积极谋划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如“东突”或其他恐怖组织正凭借网络平台策划大规模恐怖主义犯罪),事发突然,为有效遏制犯罪,此刻获取他们的QQ、微信等隐私通信信息自然有着证据可采性。“它反映了立法者惩治犯罪的客观需要,从而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目标做出的一种平衡。”[8]
三、结语
信息社会和互联网给生活带来的变革令人们难以估量。鉴于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很难完全适应信息时代之迫切需要,我们理应从当前时代脉搏入手,构建科学严密的网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有这样,刑事司法才能真正走向完善化与科学化。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60.
[2]杨缨.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J].犯罪研究,2005(1):66-74.
[3]解兴权.通向正义之路——法律推理的方法论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5.
[4]陈永生.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的法律规制[J].现代法学,2014(3):111-127.
[5]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外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21.
[6]杜学毅.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126.
[7]宋志军.刑事证据契约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
[8]雷超.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