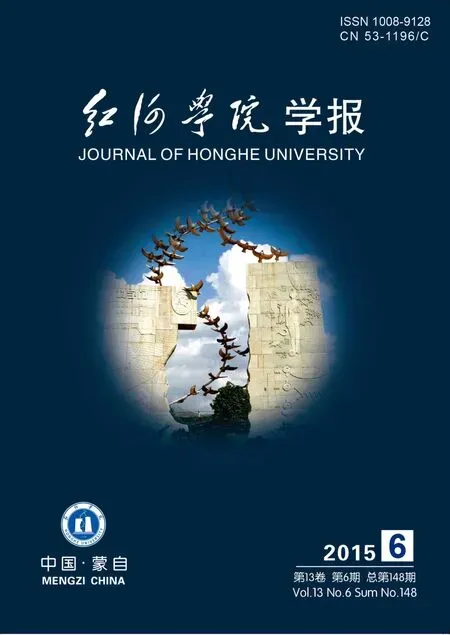论路翎小说人物境遇的原始生命力书写
田德芳,马 帅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西安 710100)
引言
自新文学出现以来,文学界对原始生命力的呼唤不绝于耳。早在五四初期,闻一多先生就说:“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应该拿出人性中的最后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阴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1]鲁迅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在作品描写了狮虎﹑鹰隼﹑狼﹑猫头鹰等意象作为野性和力量的象征。他说:“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家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以,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2]在理论呼唤下一部部表现原始生命力的作品接连问世,从周作人的新诗《小河》到艾青诗中孕育反抗力量的底层人民,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到艾芜笔下抛出正常生活的边缘流浪者,再到路翎小说里原始昏暗孕育反抗的矿区,从田汉戏剧里古谭的呼唤到曹禺笔下生命孕育其中的原野,现代文学形成了原始生命力书写的热潮。
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从理论到创作出现了原始生命力的呼唤,但是到目前为止,各界对原始生命力的内涵尚无一个准确的定论。较早对这个名词做出系统阐释的是美国著名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其在《爱与意志》[3]一书中,对原始生命力的含义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并指出原始生命力作为一种本能存在于世间一切个体身上,它控制着人类自身。作为一种本初的力量,原始生命力是能使个人完全置于其力量控制之下的自然功能,是一切生命肯定自身﹑确证自身﹑持存自身和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如性与爱﹑愤怒与激昂﹑对强力的渴望等。原始生命力既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而在正常状态下它同时包含这两方面。在这里原始生命力类似于荣格人性画像中的“阴影”,是一种强大的原形功能,是最好的东西和最坏的东西的发源地,是千百亿年来遗传来的未经驯服的动物精神,是能够掌握人的命运的一种狂暴的自然力。[4]虽然罗洛·梅比较系统准确的阐述了原始生命力,但他片面夸大了本能作为人行为的动因,而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
路翎在《饥饿的郭素娥》《燃烧的荒地》《卸煤台下》等表现原始生命力的小说中体现了罗洛·梅的观点,认为中原始生命力是指人追求合理存在的一种原始的本初欲望。这种本初的欲望低级阶段表现为对生存的渴望﹑性与爱的渴望,当这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要素得以满足的时候,就会表现为与社会和他人相互肯定的力量;当无法满足的时候,就会表现为对其认为不合理存在的强烈反叛。但是道德伦理社会规范等文明形成后制约着原始生命力的彰显,在路翎小说中体现为人物在生命异常的境遇中,原始生命力量受到道德压抑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这种悲剧的产生源于人物反抗的盲目性、冲动性以及无法超越道德的压抑,具有崇高的美学意义。
一 生命异常的境遇
路翎表现原始生命力书写的小说中,人物大都处于异常的境遇,异常境遇既包括特殊的自然环境,也指社会家庭环境对生命力量的压抑扭曲。身处异常境遇下的生命生理欲求和心理欲求得不到满足,造成生命力的压抑或者反抗,从而释放自身原始的生命力量。由此可见异常境遇是孕育原始生命力的温床,是促成生命历程改变的要素,异常境遇的书写与表现人物原始生命力相得益彰。异常境遇表现在环境上。
(一)特殊的自然环境
这种环境通常与作品中的人物生命特征相对应。自然环境的草木、山水都涂抹上了人的情感,带上了生命色彩,成为表现创作主体情感和渲染人物生存环境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内容。路翎在《饥饿的郭素娥》中这样描写深夜:“夜快深的时候一切都寂静了,只有那大铁锤的急速而沉重的敲击声传的很远。深秋的月亮在山洼里沉静的照耀着。”[5]在《卸煤台下》这样写雷雨:“闪电刺破黑暗,把豪放的洪流映成沉重的青色。雷响,山谷震撼。”[6]在《平原》中这样写阳光:“阳光强烈的刺眼,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是笼罩着火焰一般的暑热:到处都反射着强烈的光,一切都显得辛辣、有力、鲜明,在深沉的寂静中个个显示出它们的热烈得差不多就要昏迷的生命来。”[7]……这种自然环境的描写与创作主体内在的情感相遇合,与作品人物的特征相迎合,展示了顽强的生命强力。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为人物生命力的孕育提供了最好的温床,也与人物原始生命力的表现相得益彰。
(二)特殊的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封建王朝的解体并未带走延续了千年的封建传统,新旧思想的碰撞扩大了社会矛盾与家庭矛盾。路翎的《燃烧的荒地》中的何秀英,整天受赌鬼丈夫的打骂,丈夫死后成为寡妇。她为周围人所不容,邻里的歧视、叔嫂的压迫、地主流氓的侮辱以及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的丈夫刘寿春衰老无能,情人张振山自私乖戾,流氓黄毛的好色残忍,喜欢她的魏海清自私怯懦,使得她受尽煎熬悲惨死去。这样的社会家庭环境是原始生命力压抑的原因,也是人物命运转折的原因。郭素娥、何秀英、张老二、何德祥等在残酷社会和家庭压榨下奋起反抗,站在了封建社会和家庭的对立面,走向了反抗人性压抑的道路。
(三)其生理欲求和心理欲求得不到满足,具体为强烈的求生愿望和热烈的求爱欲望
按照马斯洛的观点,这属于马斯洛的需求五个基本层次中的生存需求、爱与被爱的需要,这与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卸煤台下》中的许小东家境贫困,还受到包工的逼迫;《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大烟鬼丈夫无法满足她的性欲和温饱,还残忍地迫害她;《燃烧的荒地》中的何秀英整天受到赌鬼丈夫的打骂……这些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无法满足,直接促使了生命历程的转变。许小东再鼓起勇气去偷锅,郭素娥出轨找了机器工人张振山,何秀英与张老二私自结合。他们不再安于现状、逆来顺受,而是扬起了生命的大旗,对威胁到他们生存,陷他们于非人境地的境遇开始绝地反抗,追求自身生存,追求美好感情。
二 无法超越的道德
道德作为约束本能的准则,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发展并逐渐编织起道德的牢笼,人的原始生命力受道德限制压抑,葛兰西曾说:“有谁能够算得清人们为了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社会而付出的代价呢?这种代价表现在人们生活中和由于本能压抑所造成的痛苦。”[8]道德伦理规范就是对原始本能的一种压抑。在原始生命力的书写中,受到压抑的人物,有的在压抑中丧失生命力,更多的则是在压抑中反抗非人的生存地位,绽放生命的光彩。在描写这种反抗中,作家放弃了对道德的尊崇,但是由于受到民族集体无意识影响,原始生命力的书写与道德的关系始终是跨越而不是超越,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情节的处理和人物命运的安排。
路翎在小说《卸煤台下》中清醒的表现出了对道德与原始生命力书写关系的认识。许小东“穷迫无依的家庭打碎了一只锅”,夫妻二人为此伤心不已,为了生存,机缘巧合的雨夜他产生了偷锅的念头,求生的本能与道德观念激烈博弈,“我想不到哟!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哟!不相信你无论问哪个,我想不到哟!”……“不然还不是别人拿去。不过顶重要的,是严成武啃剥我!我多么可怜!……哦!……”他跨过了道德的界限,“把锅笨拙地用长手臂抱在胸前,向坡下逃走。”生存的本能使他牺牲了自己的清白,“但是一个从背后轰过来的熟悉的声音把他底一切希望全粉碎了。”他的行为被人发现了,“公家底东西从许小东肚子上滑下来,跌到泥水里去,偷锅贼张开求饶的手,无声的哭嚎着。”[9]虽然工友们没有责备他,还把锅送给他,但固有的道德观念使他自责压抑,“我不能做人了,老哥!”为了生存他跨过了道德的界限,但他始终无法超越道德,从而背上沉重的道德包袱,责骂自己,打骂老婆,最后把老婆卖了,自己疯了,还少了一条腿。
从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论看,原始生命力是本我即最原始﹑与生俱来的无意识部分,它是不顾任何理性和伦理道德的约束而渴望发泄的本能冲动。伦理道德的文化则代表自我,按照现实原则来调节控制本我的活动,压制本我的非理性冲动。作家在表现原始生命力时,自我对本我的压抑造成人物心里的矛盾痛苦,因为原始生命力的强大,本我会突破自我的压抑,跨越过伦理道德,按照快乐原则去指导自己的行为,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把自己陷入非人境地的人物﹑环境等进行反抗,甚至以扭曲的方式发泄出来,例如偷盗、陷害、杀人等。而在“激情”过后,自我用现实原则代替了本我中的快乐原则,由自我引申出来的超我是道德化﹑理想化的自我,管制本我的非理性行动,奉行理想原则。[10]这种理想化﹑道德化的自我对本我冲动的行为作出道德评价,使得本我再一次陷入自我的压抑,并对此作出道德评价。这个循环过程既是作品中人物的,也是作家本身的。无论是文学作品中社会化的人,还是现实社会中社会化的作家,都无法摆脱,最终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人物跨越了道德的界限,但却无法完成对道德的超越,从而走向悲剧的结局。
三 不可避免的悲剧
原始生命力是存在于人自身原始的追求合理存在的一种本初欲望,这就说明原始生命力无论在表现上多么壮烈,也终究是原始的﹑初级的,是人们对社会,个体的认识处于感性阶段,缺乏理性和自我主宰。千百年来固有的规范与认识依旧强大,这种反抗虽然强悍凶猛,也必然因其被动性﹑盲目性﹑脆弱性而导致悲剧结局,而作家无法在潜意识中超越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的观念,使得原始生命力的书写中的悲剧不可避免。
《饥饿的郭素娥》是路翎张扬原始生命力的典型作品,“强悍而美丽”的郭素娥在逃荒过程中被父亲抛弃,成为比她大二十四的刘寿春捡起来的女人。这个男人吸食鸦片﹑毫无活力,给她带来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煎熬。五年之后,她“带着一种赤裸裸的欲望与期许”的眼睛,寻找到了身材壮实的机器工人张振山,并期望他能够带她去城市。随后他们的关系暴露,刘寿春的家族势力、流氓势力和地方政权的残酷压迫了这个“饥饿的”、在他们眼里违反伦理道德的女人。在他们面前渺小孤独无助的郭素娥爆发了原始生命力,她用碗砸中了刘寿春,“你们是畜生,你们要遭雷殛火烧,你妈的屄,我被你们害死,你们这批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还几乎掐死刘寿春的堂姐,即将折磨致死的时候依然发出了“做鬼也要杀死你”的呐喊。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死亡,“她用原始的强悍抨击了这社会的铁壁,她悲惨地献出了生命。”[11]
邵荃麟虽然称赞“这本书里充满着一种多么强烈的生命力”,但他也认识到“这样一种奴隶的原始的斗争方式,自然是要失败的”。[12]“失败”了的不仅仅是郭素娥,还有《燃烧的荒地》中的张老二,他虽然杀死了陷他于非人境地的地主,但自己也被枪毙;《卸煤台下》中的许小东为生存偷锅,最终卖妻,走向疯狂;《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中的王家老太婆为了买一套寿衣,在风雨夜与小猪的周旋中倒下。
在这些表现原始生命力的小说书写中,人物命运和结局大都具有悲剧性。这些悲剧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崇高,这是作家书写悲剧的意义所在。尼采说:“肯定生命,甚至在生命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13]在《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被蹂躏致死,“但她却扰动了一个世界”,张振山远走他乡,自私怯懦的魏海清在几年后与杀害郭素娥的凶手黄毛搏斗而死,多年以后的矿区人们依然记得这个美丽强悍的女人。在生命最异样的时候正面迎接死亡,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和人心的净化。
罗洛梅认为原始生命力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在原始生命力被体验为一种盲目冲动时为第一阶段,当原始生命力进入反对他人、攻击他人,迫使他人来迎合我的需要渴望时为第二阶段,当原始生命力成为与他人相互肯定的力量时为第三阶段。[14]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这种盲目性和冲动性的反抗,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和强大外来敌人的压迫下,他的脆弱性显而易见,必然导致其悲剧的结局。但是这种悲剧却迎来了第三阶段,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和尊严的活着,他们奋斗反抗致死,他们的悲剧折射出生命的意义,具有崇高的美学色彩,这是作家书写原始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悲剧的叙写是为了反证生存的可贵,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活着是为了生活的理想和理想的生活,并为之不懈奋斗。纵然面对死亡,也不退缩,在死亡中折射出生命的可贵。
路翎小说中这些狂野的生命,为现代文坛注入了一股强烈的生命力,使人们不得不有感于我们“种的退化”,“先民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中国人还是有棱有角,可怜自洪水泛滥之后,他的子孙,便完全淘成了烂泥了,凭空有了可塑性和服从性,要方成方,要圆成圆”。[15]我们的民族缺少的正如胡风评价路翎的“主观战斗精神”,他们“要借野性的呼唤,唤回现实中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已经失去的原始生命力,要求人们返回人的自然本质。”[16]他们有感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对生命的压抑,在艺术中对充满野性和活力的个体力量发出由衷的赞美。纵然他们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敌人的强大走向悲剧,但是这种悲剧是为了寻求生命的意义。他的实现与否并不重要,而在于追寻生命意义的过程中,这并不是鲁迅的“阿Q精神胜利法”,而是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生命的价值也就在此得以实现。作家礼赞“人一样的生活”,激烈的批判“文明的缺憾”,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意义得以升华为民族的国家的追求。正如评论家所说:“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大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17]
作家对于原始生命力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它是魔鬼与天使同在,兼具理性与非理性,创造性与毁灭性共存的,一味的放纵原始生命力,将会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原始生命力的写作后期,作家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他企图让野性的力量逐渐转向文明,即把蛮性向理性的转化,正如端木蕻良所说:“两个多棱的家伙(《科尔沁旗草原》中铁岭与李三麻子),写这两块顽铁,咋样被群众所改变,他两咋样成了精钢,成了中华民族在这次大斗争里面活的标本。”[18]他想要寻求把原始生命力整合到自我的人格之中,从而使得这些书写原始生命力的作品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1]杨守森.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5.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4.
[3]罗洛梅.爱与意志[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4]商磊.本能与道德[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4(02).
[5]路翎.饥饿的郭素娥[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7.
[6]路翎.路翎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221.
[7]路翎.路翎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11.
[8]葛兰西.葛兰西文选——“兽性”与工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51.
[9]路翎.路翎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14.
[10]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新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8-109.
[11]胡风.饥饿的郭素娥序[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4.
[12]邵荃麟.饥饿的郭素娥序[M].北京:北京文艺出版社,1993:64.
[13]尼采.杨恒达译.悲剧的诞生[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86.
[14]刘海洲.从原始生命力到现代人性的回归——评艾芜的<南行记 >[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1).
[15]端木蕻良.力量的世界[J].南开双周,4(7).
[16]刘志平,李晓明.生命的狂野与自由——解读现当代文学中的原始生命意识[J].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08,22(2).
[17]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300.
[18]马伟业.野性的呼唤:端木蕻良小说的一种文化选择[J].民族文学研究,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