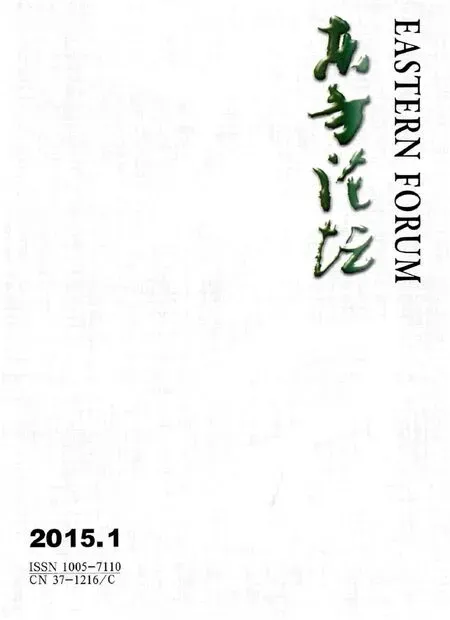赫德与李鸿章的恩怨
贾熟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北京 100006)
赫德与李鸿章的恩怨
贾熟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北京 100006)
赫德是英国人,李鸿章是中国人,赫德是总税务司,李鸿章是直隶总督,他们都效忠于清政府,都争取得到清政府的重用,他们都希望在中国近代化方面作出贡献。他们有合作的一面,但是,国籍、职位、年龄的不同,又使他们矛盾重重。他们的恩恩怨怨,都与中国晚清史上的重大事变息息相关,很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中国;英国;李鸿章;赫德;中国近代化
赫德·鹭宾(Robert Hart,1835-1911)[1](P730),英国北爱尔兰人,在中国,他以姓称于世。1854年7月来华,被分配到英国驻香港贸易督察处当翻译学员,10月,调至宁波领事馆任助理。1857年12月,英法联军陷广州。1858年3月,他奉调到广州,任英国领事馆二等助理及二等翻译。11月,升任正式翻译,1859年,被聘为广州新关副税务司,10月,升任税务司。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等逃往承德,10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1861年4月,总税务司李泰国要返英就医,推荐赫德代行其职权。李泰国(1832-1898),英国人,曾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英、法联军侵华时,担任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的翻译,后被南洋通商大臣任为总税务司[1](P320)。赫德到了上海,6月,又到了北京,得到了恭亲王奕的高度赞扬。7月,赫德劝清政府速购轮船、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命赫德代买。1862年3月,赫德致函李泰国,请李泰国在英国代清政府购轮船、军火。4月,福建延建邵道道员李鸿章统率其淮军到达上海,与太平军作战。清廷命李鸿章升任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出身进士,后因镇压太平军、捻军、办理洋务之功,曾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大学士[1](P322)。
1863年1月,李泰国与英国海军军官阿思本订立合同,中国所购兵轮由阿思本全权指挥,不直接接受中国政府之命令。赫德认为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种办法的,但是,李泰国仍然坚持己见[2](P57)。阿思本为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舰队,又称“欧洲舰队”“吸血舰队”,由中国政府耗资白银二十一万三千两购买之七艘兵轮组成,用来助攻太平军,定期四年。初议由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提出[1](P374),6月,赫德与李泰国到了北京,向总理衙门大臣奕等报告了此事的经过。奕等征求江苏巡抚李鸿章等人的意见,李鸿章赞扬赫德而贬低李泰国。两江总督曾国藩在8月给李鸿章的复信中写道:“前见台端致总理衙门书,伸赫德而抑李泰国,以为操纵有法,权衡至当”[3](第6册,P3886)。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进士。以镇压太平天国、镇压捻军、办理洋务新政之功,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大学士,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1](P702)。9月,阿思本舰队抵达上海,清朝政府任命总兵蔡国祥为总统,阿思本为帮统,归曾国藩、李鸿章节制调遣。李泰国、阿思本认为与原订合同不符,引起双方争执,亦为美、法、俄等国公使所不满。11月,清政府奕等人同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意见,将阿思本舰队解散,全部兵船遣回英国,买价银二十一万三千两(合七万一千英镑)仍由英国交还,另与阿思本银一万两,将自称为清政府代表的李泰国革职,以赫德继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奕(1833-1898),爱新觉罗氏,为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奕之异母弟,封恭亲王,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后又曾受命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P539)。12月,洋枪队统领戈登引诱太平军苏州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刺杀主将幕王谭绍光,献出苏州城[4](P368)。郜永宽等要求李鸿章保举他们担任总兵官,李鸿章即将郜永宽等杀害。戈登认为李鸿章杀降是不道德的,要把李鸿章抓起来当作俘虏。英国提督柏郎与戈登商定,常胜军归他节制,不再对太平军作战。戈登(1833-1885),英国军官,参加过英法联军侵华的战争,曾抢劫并焚毁圆明园,继白齐文之后,担任常胜军统领。清政府曾赏给他穿黄马褂,升他为提督,后在非洲苏丹任殖民总督,被苏丹起义军击毙[4](P367)。清政府总理衙门派赫德前往调解李鸿章与戈登的纠纷。1864年1月,赫德到苏州拜会了李鸿章,认为李鸿章杀降杀得对,又到昆山,找到了戈登,多方解劝,2月,赫德与李鸿章、戈登在苏州达成协议,戈登答应在春节之后,重新加入对太平军的战争;李鸿章宣布承担苏州杀降的责任,说明杀降一事,戈登在事前一无所知。李鸿章在请求清政府给赫德升加按察使衔的奏折中,首先列举了他“经理洋税,接济饷需,用资战胜”太平军的丰功伟绩,接着,又极力夸奖他赞助戈登进攻太平军十分卖力[2](P68)。4月,赫德奉奕之命至常州,办理常胜军解散事宜。6月,常胜军已经解散,戈登即将回国,李鸿章致函戈登,相约在戈登回国之后,双方继续保持联系,仍请由赫德处转寄[5](P374)。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归于失败。8月,清政府赏给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伯爵。12月,赏给赫德按察使衔,赞扬他接济清军军饷,调停常胜军之功[6],批准了李鸿章的请求。
1865年,中国海关在赫德等人精心管理之下,已从1861-1863年每年收入的500万两增至每年700万两,成为清政府仅次于田赋的最大收入[7](1,P672)。1868年8月,捻军失败。清政府命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1869年11月,赫德以办理北京同文馆之功,被清政府赏加布政使衔。1870年8月,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担任直隶总督,从事对外交涉事宜。1872年6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1873年2月,同治帝载淳亲政。1875年1月,载淳病故。2月,英国翻译官马嘉里自蛮允往迎柏郎,行至户宋河被杀害。5月,清政府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6月,又命李鸿章之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前往云南查办马嘉理案。赫德毛遂自荐,表示愿在中国与英国之间担任调停之责。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催请提京审讯马嘉理案人员,接着,又下旗出京,以战争相威胁。威妥玛(1818-1895),英国外交官,汉学家,英国陆军出身,参加过鸦片战争,曾任英国驻华汉文副使、驻上海副领事,英国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汉务参赞),公使,归国后,曾任剑桥大学第一任汉文教授,编有《英汉字典》,著有《寻津路》《语言自迩集》等[8](P497)。7月,赫德至天津会晤李鸿章,调解马嘉理案,又到上海会晤威妥玛、梅辉立,劝他们到烟台与李鸿章谈判,同时也通知了李鸿章。清政府即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命即赴烟台。梅辉立(1831-1878),英国外交官,生于澳大利亚,曾任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学生、汉务参赞,著有《棉花传入中国记》《中国辞汇》《中国政府——名目手册》《中日商埠志》《中外条约集》等书[8](P321)。8月,赫德与威妥玛一同到烟台,与李鸿章谈判。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由于我的建议,伟大的李已被派到这里‘全权’对付威妥玛,我们将尽力在这里解决问题。……威妥玛的态度有引起战争的危险。他的首席顾问梅辉立是好战的,据说在各方面都比巴夏礼爵士本人更巴夏里。……如果不能在这里使威妥玛就范,我们就必须那么办了。……威妥玛和我本人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他生气了,现在我们之间只是见面点点头而已”[7](1,P434)。在赫德看来,经过他的调解,在中国和英国之间,避免了一场战争。金登干(1833-1907),英国人,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委巡各口款项事税务司,总理文案税务司。经赫德推荐,又担任了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主任。他曾代表清朝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中法议和草约》,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中葡里斯本会议草约》。清政府曾授给他二品顶带[8](P70)。巴夏礼(1828-1885),英国外交官,曾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曾任驻上海领事、驻华公使、驻日本公使、驻朝鲜公使[8](P375)。9月,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规定中国对马嘉理案赔款、谢罪,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重庆为通商口岸。
1877年1月,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等抵达伦敦,对金登干的工作高度赞扬。5月,郭嵩焘致书李鸿章,请赶办铁路、电报以树富强之基。1878年9月,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复函,支持赫德试办华洋信局。当时,赫德已派令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在天津试办。德璀琳(1842-1913),德国人,他在天津工作了三十余年,曾十次担任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是赫德的亲信,同时,也是李鸿章的亲信[8](P110)。华洋信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际邮政局。
1879年3月,日军侵入琉球,4月,改琉球为冲绳县。赫德拟作中国海军总司令,中国海军分为两支舰队,分隶南北洋水师,而用人、支饷、造械诸事,则集中由他以总海防司的身份兼而管之[7](1,P682)。总理衙门函告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宝桢等,征求意见。李鸿章幕僚薛福成于8月10日,上书《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他写道:“顷见总理衙门来书,将以赫德总司南北洋海防,……详绎总理衙门之意,岂不以中国创办水师,久无成效,而倭人发难,擅废琉球,外倭日逼,亟图借才异国,迅速集事,殆有不得已之苦衷。……夫赫德之为人,阴鸷而专利,怙事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赫德一人之手,……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复如今日之可驭矣!……宜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遥制,须令亲赴海滨……其送税务司一职则别举人代之,赫德贪恋利权,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9](P53)。薛福成(1838-1894),字淑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曾充曾国藩、李鸿章幕僚,曾任浙江宁绍台道道员、湖南按察使,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1](P760)。9月3日,李鸿章与沈葆桢采纳薛福成的意见,联名函达总理衙门,不赞成赫德总司海防。总理衙门以此说转告赫德,赫德果然不愿放弃总税务司的职权,总海防司之议遂罢。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福建闽侯人,出身进士,曾充曾国藩幕僚,历任江西九江知府、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1](P370)。11月,李鸿章经赫德在英国订造之“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舰,在英国海军副将琅威理统带下到达大沽口。琅威理(1843-1906),曾任英国水师总兵。李鸿章曾聘任他为北洋舰队顾问兼副提督,训练水师[8](P271)。
1880年,中俄因伊犁交涉,关系紧张。1月29日,赫德致函李鸿章,论防御日本之策,认为南北洋应该设置海、陆军三处备战。3月27日,赫德电令金登干,为李鸿章购爱普西隆型军舰五只。5月27日,又电令金登干为李鸿章购递送公文使用的快船及枪械若干。6月4日,清政府由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函商,再经过赫德,电召戈登来华,商议对俄办法,当时,戈登在印度。7月21日,戈登到天津会晤李鸿章,商议对俄办法。赫德恐此举触俄国之怒,曾阻止戈登来天津,为戈登所不满。25日,戈登自天津赴北京,到北京后,拒绝与赫德见面,并写信给英国公使、法国公使,谴责赫德[2](P202)。8月2日,戈登自北京到天津。5日,向李鸿章条陈二十件事,大都与办理交涉,力图自强,先练陆军,普设电报,自管关税诸大端有关者。自管关税,就是不许赫德继续担任总税务司了。9日,戈登因为与赫德有隙,不愿再留,威妥玛亦劝其速归,离开天津归国。临行,告诉李鸿章,倘中俄开战,仍可来华帮助打仗。12月27日,李鸿章奏派督操北洋炮船记名提督丁汝昌等赴英验收新购之“超勇”“杨威”二船。丁汝昌(1836-1895),字禹廷,安徽庐江人,初隶长江水师,曾任海军提督,统率北洋舰队,甲午战争战败,在威海卫与日军激战,击沉日舰七艘,然后服毒自杀[1](P6)。
1881年11月,丁汝昌与总教习葛雷森率领巡洋快舰“超勇”“杨威”回到大沽口,李鸿章登舰试航到旅顺。12月,李鸿章奏准以记名提督丁汝昌统领北洋舰队,清政府授赫德以头品顶带。葛雷森是英国人,通晓汉语汉文,曾在英国海军服役。1870年,进入中国海关,曾任海关缉私大巡船“飞虎”号管官,曾在天津开办一所水师学堂,主管一艘教练船,培养海员,得到李鸿章的信任,清政府授予总兵衔,派为北洋海军总教习,地位仅次于海军提督丁汝昌。这又引起赫德的不满,认为葛雷森是脚踏两只船,投靠李鸿章,对他忘恩负义,于是他又向李鸿章推荐了琅威理,被李鸿章任为北洋舰队总查。葛雷森不愿在琅威理手下工作,回英国休假两年,回到中国后,赫德又派他为委办缉私船税务司。1890年10月,葛雷森在英国病故。赫德请金登干参加了葛雷森的葬礼[10](P27)。
李鸿章通过赫德购买了一些炮艇和巡洋舰,后来,一提起此事就反感。1883年7月19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在购买这些舰船上我们做得对,我感到十分满意,但李从未公平对待这些船,既没适当地保养,也没很好地配备船员。我听说李一提起这话题就反感,李虽是个大人物,但缺乏经验而且容易受人影响。当他自己不会使用一件东西时,他就相信那个说这个东西不能用的人。因此,他从上海回来,那里所有的人都宁愿他通过他们去买,以让他们得到捞油水的机会,他头脑里装满上海的言论,这些话自然都是反对这种舰艇的”[7](3,P313)。
赫德也讨厌李鸿章听德璀琳的话。1883年8月2日,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保密:有一次人家告诉我,德璀琳劝李听从我的劝告,但把事情交给别人去办。我给李送去了伦尼浮坞的详细说明等资料,现在报纸上说什么切青将提供一座浮坞!这就是已经证明了的”[7](3,P321)。
1884年,由于法国侵略越南,中法关系紧张。德璀琳在赴广州途中,与法国舰长福禄诺同行,福禄诺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和解,德璀琳电告李鸿章。3月,李鸿章命赫德电促德璀琳从广东北上,商议中法交涉问题。德璀琳到天津后,赫德致电金登干,命他秘密探询法国总理茹斐礼对中法和议的具体条款要求,暗中插手中法和议[7](3,P529)。5月,李鸿章与法国水师总兵福诺在天津订立《天津简约》五项,亦称《中法会议简明条款》。6月10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李一向认为我是他的批评者,而不愿我的势力太大,他利用我的下属来反对我”[7](3,P560)。7月5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又指责德璀琳不该插手中法谈判,李鸿章办事含混,订约不详,把事情弄糟了[7](3,P577)。清政府聘赫德作中法之间的调解人,到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他一味压清政府对法赔款,江苏士绅深为不满,电李鸿章要求调回赫德。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表示:“赫无坏意,似勿急调回。”总理衙门仍于8月将赫德调回北京。下诏与法国宣战[7](3,P592)。
1885年1月,赫德命金登干赴巴黎,以交涉被扣海关船为名,实际上是商办中法和议。2月17日,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我正抓住冲突双方‘死不放手’,我得把事情亲自抓在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唯一机会,我甚至不让大人物李鸿章知道,也不让他插手此事”[7](4,P25)。4月,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代表毕乐签订《中法和平草约》。李鸿章被排斥,自然不会快意,于是就利用英国任命赫德为驻华公使来动摇法国对赫德的信赖。这种做法丝毫不着痕迹,所以赫德认为是李鸿章打击他的巧妙手法[7](4,P110)。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越南条约》。李鸿章说,“进和议者二赤(案:指赫德),我不过随同画诺而已”[2](P235)。
赫德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公使,赫德向清政府推荐其弟赫政继任总税务司,事实上,仍然是他兼任总税务司。李鸿章则推荐其亲信德璀琳继任总税务司,双方斗争很激烈[7](4,P130)。8月,赫德宣布交卸总税务司职务。接着,他又不愿放弃总税务司职务,正式辞去驻华公使。9月12日,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李鸿章愿意我接受公使职位,而北京的人却喜欢我留在原任”[7](4,P165)。
1886年2月11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中法勘界委员发生争执,几乎决裂,但是,我已取得皇帝特别谕旨,严令中国委员不得再制造麻烦,一场纠纷就此结束。如再争下去,战事可能重开!幸运的是,我在这里,而且能够说话!李大人不肯照我的话办事,生怕决裂,并怕为自己惹出是非”[7](4,P291)。
1889年2月,因光绪帝即将亲政,奖叙大臣,以赫德久办洋税,精明切实,收数逐年增加,赏给三代一品封典。1893年8月,总理衙门命赫德以总税务司兼管中国邮政。
1894年7月,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10月,总理衙门、户部与赫德筹作战经费,定一千万两汇丰银行借款合同。11月,清政府命赫德传谕琅威理迅即来华,以备任使。12月14日,李鸿章电户部左侍郎张荫桓:“顷召汇丰美德伦面询,……但愿户部径商汇丰,可自为政,不须借重赫,赫亦无所作祟阻挠,望告大农,勿亟此事。”次日,张荫桓电李鸿章:“汇丰若必须赫德经手,部中仍与赫商”。[11](P268)
1895年4月,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中日马关条约》 。8月,清政府命李鸿章入阁办事,调王文韶为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物北洋大臣。李鸿章已被驾空,失去了实权。
1896年2月,清政府派李鸿章为正使,前往俄国贺俄皇加冕,再前往英、法、德、美等国,商议增加进口关税问题。李鸿章奏准以赫德之弟赫政,李鸿章之子李经述,德国人德璀琳等为随员。8月,李鸿章等到达英国。21日,赫德特别致电金登干,请他向“特使问候,希望特使阁下此次欧洲之行愉快,并祝身心双健首途回国”[7](9,P46)。10月,李鸿章回到北京。清政府命李鸿章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行走。又可以参与对外交涉事务了。
1898年3月,李鸿章与俄国署理驻华公使巴布罗福订立《旅顺大连租借条约》。4月10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李鸿章“勤奋、愉快,但是目前他还不是一位实权人物,至于他真正的倾向则难说,他谈起话来,好像他认为只有英国可以信任,而行起事来,好像是受俄国雇用的人!他老守旧派,思念过去,而不肯为‘新风尚’做任何事情”[7](6,P832)。9月,清政府命李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金登干在给赫德的信中写道:“人们认为,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是英国外交的巨大胜利”[7](6,P886)。
1899年12月,清政府以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1900年5月,实授李鸿章为两广总督。6月,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发。清政府命李鸿章迅速来京。义和团进入北京。赫德避入被围困的英国驻华使馆,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称:“京城局势危险已极,各使馆甚虞被击,均以为中国政府若非仇视外人,即系无力保护,倘稍有不测,或局面无速转机,各国必定并力大举,中国危亡即在旦夕。应请中堂电奏皇太后,务须将各使馆保护万全,并宣明凡有臣工仇视外人之条陈,朝廷必不为所摇惑。”李鸿章当天转电总理衙门,称:“事关紧急,不敢壅与上闻。请速代奏[11](P926)。清军与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清政府对八国宣战。7月,清政府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促借坐俄国船北上,或由陆路前来。8月,清政府第九次电促李鸿章迅速来京。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大肆抢掠。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离京西逃。总理衙门请赫德筹办和议,并请他转达李鸿章,商借海轮,使李鸿章即行北来。赫德与在京的大学士崑冈等晤谈,请奕劻迅速回京,先与各国公使会商。清政府准全权大臣李鸿章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李鸿章电请派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为全权大臣。9月,清廷谕李鸿章:此次到京,安危存亡所系,旋转乾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10月1日,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11日,到达北京。14日,李鸿章与赫德、庆亲王奕劻会晤磋商,决定照会各国公使,开始议和[7](7,P101)。次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李鸿章和庆亲王急于想将问题解决,但是,我很怀疑他们是否当真悔悟或认识到中国犯下的大罪的严重性。……经过这次事件,我的地位肯定会更为重要”[7](7,P103)。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与奕劻将和约大纲十二款画押。29日,清廷下诏变法。3月31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此间的事情令人极为不快,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什么改进的希望。谈判进展缓慢——不知何时我们才能谈出结果。然而,我有耐性,李鸿章有胆识,夜再长也有天亮之时”[7](7,P176)!4月21日,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遥为参与,将一切因革事宜,悉心评议,次第奏闻。5月7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新的政务处(庆、李、崑、荣、王、鹿以及张和刘)将倡议必要的变法[7](7,P189)。9月7日,李鸿章与奕劻和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 。14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李鸿章很消瘦——但他已尽其职,并作得不错,可怜的老家伙”[7](7,P237)!11月6日,赫德致电金登干:“李总督病危”[7](7,P346)。次日,李鸿章病故,年七十九岁。清廷给他晋封一等侯爵,予谥文忠,追赠太傅,入贤良祠。8日,金登干在给赫德的信中写道:“我把您‘李总督病危’的电报交给丁柏蒂先生,他非常感激能早得到此讯。他说:除了俄国和中国的宫廷人士而外不会有人感到很‘悲伤’”[7](7,P262)。10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可怜的李鸿章在死前三十个小时还在工作,精力旺盛——只要有他在场定夺,他决不受驱使,决不让任何人插手事务,令人惊叹!他7日去世,8日刚成殓之后,我就到他的卧室吊唁。公使团于9日吊唁。……除了俄国损失了它的这个人之外,他的死将不会有什么影响,即不会有坏的影响。实际上,这些老的守旧人物让位于后来者,对中国来说将更要好些,但是这些后来者也同样会犯那许多的错误——只不过是另一类型的错误”[7](7,P266)!
赫德是英国人,李鸿章是中国人。赫德是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赫德比李鸿章小十二岁,应该说是两代人。但是,他们都效忠于清朝政府,都争取清朝政府的重用,都希望能在中国近代化方面作出贡献。他们有着明显的共同点,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少矛盾,甚至是争斗。郭嵩焘将出使英国,担任中国驻英的第一任使节,临行,收到慈禧太后的召见。慈禧太后问郭嵩焘:“赫德替中国办事,尚有心腹否?”郭答:“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氏,岂能不关顾本国?臣往常问之‘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德言:‘我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臣问:‘无事时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赫德笑言:‘我固是英国人也。’可见他心事是不能不帮护英国”[12](P32)。赫德也可以算是明人不说暗话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赫德为李鸿章等筹集军饷,在李鸿章于苏州屠杀太平军降将之后,戈登扬言要与李鸿章的淮军开战之际,赫德又大力奔走各方,进行调解,促使常胜军继续与淮军配合,对太平军作战,当然得到了李鸿章的好感。李鸿章在处理阿思本舰队时支持赫德,贬斥李泰国,使赫德取李泰国而代之。李鸿章又保举赫德,使清政府给赫德赏加按察使。这些措施当然使赫德对李鸿章深为感谢,对李鸿章颇为尊敬,称李鸿章为“伟大的李”。后来,赫德准备兼任海防司,在掌握中国的财权的同时,再掌握中国的海军,使中国海军英国化。李鸿章等担心尾大不掉,阻止了赫德的奢望。李鸿章通过赫德在英国购买了一批炮艇、巡洋舰,在质量、性能方面,又不能令人满意,很反感;赫德反而怪罪李鸿章没能配备合格的船员,没有进行适当的保养。李鸿章一再要提拔德国人德璀琳,要以德璀琳取代赫德,也使赫德牢骚满腹。在中法战争期间,赫德又极力包办中法议和,尽量排斥李鸿章,李鸿章也是很不高兴的。赫德还认为李鸿章在办理中外交涉的事务中亲俄疏英,也使他很不愉快。赫德说到李鸿章,曾经说过“他像我一样,年轻时交上好运,就此扶摇直上,位极人臣,其实,我再说上一遍,他像我一样,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因为身居高位使他声名显赫而已。当他接待外国人时仿佛应付裕如,但揭去他的这张皮,他还是中国佬,同其他官僚同样是无能之‘辈’。德璀琳很崇拜他,我却不那么看待他”[7](6,P244)。但在李鸿章死后,他还是赞扬李鸿章一直工作到最后,精力旺盛,不受人驱使,令人惊叹!赫德与李鸿章之间,恩恩怨怨,他们之间的恩或怨,都与晚清史上的重大事变息息相关,是很值得深入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1]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2] 王宏斌.赫德爵士传[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3] 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2.
[4] 郭毅生.太平天国大辞典[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5] 田余庆.太平天国史料[Z].北京:开明书店,1950.
[6]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 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Z].北京:中华书局,1990.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9] 贾熟村.李鸿章与薛福成弟兄[J].清史研究,1996,(1).
[10] 贾熟村.赫德与葛雷森的恩怨[J].东方论坛,2012,(4).
[11]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2] 贾熟村.赫德与郭嵩焘[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第31卷,第1期.
责任编辑:侯德彤
Gratitude and Resentment between Hart and Li Hungchang
JIA Shu-cun
(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6, China )
Robert Hart was British and worked as inspector-general of Customs in China; Li Hungchang was viceroy of Zhili. Both serving the Qing dynasty as high officials, they hoped to contribut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by working together. However, there were conflicts between them due to differences in nationality, position and age. Their relationship had a crucial bearing upon the major event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and is worthy studying.
China; Britain; Li Hungchang; Hart; modernization of China
K256
A
1005-7110(2015)01-0001-06
2014-11-26
贾熟村(1930-),男,河南偃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