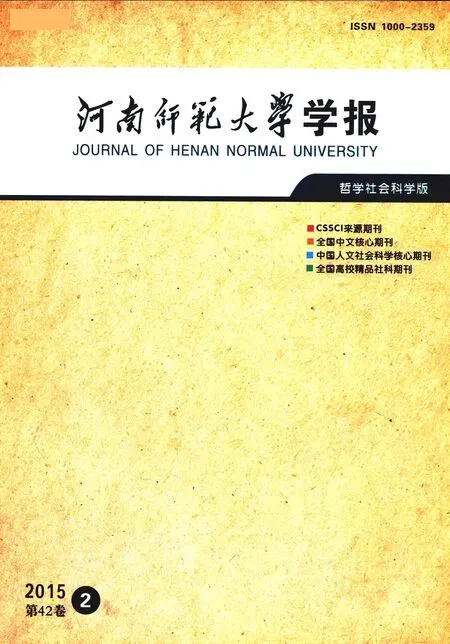论情态证据的产生与认知原理
蔡艺生
(西南政法大学 刑事侦查学院,重庆401120)
情态证据指的是在庭审时,被告人或证人的面部、声音或身体等各部分及其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1]。20世纪以来,国外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就情态证据的是非问题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现代司法试图构筑精密体系,并认为法律的理性研究的未来属于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2]。因此,情态证据往往因为其迥异性,而被斥为“主观性”以致被忽视。但是,从历史趋势上看,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是一种回归过程。诚如波斯纳所言:人首先是物理性的、生物性的人,然后才是社会性的人。“人性”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而非结束[3]。在法律或社会规范中,认知和情感并非无关因素,只是它们尚未被心理学家充分理解,因此还不足以支撑起一种社会规范理论[4]。不过,我们无法也不应抹去这种认知规律。而且,当某种传统法学范式或理论不能为当下社会提供有效的答案时,我们应该调整或丰富研究范式。在此,笔者试从情态证据的现有实践存在和理论构建中,勾画情态证据的产生与认知原理。几十年来的心理学等相关研究早已显示:引起情态反应的内在刺激是心理性的。情态的产生,虽然与个人的认知有关,但在情绪状态下伴随产生的生理变化与行为反应,当事人却是无法控制的。因此,在庭审时,当当事人被以各种形式唤起对其作案经历的长期记忆或未来危险的意识时,当事人就会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这些情绪变化都是无法控制的,必然导致生理心理上的异常情态反应。审判者可以据此分析当事人与案件的相关度并获取与作案人作案经历有关的讯息。罪犯和无辜者之间心理上的重要差异,仅仅在于一个当犯罪发生时,他在现场,他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在他心里装着当时当地的景象。而一个无辜者,对此一无所知。究其根本,情态证据是对人类本能和心理的一种司法运用,是基于人的情绪发生变化时由植物神经系统作用而引起动作或生理变化的原理。
一、情态证据的产生原理
20世纪最负盛名的“应激理论之父”汉斯·赛耶指出:当人遇到紧张或危险情境而使身体与精神负担过重却又需迅速采取重大决策时,就可能导致应激状态的产生。1963年,中国著名的生理学泰斗蔡翘将汉斯·赛耶的“病理应激”的理论推进到了“生理应激”理论,强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刺激反应恢复到原来正常状态而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的过程”[5]。即,现代应激理论认为,应激是个体面临或察觉(认知、评价)到环境变化(应激源)对机体有威胁或挑战时做出的适应和应对的过程[6]。而个体的情态正是这种压力反应的集中表现。司法为了准确激发被告人(或证人等)的情态,就必须有意无意地施加各种合理的压力。
(一)压力施加
压力施加是指为了激发压力反应(情态反应)而通过主客观因素营造压力。在心理学上又称“应激源”,是指引起应激的各种内外环境刺激。在心理学视野中,根据其属性,可将应激源分为四类:一是躯体性应激源,指作用于人的机体,直接产生刺激作用的刺激物,包括各种理化和生物刺激等;二是心理性应激源,包括人际关系的冲突,身体的强烈需求或过高期望,能力不足或认知障碍等;三是社会性应激源,包括:客观的社会学指标和社会变动性与社会地位的不合适;四是文化性应激源,即因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改变造成的刺激或情境[7]22。
在情态证据理论视野中,压力的来源是综合性的,既有躯体性和心理性,也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
一是被告人或证人等的躯体性应激源。包括身体的受束缚状态,如手铐和脚镣等警械,甚至包括各种肢体性的接触或压迫,如空间限制等。二是被告人或证人等的心理性应激源。包括对方证人的指控,共同犯罪嫌疑人的坦白,亲人对其犯罪行为或人格的唾弃和否定,他人对其伪证行为的揭露,身体渴望自由等的强烈欲望,对犯罪事实、侦查机关或反侦查行为认知的错误或障碍等。三是被告人或证人等的社会性应激源。包括从普通人到被告人或证人乃至罪犯的转变所带来的社会交往、生活、工作和未来的变动。四是被告人或证人等的文化性应激源。包括日常语言到法言法语的转变、日常生活到监禁或法庭程序的转变、社会公序良俗到法律价值观的转变、个人认知和公众认知的冲突等。
整个审判过程,必然从以上四个方面给出庭的被告人、证人、控方、辩方、法官和旁听群众等带来不同的压力施加,并且庭上各方又会交叉进行压力施加。而且,各种压力既来自当下庭审,也可能由此而诱发各方对过去或未来压力的感同身受,进而营造出一种“超越时空”的压力环境。而且,情态本身也可以传递压力,并激发新的情态,由此循环反复。同时,这既是一种对被告人和证人的有意的压力施加,同时对其他各方也是一种检验和考验。如,庭审中,旁听群众群情激奋的情态对法官判决施加的压力,使其更加谨慎而全面地思考问题等。同时,压力施加是可以不断累计的。即,紧张不安和焦虑保持在身体中并随着遇到的每一件能引起紧张情绪的事情不断积累上升,最终导致了显著的情态反应。
(二)压力中介
应激是个体“察觉”环境刺激对生理、心理及社会系统过重负担时的整体现象,所引起的反应可以是适应或适应不良的。即压力施加后,个体的“察觉”是一种将压力内化到个体内心的中介。应激的发生并不伴随于特定的刺激或特定的反应而发生于个体察觉或“估价”一种有威胁的情境之时。这种估价来自对环境需求的情境以及个体处理这些需求的能力(或应对机制)的评价,个体对情境的察觉和估价是关键因素[7]23。压力中介包括心理中介与生理中介两种。
在情态证据的产生原理中,被告人或证人等的压力中介必须考虑如下两点。
一是压力承受力。承受力要素来自两方面,经验累计和记忆定形。如,大量的作证经验,使得从躯体、心理、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具备了较大的抗压性;或者证人先前对事实记忆错误,但是自我内心确信其为真。二是对压力的理解问题。即该压力应该能为对象所关注和理解,否则,对牛弹琴显然不能激起“牛”的任何反应。当然,需要提醒的是,这些压力中介差异因素的存在不必然导致情态“失真”,只要随后的情态观察与判断具有合理的设计。
(三)压力反应
当个体经认知评价而察觉到应激源后,就会引起心理与生理的变化,即,情态反应。
压力反应的内在机制决定了情态表现是如何成为一个人所不可缺少的部分,即情态表现的源头。这些内在机制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包括生理机制和经验机制。
首先是压力反应的生理机制。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机制。社会常识及生理学等研究都认为,脑与行为是密不可分的,压力通过心理和生理机制催生了情态反应[7]25。
其次是压力反应的经验机制。这是人类在共同生活当中,所逐渐发展成型的机制。它与生理机制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而前者则是后天养成的。当然,经验机制又有所区别。一是压力反应的普遍经验机制。这是人类在所有环境中都普遍使用的共同经验。如,不管文化如何差异,手都会被用于送食物入口。二是压力反应的特殊经验机制。这是根据文化、阶层、家庭和个体而变化的经验。正是这些生理或经验机制决定了当事人的情态表现并影响着他人对其情态的感知和解读是否顺利和客观。
在生理和经验机制的作用下,一旦当事人感知到压力,各个机制会自发或自觉地发挥作用,从而让个体表现出不同的压力反应。个体不仅会出现情态变化,还会出现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变化,并形成综合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有长期压力的累积所表现的,也有即时压力而激发的;不仅有面部、身体和声音的表现,还有气味和其它人类未知的表现(如第六感等)。而司法在辨别是非曲直当中需要捕捉这些情态表现,不仅是为了识别谎言,也是为了更好地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或传递一种情感和信念。
二、情态证据的认知原理
在压力控制与激发后,必须对情态进行观察与判断,亦即对情态进行解码。在众多情态表现中,除了“语言性情态”,其它情态要么是一种下意识的表现,要么难以用语言进行替代,更难以用语言性的思维进行评论或回应。因此,在对情态进行观察和判断时,就需要进行合理的设置与构建。
(一)情态证据的观察
为了更好地观察情态,同时对情态的观察本身也是一种激发情态的压力。因此,应该从主观和客观上进行设计。首先,该观察者在主观上应该注意到其重要性;其次,在客观上,应该为观察者提供良好的观察机会和环境。
1.情态证据观察的主观要求。首先,观察者应该意识到观察情态的重要性。这也是深植于司法历史之中的传统,即,观察证人情态对判断其可靠性具有莫大的作用。因此,三千年来的司法体系都坚信一个前提预设“观察证人情态的机会具有重大价值”[8]。而且,此种对情态的判断不仅关系到证人的可靠性,还关系到被告人和证人的人格权、财产权、自由权甚至生命权等。必须认识到被告是案件的焦点和中心,是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人,不仅要裁断事实,还需要对被告的主观恶性和悔过程度等进行价值评价。因此,对情态的观察应该严肃而细致。
其次,观察者应该对情态进行整体性的观察。不仅要观察情态的片段,更要观察情态在被告人或证人的整个庭审中或作证过程中的整体表现,还要观察其它证据与情态的相互关系。观察者应该保持一种谨慎而开放的心态,不应该先入为主、以偏概全。
2.情态观察的客观要求。首先,应该让观察者能够面对面地观察被告人或证人。因为,情态表现往往是一种在具体语境下的微妙反应,对情态的捕捉需要求与之处于共同的语境,才能身临其境地感知其情态反应。因此,就需要观察者与被告人或证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即身体上的直接观察而非通过视频进行观察。二者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被观察者的身体应该尽量地暴露在观察者的视野中。
其次,为了让观察者充分进行观察,需要为之提供足够的观察时间。在长时间的观察中,观察者可以对被告人或证人进行全面的判断,重新修正内心预先存在的偏见,或者重新预设内心的倾向或背景知识等,并对内心的判断进行验证。而且,一旦被告人或证人试图进行情态伪装,那么这种长时间的观察将能尽可能地促使其暴露真正的情态。所以,在西方的司法体系当中,都强调传闻证据规则、直接言辞原则和迅速及时审判原则等,赋予审判者面对面观察和判断的机会。
同时,还必须给观察者提供深入的观察机会。通过对被告人或证人的情态刺激,激发其极端情态,让审判者进行更好的观察和判断。如,交叉询问的存在,使得证人一直处于一种对未知的恐惧[9],这种恐惧加上控辩双方的提问设计,可以促使其展现正反两个极端的真实情态,利于审判者的深入观察和判断。
综上,被告人或证人的“心灵是我们注视的焦点,在我们注视这一焦点的同时,我们也附带关注由他的心灵以不可言传的方式协调起来的言语和动作”[10]。甚至这种观察和判断为我们所下意识地进行,虽无法言述,但却意义非凡。正如美国约瑟夫·哈奇森所说:“当案件陷入胶着时,我详细调查所有已有证据材料,并进行深思熟虑。然后,让自己的想象力发挥作用,超越各种理由的束缚,等待着一种感觉——预感——理解的直觉性闪现,这将在问题和决定之间跳跃出火花,为司法脚下最黑暗的道路指明前行的方向。”[11]而“司法裁决的过程也很少是先有前提,而后随之从中推理出结论。司法裁决往往先有模糊的结论,然后再寻找前提去证实它”[12]。为此,我们应该从主观上和客观上为情态观察提供尽可能的条件。
(二)情态证据的判断
压力控制和激发、情态证据的观察都是为了情态证据的判断,即,对情态证据进行“解码”。确定情态含义不仅需要观察其外在表现,更需要了解其表达的语境(场合)和正常表现,进而察知其准确含义。
1.情态证据的语境。相比情态,语言和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性表达形式,其在清晰性、可管理性和连贯性上有了质的发展。因此,语言文字在感情的表达、向别人的诉求和事实的陈述等领域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10]114-115。但是,即使是语言和文字,“也只有在其具体的场合所附带体系中,其意义才是确定的。离开了特定的场合和体系,其意义就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变化”[10]166。而情态一方面本身很少形成符号表达效果;另一方面语境对其有重大甚至关键意义。因此,在对情态的理解中,不仅需要了解情态的先存性意义,更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理解其含义。
当然,某些情态已经获得了符号性表达的认可,成为一种语言性情态。如,点头表示同意。但是,更多情态远远没有达到符号性表达的效果,实际上难以单独确定其含义。这就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语境进行综合判断。对语境掌握得越全面彻底,就越有利于对情态进行准确把握。情态表达的语境包括表达者的个人生理和经验前提、表达者在当下和未来所面临的情势等。同时,观察者对被观察者的情况和事实了解的越多越对其是种巨大的压力,越能激发其真实情态。
2.情态证据的解读。在了解了情态证据的语境之后,随之应该判断其正常的情态反应标准。如,跟某人熟识熟知后,就可以准确知道其在某个情态出现时究竟代表了什么意思。这种正常情态反应标准的判断,实质上类似于对词汇词义的识别。一旦认知了词汇的词义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沟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情态都能够理想地进行语境的感知。因此,此种对正常情态反应标准的判断,就必须依赖于观察者个人经验总结。如,法官虽然不知道被告人是否被刑讯逼供,但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可以从被告人的“情词”(如被告人在看到侦查员时的恐惧眼神等)中推断出事实。或者,陪审团虽然与被告人不熟知,也不知道案件情况。但是,基于陪审团与被告人所处社会环境的一致,陪审团可以较为准确地推断被告人的情态意义,并且在庭审过程中通过被告人在各种压力下的不同反应和证据材料的不断质证,不断形成对其情态语境的准确理解和对情态的准确解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观察者对情态的解读并不是片段的,更不是一时的,而是在集中的庭审中不断的自我检验的。而且,这种解读与检验并非必须有意进行。同时,庭审各方都可以看到情态,各方对情态的反应可以进行互相的验证,并共同对被告人和证人等形成新的压力。特别是在陪审团审判中,陪审员之间可以结合各种证据材料和各方反响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形成对情态的具体、客观而可描述的解读,最终实现公共意志对法律的再次即时更新。
当然,情态证据产生和认知的各个阶段和环节并不是截然区分的,而是相互交织和穿插的。在人类漫长的司法演进中,该原理的各种自发或自觉的运用无处不在,体现在各种司法制度和技术的设计当中。只要能辅以相应的制度和技术设计与保障,如,司法亲历性、司法权威和司法裁量权的合理设计,情态证据完全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情态证据在古今中外的司法实践中都广泛存在。如,西方陪审团制度、当庭作证、对质权、传闻规则和交叉询问等都是以情态证据为基础而确立的[13]。我国古代的策略思想中“钓情”“知人”“察势”和司法审判中的“五听断狱讼”(古代曾经以“情词”指代“口供”)等更是将情态的运用推到了高峰。
三、余论
综上,情态证据运用的具体原理是:通过合理压力刺激被告人(或证人等)的记忆和心理,激发其情态;司法人员则基于对被告人(或证人等)或案件的了解,结合其它证据材料判断情态所蕴含信息,并最终确定是非曲直。纵观人类司法的进程,无论是弹劾式诉讼制度、纠问式诉讼制度抑或辩论式诉讼制度,都以种种因应当下社会语境的制度保障着情态证据的运用。而且,基于情态证据和其它证据的异同,其制度设计表现出了根植于悠久传统和人性的某种特殊性。当然,由于情态证据产生和认知原理的要求,其制度保障的基本要求仍为保障合理的压力控制与输入、有效的情态观察与判断。这就要求司法在亲历性、权威和裁量权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包括情态证据运用的前提、语境和裁量三个方面的制度设计。对于书证和物证自身而言,此种司法具有间接的效果。即,对专家证人或举证者具有约束力。就此内在逻辑关系而言,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都体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
对情态证据研究的欠缺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可叹的[14]。随着人类感觉察觉的事实与用来发掘感官所不能即的世界的辅助工具所揭示的真相之间鸿沟的扩大,人类感官在事实认定中的重要性开始下降。科学将持续地改变生活,伟大变革摆在了所有司法制度面前,这些变革最终可能与中世纪末期出现的改革一样重要[15]。情态证据的运用或许代表着人类认知本能的核心与最后坚守。或许,这正是情态证据的可贵之处,即,保持一种人们无法掌握的存在,为司法提供一种必需的神秘感或威慑力。
[1]蔡艺生.从情词到口供:论情态证据的正当性与合理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1).
[2]Oliver Wendell Holmes.Jr.The Path of the Law[J].Harvrd Law Review ,1987:457.
[3]Gary S.Becker.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J].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13).
[4]埃里克·A.波斯纳.法律与社会规范[M].沈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4.
[5]蔡翘.Selye应激学说与生理应激[J].生理科学进展,1963(1).
[6]王明辉,张淑熙.应激研究综述[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7]格雷·白莲.医学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Olin G.WellbornⅢ.Demeanor[J].CORNELL L.REV.1991:1075.
[9]Edward J.Imwinkelried.Demeanor Impeachment:Law and Tactics[J].Am.J.Trial Advoc,1985:183-186.
[10]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许泽民,译.陈维政,校.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478.
[11]Joseph C.Hutcheson.JR.The Judgement Intuitive:The Function of the“Hunch”in Judicial Decision[J].CORNELL L.Q.1929:274-278.
[12]Kevin W.Saunders.Realism,Ratiocination,and Rules[J].OKLA.L.REV.1993:219.222-223.
[13]蔡艺生.让尾巴摇狗:美国情态证据实证研究[J].时代法学.2012(6).
[14]Edward J.Imwinkelried.Demeanor Impeachment:Law and Tactics[J].Am.J.Trial Advoc,1985:183,234.
[15]达玛斯卡.漂移的证据法[M].李学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