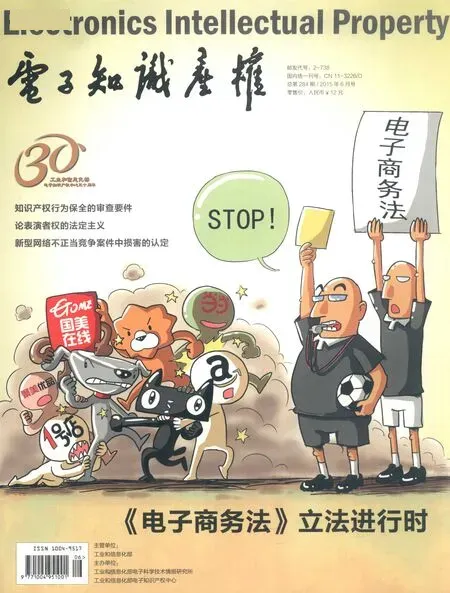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损害的认定
文 / 刘建臣
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损害的认定
文 / 刘建臣
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损害应包括实际损害和损害可能,该损害在民法分类上往往属于与一般财产损害相对立的纯粹经济损失。纵然不正当竞争和纯粹经济损失在法律评价标准上具有内核一致性,但是后者要求行为人主观故意,与不正当竞争认定主要从客观角度相左,因为竞争制度的规律不依赖行为人的主观意向。适用纯粹经济损失的法律标准去评价网络不正当竞争损害,会造成法律的重复评价、拔高不正当竞争的认定标准进而损害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违背竞争法发展趋势,宜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予以评价。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损害;实际损害;纯粹经济损失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我国互联网市场正值蓬勃发展的向荣之际,互联网企业以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新姿态不断地创造经济和效益的神话,改变着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然而,在我国互联网市场发展至目前的特定阶段,网络行业的通行商业惯例多处于待形成阶段,公认商业道德尚未达成共识,这使得互联网市场在互相角逐、自由竞争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市场竞争的无序性,不正当竞争时有发生。对于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规制,《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均无从适用,法院多适用该法第2条的一般条款作为裁量依据。1. 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是相对于传统不正当竞争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而言的概念,《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明确规定该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法院多适用该法作为一般条款的第2条予以规制。然而,作为立法技术的产物,一般条款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赋予法官在不正当竞争认定方面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明确该条的司法适用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带配额案”中对其予以了细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一般条款的适用须满足以下三个要件:“(1)法律对该种竞争行为未作出特别规定;(2)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确因该竞争行为而受到了实际损害;(3)该种竞争行为因确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或者说可责性。”2. 参见山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山东山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山孚日水有限公司诉马达庆、青岛圣克达诚贸易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065号民事裁定书。由此看出,第一个要件为同部法律中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适用关系,第二个要件聚焦于因果关系和损害,同时将行为限定为具备竞争关系的主体间之“竞争行为”,第三个要件则是竞争行为的法律评价层面,是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评价标准。对于第一个和第三个要件来说,前者是在遵循法理的基础上作出,后者为对该法第2条的总结,因此并无疑问。然而对于第二个要件中“损害”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未能明确。如按损害是否已发生来区分,究属实际损害还是损害可能即可?对于实际损害而言,是一般财产损害还是纯粹经济损失?对于损害类型的厘清,在学理和司法实践均有重要意义,比如财产权损害和纯粹经济损失的法律保护标准就存在区别,后文将予以详述。
二、不正当竞争与民事侵权行为的关系
损害是民法上的概念,指“权利或利益受侵害时所生之不利益。易言之,损害发生前之状态,与损害发生后之情形相比较,被害人所受之不利益,即为损害之所在”3. 王泽鉴:《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对损害予以特别规定。因此,要适用民事侵权法来界定网络不正当竞争导致的损害时,须先探究不正当竞争行为与民事侵权行为的关系。
(一)民事侵权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
关于侵权行为与不正当竞争的关系,学界通行的观点为不正当竞争本质上属于侵权行为。如有学者指出,“不正当竞争法肇始于侵权行为法”4. 谢晓尧:《在经验和制度之间——不正当竞争司法案例类型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另有学者指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正当竞争行为都属于侵权行为”5. 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因此,不正当竞争理应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范畴。与此相对应地,民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故民事侵权法对侵权行为的认定要件及其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分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以及民事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一般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理,对于不正当竞争的认定及民事责任的承担,应首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失位时,应适用《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因此,在认定法律未明文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无须以保护性规范的形式转介入《侵权责任法》认定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即第6条第1款)中,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予以认定。但是,对于作为不正当竞争认定要件之一的损害,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未规定时,应从民事侵权法的语境下予以考量。
(二)损害与违法性的区分
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肇始于侵权行为法,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身未对损害予以界定时,应适用侵权法的理论对损害进行解释。民事侵权法意义上的损害是认定侵权的要件之一,用以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事实基础,因此才有“若无损害,则无赔偿”6. 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之说,然而特定行为被法律否定性评价的原因在于其违法性,这正是侵权法在规定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时,将损害和违法进行区别对待的理由所在。在民事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中,对于违法性这一要件的认定,存在“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两种学说。根据“结果不法”说,其作为违法性评价的,乃是人的行为,而非侵害结果本身,侵害结果不是违法性评断的对象,“结果非价值”是该侵害行为被赋予违法性评价的理由7. 同注释6,王泽鉴书,第220页。。结果不法说是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8. [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我国台湾地区继受了德国民法对侵权认定的一般条款,亦承认结果不法说。我国大陆地区对违法性是否得作为认定侵权行为的要件之一尚存争议,但已有知名学者表示强烈支持。9. 如有观点认为,尽管《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没有规定违法或者不法的字样,但第2条明确规定“依照本法”,其实已经包含了违法性的要求。此外,日本民法典第709条亦没有规定违法性,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承认违法性是认定侵权的要件。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具体到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并不规制给经营者利益带来损害的事实,而规制基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带来的损害,因为任何竞争的存在均会影响相关经营者的利益,正当竞争亦会带来利益受损。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霍姆斯所言:“良好的政策应让损失停留于其所发生之处,除非有特别的理由予以干预。”10. [美]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因此,在判断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时,重点不在于是否存在利益受损,而在于是否违反诚信原则以及公认的商业道德,即存在违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在腾讯诉奇虎不正当竞争上诉案(下称“3Q大战”)中指出:认定上诉人的前述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互联网行业公认的商业道德,并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损害的认定
(一)实际损害与损害可能
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文义来看,该法将损害明确为已发生之实际损害,如第2条第2款规定的“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第5条的“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及“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第10条的“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第14条的“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因此,从文义解释出发,将该法规定的损害理解为实际损害,符合“法律解释必须在文义所及的范围内用之”12.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
然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损害限定在实际损害的范围内,与国际条约及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不正当竞争立法的规定明显不同,后者均将损害界定为“实际损害+损害可能”。纵然《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中并未明确损害的范围,但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根据以上条约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条款》第1条便开宗明义地规定:“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或者可能受到损害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应有权获得救济”;欧盟于2005年生效的《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第5条规定:“显著歪曲或可能显著歪曲普通消费者购买意识的行为属于不正当行为”;德国于2008年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条第1款规定:“足以显著地侵害竞争者、消费者或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的不正当商业行为是不合法行为”,其中“足以”二字表明,并不需要发生显著地损害消费者做出决定能力的实际结果,而只需要具有客观的可能性13. 范长军:《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1页。。
此外,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损害限定在实际损害范围也有悖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虽然后者并未明文规定损害的概念,但是该法的立法者在阐述立法理由时提道:“损害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对受害人造成了不利后果,此种不利后果既包括行为人实际给受害人造成的现实损害,也包括有可能给受害人造成的危险,即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害”1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为避免《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上的局限性,最高人民法院在2007年颁布的对该法适用的司法解释中对损害进行扩大解释,明确将“损害可能”纳入其中15. 如该解释第4条将反法第5条规定的“混淆”扩大解释为包括实际混淆或足以造成混淆,以及第8条规定“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等。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从而与国际条约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规定一致。综上,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损害应包括实际损害与损害可能。
(二)一般财产损害与纯粹经济损失
如上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带配额”案中将一般条款细化的三个要件,是适用一般条款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司法适用标准,然而其却并未对第二个要件中“实际损害”的类型予以界定,因此产生了在一般财产损害之外16. 不正当竞争行为导致的损害多数指向的是财产损害,然而特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亦会导致非财产性损害,比如仿冒行为、商业诋毁行为等,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民事责任中规定了赔礼道歉和消除影响的问责方式。,是否包括纯粹经济损失的问题。更有学者肯定地指出,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导致的损害往往为纯粹经济损失17. 薛军:《质疑“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载《电子知识产权》2015年第1—2期。。然而,网络不正当竞争损害绝非仅停留在判断是否为纯粹经济损失的层面上,深层次问题是,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内该如何理解适用以及不正当竞争与纯粹经济损失之间的法律评价该如何厘清。
1、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损害是否构成纯粹经济损失
对于实际损害而言,理论上又可分为一般财产损害和纯粹经济损失。一般财产损害是指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他人的直接或间接损害;纯粹经济损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虽未直接侵害受害人的权利,但给受害人造成了人身伤害和有形财产损害之外的经济上损失18.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0页。。在纯粹经济损失的场合,受害人虽遭受了经济损失,可该损失却与其人身或财产受到的侵害无关。具体到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导致的损害而言,营业竞争并不会直接给竞争者带来人身损害或财产的有形损害,而是一种独立的利益损失,大多数损害在民法理论上应界定为纯粹经济损失。基于互联网“注意力经济”的特点,潜在商机的数目直接取决于吸引用户眼球的能力,并在流量效应的功能下通过广告费用或向用户推广各种增值性服务以兑现利益。
以屏蔽网页广告为例,大流量的网站往往围绕其庞大的用户访问量搭建网络广告平台,并通过广告商的广告投放费用获利。然而,屏蔽广告软件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利益格局。广告遭屏蔽后,网站经营者无法履行与广告投放商之间所缔结合同项下的展示广告义务,因此可能会因违约而遭受支付违约金的合同非难。此外,因广告投放商的广告效益无法在网页上兑现,反过来又会减少该网页的投放量或降低广告投放费用,致使网站经营者遭受不利。屏蔽广告行为给网站经营者带来的损害限于以上所述,但无论哪种皆非财产的有形损害,该损害属于独立存在的纯粹经济损失。19. 我国法院在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中虽未明确指出损害属于纯粹经济损失,但对该损害类型予以了保护,认定行为人构成不正当竞争。具体到屏蔽网页广告案件,如“优酷诉金山”案和“爱奇艺诉极路由”案均明确承认了这种损害类型,并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将屏蔽网页广告行为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3155号民事判决书。再如,“3Q大战”中奇虎公司专门针对QQ用户开发扣扣用户保镖,移植腾讯的用户量并通过广告费或其他增值性服务获利,该行为并未给腾讯公司带来财产的有形损害,亦为纯粹经济损失。
2、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要件及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定位
正是基于纯粹经济损失为独立存在的一种经济利益损失这种特性,因此在侵权法的利益衡量上,其不能与人身权或财产权等权利等同并重,应当区别对待20. 程啸:《侵权责任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侵权法上将权利与利益区别对待是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德国民法典在侵权行为一节中明确规定“在侵害权利时,过错同时包括故意与过失,而在侵害利益时,过错的认定仅限于故意”。21. 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故意或有过失地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该法第826条规定,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加损害于他人的人,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参见陈卫佐:《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315页。纯粹经济损失属于权益的范畴,《德国民法典》对其保护适用第826条“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加损害于他人的人,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的规定,以故意为要件。区别对待的原因在于侵权行为法旨在权衡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而具有界限属性的权利是确定他人行为自由的重要标准,社会一般公众对权利的界限往往能够认识到,但是权益并不为公众所能预见,对利益的过度保护会妨碍行为自由。22. 如驾驶员驱车撞上某演员,致使该演员无法参加当天的演出,从而无法取得演出费用。由此产生的侵害有人身损害与作为间接损失的演出费用,前者属于对人身权的侵害,为公众所能预见,而后者作为利益,不能为公众所知悉。因此,对后者的赔偿,理论上以故意为要件,即明知其去演出,仍驱车撞伤致其无法参演。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在继受德国民法的基础上,做出了同样的规定。23.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款前段和第2款继受的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内容,该法第184条第1款后段继受的是德国民法典第826条的内容。参见注释6,王泽鉴书,第268页。因此,对于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或地区的规定是以行为人故意违背善良风俗为要件。
我国大陆的通说认为,《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并未将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限定在绝对权,因此,纯粹经济损失也可以纳入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24. 同注释20,程啸书,第57页。。然而,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要件却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发生了异化。该法并未对权利和利益予以区别对待25. 立法者未作区分的理由在于,他们认为权利和利益虽然存在区别,但是不必设定不同的构成要件,许多权利和利益本身也没有明确界限,权利本身体现的就是利益,且权利和利益之间是相互转化的,有些利益随着社会发展纠纷增多,法院通过判例将原来认定为利益的转而认定为权利,即将利益“权利化”。参见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页。,在该法条文无明确规定适用严格责任或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时,对权利和利益的侵害均适用该法第6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原则。而过错同时包括故意和过失,这意味着即便在轻率、疏忽等过失的情形下,行为人也要为侵害他人不特定利益的行为承担不特定侵权责任,这极大地限制了行为自由。正是出于这种理由,我国学界的通说建议采用“目的性限缩”的方式,将权利与利益区别对待,尤其是在纯粹经济损失方面,以行为人故意背俗为保护要件26. 葛云松:《<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王利明:《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载《法学家》2009年第3期。。此外,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深法官为代表的司法界也主张将权利与利益区别对待,并总结出了可保护利益的四个考量因素。27. 司法界的观点为:虽然《侵权责任法》原则上将民事权利与利益均列入保护范围,但是由于民事利益的特殊性,并不能不加区分地一概予以保护,在界定受保护的民事利益时,可考虑的因素有民事利益是否被特别法规纳入保护、行为人主观为故意、行为人与受害人是否有紧密关系及实施侵害行为时对所致损害是否合理预见、平衡保护利益与行为自由。参见奚晓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7页。
3、纯粹经济损失违法性评价与不正当竞争法律评价的厘清
如前文所述,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评价依据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与公认的商业道德。然而,纯粹经济损失的违法性评价为“故意违背善良风俗”。因此,二者违法性评价标准存在差异。在将多数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导致的损害界定为纯粹经济损失的前提下,即便已经对经营者的行为做出了不正当竞争认定,即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商业道德,是否还应当去证明行为人有“故意违背善良风俗”呢?这直接指向了两个法律评价标准的适用关系问题。
首先对于民法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和善良风俗来说,两个原则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一般条款和法官造法、弥补法律漏洞、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且两者适用范围均在不断扩大,都已经支配私法全领域28. 于飞:《论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区别适用》,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2期。。此外,两者的适用仍存在逻辑内核的一致性。德国著名民法学者拉伦茨认为,相较于诚实信用原则,善良风俗只涉及来自人的社会条件的最低要求,并且只要求在某种情境下遵守这一要求;秘鲁学者德拉普恩德和拉瓦叶认为,善良风俗只涉及特定时空的道德,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高于这一标准,确切地说,它以专门的约束为前提,并确定了行为的参与者之间的信赖。基于上述两位学者的分析,徐国栋先生认为,诚实信用与善良风俗的区别在于两者的适用层次不同,善良风俗是社会对主体的最低要求,而诚实信用则是较高的要求,故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必定违反诚实信用,而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未必违反善良风俗29.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增删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64页。。此外,德国学者Vollkommer教授明确指出,《德国民法典》第138 条关于违背善良风俗的规范,是《德国民法典》第242 条诚信原则的特别规定30. 郑友德、范长军:《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具体化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同理,《德国民法典》第826条关于侵权行为违背善良风俗也被认为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然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较为特殊,其具有特殊的适用对象,即应在竞争的语境下对该原则予以考量。同样,善良风俗原则因具体至竞争法的语境亦具备特定意义,如德国1909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规定的“善良风俗”原则就仅仅适用于涉及竞争权益的行为31. 该条规定,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违背善良风俗者,得请求其不作为损害赔偿。,而非民法意义上善良风俗原则指向的社会道德层面。因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意义上,诚实信用与善良风俗并不是如民法般具备包含关系,对二者的竞争法关系,商业道德就搭建了一个可供解释的桥梁。
其次,商业道德与善良风俗亦存在内核上的一致性。善良风俗立足于社会道德的层面上,其既包括了法制本身内在的伦理道德价值和原则,也包括了现今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行为准则32.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99—604页。。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因受前苏联的影响,未使用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概念,而是使用“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依学界通说,在性质和作用上,前者相当于公共秩序,后者相当于善良风俗33.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随着时代的发展,善良风俗原则早已脱离仅调整家庭伦理的范畴,而进入调整当事人间利害关系、确保市场交易安全领域。比较而言,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商业道德是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道德的经济伦理标准,它以特定商业领域普遍认识和接受的伦理标准,认定特定竞争行为是否违反公认的商业的道德34. 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创新性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商业道德既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内在的伦理道德价值和原则,又是维护作为公共秩序体现的经济秩序的道德标准,因此,商业道德理应是善良风俗的组成部分,二者内核上具备一致性。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善良风俗的标准涉及商业竞争中对竞争者外部行为提出的道德要求,在这方面曾参照盛行的社会商业道德35. 同注释30,郑友德等文。。具体到我国,梁慧星先生在对公序良俗进行类型化梳理时,明确将违反公正竞争的行为列入其中36. 梁慧星:《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8页。。
须注意的是,正如最高法院在“海带配额”案中提出的那样,在规范竞争秩序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诚实信用原则更多地是以公认商业道德的形式体现出来的。3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065号民事裁定书。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商业道德,与民法意义上的善良风俗原则具有内核上的一致性。由此可见,纯粹经济损失的法律评价标准与不正当竞争的评价标准基本一致,无须在已认定行为人构成不正当竞争时,再行善良风俗之检讨。但是,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不正当竞争认定无此必要,而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就必须以故意为要件。
四、网络不正当竞争损害与纯粹经济损失的剥离——代结论
即便是网络不正当竞争损害依民法理论属于纯粹经济损失、二者的法律评价标准的内核一致、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可以通过技术中立原则或者事实推定的方式以确定,但是,具体到法律适用上,应以《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调整,不宜适用《侵权责任法》。如果将纯粹经济损失纳入《侵权责任法》第2条保护的权益内以规制该行为,除违反“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法理外,还会拔高不正当竞争的认定标准以及违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发展趋势。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其“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其首要目的在于规范竞争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反射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并非像侵权法那样注重填补损害。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不注重经营者的主观过错,而是从客观的角度去考虑和认定竞争行为的正当性与否,有时也不排除主观因素,但客观性更为关键38. 同注释34,孔祥俊书,第9—10页。。而侵权法上基于利益的不确定性与非公示性考量,对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以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为要件。因此,纯粹经济损失在主观认识上的要求比不正当竞争要求的标准高。显然,如果已将行为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因为其造成的损害属于纯粹经济损失,对其保护又要求主观故意,则客观上相当于拔高了不正当竞争的认定标准。造成的结果是部分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欠缺经营者的主观故意进而摆脱《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非难,势必会造成竞争秩序的破坏,违背该法的立法目的。
此外,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发展趋势方面来说,该法正在向“去主观化”和“去善良风俗化”的方向发展。德国作为世界上首个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国家,其1909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的一般条款在判断竞争行为是否背俗时,不但要考察客观方面的行为内容和目的,还要考察主观方面的行为人的动机。39. 对主观方面的要求不需要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的背俗性,但是需要行为人知道构成背俗性的事实,或他有意不理会知道事实真相这一情况,即不顾危险而行动。参见注释13,范长军书,第104页。而在2004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生效以后,德国司法实践和学术界一致认为,第3条一般条款的适用不需要主观方面的要件,因为竞争制度的规律最终不依赖于行为人的意向。2008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中的“不正当商业行为”也是从客观方面予以考察,只须该行为足以显著地侵害竞争者、消费者或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即可。此外,由于陈旧的原则性规定过于宽泛从而使得最后都以法官个人的标准把握,因此德国在2004年修法时明确删除了“善良风俗”原则,而换之以“显著妨碍竞争”的违法性评价,在2008年修法时延续了这一规定,这与欧盟的《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精神相吻合40. 郑友德、伍春艳:《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十问》,载《法学》2009年第1期。。因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上述发展趋势下,如果适用主观性和原则性极强的纯粹经济损失的法律评价标准,势必会违背该法的发展趋势。综上,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宜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评价,用纯粹经济损失的法律标准将会造成法律重复评价,拔高不正当竞争的认定标准,进而损害互联网市场的竞争秩序。
Determination on the Damage Related to New Unfair Competition Cases on the Internet
The damage of newly unfair competition on the Internet shall include actual and possible damage, the former of which, under the classif i cation of civil law, usually falls into the scope of pure economic loss which is contrary to general property damage. Even though the legal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unfair competition and pure economic loss are consistent in nature, the latter requires conductors’ subject intention, which has conf l ict with the elements of unfair competition determined in an objective way.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rule of competition system does not rely on conductors’ intention. It would cause a repeated evaluation, promoting determination standards of unfair competition and thus harm the order on the Internet if we apply legal standards of pure economic loss to judge the damage caused by unfair competition on the Internet.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is the right choice, rather than the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 loss, of determining newly unfair competition on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Unfair Competition; Damage; Actual Damage; Pure Economic Loss
刘建臣,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