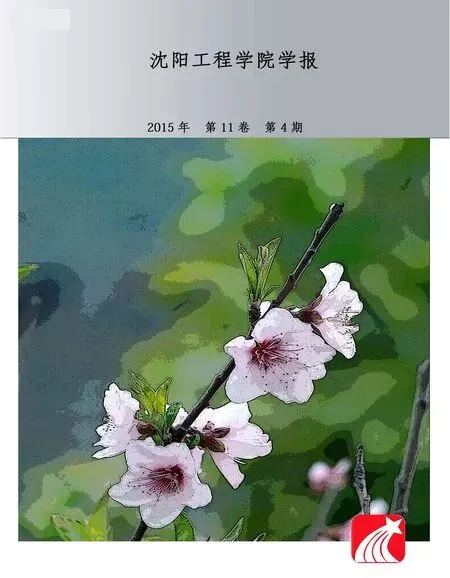“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中国因素探究
汪强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重庆 402160)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中国因素探究
汪强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重庆 402160)
在生产力水平这一根本原因之外,开放与包容的“和合文化”传统、厚重历史造就的文化独立与自信、愈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中国成功结合的特有因素。对这三者的坚持是实现民族复兴,进而取得更加辉煌发展的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合文化;独立与自信;党的领导
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一开始不太自知的模糊探索到逐渐清晰并被自觉加以推动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已历经30多个年头。30多年的结合实践,已用事实无可争辩地消除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疑问。结合后中国经济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二者结合的有效性与优越性。但实践经验或成就并不直接等同于认识上的理性自觉。由二者有限的结合所决定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也急切地需要更加深刻的理论关照予以解决。因此,在30多年后,再次理性审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意义重大。另一方面,30多年改革实践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材料,也使得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有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再认识成为可能。基于此,笔者尝试思考并回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何以首先在中国成功地实现结合,即在普遍的历史规律之外是什么样的特殊性促成了二者在中国的结合,以期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够实现结合”这一问题,理论界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即从根本上讲,由无法跨越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在人对物的依赖——商品经济阶段,市场经济必然成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文明民族和国家的不二选择。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在现实历史发展中表现为:资本主义通过吸收社会主义元素,特别是事实上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制度设计,缓和其固有矛盾,延长其制度生命;新生的不够格的[1]225社会主义通过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方面的技术方法和成功经验,加速其制度体系的完善,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充分展现其优越性,并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因此,目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借鉴又相互竞争的关系。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市场,既可以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可以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相结合。这是历史必然性的问题,是普遍性问题,但偶然性问题、特殊性问题即为什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实际的结合会首先诞生在中国,并且在中国取得成功,却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笔者认为,除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二者结合的原点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诞生并成功于中国,至少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和合文化使得中国人更善于实现差异存在,甚至对立物的辩证统一
悠悠中华,上下五千年,在与其比肩的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哈巴拉等古老文明相继陨落之后,却仍泰然于世,且生机勃勃。作为仅存于世的“第一代文明”[2],是什么让中华民族可以“一己之力”完成跨越五千年马拉松式的文明发展?这当然与自然禀赋、地理环境、人口数量有关,但更与使中华成其为中华的文化特质有关。这便是与西方非此即彼的文化观念相对的,强调“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
主张“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必然导致一种对异质他物的开放与包容,以及在消化吸收后的开拓与创新。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才能够避免因长时间陷入某种极端主义而导致自身与自身或与其他文明、自然界之间尖锐的对立与冲突,不会因对立与冲突的不可调和而造成文明发展的中断甚至根基的崩塌,反而能在一种天人合一、中庸平和的和谐环境中,求同存异、兼收并蓄,进而在融会贯通中实现革故鼎新。
这种开放与包容的文化特质,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明之中。无论盛世还是衰世,它都有如一种基因般的存在,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进程。在盛世,它躬逢其盛得以充分彰显,或者说,因为它的充分彰显,其世才得以为太平盛世;在衰世,它因专制抑制而蛰伏,或者说,因为它的蛰伏不动,才导致世道艰辛。浩浩中华,上下五千年,其勃勃生机的文化根源不外乎如此。
对于中国来说,科学社会主义是舶来品,市场经济也原非所长之物。但这并不影响二者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同以往所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异质文化一样,只要契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它们都能获得蓬勃发展。此外,在西方,二者原都有着各自的“标准”内涵和形式,并且作为直接对立物保持着不可相容的存在状态。但当它们来到中国,原本的两难问题却发生了性质变化,二者的关系从绝对的异己与排斥,变为了在各有所长、各有所司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和差异互补,进而融合为一种全新的、中国化的形态,实现了历史性的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与盲从西方对立思维从而陷入非公即私、非市场即计划、非社即资等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大吃极端对立思维苦果后重新觉醒的开放与包容的“和合文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经典体制”[3]是作为原始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而被创立出来的。原始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强调绝对的市场自由,排斥任何市场之外的调节和干预,悬殊的贫富差距、愈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极端尖锐的阶级对立,使其势必难以为继。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经典体制随之而起。它以另一种极端方式否定了原始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用完全的计划取代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用单一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用均等化倾向取代贫富差距,用社会统一或同一化取代阶级分化与对立……中国古已有云:物极必反,应该执两用中,才能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极端之存在必不能长久。因此,原始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经典体制也在运行60年后土崩瓦解(苏联)。然而,谁也不能未卜先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多种原因,我们的国家建设完全沿袭了苏联模式,继承了经典体制几乎所有的基本特征。同时,受冷战及苏联的影响,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开始主导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涉及社会制度或者意识形态时,表现得尤为激烈。这一状况在“文革”期间发展到了极致。在政治泛化阴影笼罩下的社会生活,充斥的不是开放与包容,而是日益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原则对立。从思想到行为,从生活到工作,从家庭到社会,人们都给己方划定了一个个封闭的圈,贴上一道道充满政治意味的标签,并相应地在自身之外设立了一个个对立面,将人生的意义归结为同对立面的不懈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这种背离开放、包容文化传统的极端对立的集体疯狂,显然不可能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混乱、停滞、倒退甚至崩溃。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痛定思痛,开始自我反思,反思我们的政策主张、反思我们的制度设计,更反思影响政策、制度决定的思维方式,提出要回归“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首先做到“解放思想”。这其中,显然包含了对当时严重束缚人们头脑的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的批判,以及通过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必然导致的客观上对“和合文化”的某种恢复。当然,此时的“和合文化”必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正因为有了这种恢复与发展,我们才开始抛开成见,在看似截然对立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求同存异,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探寻实现二者历史结合的有效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在这样开创性的历史实验中成功诞生。
二、厚重历史造就的文化独立与自信使得中国人更敢于也更能够坚持自我
2008年,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勤劳智慧的民族品格、不懈进取的创造活力、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4]“从汉代到明代初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一直领先长达十四个世纪以上。在那个时期,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发明中,相当部分是中华民族的贡献。”[5]正是这独一无二、连绵五千年且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其厚重、深邃的历史积淀,使其有着其他文明无法比拟的独立和自信。
独立——对自我的坚持,自信——对坚持自我的信念,是任何文明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一旦失去了独立与自信,文明的湮灭也就为期不远了。只有坚持独立、坚定自信,才能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交流甚至竞争过程中,既学习借鉴他人之长为己所用,又不至失去自我,而被征服、被同化。中华文明正是如此走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虽然有时一路坦途,有时也步履蹒跚,但文明的发展始终未曾中断,中华特色始终得以保持。即使面对近代灾难深重的百年耻辱,中华文明的独立与自信也没有被颠覆,反而通过一种激烈异常的自我否定,开始了对自身的扬弃,从而在苦难中完成了涅槃,实现了新的发展。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首先在中国实现实际的结合,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与经历历史激流荡涤后,恢复并发展了对中华文明独立与自信的理性自觉是有直接联系的。历史反复证明,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坚持自我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先进文化成果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实现“本土化”的再创造,是一个文明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否则,或者是迷失自我从而成为其他文明的附庸,或者是陷入“文明冲突”的噩梦之中而无法自拔。这其中的关键,开放、包容的态度是一个方面,本土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相对关系的处理,特别当本土文明处于相对弱势时,如何从自身实际出发,既学习、借鉴,又能坚持自我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开放与包容如前文所述,是中国的文明根性;悠久历史造就的独立与自信,使得中国更敢于挑战并打破西方的话语和政治霸权,并以自身为核心和标准进行新的制度创造。这不仅是中国从自我出发而又复归自我的结果,也是世界多样性的必然体现,更可能是终结文明冲突从而实现人类大同的一项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以相对于西方发展历程而言独具特色的方式实现的民族复兴,不仅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意义重大,而且通过在西方发展模式之外成功地实现了新的道路探索,打破了西方“历史终结”的论断,为其他落后国家或民族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树立了积极的榜样,并且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之外,推广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为世界的和平、和睦做出巨大贡献,从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三、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是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的关键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具有伟大的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意义。二者的结合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前文所述,“和合文化”、中华文明的独立性与自信心等,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开放、包容的“和合文化”、深厚历史积淀造就的独立与自信仅仅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结合更具有可能性。而可能性要实现向现实性的转化,还必须具备相应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在客观条件基本具备,即可能性已是现实的可能性而非抽象的可能性时,主观条件成熟与否就成为决定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关键因素。就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况来讲,客观条件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追求深入人心,经过历史检验从而被充分印证了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说明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广泛共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中无法撼动的领导核心地位。苏东剧变后的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不是改旗易帜,而是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并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多种所有制的并存、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以及个别利益之间的对立、普遍存在于不同所有制经济以及同一所有制经济内部的交换等,决定了市场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而主观条件方面: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左”倾错误逐步得到纠正。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极“左”错误论断,数十年思想禁锢开始瓦解,“实践标准”得以重新树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二是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实事求是地区分社会主义的“表层特征”和“深层本质”[5],从苏联式的对社会主义的机械理解中解放出来,开始以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为根本指引,探索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相联系,关于市场与计划的意识形态偏见被打破,在恢复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和方法指导下,二者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二者与社会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得以理清——作为“方法”[1]203的计划与市场,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属性,只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利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变化,在既有文化传统和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几经挫折后更加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勇敢地推进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成功地推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两个原本被视作水火不容的对立物的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综上所述,开放、包容的“和合文化”、独立且充满自信的中华文明以及在实践中不断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首先在中国实际地实现结合的特有因素。这些因素既有历史传统又有新的时代内涵,既是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历史证明了其优越性,实践的发展更需要其进一步弘扬。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并推广开放与包容的“和合文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方法,正确地对待坚持自我与学习借鉴的相互关系,在复兴的基础上中华文明必将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易中天.中华文明的根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4(5):1.
[3]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8-19.
[4]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8-5-9(2).
[5]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90.
[6]董德刚.当代中国根本理论问题——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127.
The Exp loration of the Chinese Factor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ocialism and the M arket Econom y
WANG Qiang
(Party Policy O ffice,Chongqing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College,Chongqing 402160,China)
Beside the productivity,the open and comprehensive tradition named harmonious culture,the culture independence and confidence coming from the long history and thematuring party are the special Chinese factor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ocialism and themarket economy.The persistence of these factors is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better development.
socialism;market economy;harmonious culture;independence and confidence;the party's leading
F123.9
A
1672-9617(2015)04-0500-04
(责任编辑伊人凤校对祁刚)
10.13888/j.cnki.jsie(ss).2015.04.012
2015-06-28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引进基金项目(KRC201408)
汪强(1981-),男,四川彭州人,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