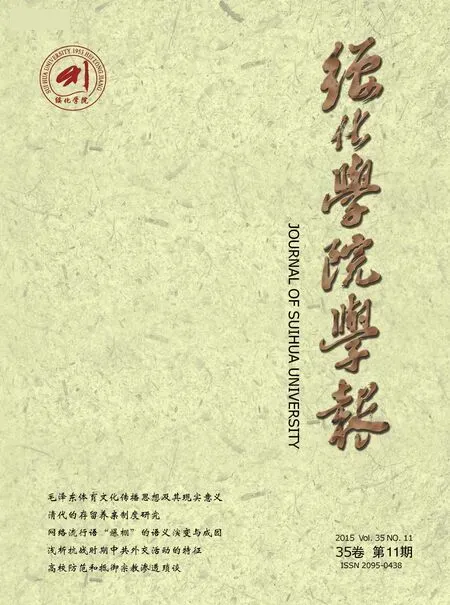《棋王》叙述视角与“棋”关系探究
王树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棋王》叙述视角与“棋”关系探究
王树奇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棋王》一直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作者在文中将道家哲学赋予象棋之中,从而在主人公王一生成为“棋王”的过程中将民族精神的根追寻至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棋王》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其通过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王一生传奇般的经历。文章通过对文本视角的选取和“棋”本身特点的比较,可以发现,文本中叙述视角的选取和被作者赋予了极大哲学内涵的“象棋”这一故事载体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具有极大关系。
观棋;观文;棋王;叙述视角
象棋属于二人对弈类游戏,与围棋、国际象棋等棋类游戏一样在世界上具有极大的游戏人群,而这种二人对弈类游戏也一直被视为是逻辑思维和智力水平的集中体现,具有很强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印记。特别是在中国,棋在发展过程中大致具有了三重的“棋道”境界:“一是作为茶余饭后消遣解闷的工具,具有游戏性和娱乐性的功用。二是对局者在棋盘上运筹帷幄,攻守征伐,具有战斗性和竞争性的特点。三是弈棋与人生宇宙相通,将弈棋看作是人生、宇宙的一个缩影,所谓‘世事人生一局棋’,具有象征性和哲理性。”[1](P1)而中国蒙学读物《名贤集》上早已有“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的棋训。值得注意的是,由这句常用的棋训可以看出,我们常常忽视了枰间一个重要的角色,即“观棋”者。除了“落子”者外,“观棋”者的存在对于棋局仍然是至为重要的一环,而由此出发去观照《棋王》这一文本的艺术审美魅力,我们又会发现其新的美学价值。
一、“棋”与“文”——由“艺”及“道”的哲学追求
中国哲学素有“道摄万物”的传统,自老庄以降,哲学意义上的“道”得以确立,“道”成为涵盖一切、统摄一切的存在,是宇宙的原始本源及支配万物的规律所在,对于这一哲学至境的追求,几乎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有活动的终极内核。在“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视阈下,“作文”已经成为“求道”的重要途径,“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2](P24),“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3](P15)。而同时,当“弈棋”进入古人的视野,在探究“棋理棋术”之时,发掘“棋道”与“大道”相通之处,便势必成为弈棋论棋的最终指向。“夫棋之制度也,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云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世道之升降,人事之盛衰,莫不寓是。惟能者,守之以仁,行之以义,秩之以礼,明之以智。”[4](P3)可见,即使在古代出现的专门性的弈棋指导性书籍之中,在谈论专门的弈棋技巧和布局之前,古人也早已将宇宙万物、人世变化的规律赋予其中。作为指导弈手弈棋的必备“导论”,这种哲学高度的审美追求已经超越弈棋本身而具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而“弈”与“文”在此时便取得了共通性——“文,介乎道艺之间,上以通道,下即为技,弈本为技,黑白相间而文成,依乎天理,遂成天地之文。人生而静,感物而动,文如此,棋亦然。感物而同天地之道,文亦道也,棋亦道也”。[5](P133)从何云波先生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讨论弈之道与文之道的系统有着极其相似的话语呈现,这一相似的背后实际上是二者最终美学追求的殊途同归。所以,由弈棋之道建构其哲学审美之道,进而介入文学作品的生成,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二、“观文”与“观棋”——“观者”的自我建构
相对而言,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弈棋是一种封闭的视野,而观棋则是一种开放的视野,因为弈棋是棋手间的“创作”活动,而观棋则是面向所有人。同样,文学写作是一种封闭的视野,而文学批评则也是一种相对开放的视野。而在这两种创作活动中,读者与观棋者都作为旁观者而间接参与了文本或者棋局的生成与构建。因此,在接收美学注意到文学批评中读者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再去反观“棋局”的生成,便会注意到“观棋者”和“旁观者”的作用——而当弈棋活动进入到文学文本的创作中,“读者”与“观棋者”的角色在这两种创作活动中达到相当程度的契合,又给文学作品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
如若将对于“作文”与“弈棋”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等量齐观的话,两者所具有的共通性似乎是颇为值得推敲的。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是去了解作品的“机心”——“不要以好胜的人为来破坏诗给我们的美感,他们怕‘封’(分辨、分析)始则道亡,……我们的批评在文学鉴赏时,只求‘点到即止’。”[6](P3)这种中国式的含蓄蕴藉的批评方式很大程度上要求对于文学的批评不要过于细致的分析与辨别,而是“佛祖拈花,迦叶微笑”式以心传心的领悟与欣赏。所以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提到这种批评方式“其异于亚里士多德者,其一要求‘聆听雅教’,其一要求‘参与创造’”[6](P4)。这也就意味着读者之于文本是有着双向的作用的,读者具有被动的“聆听”与主动地“创造”双重角色。而当弈棋进入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时,由于他们一定程度上共同的终极“求道”指向,两者之间势必会产生互相影响。
由是,当“聆听雅教”与“参与创造”的读者欣赏“机心”进入弈棋时,则不仅要求观棋者对于整个棋局加以关注,更注重观棋者对于整个棋局产生的影响。当然,此时的“观棋者”并非是真正单指存在的实体个人,而是对于弈棋者产生思维影响的外部世界。“世界诚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世间万物只有通过人的意识,才能显示自身。人揭示了世界……,作者单独一人不可能完成作品,作者创造作品的过程和方式不同于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和方式”。“需要有一个人们称之为阅读的具体行为,作品才算完成。”[7](P8)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会出现……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8](P124)由此可见,阅读者对于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产生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的,而观棋者对于棋局的影响,则是发生在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是这样一种生灵,他不能看到某一处境而不改变它,因为他的处境使对象凝固,毁灭它,或者雕琢它,或者如永恒做到的那样,把对象变成他自身。”[8](P107)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观棋者们由于对于棋局的观望而使得其变得与原来本初状态有所不同,因为观者的存在而使得对象成为了自身的存在,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东西一旦被叫出名字,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无邪性质。如果你对一个人道破他的行为,你就对他显示了他的行为。”[8](P106)由于他自己的行为已经被别人所道破,使得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在被观看,他们的行为必然与未意识到被现实被道破之前存在着区别。可以认为,在文本欣赏和弈棋观赏中,读者与观棋者因为视角观照文本或棋局的角度趋于一致,以及这种角度使得他们成为存在主体构建的参与者、生成者及组成部分,他们不再仅仅是一个处于外部世界的旁观者,在观棋过程中,观棋者诚然没有参与现实中弈棋者们的棋局,却在自己的意识中构建出了深切体现自己存在的实体——“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已对于世界而言是重要的。”[8](P120)
三、“我”的双重身份——《棋王》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
当“作文”将“弈棋”纳入自身的构建范畴之后,“观文”与“观棋”这两种活动便一定程度上融为一体,读者与观棋者取得了角色的一致性,这就为由“观棋”出发而去“观文”提供了可能性。而当我们由此出发去发掘“棋”之于“文”的影响时,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其对于小说文本叙述视角的影响。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和对棋手对弈的欣赏进行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种“创造”活动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将作家创作文学作品比之于棋手“创作”棋局的话,那么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品析则具有观棋者对于棋局的观赏的相似性。作为动态过程的“观文”和“观棋”,则更加契合了“观文”者和“观棋”者的心理:“阅读过程是一个预测和等待的过程。人们预测他们正在读的那句话的结尾,预测下一句话和下一页;人们期待它们证实或推翻自己的预测,组成阅读过程的是一系列假设、一系列梦想和失望;读者总是走在他正在读的那句话的前头,他们面临一个仅仅是可能产生的未来,随着他们的阅读逐步深入,这个未来部分得到确立,部分则沦为虚妄,正是这个逐页后退的未来形成文学对象的变换的地平线。”[8](P122)我们会发现,萨特关于文学阅读过程的解读与一个平常的“观棋”者的心态是很大程度上一致的,所谓观棋不语,观棋者对于棋局的反映都只能是内在的心理活动,但是,观棋活动无疑是一个“预测和等待的过程”,观棋者们无疑不是在预测棋手们的下一步棋路,甚至是下几部棋路,同时棋手们的棋路也在证实或推翻观棋者们的预测,整个观棋过程和萨特所说的阅读过程一样,是“一系列假设、一系列梦想和失望”,观棋者们永远走在棋手之前,所以他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可能产生的棋局。正是这两种逐渐后退的过程现象使得“作文”与“弈棋”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一致,而进而使得“观文”与“观棋”者在心理期待的过程中得到了共鸣。
以棋故事为载体的小说文本影响较为重要的有阿城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棋王》以及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于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象棋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两篇文本均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单就《棋王》来说,其并没有采取小说多用的“全知式”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而是把叙述视角定位于第一人称代词“我”,而“我”作为叙述者在作品叙述上属于次要人物,这种视角属于“内聚焦型”的叙述视角。这种叙述视角的采用,使得“每件事情都严格的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叙述者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者)的感官去听,去看,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收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9](P27)。换言之,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是具有局限性的,他获取信息的途径是有限的,叙述者的视野也即是读者的视野,他不能介绍自身的外貌,无法深入解析其他人物的思想,只能发表自己的所感所想,其他人物的出现只有进入叙述者的视野或思想才能得到介绍——而显然这种介绍又仅仅是叙述者的主观所见所感。由于视角选择的限制性,读者“难以深入地了解其他人的生活,难以把握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这种聚焦方式在赢得人们的信任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空白和悬念,而这些空白和悬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读者的一种解放。”[8](P30)可以看出,这种局限性的视角与观棋者们的视角又是极度吻合的,观棋者的视野同样是有限的,观棋者只能对自己看到的形势做出自己的判断,只能揣测弈棋者们的心理而不能全然知晓关于棋局的所有信息,这也就意味着,读者在欣赏文本时,在填补由内部聚焦所造成的空白和悬念过程中显示出了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在对于整体文本的构建过程中成为了其内在的构建因素——“观赏者的想象不仅有调节的功能,还有构成功能;它并非在做游戏,它只是被吁请越过艺术家留下的痕迹,重组美的客体。”[8](P128)而观者在实现自己的构成功能、重组美的客体的同时,“我”的价值得到了最为直接的体现,“我”的双重身份此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观棋者”与“棋局”的关系,正如“读者”之于“文本”的关系一样,每个读者对于文本的阅读会使对文本的解读赋予个人化的色彩,一千个读者也就具有了一千个文本。同样的,每个“观棋者”对于“对方”的棋路走势,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和回应,并且不断“预测和等待”,完成一系列“假设、一系列梦想和失望”。一千个“观棋者”实际上也就有了一千个棋局、一千场对弈。这种效果的实现,是要以读者置身其中的才能够实现的。读者不断地填补空白,确立自己的存在,观棋者不断做出自己的判断,走出自己的棋局,于是二者在文本生成中自然而然地都站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位置,从而确立了两者面对的“世界”与“自身”的统一性。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使得《棋王》的叙述具有强烈的个人传奇性色彩,故事叙述的主人公“棋王”王一生传奇的经历通过叙述者“我”的叙述而被读者所知晓,然而“我”仅仅是王一生部分经历的“观者”而已。当第一人称的视角确定之后,“叙述者的工作由‘我’全面接管过来,目击者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他多少卷入故事的行动。与主人公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既然作者选择一个人物来叙述故事,他就只能表现该人物作为一个旁观者能够观察到的东西,例如,它不能直接表现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只能揭示目击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目击者可以说是站在故事的边缘讲述故事。”[10](P199)事实上,在王一生与“我”分开的时候,“我”也只能通过自身所闻所想来猜度臆测,为读者填补关于王一生的种种未知,而包括最后车轮大战后“我”通过王一生有所“悟”,然而“我”叙述的主人公“棋王”王一生到底“悟”没“悟”,又“悟”到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整个叙事最后的“机心”仍然可以认为是在“我”,而“我”在文中始终处于“观棋”的视角和位置上。在文本之中,“我”作为“观棋者”而从“下棋者”王一生及其棋局中悟到了人生的道理,王一生的棋局由于“我”的观察思考而成为了“我”自我建构的一环。同时,在文本之外,读者也同时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对主人公王一生及其所代表的“道家”思想进行个人化的体悟与领会。对“我”由于视角所限而无法交代的未知空白,读者用自己的想象来加以填补和具体化。而这种填补和具体化的过程,不仅使得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内化为了自我构建的一部分,同时在此基础上,“观棋”与“观文”最大程度上得到了契合。这里实际上出现了两个“观照”系统,“我”(观棋者)——王一生(下棋者)——棋局;读者(观文者)——文本作者——文本。而两个系统间的纽带即在于“我”作为“观棋者”与读者作为“观文者”在采用第一人称内部聚焦的视角时所得到的“吻合”的观照效果——即“我”与“读者”在视野上得到的观照效果的统一,两个系统得以接合的根本前提便是“棋”与“文”的互相观照。
(一)观棋之道——“我”之悟道。邵雍在《观物内篇》中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而他也在其观棋诗《观棋大吟》中提到:“人有精游艺,予尝观弈棋。算余知造化,著外见几微。”[11](P181)而李渔也对听琴观棋评价道:“喜谈不若喜听,善弈不如善观。”[12](P101)可见,在古时已有人注意到对弈之中观棋者的重要性以及对于观棋的要求。实际上,早在唐时就已经在文人士大夫中形成了不以胜败寄心的观棋之风,直至明清,均有名人棋士留有观棋诗作,如邵雍、苏轼、黄庭坚、陆游、解缙、尤侗等,“观棋悟道成为中国围棋史及文化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3](P71),自东汉班固作《弈旨》开“以易解弈”之先河,将其中哲学思想纳入棋道的解读和建构,这种思想也必然影响观棋之道。
在《棋王》之中,“我”叙述的焦点自然是在棋王王一生身上,“我”作为向读者传达王一生所言所行的“视线”,自然是在棋王之“棋”上。“我”观棋王之“棋”,在火车上看他与“抱缸子”的人下,我看得应该说较为仔细,详细地叙述了几部棋路,却又说道觉得这平常的开局没意思且对象棋没兴趣,便“转了头”——整个过程中“我”一言未发,一举未动,并未对棋路发表出自己的看法,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观棋不语”者。接下来观王一生与“脚卵”倪斌之棋,“我”依然是对棋局不发一言,只是在有几人说“好没意思”离开后依然继续观战,并注意观察了两位棋手——“像是瞧从来没有见过的两个怪物”,直到看出是谁赢了,大家都松动起来,盯着王一生看。包括“我”在内的众知青在整个过程中都对棋局默契地保持了静默的状态。直到最后王一生大战九人的车轮大战,我作为一个人群之中的观棋之人,仍然保持了“无为”“不语”的观棋者风范,开棋之后“我”并未交待棋路而是直接呈现自己“观棋”的“幻象”——“读过的书”“项羽刘邦”“士兵”“樵夫”“呆子的母亲”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这东西是什么,“我”没有交待,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我”从“观棋”过程中是有所“悟”,有所“得”的。他对于对局时王一生的话也并未一字出口,只是赌一口气,“死顶吧”,自己“捡个地方坐下,仰头看最后的围猎……”“我”观王一生之棋,恪守观棋不语的棋训,虽然一直声称不懂棋、没兴趣,却局局都能看出门道——“简单的开局”、下棋是“精细的”“走盲棋”“后方老帅稳稳地呆着,尚有一‘士’伴着,好像帝王与近侍在聊天儿,等着前方将士得胜回朝……”最后在观完王一生一场浩大的车轮大战之后,兀自醒悟到了“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自从在火车上认识王一生以来,“我”并未与王一生有长时间的交往,分开后每个人在各自的农场都有自己生活,王一生进入“我”的视野,“我”便开始对了王一生及其“棋局”的“观照”,当王一生消失在我的视野,“我”便停止这种“观照”。“我”在道听途说关于“棋王”王一生事迹到认识王一生再观“棋王”之棋的过程中,渐渐把“观棋”融入自己本身存在的建构之中,严格遵循“观棋”之道,并在此过程中完成自己的“悟道”过程——对于“衣食”、对于“棋”、对于“真人生”。
(二)观文之道——“读者”之悟道。阿城《棋王》一文的语言风格,总体上以白描为主,全文行云流水、没有制造激烈的戏剧冲突,只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带领”读者去了解了“我”“听说”的王一生以及“我”“看到听到想到”的王一生,一定程度上来看,读者所看到的王一生,正是“我”所看到的王一生,而“我”和王一生各自分开的时候,“我”又把自己听到和想到的王一生“转述”给了读者们,一定程度上对读者对于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的理解是有“牵制”性的,可见,读者诚然可以对由于人称选择导致的视野空白进行个人化的填补、构建以及重组,但是作者可以通过“我”去“左右”读者的所见以及所闻——“既然作者与读者的自由通过一个世界彼此寻找,相互影响,我们既可以说作者对世界某一面貌的选择确定了他选中的读者,也可以说他在选择读者的同时决定了他的题材。所以所有精神产品本身都包含着他们选中的读者的形象。”[8](P145)
诚如萨特所言,既然读者的形象是被选中的,那么,读者便是经由作者、作品以及“我”去介入作品之中的或者说去将自身内化为作品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读者,由于自身着眼点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其作为读者对作品解读的多重性特征。如《〈棋王〉与道家美学》《从儒、道精神解读寻根文学〈棋王〉》《浅析〈棋王〉的文化寻根》等,纷纷将其视角定位在《棋王》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上,而有些则将注意力放在了文本的叙述上,如《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棋王〉的叙述层次及其艺术功用》《〈棋王〉的叙事艺术》等等,可以看出,对于同一作品的不同解读是文学批评司空见惯的特征,读者对于《棋王》的阅读接收过程也正如观棋一样,呈现出读者作为观者的个人化解读,读者在其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观赏自由。应该看到的是,作品中的人称叙述将“读者”的地位置于一个与“叙述者”“我”“观棋者”三位一体的角度,使得文本呈现出强烈的读者存在感,使得阅读本身成为读者显示自身的重要部分,而读者也在此过程中领悟出《棋王》之于自身之“道”。
结语
可以看出,《棋王》一文中对于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选取,不仅在叙事意义上有重要意义,而且与其文本中“棋”这一叙述媒介本身在中国文化视域下所具有的特点密切相关,从“道摄万物”到“文以载道”再到“弈与文通”,使得整个弈棋过程和文本的创作过程得以贯通,最后获得了“观棋者”与“观文者”身份的契合,使得“观文”与“观棋”在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和建构上呈现出合而为一又各具特点的跨学科意义。
[1]张如安.中国象棋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2][南北朝]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元]晏天章、严德甫著,虞集序[A].玄玄棋经[M].天津:天津科学出版社,2009.
[5]何云波.弈与文通——中国古代棋论与文论的比较研究[J].中国比较文学,2005(2).
[6]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7]施康强,萨特文集7·文论卷·导言[A].萨特文集(7)文论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法]萨特著,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罗钢著.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1][宋]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清]李渔,沈勇译注.闲情偶寄[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13]张东鹏.中国哲学与围棋之道[D].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12.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207.427
A
2095-0438(2015)11-0041-04
2015-06-19
王树奇(1989-),男,河南林州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学术创新项目“棋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WXY14YJS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