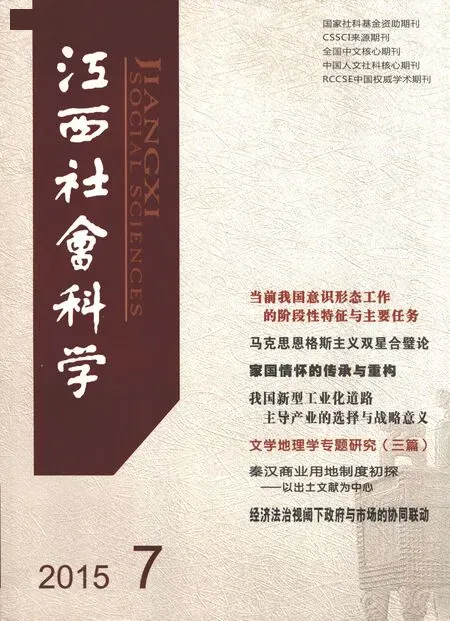明代江西仓储述论
■谢宏维 温小红
仓储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悠久,意义重大,关乎国计民生,被视为“天下之大命”。明代极为重视仓政,继承汉代常平仓、隋代义仓及宋代社仓之遗意,广设仓储,“国家设仓庾储粟以赈军民,两京直隶、各布政司府州县、各都司卫所以及王府,莫不具备”[1](卷21《户部八·仓庾一》)。仓储建设也有新的发展。关于明代仓储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为我们认识这一研究对象构建了基本框架。尽管如此,这一领域仍留有一定深入的余地。目前尚未见专门研究明代江西仓储的成果,本文即以明代江西仓储为个案,通过区域性实证研究,以期加深对明代仓储体系、荒政及江西区域社会变迁的理解。
一、明代江西仓储概况
明代仓储实行分级储粮的多仓制,有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粮仓和地方各种粮仓,还有藩王的王府粮仓。仓储名目繁多,有京仓、通仓、水次仓及预备仓、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名称,以及全国各地各具特色的其他众多称谓。仓储的用途大致有三:一是供军饷,二是供官俸及城市市民口粮,三是备荒救灾。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京卫有军储仓。洪武三年(1370)增置至20所。各行省有仓,以供官吏俸取给。边境有仓,收屯田所入以给军。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赈凶荒。“凡京仓五十有六,通仓十有六。直省府州县、籓府、边隘、堡站、卫所屯戍皆有仓,少者一二,多者二三十云。”[2](卷79《食货志三·仓库》)明前期,国家重视和支持预备仓建设,积谷备荒几乎全赖各府州县预备仓。及至明中后期,社仓、义仓建设逐步受到明廷的重视,逐渐成为民间重要的仓储制度。
自六朝以来,江西地区的经济开发迅速展开,农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粮食产量增加。自东晋起,江西已成为重要的产粮基地和粮食输出地,也是重要的粮食积储地。“自晋迄陈,称大储备处者有三,豫章仓实居其一。”[3](卷88《经政略·仓储》)及至明代,江西仓储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大力发展。
根据《明实录》、《明史》、《明会典》及江西各府、州、县地方志等资料,兹将明代江西各地仓储情况列表如表1所示。
尽管上述统计数字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①,但应可反映明代江西仓储的大致情形和发展趋势。明代江西仓储类型多样,名称各异,有预备仓、预备粮储仓、便民仓、存留仓、兑军粮仓、水次仓、社仓、义仓、赈济仓等。从表1看明代江西仓储众多,而这些仓储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官仓,一为民仓。其中,官仓包括预备仓(预备粮储仓)、存留仓、便民仓以及与漕运相关的水次仓、兑军粮仓。民仓则主要有社仓、义仓。
从数量上来看,明代江西13府仓储总数为393所,其中以预备仓(预备粮储仓)为主的官仓占绝大多数。江西各府仓储的数量不一,其中以吉安府数量最多,达60所;其次为南昌府,达46所;再次是广信府,为39所。其他各府数量,袁州府34所,赣州府33所,饶州府32所,九江府28所,抚州府23所,临江府22所,瑞州府21所,建昌府20所,南康府19所,南安府16所。各府仓储的数量悬殊与分布不均,与各府所辖州县多少、农业发展水平、灾害发生频率、地方官员的重视及民间财力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

表1 明代江西各府仓储数量统计表
从仓储的建立时间来看,预备仓等官仓创建最早,社仓、义仓等民仓则相对较晚。明代江西最早建立的预备仓是洪武元年袁州府知府裴颙重建的永丰仓[4](卷4《储恤》),建昌府新城县知县沙良佐重建的预备仓之中仓[5](卷10,《恤典》)。袁州府分宜县的济留仓亦于洪武初创立[4](卷4《储恤》)。南康府丰济仓于洪武二年创,广信府广济仓于洪武三年建,南康府都昌县存留仓于洪武五年建。这些预备仓的创立,与洪武初“令天下县份,分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1](卷22《仓廪二》)的谕旨有密切关系。不过,这时的仓储并不多,很多府县还没有建立。洪武二十年之后,江西各地创建预备仓更为普遍。洪武二十年,“令各县皆立预备粮储仓,官备钞收买谷在仓,遇岁荒歉发以赈饥。民计口关支,秋熟则抵斗还官”[6](卷4《南昌府·建置沿革·恤典》)。南安府南康县于洪武二十二年建预备仓。洪武二十三年六月,明太祖遣老人往江西诸郡县收籴备荒粮储,凡钞1 553 924锭。[7](卷202,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丙戌)瑞州府便民仓、临江府新淦县预备西仓、建昌府南丰县预备仓、抚州府临川县预备仓、南康府建昌县预备粮储仓、南康县预备仓俱建于该年。南康府都昌县预备粮储仓,洪武二十四年籴谷储积以备赈济。丰城县预备粮储仓于洪武二十六年创建。此外,赣州府雩都县预备仓,袁州府萍乡县存留仓,饶州府鄱阳县大有仓,九江府广盈南仓、北仓俱洪武间建。可见,江西大多数府州县在明初尤其是洪武后期创建了预备仓,为明代江西仓储盛行奠定了基础。
明代前中期,预备仓、便民仓的修建仍在继续,有的属于新建,有的则是在旧仓基础上进行改建。抚州府崇仁县中镇仓,正统四年(1439)建。瑞州府上高县便民仓,正统、天顺间修;新昌县便民仓,景泰间推官秦连建,成化十八(1482)年,知县汪道修厅三间仓四十间。袁州府分宜县预备仓,东仓、西仓、南仓、北仓、石镇仓、严渚仓、美塘仓、浆源仓,俱景泰初建;府城南预备仓,成化元年知县靳敏改建,弘治间郭絍、戴乾各添设廒一所;城东预备仓,弘治十四年(1502)立。[4](卷4《储恤》)万载县便民仓,成化十二年立;官田仓,弘治初立。赣州府会昌县昌聚仓,成化中建;龙南县预备仓,成化年间建,弘治年间增建;宁都求宁仓,弘治年间重建;瑞金县永丰仓于正德间改建。抚州府乐安县河南仓,成化年间建。建昌府南丰县预备粮储仓,成化十五年建;南城县西仓,正德十一年改建。九江府彭泽县预备仓之新南仓,景泰五年知县王本增置,新北仓,正统知县邓周增置;瑞昌县预备仓,弘治五年建。临江府新喻县预备仓,弘治七年改迁县治东北。南安府上犹县预备仓,弘治十八年建。
至嘉靖、隆庆年间,预备仓已较少新建,多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加以修缮改建。如南昌府武宁县市镇仓,嘉靖二十二年(1544)改建。九江府瑞昌县永丰仓,旧在十字街之东,东山寺之右,弘治五年知县朱廷宗迁建于小南街,正德十一年知县黄源大以东山寺址宽,申请迁建中厅一间,左右廒各一间,前七间,左右各三间。嘉靖间,左廒倾坏,知县骆秉韶建。[8](卷2《建置志·仓》)临江府新淦县便民仓,旧名粮储,弘治间在县西北,正德间改迁南河口,更名便民,后废。隆庆四年,知县李乐改建于城隍左。[9](卷4《建置·仓储》)岁久滋弊,此时,预备仓名存实废,有些仓甚至被改建为其他场所。如南昌府广积仓,嘉靖三十八年改为校士公署。[10](卷4《创置志》)至此,预备仓已走向衰败,无法承担积谷备荒的重任,故“社仓、义仓不可不广”[11](卷566,万历四十六年二月戊戌)。
早在景泰年间,社仓即见于南康府。正德《南康府志》载:“社仓,景泰间知府陈敏政效前立法以赈饥,敛士人掌之。”[12](卷4《公署》)弘治中,江西巡抚林俊尝请建常平仓及社仓(义仓)。林俊指出,此时江西各州县预备仓积谷并不多,“今欲公私两便,惟有常平可复而已”。又再劝社民各立义仓,其法为“社中富民任其出谷六百石或四百石别处一仓,极贫利一分、次贫利一分,春借秋还”。若常平既复,社仓又行,则饥馑有备,达到备荒救灾的目的。“此预备至计,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为急者。”[13](卷87《请复常平疏》)至嘉靖八年,“乃令各抚、按设社仓”。具体做法是,“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正,能书算者一人为社副,每朔望会集,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户主其事。年饥,上户不足者量贷,稔岁还仓。中下户酌量振给,不还仓。有司造册送抚、按,岁一察核。仓虚,罚社首出一岁之米”[2](卷79《食货志三·仓库》)。此后,江西社仓和义仓得到初步发展。建昌府新城县、南城县,瑞州府新昌县,临江府清江县,广信府贵溪县皆创立了社仓或义仓。南昌府进贤县社仓36仓,俱万历间县令黄汝亨建。
从明代江西仓储发展的大致历程可以看出,明前期,江西仓储以预备仓为核心的官仓为主,明后期预备仓政走向衰败,社仓、义仓逐渐兴起,不过规模有限。
二、明代江西仓储的修建与组织管理
从修建主体和组织管理来看,明代江西的仓储分为官修和民修两大类。明前期,仓储的修建者主要是地方官员,如知府、知县、典史、同知、兵备副使等。至明中后期,除地方官员倡修外,还有地方士绅、富民(义官、义民)及宗族、宗教组织等主持或参与修建。
明前期,江西大部分的仓储都是由知县修建,知府、典史、同知、兵备副使修建比较少。如南康府都昌县存留仓,洪武五年知县孟泰初建。抚州府崇仁县中镇仓,正统四年知县宋彬建。袁州府分宜县预备仓,东仓、西仓、南仓、北仓、石镇仓、严渚仓、美塘仓、浆源仓,俱景泰初知县吴江建。万载县便民仓,成化十二年知县陈璨立。赣州府龙南县预备仓,成化年间知县萧经建,弘治年间知县张文增建。临江府新喻县预备仓,弘治七年知县芦翊改迁。从各地方志记载来看,明代江西的预备仓的修建主体是地方官员,人员组成比较单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以天灾及赈灾为契机,正统、景泰、天顺年间,明廷推行“旌异优免”、“冠带荣身”、“纳米入监”等政策动员民众赈灾助饷②,掀起了一股由官方倡导、地方富民捐纳,共同修建仓储的热潮。江西地区在此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万历《明会典》记载:“祖宗设仓贮谷,以备饥荒,其法甚详。凡民愿纳谷者、或赐奖敕为义民,或充吏,或给冠带散官。正统五年,议准凡民人纳谷一千五百石,请敕奖为义民,仍免本户杂泛差役。三百石以上,立石题名,免本户杂泛差役二年。又令各处预备仓,凡民人自愿纳米麦细粮一千石之上、杂粮二千石之上,请敕奖谕。”[1](卷22《仓庾二》)正统二年五月,明廷旌表江西吉安府胡有初、谢子宽,浮梁县范孔孙等10人为“义民”,因“各出稻千石有奇,佐官赈济”,诏赐玺书旌劳。[14](卷30,正统二年五月戊午)明廷给予出谷1000石,“佐官赈济”的南方富民以“义民”的国家荣誉,并免除其家若干年杂役。景泰三年,江西巡抚韩雍劝富民纳粟两千石以上,奏赐冠带,旌为义官;1200石以上,奏赐玺书,旌为义民。[10](卷24,《杂录类·纪事》)景泰四年(1453)九月至五年二月的半年间,明廷分6批旌表的富民的分布令人惊叹:景泰四年九月,旌表江西南昌府万邦敬等28人、吉安府彭遵等16人;十月二十七日,旌表江西瑞州府杨景和等11人、袁州府谢琳等17人;十一月,旌表江西临江府黄汉高等22人、南安府傅伯真等4人、赣州府李宜吉等15人;十二月,旌表江西抚州府汤汝佐等41人。五年正月,旌表江西建昌府管文升等9人、饶州府周仕英等28人;二月,旌表江西广信府潘永年等6人、南康府万志谦等4人、九江府汤彦海等4人,又旌表直隶永平府民许敬等5人。210名受到旌表的富民,除最后一批北直隶永平府5人之外,均来自江西,而且全部被列出姓名。景泰六年,建昌县“添设存留仓并义仓,劝民出谷储积,以广赈给”。该县富民胡孟哲、胡缉定、李永端、杜世文、彭希仁、赵希明、吕均辉、李成郁、杨泰观、黄伯琛、周威文、李英、魏济、李廷瓒、顾鉴、胡秉常、杨应起、邹景云、淦节厚、陈炅、宋弘可、吕彦中、龚俨、彭尚文、魏勉旃、胡元节、彭永文、邹贵泉、刘继州等,各输谷千余石。[15](卷2《仓狱·仓廪》)这种官方“劝富民借谷”并予以旌表的做法,拓宽了仓谷的来源,客观上促使仓储的性质与管理发生变化。
从明中后期开始,江西仓储的修建主体比明前期更加多样化,不仅有地方官员,还有当地富民(义民)、宗族等。由地方官员主持修建的仓储仍然较多,如九江府德安县预备仓,嘉靖二年知县梁一桂创。瑞州府新昌县义仓,知府邝璠改迁。广信府贵溪县社仓,知县卢格建。临江府清江县社仓,隆庆二年知府马文学劝借民粟,贮之备荒。[9](卷4《建置·仓储》)隆庆三年,德安县令陆勋立义仓,“劝富民输谷数百石,以备赈贷”[16](卷8《职官志·名宦》)。进贤县社仓36仓,俱万历间县令黄汝亨建,“其实粟之法,首捐赎,次劝义民,小讼愿息,输石斗者听”。有完全由民间修建的仓储,如建昌府新城县义仓有二,一为义民杨振邦于成化年间发粟300石储之于社,一为义民程正宗建,积谷1000石,令孙汉善继之。[17](卷6《恤政》)“江右四君子”之一的新城人(《明史》记为南城人)邓元锡,嘉靖中期17岁时,即在家乡施行社仓法,惠其乡人,储粮备荒,赈灾扶困,深受邻里爱戴。[2](列传第171《儒林二·邓元锡》)还有的粮仓是由宗族复建的,如南城县社仓,宋时吴伸、吴伦所建,自宋迄元屡遭兵焚。正德十一年七月,伸、伦子孙告县兴复,时宰孙君甫义之,易其扁曰“崇古惠民”。[5](卷10《恤典》)
仓储积粮的来源及其管理是仓政极为重要的问题。明代江西仓储的仓谷来源主要有地方赋税的存留、官钱专款籴谷、赃赎银款、息粮收入及奖劝富民纳粮等。不同时期的仓谷来源是不一样的。总的来看,从明前期到中后期,储谷来源由单一化逐渐向多元化转变,从主要依靠官府逐渐向民间劝借转变。南安府南康县预备仓积粮来源的变化是一个典型个案。明初,南康县有预备仓4处,东仓在太平三里河岭头,西仓在西门外,南仓在太平一里南水渡口,北仓在义仁四厢古驿村,俱洪武二十三年知县吴玄建,“官籴谷贮仓备荒”。先是洪武二十二年县丞戴珍建有县仓一所,在县治仪门左,收贮赎罪谷石随时给济。后将在乡四仓迁并于此,就近便于查防侵蚀漏卮之弊。至正统七年,巡按薛希琏劝借义民蔡有经、王子安、郭溥、王富儿、刘伯通、黄大备、邓汝器、蔡惟庸、吴子彰、吴永嘉等各出谷赈济,奏闻,旌表有敕。景泰四年,巡抚江西、都察院右佥都御使韩雍劝借于义官陈孟琦、蔡朝俊、王世隆,义民朱子华、赖懋善、杨瑶、赖懋贵、王琏中、刘用清、王彦佐、张永康等。天顺五年(1461),知府汪鉴劝借义官王琏中、杨瑶等。成化四年,同知施奎劝借义官王贯实、阳子瞻、蔡邕宁、刘用丹、王世全、蔡应钟、郭嘉谋等合力捐谷储备。十五年,南安府发生大饥荒,知府张弼建议劝借义官王佐、杨玉莹、刘源庆、赖经魁、赖懋端、赖吉麟、杨金绅、赖吉瑞、何观海、蔡斐安、商名修、袁安、刘景华、王仁坚、吴广、朱用祥、张颐顺、李继显、田胜凯、卢英、李安、王贯魁等就于本府纳银籴谷储仓,事闻,荣以冠带。嘉靖八年,王贯魁之子纳谷1600石备粮,奏闻,旌表有敕。[18](卷4《储恤》)嘉靖后期,南康县地方士绅指出县仓预备仓“奸弊百出”,希望能在各乡兴建社仓义仓:
有司能以民事为念,莫若及时闲暇仿隋制,俾民于各社立仓,每岁收获之时,上户一石,中户七斗,下户四斗,大熟稍倍之,岁久而积多,掌之以社长,正之以各社之有行谊者。或遇凶饥,即发此谷赈济,县官岁稽其出入之数。其有慕义出谷稍多者时一奖劝之。如此则不必文移往覆之烦,而各乡皆可以自给矣。故曰:赈饥莫要乎近其人,义仓取之于民不厚而置仓,当社饥民之得食也,其庶几乎。要之,县仓在官,义仓在民,二者兼而行之,亦救民于未荒者也。[18](卷4《储恤》)
明代洪武、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嘉靖朝的各个时期,南康县预备仓的仓谷来源趋于多样化和民间化。从官府籴谷贮仓到劝借富民捐谷、纳银籴谷储仓,再到地方士绅倡建社仓义仓,可以窥见仓储转变的某些新动向,也昭示了明朝地方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和富民、士绅、宗族等地方势力的崛起。
预备仓作为明朝政府的官仓,在管理上有严格的措施。第一,预备仓的仓谷有规定,其积粮来源前后期有所不同。洪武到成化、弘治时期,预备仓一般能得政府的专款或地方存留余米;从正统开始,“捐纳”成为一项重要的谷本,到成化时,或奖敕,或充吏,或与冠带,或度碟;赃罚纸赎沦为谷本亦始于正统,到嘉靖、万历时为甚,几乎成为此时期积谷的主要来源。积粮的标准,明代前后期也不一样。第二,赈谷有通例。预备仓谷的发放经过了赈贷、赈粜、赈济等形式的演变,有时赈济也寓于赈贷和赈粜之中。赈谷有一定标准。明代江西地方官员报告,“该省查照地方被灾分数,督行府县各掌印官与同仓谷相兼赈济”,附近之民计丁给谷,僻远之民计丁给银,“大口六斗,小口三斗”。[10](卷25《艺文类·奏疏》)“每岁四五月,青黄不接,查该乡贫民量给,收成之际,令其每石出息二分,本利一并还官。若年岁荒歉,即作赈恤不取。”[10](卷25《艺文类·文移》)第三,守仓有严法。洪武时,预备仓由官府授权大户看守,老人管理支放,稍后设仓官、土官经营,正统时罢之,仍旧由州县官亲临收放。严行自负盈亏,严禁侵盗仓粮,凡各处预备仓有侵盗私用、冒借亏欠等项,只要补赔,可免治罪。否则,以监守自盗论处。至于借用未还与亏折等项则限期归赔,过期罚米赎罪。成化时,再次申令预备仓由州县掌印官亲管放支,不许转委作弊。弘治十年,规定三年一查地方积谷之数,并以此作为地方官政绩的一项指标。
而对于义仓与社仓,官府一般只给予指导性意见,较少进行干预。社仓基本属于民办民营,谷本主要由民间自积,通过劝借与劝捐两种方式筹措,其范围已由富民扩大到社内各户,令社众按定额向社仓输谷,加强对社谷散敛的管理。严格控制社谷的使用,切实加强对借贷的管理。为防借多难还,社仓普遍对民户借谷定有限额。“秋成谷贱,六石籴入,春夏谷贵,五石四斗粜出;秋成五石籴入,春夏四石五斗粜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备折耗存积。俱令社长、社正开报,贫民每丁止买二钱,以杜兼利。”[10](卷25《艺文类·奏疏》)社仓内部还建立有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机制。一般从本乡本里选人监督社仓之管理。社谷“岁久而积多,掌之以社长,正之以各社之有行谊者”[18](卷4《储恤》)。社仓通常设社正(或称社长、义正、社首)一名,社副(或称义副)一二名,社杰(或称社干、斗级)若干名,社直若干名。他们分工明确,互相牵制。实行社仓管理人员更代盘查制度。一些社仓的管理人员并无明确的任期,往往“称则勿易,不称易之”[9](卷4《建置·仓储》),但多数社仓的管理人员有明确的任期,一般一年一换,一换一交。新老管理人员交接之时,双方须共同盘查仓粮,并登记造册,具结为凭。社仓很大程度上实行乡里自治,不过也要受到官府的监督。嘉靖三十一年,鄱阳知县谓“社仓之建,盖仿古常平仓遗意,诚救荒良策”,“社仓之设,佥邑之殷耆而公平者为长、副,司其出纳,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照户口众寡登簿给发,或一石或五斗,不许过多,多恐有弊,愿借者听。随报随给,至秋成还仓,每石收耗谷一斗,外不起息,若其年无秋,须缓征,徐补之”。于每年仲冬晓谕社长人等,将现存社谷各开实数、手本并结状呈县,不许假捏虚报,如有亏欠,少则勒限追赔,多则计赃究罪,如此则“人知警惕,谷无虚名”。[19](卷3《公署·仓厫附》)南康县社仓,县官每年稽查社谷出入之数。万历间,进贤县建立社仓,“每年择忠实里保二人董其事,官置簿三扇”。
三、明代江西仓储的作用及评价
在灾荒饥荒来临之际,明代江西的仓储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一定的实效。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南安府上犹县知县戴辰、耆民沉思达奏岁歉民饥,请以预备仓粮贷给。明太祖谓“天下预备仓廪,正为荒歉而设”,“即遣人与县官、耆民照户给之,务使饥民切沾其利也”。[7](卷217,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壬辰)同年六月,南康县亦岁歉民饥,以预备仓粮贷给饥民。[7](卷218,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辛未)宣德二年(1427)三月,九江府彭泽、德化二县各奏去年水旱,民皆缺食,已借官仓粮给济,秋成偿官。[20](卷26,宣德二年三月己丑)星子县自宣德二年以来水涝不收,致使第二年春夏民皆缺食,发预备仓粮赈济。[20](卷48,宣德三年十一月辛亥)宣德三年春夏以来,彭泽县民多缺食,将预备仓谷及存留各年粮米给贷,俟秋收偿官。[20](卷47,宣德三年九月庚戌)宣德八年五月以来,瑞昌县民饥者众,贷本县预备仓谷5132石赈济。[20](卷104,宣德八年八月戊戌)宣德九年十一月,吉安府所属九县岁旱民饥,已借预备仓谷给尽,奏请再于府县大有等仓粮储内量借赈济,俟明年秋成还官。明宣宗命行在户部即如所言给之。[20](卷114,宣德九年十一月辛卯)正统三年十月,赣州府兴国县岁旱无收,人民缺食,已将预备仓粮验口赈给,具以数闻。[14](卷47,正统三年十月庚申)正统十四年,吉安、南昌、临江三府四月以来骤雨,发生洪灾,官民廨舍俱被冲塌,麦苗淹没,人畜垫溺,发预备仓粮赈贷。[14](卷179,正统十四年六月壬戌)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崇仁县发生饥荒,“邑令陈公尽发惠民仓及社仓谷平粜,有饿莩及不能籴者,日给糜粥食之。县簿张亦殚心共救,岁虽饥而不害”[21](卷10《祥异》)。
而且,社仓与保甲、乡约相辅相成,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巩固明朝的统治。社仓的创办,须依托保甲、乡约。明代社仓的普遍设置,又带动了保甲、乡约的推广。在南赣地区,只要“有司加意于十家牌法,以联属其民,则民志一,而(义仓等)诸政可举”[18](卷4《储恤》)。
明代江西的仓储在备荒救灾和社会控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弊端,如米谷资金严重不足,利益分配不均衡,民不沾实惠,吏治败坏,管理混乱,仓谷多被侵盗挪用,致使谷本渐失等,从而影响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如鄱阳县社仓,万历壬子(1612)后,“主计者因填补他项,收银而不收谷,遂成无米之炊。后来上司每下积谷之令,仓设于县前,只有罚谷之名,未见积谷之实,恐所在皆如是也。社仓则艰于放本,常平仓亦艰于籴本”[19](卷3《公署·仓厫附》),南康县“各仓非有司能专,岁凶告给,文移往复,动经旬月,比及报可,又奸弊百出。所谓受惠者,皆近郭力能自达之人耳!其诸山谷乡遂之远,安能扶携及时以就给令之廪哉”[18](卷4《储恤》)?故一些仓储时兴时废,难以持久,甚至徒具形式,有名无实。因此,对明代江西仓储的作用不宜评价过高。
总之,明代江西的仓储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大力发展,类型多样,数量较多。大致来说,明前期,江西仓储以预备仓为核心的官仓为主,明后期预备仓政走向衰败,社仓、义仓逐渐兴起,不过规模有限。同时,其修建与组织管理经历了由单一的政府官办包办向多元化的社会办理的转变,这昭示了明代江西区域社会发展面临的某些新动向,即地方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与富民(义民、义官)、士绅、宗族、乡族等地方力量的兴起。明前期,地方上许多重要的公共设施(如仓储、水利工程等)多由政府出面组织兴修,进行直接管理。明中期以后,由于地方财政日益困乏,政府相继放弃了许多原来的行政职能,尤其是把管理各种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士绅及宗族、乡族势力。地方政府只参与一些较大的公共事务,其他则授权给士绅,由他们组织乡民筹措经费并自行修筑、管理。
注释:
①材料取舍不同,加之考证之据不足,统计数字可能会有偏差,如万历《南昌府志》卷4《创置志》所记宁州仓庾数即与他书有异。
②参考方志远:《“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景泰、天顺时期赈灾助饷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16](清)沈建勋.(同治)德安县志[A].中国方志丛书[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18](明)刘昭文.(嘉靖)南康县志[A].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4册)[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
[19](清)陈志培.(同治)鄱阳县志[A].中国方志丛书[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20]明宣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1](清)盛铨.(同治)崇仁县志[A].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49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唐宋义仓与明清义仓之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