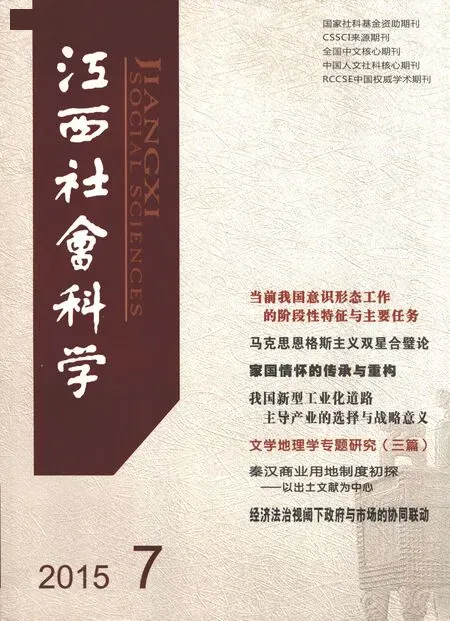地权变动与清代东北移民
■管书合
移民和地权关系,是影响清代东北历史进程的两个关键问题,学界已经分别做了相当深入和有分量的研究。而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却尚未引起注意。台湾学者赵中孚曾提出,“东北三省特殊的地权关系,是据以分析东三省移垦社会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1]。不过该文主旨在于考察清代东北地权关系与封禁政策的关联。本文拟在考察清代东北地区移民及移民社会的发展脉络与地权关系的变化过程基础上,初步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关内人民涉足和经营东北,虽然可以远溯至先秦时期,但直到明末清初,这一地区仍然可以根据地形、经济和文化划分为三个区带,且特征鲜明。在从山海关到开原之间的辽河下游地区,亦即辽沈平原,是满汉等族杂居的农耕文化区;开原以北至外兴安岭之间森林,是散居着索伦、达斡尔、鄂伦春、锡伯、赫哲、奇勒尔、恰克拉、费雅喀和库页人等部落的渔猎文化区;西部的草原,则是蒙古诸部的游牧文化区。
清初,因长期战乱和满族人口大批“从龙”入关,辽沈农耕区人口锐减、农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2](卷2)。为恢复生产,顺治初年采取鼓励关内汉人移居的政策,其中尤以顺治十年(1653)颁布的辽东招民开垦令最为著名。不过,这种鼓励移民的政策只是权宜之计。一方面,至康熙七年(1688),清廷即废除辽东招民开垦令;另一方面,在招徕汉人同时,清廷在东北同步推行了“封禁”和“旗民不交产”的政策。
对于东北地区封禁政策的开端,学界尚存争议,但本文认为起始于顺治年间柳条边的兴建[3]。清代柳条边有“老边”与“新边”之分。老边始建于顺治八年,基本上是沿着明朝辽东边墙的走向而修筑,分为东西两段。东段是为防止朝鲜人入境采参、开垦而筑,自鸭绿江口至开原;西段主要是为了划定蒙古诸部游牧区的界限而筑,自开原至山海关。“新边”修筑于康熙九年至二十年,主要为划定蒙古科尔沁诸部游牧区的界限,东自吉林北界,西抵开原威远堡。柳条边的各个边门设有守边官和兵丁,负有守卫、稽查、巡查和修浚之责[4](P27-57)。
这条“人”字形柳条边,基本上是沿着东北地区原有的三个经济、文化区的分界处修筑。这样一来,汉满等族的农耕区、蒙古族的游牧区、东北其他少数民族的狩猎采集区就被明确地区分开来。柳条边的修筑,明显寓有将汉族移民限制在原有辽沈农耕区的意图。
及至康熙七年废除辽东招民开垦令,不但标志着鼓励性移民政策结束,同时意味着封禁政策进一步趋严,开始禁止汉民流入盛京及东北地区垦荒种地,“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皆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5](卷134)。不过这一政策在实际中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
除封禁政策外,另一个影响移民的重要因素是地权关系和土地政策。同关内相比,清初东北的地权关系特殊而又复杂。从所有和管辖区分,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皇产官地,为皇室所有,分辖于内务府,盛京户部、礼部、工部;二是旗地,为八旗成员所有,由旗署管辖;三是民地,为汉人所有,由民官管辖;四是蒙地,蒙古八旗或蒙部所有,由各盟管辖。
这四类土地由民法物权的角度看,又可分为三项:私有地、公有地和国有地。私有地包括民地(红册民地、民人各项余地和民佃旗地),一般旗地(旗红册地)。公有地分为寺庙地、学田、义地、善堂等项。国有地包括各类皇产官地。
总的来说,清代中前期,东北的地权少量为私有,多为官有和国有土地。私有部分又以旗地为主,如顺治十八年旗地为2 652 582亩,民地60 693亩;康熙三十二年旗地为7 271 569亩,民地311 750亩[6](P374)。
顺治七年,清廷颁发“旗民不交产”例,严格禁止汉人购买旗人土地。虽然这一政策并不限于东北地区,也同样适用于关内,但由于东北特殊的地权关系,这一政策对东北的意义显然要大于全国。自招垦令废除后,从理论上讲,汉人已不能再获得新的合法土地所有权,因此也就很难在东三省落户生根。
所以,在顺治、康熙、雍正三代,关内人民移居东北地区的步伐虽然始终未停,但进展缓慢。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顺治十八年,东北地区汉族人丁数为5557,康熙二十二年为26 227,雍正十三年(1734)为45 089[1]。可以看出,除去人口的自然增长,实际增加非常有限。而且这些人口主要集中于辽沈地区,只有极少部分进入吉林、黑龙江地区。
二
清初,关内人民移居东北并不踊跃,内部固然是受限于封禁和土地政策,但从整体来看,也和关内经过长期战乱、人地矛盾趋于和缓有关。不过到了清中后期,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顺治十八年全国在册人口不过1920万,康熙中后期,则达到7000万左右,乾隆初年人口突破1亿,乾隆末年已接近3亿,嘉庆十七年(1812)时为36 000万,道光二十年(1840)已达41 000万。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人地矛盾日趋尖锐。在生存的压力下,东北地区地广人稀,沃野千里,自然成为邻省人民比较理想的谋生之地。不待凶年,迁来之民已源源不断,若遇灾歉,更是扶老携幼,不绝于途。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康熙降谕山东巡抚张鹏,“今见山东人民逃亡……至边外各处为非者甚多”[7](卷24)。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上谕又云:山东人民往关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2](卷250)。
面对这种冲击,清廷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封禁政策,从乾隆五年(1740)到十四年,相继在三省及东三盟蒙古地区实施全面封禁:一,除前来贸易、佣工外,严禁汉族内地流民进入东北地区;二,已迁居东北且有产业的汉族流民准其入籍,编设保甲,严加管理,其余限期回其原籍;三,严禁汉人在东北开荒,一切可耕荒地均保留给予旗人;四,严禁汉人在东北私自从事挖参、捕貂、采珠及有关产品的买卖活动。
但是这些政策在实际推行中却往往成效不彰。对此,学界已有较充分的研究,一般将其原因归纳为三点:移民洪流不可遏阻、政府政策的摇摆不定、东北地区满蒙社会成员的抵制以及地方官员的纵容[8][9][10](P1567-1572)。除此之外,如何安置华北地区的饥民、流民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以往的讨论中尚未引起注意。
关内各省人口激增的后果,不但人地矛盾日趋紧张、人民生存压力增大,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政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越来越脆弱[11](P259)。康熙皇帝就曾注意到,即使丰年,“穷人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少壮者流离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7](卷21)。1804年,阮元也曾总结说:“夫水旱之事,不能必无。国家休养之恩,百数十年矣。昔之八口食十亩者,今数十口食之矣;今之六分灾,敌昔之十分灾也。”[12](卷42)
而恰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华北地区自然灾害频仍。仅以直隶地区为例,在1743—1744年、1759年、1760—1761年、1792年、1801—1802年、1812—1813年,发生六次特大旱灾和洪灾,小型的自然灾害更是层出不穷。在频繁的自然灾害影响下,大批饥民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一严重问题。对统治者来说,允许其出关谋生虽事出无奈,却也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
所以,即使在封禁最为严格的乾隆时期,面对大批灾民出关时,也不得不经常做一变通。如乾隆八年,直隶的天津、河间等地受灾,饥饿的流民纷纷外出寻求生路,乾隆密谕关口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阻拦,即时放出”[13](卷195,乾隆八年六月丁丑)。翌年,河南、山东等地灾民涌来,乾隆再谕各口:“查明实系穷民,即行放出,不必过于盘诘,亦不必声张,务须善为办理,以仰副朕轸念灾黎多方体恤之至意。”[13](卷208,乾隆九年正月癸卯)乾隆五十七年,河南、直隶等地“夏旱秋蝗”,灾民出山海关者络绎不绝,乾隆为此特意下令:“山海关外盛京等处、虽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藉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至滋生事端”,不必“查验禁止。”[13](1407,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癸丑)
因此,封禁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严格,往往是禁中有弛,尤其在道光之后,基本上有名无实。从人口数据来看,根据《盛经通志》记载,乾隆六年,盛京地区仅有人口359 622人,乾隆十六年,增加到792 093人,嘉庆二十五年时已增为1 757 248人,道光二十年为2 158 600人。不过,鉴于人口统计制度并不完善和大量流民隐匿不报 (如前文所述康熙对山东人民流入东北的人数估计即与官方统计相去甚远),这些数字显然并不准确,但大体上也可反映移民不断增加的趋势。
源源不断的关内移民,为东北地区提供了丰富人力资源,加快了该地区的土地开发进程,也逐步改变了这一地区特有的地权关系。乾隆四十五年东北地区旗地为21 075 794亩,民地为4 732 193亩;嘉庆十七年旗地为23 688 350亩,民地为5 201 341亩[6](P374)。同上文所列顺治、康熙年间相比可以发现,无论旗地还是民地,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同顺治年间相比,旗地增长近9倍,民地增长86倍多。民地的增加部分,除了一小部分是原属旗地的退圈地外,基本来自汉人垦荒后的升科起赋。
若单从数据来看,东三省的旗地数量对民地始终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受限于“旗民不交产”的禁令,汉人不但购买旗人的土地受到严格限制,种植官地和开垦官荒亦不可能获得实质上的所有权,故民地在数量上要远逊旗地。但是,另一方面,汉人可以通过永佃和典、押、租、借的不同方式,分别从使用权上控制一般官地和一般旗地,从而达到所有权的另一转移。一般说来,汉族移民获得土地使用权要分三个步骤:“始而为庸工”,“继则渐向旗人佃种田亩”,最后,“迨佃种既多,旗人咸图安逸,不知力作”,最终获得对土地的支配权[14](卷102,道光六年八月乙卯)。清末民初曾长期任职于东北的林传甲亦就此总结称:“汉人初至时,为满人佃人,披荆斩棘,茹苦食辛。满人不解农事,渐至变卖土地,归于佃户,满人固有荒地,亦多私卖、私典与汉人者。蒙古王公荒地,亦多私招汉人开垦,其杰出者为揽头,包揽大段,招户分垦。无业人民依以为食,名曰傍亲,或曰傍青。”[15](P380)
持续的移民和地权关系的变动也给东北社会造成深刻变化。一方面,在原来以农耕为主的辽沈地区,人户和土地开辟与日俱增。嘉庆五年朝鲜使臣自朝赴北京,一路所见:“自栅内(凤凰城边门内)至辽东,虽僻峡深谷,在在人家,处处山田,又见其人多地狭。而自辽阳至京郊,广野数千里之间,烟火相接,鸡犬相闻,或百步一村,或数里一庄,多则五六十户,少亦一二十户。若其大处闾阎市肆,扑地交错,连亘四五里,人口之繁殖,未有盛于今时云。”这一情形,实际已与关内基本趋同,也标志这一地区移民社会已转变成接近关内的农业社会。
另一方面,农耕社会随着移民的足迹突破辽河平原,进入吉林地区。清初,吉林地区汉人为数不多,乾隆时以“吉林原不与汉地相连,不便令民居住”[13](卷1023,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丁巳),严令封禁。但这亦无法阻挡移民的脚步,到嘉庆十七年已经达到307 781人,比乾隆中叶的56 673人增加了5倍多,其中尤以伯都讷、吉林乌拉、长春三地为多。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十四年,伯都讷先后七次清查流民,每次都有新流民、新垦地出现。该地原有民户1655户,民地100 045亩,七次分别查出新户和新垦地6107户,197 483亩,分别增加了4倍和2倍[10](P1573)。吉林乌拉及其周围的永吉州在乾隆三十三年时有民人8961丁,民地428 513亩,嘉庆十五年分别增加到25 149丁、1 037 273亩[16](P27-28)。长春一地原为郭尔罗斯蒙古王公的牧区,嘉庆五年,因流民麇集,设置长春厅管理。设治后,地方政府即陆续对境内人口进行清查。根据嘉庆十六年政府人口清查的结果,该地境内共有居民11781户、61 755口,开垦土地39573亩[17]。
当然,尽管有上述各方面的发展,但总体上看,封禁政策和特殊的地权关系仍是严重的窒碍。各方面的突破,不过是生长在制度和政策的罅隙中。所以直到19世纪中期,在主要的经济指标方面,东北地区与关内各省仍存在不小的差距。美国学者施坚雅(G.W.Skinner)在其关于传统中国区域体系的理论中,把中国分为九大相对独立的区域模式,东北地区是其中之一。但在他看来,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这一地区的发展要远远落后于其他八个区域[18](P57)。
三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日益加剧,东北地区首当其冲,不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大片膏腴之地被俄国割占,而且日渐沦为帝国主义争相竞逐的禁脔。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东北的主权名义上虽在中国,但实际上形成日俄以长春为界分据南北的局面。其情形正如1909年调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所言,“其切肤之痛,较之各行省有特别之危险”[19](P1249)。作为应对,解除封禁并移民实边逐渐成为中央和地方的共识,并落实为具体的政策。
概而言之,道、咸、同三朝,在业已缓弛的封禁政策基础上,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先后奏请开放山场河谷,任由移民开垦。至光绪初年,政府开始主动招民开垦,标志着封禁政策正式被废除。不过在庚子以前,大部分放垦地集中在吉林南部和奉天省北部即东蒙古草原一带,多是围场、山场、河谷地。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和通车,移民足迹开始遍及松花江以北地区,三省土地呈全面开放之势。造成东北地区无论在人口数量、土地开垦,还是在地权关系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在人口上,三省均有大幅度的增长。根据相关统计,奉天在道光二十年人口为2158600人,宣统三年(1911)为11 018 517人[20](第三章“人口”);吉林同治元年(1862)为33万人,宣统三年为5670838人[21];黑龙江在嘉庆二十五年人口为167626人[22](P347),宣统三年为1 858 793人[20](第三章“人口”)。三省人口增加迅速,显然是得益于关内人民大批移居的结果。
4.1.1 游泳自救能力是游泳者在水中出现危机状况时运用自身所掌握的技能自救脱险的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水上救助能力是救助者对水中遇险者在岸上实施救助的知识和技能。
三省耕地增加也幅度惊人。奉天省耕地面积在咸丰元年(1857)为11 524 200亩,宣统二年增至68 226 611亩;吉林省耕地面积咸丰元年只有1 439 600亩,光绪三十四年增至49 324 179亩;黑龙江省原来耕地面积极少,但光绪三十四年已拥有耕地22103970亩。清末东三省耕地已超过亿亩,形成一个新兴农耕区域[23](P499)。
东北地区地权关系在清末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大量原封禁政策下归国有或公有的土地私有化。首先,在新增的耕地中,绝大部分由官荒放垦而来。在放垦之时分为两类:一类由垦民交纳或者不交纳地价,然后由厅或州县征赋,所有权归垦民所私有;一类是交纳或不交纳押租,然后每年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量的大租或小租,即可永远承种。这种土地名义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个人只有使用权,但实际上与个人控制无异。其次,大量皇产官地次第丈放。凡购买者,由政府发给印照,并规定“永远为业,不准扛欠课赋,如欲将地典卖他人,亟应遵照契税章程,随时赴地方衙门报明”[24](P115)。也就是说土地所有权已转归私人,买卖自便。再次,东北地区放垦的蒙地在晚清近百年间共计6 438 354垧,在光绪二十八年前放出的尚具有双重性,既要收押租地租,又归蒙古王公所有,但垦民拥有永佃权,亦即拥有部分所有权;光绪二十八年后放出的则基本属于私有财产[24](P135)。
地权关系的另一根本性变动是 “旗民不交产”的废除。清中期后,全国各处旗地私有化趋势已无法遏止。咸丰二年,政府不得不放弃买卖旗地的限制,但东北地区除外,不过已很难维持。光绪十八年吉林将军长顺指出:“近数十年旗民私自交产,大半归民垦种,而佃户亦辗转兑卖,几至无可根查,故往往考诸司册,户名依然,而产业则亦更数姓矣。”光绪三十二年,奉天将军赵尔巽奏称:“然历年既久,势难禁其交易。有时退兑佃缺,俨同业主,惟变其名曰开刨工本,实则与买卖无异。”[25](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故奏请旗地自由买卖,朝廷议准。至此,清初以来东北地区特殊的地权关系完全被打破,土地流通基本和关内一样依靠市场来进行。
地权关系、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同时发生根本性变化,其间显然有内在的密切联系。首先是地权关系的变动,对于关内山东、直隶等地人民来说,在地广人稀的东北较之自己的家乡更易获得土地,所以前往者络绎不绝,始则春去冬归,继而招亲引朋同往,最后携家带口前往定居。而源源不断移民的到来,又为新垦区提供劳动力,保证了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换言之,移民绝大部分是为新垦区的土地所吸引而来。
以往因史料所限,对于清末东北移民的具体情况无法做更深入的探讨,笔者在查阅史料时发现,清末东北地方政府曾对此做过一次全面调查。宣统三年春,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通饬三省各府、厅、州、县,要求调查各属境内的山东、直隶等关内人民移居及往来情况。①从档案中所能见到各处回复,可见表1。
从表1中可发现移民在三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一是奉天除新开发的洮南、凤凰两处外,大部分地区已经过长期开发,故移民为数不多。二是吉林的长春、宾州、德惠、双阳等处因开发较早,移民数量较少;新城、五常、延吉、方正等处已经过一定程度开发,移民一般皆有产业,故携家带口,长期定居;宁安、额穆、桦川、富锦等处新近开发,人民以移民为主,且流动频繁。三是黑龙江普遍开发较晚,地广人稀,基本依赖移民的开发。由此可见,清末关内新移民基本流入新开发地区,土地的吸引应该是关键的因素。
为新开垦地区的土地所吸引,奉、吉两省开发较早地区之人民亦趋之若鹜。尤其是黑龙江全面放荒招垦后,“奉吉之民至者渐众,近则每年移入之民不下十余万”[26](P2071)。清末黑龙江肇州地方官的一份报告亦称:“厅属垦户籍隶奉吉两省者十居八九,向系秋去春来,时值春耕,来往大车络绎不绝。”[27]
经过数十年的开发,清末东北人口与耕地均获大幅增加,成为中国又一重要农业区。在此基础上,工商业日渐繁兴、城镇普遍兴起、市场体系逐步发育完善,不但与关内的差距迅速缩小,而且后来居上,在全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居于领先地位。1911年时即有论者根据海关报告评论称,“满洲经济之兴盛超乎各省之上”[28]。
总结清代东北地区地权结构及土地政策与移民之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清代中前期,东北地区特殊的地权关系和土地政策是影响关内移民的严重窒碍,但移民的源源不断涌入也日渐对其进行侵蚀,造成其在清末的根本瓦解;而地权关系和土地政策的根本变动,又反过来成为清末东北地区快速开发与发展的重要。可以说,东北地区特殊的地权关系及其变动,是影响清代东三省移民和移民社会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清代东北地区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

表1 宣统三年春东三省关内人民移居及往来情况调查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和土地本是两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两者的有效结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否,也端赖两者有效结合的程度。清代中前期,东北地区特殊的地权关系和土地政策本是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制度安排,严重影响了人口和土地的有效结合,给该区域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然而,在不断变动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任何无法配合社会经济现实的制度及其有关事物,都将不免被淘汰”[1]。清末东三省地权关系的根本性变动,正是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近代东北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
注释:
①1910年秋,满洲里发生肺鼠疫,数月之内,传染至东三省大部分地区及关内山东、直隶等省。清政府不仅在东北各地实行隔断交通,严行检疫,还在山海关、烟台等处设卡留验。1911年春,拟议全面禁止山东、直隶人民出关,以防传染。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为此电饬三省各府、厅、州、县,要求查明:“究竟是否向有直、东两省小工在境内营业,其人数几何,若绝对禁止于各属生计上有无窒碍。” (《通饬各府厅州县》(正月二十三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26-13。)
[1]赵中孚.清代东三省的地权关系与封禁政策[A].近世东三省研究论集[C].台北:成文出版社,1999.
[2]清圣祖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3]贾文华.清代封禁东北政策研究综述[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4]杨树森.清代柳条边[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
[5]大清会典事例[Z].沈阳:辽宁省社会科学院,1990.
[6]杨余练,等.清代东北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7]清圣祖圣训[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刁书仁.论乾隆朝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11).
[9]任玉雪,李中清,康文林.地方政府的行政实践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冲突及重塑:以晚清双城堡民界的出现为例[A].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1年第82本第3分册.
[10]佟冬.中国东北史(第四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11]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M].徐建青,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2]皇朝经世文编[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13]清高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清宣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林传甲.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16]吉林志书[A].李澍田.吉林史志[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17]代理长春知府章绍洙为清查人口详送事[Z].长春:吉林省档案馆,档号:J023-04-0047.
[18]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M].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19]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Z].北京:中华书局,1959.
[20]中国经济年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21]吉林民政司呈吉林全省户口总数[Z].长春:吉林省档案馆,档号:J023-04-0054.
[22]吴雪娟.满文文献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23]李澍田.中国东北通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24]乌廷玉,等.东北土地关系史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25]光绪朝东华录[Z].北京:中华书局,1958.
[26]何煌.黑龙江垦殖说略[M].黑水丛书本.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7]肇州厅理事抚民同知崇缓呈报防疫事[Z].哈尔滨:黑龙江省档案馆,档号:21-2-47.
[28]满洲经济之效果[J].远东报,1911-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