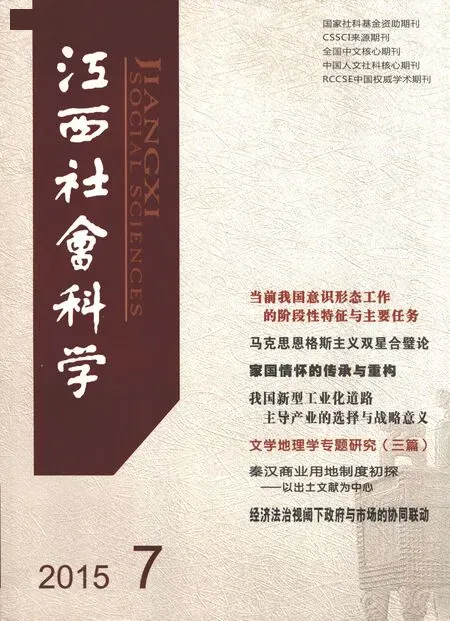反垄断规制中不正当价格的认定方法
■张志伟
我国《反垄断法》明确列举了三类价格滥用行为:不公平定价(包括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掠夺性定价和价格歧视。其中,不公平定价是剥削性滥用行为,其本质是一种利用垄断地位攫取高额利润,反垄断法规制的目的是要将价格回复到“合理”水平;掠夺性定价和价格歧视是排他性滥用行为,其本质是通过排挤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的方式维护自身垄断地位,反垄断法规的目的是维护自由的竞争秩序。但是,不论属于何种滥用,在认定这三类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时,《反垄断法》都要求必须考虑其是否存在“正当理由”。问题是,在如何认定价格本身是否“正当”的问题上,目前还未制定出有效标准,不正当价格的认定问题已然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价格滥用行为规制的难题
(一)不公平定价的规制难题
对于不公平定价而言,何谓“不公平”的价格本身难以衡量。它无法用经济学模型予以解答,只能借助于主观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对不公平价格的规制就很可能演变为 “规制权本身的滥用”。这也是有些国家(比如美国)不将其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原因。美国最高法院曾在Verizon案中指出:“仅仅拥有垄断力量,以及相伴随的垄断高价,不仅不是违法的,而且是自由市场体制的重要元素。”①他们认为不公平定价行为(包括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的存在自然会吸引潜在竞争者进入相关市场与这些企业分享垄断利润,市场竞争本身就能够将这种垄断行为带来的危害抚平,无须反垄断法的额外介入。
在特定新兴行业,价格是否“公平”的认定就更加困难。比如,互联网企业往往是双边市场下的平台企业,它对平台一边用户收取高价,对平台另一边用户收取低价 (甚至是零价格或负价格)。这种行为是创造需求方规模经济从而创造市场的一种必要行为,我们很难将其认定为不公平定价行为。
(二)掠夺性定价的规制难题
在经济学上,对掠夺性定价予以规制的理由是经济学家阿瑞达和特纳1975年提出的 “阿瑞达——特纳规则”:企业低于边际成本销售商品肯定会亏损,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亏本销售,说明企业具有排挤竞争对手的意图,因此,如果商品的价格低于短期边际成本,这个价格就可以视为认定掠夺性定价的重要因素。[1](P254)还有学者进一步主张,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哪怕对产品的定价高于平均可变成本,但是只要定价低于产品的平均成本 (包括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不变成本),仍然可以构成掠夺性定价。[2](P284)[3](P869)这意味着,任何低于企业平均成本定价的行为都可能构成掠夺性定价行为。尽管如此,在实践中要证明构成掠夺性定价仍然十分困难。典型的掠夺性定价包含两个阶段:一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竞争者排挤出相关市场;二是排挤成功后实施垄断价格。因此,掠夺性定价包含一个先低后高的定价过程。如果仅有第一个阶段而没有第二个阶段,低价信号既可能是掠夺性定价,也可能是竞争性价格。此时,不对这种定价行为予以规制可能效果更优。
(三)价格歧视的规制难题
对于价格歧视而言,仅仅是“价格差异”不构成价格歧视,因为价格差异可能存在诸多合理之处,反垄断法只对那些“没有正当理由”的差别定价行为予以规制。在经济现实中,价格差异普遍存在且具有普遍的效率合理性。比如,卖方对于购买大量产品的买方提供价格折扣而对购买少量产品的买方不提供价格折扣,这种数量折扣显然具有交易上的合理性。因此,价格歧视也许只是企业应对市场环境和市场竞争的本能反应,与其说它是一种反竞争行为,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竞争行为。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价格歧视不是反托拉斯法的一个合适目标。在任何情况下,这一现象都超出了法律的有效规制范围”[4](P382)。尽管如此,大多数国家仍然将其作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典型手段之一予以了规制,这是因为法律除了关注效率以外,还关注公平等其他价值。
二、传统方法的不足及新方法的展望
(一)联合商标案确立的两大标准
价格本身是否“正当”或“公平”,是判断价格滥用行为是否存在“正当理由”的主要标准。联合商标公司案②是同时被指控实施了不公平定价、掠夺性定价和价格歧视的典型案件,对该案的分析有助于总结价格是否“正当”的传统认定方法存在哪些经验和不足。
欧洲法院在联合商标公司案中,总结了认定价格是否“正当”的两个标准:一是价格与成本之差“过高”;二是价格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或与竞争产品相比是不公平的。[5](P250-252)第一个标准可以称之为“成本——价格比较分析法”,这是将经营者的价格与其成本进行比较,允许经营者在企业成本之上合理定价,即公平价格等于成本加合理利润;第二个标准可以称之为“相似产品比较分析法”,这是将争议产品的价格与其他相似产品的价格进行比较,以其他类似产品的价格来推断争议产品的价格是否公平。
(二)“成本——价格比较分析法”的不足
针对“成本——价格比较分析法”,欧洲法院在联合商标公司案中认为,经济学家已经能够通过经济分析确定一个价格是否是正当的。[5](P253)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现代企业的成本往往难以确定,比如互联网企业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往往同时供应多种产品,如何判断单个产品的成本存在难题;另一方面,什么样的利润率是合理的也存在争议,不同行业的合理利润明显是不同的,即便是同一行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具有不同的利润。对于互联网产品而言,其边际成本趋于零,长期平均成本也趋于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哪怕只收取一个很低的价格,也可能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利润率。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成本——价格比较分析法”在运用于特定行业时可能“失灵”。
(三)“相似产品比较分析法”的不足
“相似产品比较分析法”看似比“成本-价格比较分析法”更优,但是目前并没有发展出更有效的分析手段。欧洲法院曾经指出:“一个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如果服务的价格明显高于这种服务在其他成员国的价格,并且这种价格水平的比较结果不是偶然的,这种价格差异应被视为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5](P256)这是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产品价格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营者的同类产品价格进行比较。但是,这种比较必须考虑不同情境下的价格的可比性问题,即在不同地域或不同时间段,必须考虑产品的价格可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如何剔除这些影响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比较结果的关键问题。
(四)不正当价格认定新方法的展望
很多学者主张学习美国的方式,对不公平价格实行类似于“本身合法”的做法。但是,在欧盟,许多学者和官员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垄断高价对于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如果不介入,将会有损消费者利益。[6](P91-125)从我国的《反垄断法》来看,“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等表述强调了“公平”和“正当”是反垄断法的价值考虑因素。由于针对不公平价格行为的救济往往是价格规制,而竞争执法机关是否掌握了足够的技能和资源进行价格规制是值得怀疑的,[7](P575-580)这就很有可能导致“错杀”的结果。[8](P97-122)因此,构建有效的认定标准,减低“错杀”的风险,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个有效的不正当价格的认定标准至少应该满足四个条件:(1)定义明晰;(2)具有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3)操作简单;(4)增进福利。前三个条件与滥用行为的认定有关,最后一个条件与救济有关,即恰当的救济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价格行为构成了滥用,而禁止滥用行为是为了消除对社会的不利影响。
联合商标公司案确立的两大标准无法满足这四个条件。首先,当前标准没有指出什么是“公平”、“正当”,因此定义不明晰。其次,在当前标准下,企业作出价格决定之前无法预见到自己的价格决策是否可能违法,因此不具有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再次,在当前标准下,执法机构很难获取成本信息,从会计数据出发计算企业的经济利润也存在很大困难;而且,即便所有相关信息都可以获得,判断一个价格是否与产品的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合理比例也是非常困难的。最后,当前标准即便存在阻却反竞争行为的效应,也可能效果有限,相反,错杀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当前标准很难增进社会福利。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最佳的做法是继续沿用联合商标公司案确定的两大标准,并对其加以改进发展新的认定方法。
三、不正当价格认定的新方法:“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
根据认定不正当价格的四大标准,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对价格垄断行为认定中何谓“正当”予以考察。“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认为,如果一个企业的定价是通过损害其顾客权利的方式来获得收益,这个定价是不公平的;如果市场条件改变了,企业比“参考交易”施加更差的交易条件维持自身利益,也是不公平的。
(一)参考交易的确定
“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的第一步是确定“参考交易”。基本上存在四种可能:(1)企业过去在相关市场实施的价格;(2)企业在可比较的独立市场的当前价格;(3)相关市场的类似产品的当前价格;(4)独立市场的类似产品的当前价格。前两者是企业自己的价格,后两者是竞争对手的价格。
相比之下,前两者更能提供有效信息。理由有三。一是企业和反垄断执法机关可以直观地比较价格的变化或差异,从而判断竞争的变化。二是反垄断执法机关能够对价格作更加充分的比较。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价格比较不能进行,那就是产品是崭新的(不存在过去的价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产生滥用行为,因为新产品意味着投资和创新,不仅不会有损竞争,反而有利于促进竞争。三是在竞争者不存在的情况下,后两者无法拿竞争者的价格做参照。即便存在竞争者,当前企业是否存在滥用行为仍然有待商榷,因为不确定企业当前的价格行为是否会长期存在。所以,将非相关市场的类似产品的价格作为参考价格,对于价格行为是否 “公平”的认定只能发挥极其有限的作用。
(二)实施程序
在确定参考交易价格之后,第二步是确定方法实施的程序 (参见图1)。其步骤如下:(1)当前的交易价格是否与参考交易价格相近?如果是,价格是公平的;如果不是,进入下一个分析步骤。(2)在当前的价格下,企业获得的利润是否明显比参考交易更大?如果不是,价格是公平的;如果是,价格是不公平的,并进入下个分析步骤。(3)导致更高利润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因为需求扩大或供给缩小的原因导致了更高的利润,反垄断法不应该介入规制,属于正常的市场变化,价格是公平的;如果是因为缺乏竞争导致了更高的利润,价格就是不公平的,反垄断法应予以规制。

图1 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程序结构图
(三)收益和损失的衡量
在衡量收益和损失的时候,一般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收益用利润(价格减去成本)来计算,消费者的收益用消费者剩余(效用减去价格)来衡量。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强调,无论企业的成本、成交的价格如何变化,最终的效率评价只取决于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与否。由此可以产生四种情况:(1)如果企业获得收益是以损害顾客收益的方式实现的,价格是不公平的;(2)如果企业在获得收益的同时顾客也获得收益,价格是公平的;(3)如果新的定价使得企业根本没有获得收益,但是顾客获得了收益,价格是公平的;(4)如果企业的定价使得需求双方都没有获得收益,价格是不公平的。
(四)参考交易法的优点
相比于联合商标公司案提供的标准,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更能满足一个有效标准的四个条件:定义明晰、具有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操作简单和增进福利。
第一,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定义清晰,它建立在社会中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公平”价值的基础之上,可以解释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相对于可比价格而言当前价格是不公平的。
第二,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具有更强的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因为企业都十分清楚自己过去的定价,可以将其作为最佳参照。企业会认识到,如果他们现在的定价大大高于或低于过去定价,将有可能被认定为构成滥用。
第三,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操作简单,几乎所有案件都可以进行比较,而且不需要太复杂的分析。该标准的唯一缺陷是没有考虑非价格因素(比如产品质量)。因此,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产品质量发生了改变,需要在价格和非价格因素之间进行微妙的权衡,这会增加一定的复杂性。此外,更大的困难在于:如果企业同时经营多种产品或在多个市场运营,还涉及企业的成本是如何在不同产品或市场之间分配的,然而,这些困难相比于其他参照物来说并不显著。
第四,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能够增进社会福利。该标准能够增进企业胜诉的可能性,因此除了例外情况,该标准在司法中的适用将会增进社会福利。当然如果适用不当,该标准也可能导致错杀风险。为了避免错杀,执法机构应该在适用该标准时施加较高的举证责任:只有在企业获得了实质性的利益或顾客权利被严重侵害的情况下,价格才能够被认为是不公平的。
四、我国不正当价格认定的实现途径
(一)完善相关立法
实际上,在《反垄断法》颁布之前,我国就已经存在针对价格垄断的禁止性规定。比如《价格法》第14条第7项规定:经营者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牟取暴利。《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凭借市场支配地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牟取暴利。但是,这些规定都没有对何为不正当价格作出界定。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发布的 《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规定了商品的价格和服务的收费标准(统称价格)应当符合下列要求: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水平、差价率或者利润率不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或平均利润率的合理幅度。该规定提供了判断相似产品之间价格是否合理的“四个同一”和“三个平均”标准。但是,该标准也仅仅提供了分析正当价格的几个角度,即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或平均利润率,并没有提供明确的认定方法。
笔者建议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通过修订《反垄断法》或制定实施细则或指南的方式,将“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纳入我国反垄断规则中,即将企业过去在相关市场实施的价格(时间比较)和在可比较的独立市场的当前价格(空间比较)作为价格正当与否的判断标准纳入到相关立法或指南中,作为衡量不正当价格的标准。比如可以规定:“在认定价格是否正当时,可以将经营者当前在相关市场实施的价格与参考价格作比较。参考价格主要是指经营者过去在相关市场实施的价格和当前在可比较的独立市场实施的相关价格。如果当前价格与参考价格差异较大,可以推定价格是不正当的。”当然,这种推定仍然是可以推翻的,前提是经营者能够证明导致价格差异的原因是其他原因 (比如需求扩大或供给缩小等市场原因)造成的。
(二)细化行政执法标准
在电信和联通反垄断调查一案③中,执法部门认定其是否存在价格歧视的主要方法是 “成本——价格分析方法”,即观察电信、联通的价格行为是否是其成本的合理反映。这就引发了到底采纳何种成本作为成本标准的争议。根据国外先例,边际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平均可避免成本、长期平均增量成本等都可以作为成本标准。如果考虑机会成本,电信、联通的行为就更具有合理性。但是,美国和欧盟都不是基于“机会成本”的概念来分析价格歧视,而是基于现实交易中实际发生的成本,特别是那些能够为客观的事实和数据来证明的成本。[9]可见,价格歧视本身的效率合理性以及《反垄断法》中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和“正当理由”的规定的不确定性,使得依据价格歧视条款来认定电信、联通的行为引发了诸多争议。
在立法或指南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建议执法部门可以尝试使用 “参考价格比较分析法”,在积累经验和观察效果的基础上,逐步将其纳入到立法或指南中。实际上,如果电信联通案中能够使用“参考价格比较分析法”,认定的结果就会更加明确。比如,通过比较电信、联通过去在相关市场实施的价格和在可比较的独立市场的当前价格,其违法性就比较明显了。
(三)修改司法解释
华为诉IDC案是目前中国运用“参考比较交易法”的有益尝试。2011年,华为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两起诉讼:第一,以IDC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由,请求法院判令其停止垄断行为,并索赔人民币2000万元;第二,请求法院按照公平原则判定IDC的专利许可费率。④后者直接涉及不正当价格的认定。201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华为诉IDC两案的一审判决,判定美国IDC公司构成垄断,赔偿华为公司2000万元人民币,并确认将2%的许可费率降低为0.019%。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依据主要有:第一,IDC对华为的4次报价均明显高于对其他公司的许可,甚至高达百倍;第二,针对全球手机销量远不如苹果、三星等的华为公司索要高价明显缺乏正当性、合理性;第三,为迫使华为免费许可其名下所有专利给IDC使用,反而提起“337调查”和诉讼,强迫给予免费交叉许可。这明显违反了IDC自己向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承诺的FRAND原则(公平、合理、无歧视)。因此法院确认,IDC实施了不公平的高价销售行为,构成垄断行为。
以上分析实际上已经隐含运用 “参考比较交易法”,即将IDC对华为收取的许可费与其在其他独立市场收取的价格作比较,得出了价格不正当的结论。该案为在司法实践中引入参考交易比较法提供了指导。但是,仅仅在个案中运用并未形成普遍做法。而且,该案仅仅使用了空间比较的方法,并没有机会采用时间比较的做法。因此,建议通过修改司法解释的方式,使得“参考交易比较分析法”成为司法的普遍做法。
注释:
①通过此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再次重申对待反托拉斯问题必须审慎,管制机构的不恰当管制行为会破坏竞争秩序,保护竞争秩序是反托拉斯法的终极目的。See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Petitioner V.Law Offices of Curtis V.Trinko,LLP(02-682),540 U.S.398(2004).
②在该案中,联合商标公司在丹麦、德国的香蕉定价高出其在爱尔兰的定价,且其在爱尔兰的香蕉价格是亏损价格。欧洲法院在这个案件中确立了判断 “不公平价格”的两大经典标准。See United Brands Company and U-nited Brands Continental BV v.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hiquita Bananas,Case 27/76.C.M.L.R.429.E.C.R.207,1978.
③在2011年发改委针对电信和联通发起的反垄断调查中,电信、联通被认定为在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领域对其他经营者实施了价格歧视。但是这种价格歧视是否存在“正当理由”,理论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考虑到竞争的机会成本,上述行为具有合理性;还有学者认为,上述行为更宜被认定为“价格挤压”而非价格歧视。虽然最终该案由于执法部门接受了电信、联通的“整改”承诺而没有在“正当理由”的认定方面得出结论,但是已经反映出价格行为正当与否的认定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④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深中法知民初字第857号。
⑤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6号。
[1](美)马歇尔·C.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M].孙南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Williamson.Predatory Pricing,A Strategy and Welfare Analysis,87 Yale L.J.1977.
[3]Scherer,Predatory Pricing and the Sherman Act:A Comment,87 Harv.L.Rev.1976.
[4]Robert H.Bork,The Antitrust Paradox: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the Free Press,1993.
[5]United Brands Company and United Brands Continental BV v.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hiquita Bananas,Case 27/76.C.M.L.R.429.E.C.R.207,1978.
[6]Motta,Massimo&Alexandre de Streel,Excessive Pricing and Price Squeeze under EU Law,in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Annual 2003:What Is an Abuseof a Dominant Position?,ed.by Claus-Dieter Ehlermann and Isabela Atanasiu,Hart Publishing,2006.
[7]Blumenthal,William,Discussant Comments on Exploitative Abuses under Article 82 EC.,in European Competition Annual 2007,A Reformed Approach to Article 82 EC,ed.by Claus-Dieter Ehlermann and Mel Marquis,Hart Publishing,2008.
[8]Evans,David S.&A.Jorge Padilla,Excessive Prices:Using Economics to Define Administrable Legal Rules,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2005.
[9]肖伟志.价格歧视的反垄断法规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