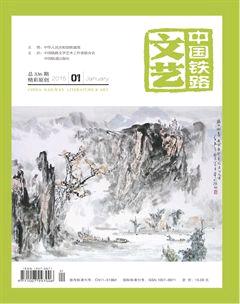流淌在铁道线上的故事
艾香氤氲
配电检修工方平最近很不爽。
工作繁忙不说,女朋友还催着买房,连师傅王路生也和他过不去,老是找他碴子,不是指出他螺栓没拧紧,就是批评他上班时间玩手机。
这个王老头,要不是看他年龄大,平日对自己不错,方平非要和他理论理论,但现在,哎,方平无奈地摇摇头,把自己撂在值班床上。
方平是豫西山区的孤儿,上小学前叫狗子。家乡山美水美,却总是穷。父亲早逝,母亲耐不住清苦,在狗子5岁时,终于撇下他,坐上汽车走了,说是去南方打工,却从此杳无音讯。很长一段时间,狗子看不得汽车,一看见就拿石头扔,惹得司机一顿好骂。
上学了,虽然教室破烂,桌椅老旧,但狗子很快乐,老师和朋友对他很好,他再不用整天抱着那条叫黑子的狗儿说话。在学校里,他有了自己的大名:方平。
中考了,方平成绩很好,用老师的话说是北大清华的苗子。但方平不敢想,从小学到初中,多亏郑州一名好心的艾辛叔叔资助,上高中再上大学,那得给人家添多少麻烦?填志愿时,方平没与老师和艾叔叔商量,就填报了郑州的一所铁路职专。不为别的,只想到艾叔叔的城市,见见艾叔叔,当面说声谢谢。
职专三年,方平试过各种办法,却始终没见到艾叔叔。艾叔叔只给他写信,写的信不少,除了嘘寒问暖,只有一个主题:见不见没关系,我也曾受人资助,等你有能力了,把这根接力棒传下去就是。听艾叔叔这样说,方平才不再坚持。他给艾叔叔寄去一个记录职专生活的日记本,以便让艾叔叔见证他的成长:白色的封面,一束艾蒿迎风飞扬。
毕业后,方平分到了郑州铁路单位。他工资不多,除去必须的生活费,剩下的钱资助了家乡的两个孤儿。不过,刚开始几年还行,等方平交了女朋友,才发现入不敷出。现在女孩儿现实得很,要物质,更要爱情。方平的女朋友只提出了一个问题——婚房,就击中了方平的软肋。
几天来,房子像大山压得方平喘不过气来:首付借借还不成问题,问题是月供,一旦贷款买房,势必资助不成孤儿了。他给女朋友打电话:“看能否缓两年买房,等孤儿们小学毕业再说。”但女朋友从牙缝里吐出两个字:“房子。”
方平正郁闷着,听见屋外的王师傅又在扯着嗓子喊:“方平,快,xx小区又停电了,带上家伙看看。”
方平忙放下手机,收拾工具,跟着王师傅几个人到了现场。
现场很乱,住户们围作一团,七嘴八舌指责着。王师傅一边说好话调解,一边迅速和工友们制定处理方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开始了。
作业前,王师傅不放心,特意问即将登高作业的方平:“你没事吧?这两天神魂颠倒的。”
方平笑笑:“没事,师傅,会有啥事呢?放心吧。”
方平登上了高高的电线杆,瓦蓝的天空上,电线像一架古筝,方平手指掠过,一片音乐的颤栗……王师傅的脸、女朋友有脸、孤儿的脸、母亲的脸……在音乐声中纠集在一起,忽然,方平感到前所未有的晕眩,在王师傅的惊叫声中,直直地栽了下去——由于精神恍惚,方平没有确认系好安全带,安全带只是虚虚地挂在线路上,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
等方平醒过来,才发现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腿上打着石膏,头上缠着绷带,王师傅和工友们一脸憔悴,忧虑地看着他。方平抬抬脚,没反应;动动头,疼得厉害。终于,他放弃了挣扎,任自己像一枚橡皮糖,粘在床上。
所幸方平只是腿部粉碎性骨折,别处尚无大碍,但腿能否复原就要看造化了。女朋友和工友陆续来看过他,但大多时候,他或是睡觉,或是躺在床上发呆,难得说一句话,病痛尚在其次,最难受的还是自责——一时失误可能让自己致残,还给单位添了不少麻烦,买房不用说了,连女朋友也可能告吹。有一阵,他时有想把腿上的石膏打碎的冲动。
一日,等方平醒来,发现病房里来了两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两个小男孩黝黑、青涩得要拧出水来,见方平醒来,眼里充满了惊喜。方平正诧异着,两个小男孩“嘘”的一声,拿出了两张奖状递给他,上面赫然写着:张小宁、李勇伟。
方平的眼一下子热了,这两个名字他再熟悉不过了——他们正是他几年来一直资助的家乡孤儿。
两个男孩齐声喊他:“艾叔叔,艾叔叔,你好点了吗?”方平点点头,激动地问他们怎么会到这里来。正在这时,王师傅推门进来,两个男孩马上“艾爷爷艾爷爷”地喊。方平一脸狐疑,王师傅一脸羞涩。
两个男孩是王师傅接来的,可王师傅怎么会找到他们呢?是无意中看见了自己的汇款地址,还是从别处看出了蛛丝马迹?
王师傅看出了方平的疑问,从包里拿出一个略显陈旧的白色塑料本递给方平。方平虽然斜躺在床上,血却一下子涌到头上:那正是他亲手寄给艾叔叔的日记本,白色的封面上,一束艾蒿迎风舞蹈。原来王师傅就是艾叔叔,原来自己一直和艾叔叔在一起。方平激动不已,望着王师傅,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这时,他听见两个男孩的问话:“艾爷爷,你和艾叔叔是一家人吗?”
王师傅认真地回答道:“当然了,我们都姓艾。”
两个男孩又问道:“那我们长大了也能姓艾吗?”
王师傅郑重地点点头,拉着孩子们的手,又看看方平,无声地笑了。
阳光照进病房,照着那本有点发黄的白色日记本,散发出一股艾草的清香。方平抚着打石膏的伤腿,望着王师傅和两个孩子,微笑着轻声说:“姓艾真好。”
父亲的旗子
妻子上班前对林子说:“你这两天留点心,父亲不知在瞎捣鼓啥呢,看看捡得这些破烂。”楼道墙角里,码放着几摞彩色广告纸,肯定是父亲的杰作。林子安慰妻子:“爹老了,多包容。”心里却嘀咕:老头子不缺钱,收这废品干啥。
父亲是某深山小站的值班员,去年刚退休,回到了农村老家。但父亲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和老家不免生疏,母亲又去得早,只能天天窝在家里,对着羊呀,鸡呀说话。再窝下去,都要闷出毛病了——典型的退休综合症。因此,林子把父亲接过来,一来换个环境,权当治疗,二来也可享享天伦,尽尽孝心。
“哎,这个老头子,是不年轻了。”想起小时候和母亲一起看父亲:翠山、红花、白屋、溪涧……父亲便是岩松了。父亲像将军,笔直地站在站台上,手中的旗子飞舞,面对着大山发令,而列车则在父亲的指挥下或驰骋千里,或戛然而止。
那时候,父亲多神气。林子仰望着父亲,眼里满是敬仰。晚上,林子做了个梦,梦中,他变成了父亲,指挥着列车缓缓驶过大山,驶过时光,驶过林子的童年……十几年后,林子真的实现了愿望,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铁路值班员,只不过,父亲在深山,而自己在都市。
那时,休班回家,父子俩便会整一盅。父亲的脸在夜色里发亮,白白的月光在酒杯里晃,林子举起杯,总有个错觉,觉得自己喝的不是酒,而是月亮。父亲一喝酒话就多,不过,说的最多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父亲说林子你多幸运,能到铁路上子承父业,要感恩哪……孩子你得当心呀,啥时候都得安全第一……
父亲来了十几天了,效果还不错。林子家属于铁路小区,离铁路近,吵是吵了点,但退休职工不少,父亲和他们聊聊天,买买菜,接接孩子,性格也开朗了许多。林子很高兴,觉得自己这招棋走对了。不过,妻子的牢骚又让他心里狐疑:这个老头子,在折腾啥呢?
周末,妻子和孩子回了娘家。中午,林子做了几个菜,和父亲整上一盅。父亲很高兴,一喝酒,话照例多起来。不过,和以前不同的是,父亲不再对林子说教,而是虚心地问林子:“安全形势如何,客流量咋样,工作要求是否更高了?”林子发现,一提起工作,父亲的脸就容光焕发,眼神亮亮的,像变了一个人。
林子就笑了笑,举杯,碰杯,再举杯,碰杯,却不喝,只看着父亲。父亲被林子看毛了,就住了口,环顾四周,看哪里出了问题。
林子见状,又笑了笑,说:“爹呀,我看你别呆在家里了,返聘得了。拿着退休金,操着局长心。要不,给你找个老伴,省得太闲了闹心?”
父亲的脸先是红了,接着又佯怒道:“你这小子,耍你爹呢?”
林子一笑:“岂敢,岂敢,真心话,真心话。”
接下来父子天南海北地聊。但林子看出来,父亲明显有点心不在焉,有些话他要说上两遍,父亲才惊醒似的,“哦,你再说一遍。”林子很无语,从老爹的表现看,肯定有啥事瞒着自己。但依老爹的秉性,又套不出什么话。干脆虚晃一枪,明的不行,来暗的吧。
林子告诉父亲,朋友有点事,要出去一趟。父亲似乎松了口气,如释重负地催他,快去快去,莫让人家等。
林子下楼,在楼下转了两圈,确定时间宽绰,能抓住父亲现行,才悄悄上楼。他在门口听了听,屋里没什么动静;敲敲门,里面没反应,正纳闷间,却看到楼道墙角里码放的广告旗不见了。林子分析了分析,父亲不在家,又没下楼,和邻居又不熟,肯定是上楼顶去了。不过,冬天楼顶风如刀子,父亲上去干什么呢?登高望远?父亲还挺风雅。
林子悄悄上到楼顶。整日忙忙碌碌,难得上楼,空气虽冷冽,却顿觉豁然开朗:蓝空深邃,阳光如泻……远处,一列火车正幽幽地开过来。
就在这时,林子忽然有了错觉,分明看到了父亲笔直的身影。不,那不是错觉,是真的。父亲手中拿着一面自制的绿色广告旗,努力挺直脊背,面对着远方的火车,像二十多年前一样,一丝不苟地平举着手臂……
林子当然懂得绿色的旗语:准许列车通过。
一时间,林子泪流满面。泪眼模糊中,林子向着父亲的背影和远方的火车,缓缓举起了手臂……
列车上的歌声
车过郑州,天空就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地。列车就在这漫天的洁白中飞速行进。
车箱内,人们一片欢呼后,很快就如沸水中的茶叶,沉入无边的岑寂。舟车劳顿和羁旅行役感,雪一样渐渐消融掉他们的全部热情。委顿和懒散开始弥漫在车箱中。由于开着空调,有人干脆打起了瞌睡。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歌声,惊得车箱里一阵私语,那欢快而明朗的调子,越来越高的尾音,分明是一首新疆民歌。是谁有如此雅兴?诗人、流浪者、乞丐、或者是个疯子?在这薄暮时分,人们又都情绪低迷的时刻。
循声望去,歌者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面对着窗外,很投入地唱着民歌。
有感于众人的注视,歌者站起了身:“对不起,打扰了。”
仿佛掷入了一粒石子,车箱内的沉闷和凝滞开始逸散。人们无声地望着歌者,希望他有下文,但他却没有唱下去的意思。
这时,一个精悍的南方男子喊了起来:“怎么?吊起了大家的胃口,就不唱了,喏,这是一百元钱,再唱两首就归你了。”
有人开始激动起来,大声地撺掇着。
歌者的脸色一时有点难看,但他并未发作。是呀,这有什么呀,唱两首歌一百元,明星刚出道时说不定还不值一百呢!有人附和着。
歌者清了清嗓子道:“好,十年修得同船渡,我们共乘一车,也是有缘,我就为大家唱两首。”
茫茫的原野上,疾驰的列车中,歌声如雪似蝶,在人们的心中翩飞着。
歌者唱完了两首歌,在掌声中说道:“谁想唱谁就唱两首,人活着总得有点念想。”
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青年站了来,他唱了首《同桌的你》。
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了起来,他唱的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
歌声连绵不断,掌声不时响起,笑语经久不息。这会儿的车箱,简直成了一个演唱会了,暖哄哄的、闹腾腾的,有一种节日的气氛。
在歌唱的间隙中,那位精悍的南方男子来到歌者面前,呈上了那张示过众的百元钞票。
歌者摆手笑道:“兄弟,我可不是为了这个唱的!”
“那你……谢谢……”南方男子脸红了,讪讪地把钱放进了口袋。
“兄弟,我给你讲个故事。”
歌者略带低沉的声音把大家带到了两年前。
在同样的区间,同样西去的列车上,乘警伟显得格外兴奋,再过两天,列车到达终点站——家乡乌鲁木齐时,伟将和他相爱已久的女友步入结婚殿堂。幸福使伟不时哼着家乡民歌。
就在这时,伟发现了一人鬼鬼祟祟地把手伸向了昏睡的旅客。伟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双手铁钳般地箍住了小偷,就在他准备给小偷上铐时,一把匕首从后面刺来,伟倒在了血泊中。
旅客愤怒了,他们并排站起来,像铜墙铁壁,把小偷及其同伙逼进了绝境……
歌者的眼睛湿润了,车箱内寂然无声,悲怆和崇高时时袭着他们的心。
良久,一个童音问道:“后来呢?”
后来,伟走了,就埋在这个区间的山包上。伟的女友穿着婚纱,在他的坟前唱了三天新疆民歌。
“你刚才就是为伟唱的吧?”那个南方男子自责道:“对不起,我不知道……”
从此,我们每路过这里,都要为伟唱唱歌,让他在异乡,能听听乡音,不感到寂寞。
“你是伟的兄长、朋友、亲戚?”旅客中有人发问。
“不,我是汉人,我只是那趟车上的旅客,从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几首新疆民歌……”
车厢一片静默。
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白莽莽的原野上,万籁俱寂,一列火车如笛,正奏响中原的黄昏。
【作者简介】孟庆玲,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在郑州供电段工作。先后在《百家讲坛》《安徽文学》、《牡丹》《百花园》等报刊发表小说、历史散文、诗歌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