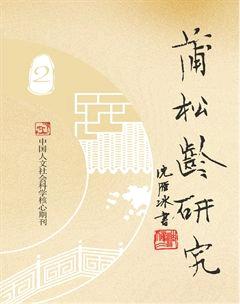《聊斋》丛脞录
赵伯陶
摘要:《促织》作为《聊斋志异》中的名著,诸多《聊斋》选注本不可或缺,全国各地高中语文课本也为上驷之选。蒲松龄对于养虫、斗蟋蟀并非内行,在写作中明显参考了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中有关捉蟋蟀的记述,指出小说中部分词语借鉴前人之处,对于理解作者深刻用心大有裨益。“以蠹贫”三字何解?今人注释多不准确,影响了读者对于小说真义的探究。本文认为此三字语本《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比喻祸国殃民的人或事,这里即指皇宫“岁征”蟋蟀的弊政。
关键词:聊斋志异;促织;帝京景物略;比笼;以蠹贫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促织》中成名之子魂化蟋蟀,手稿本文字属于暗写,青柯亭本在刻印过程中或许编者认为作者针线偶疏,于是改“但蟋蟀笼虚”三句为:“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又改“由此以善养虫名,屡得抚军殊宠”二句为:“后岁馀,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赉成。”这样就改为明写成名之子“变形”的悲剧了。何者为佳?见仁见智,这里不做讨论。有论者将此篇与唐陈鸿《东城老父传》传奇比较,唐玄宗喜斗鸡与明宣宗喜斗蟋蟀,玩物之心,毫无二致;但前者因安史之乱险些亡国,关于后者,史家则有“蒸然有治平之象”的赞誉(《明史》卷九《宣宗本纪》),两者实有所区别。至于有论者将《促织》与20世纪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变形记》之所谓“异化”说为比,则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了。关于《促织》一篇的本事来源,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斗虫》,明吕毖《明朝小史》卷六《宣德纪·骏马易虫》、明冯梦龙《三教偶拈·济公火化促织》,明拟话本小说《济颠语录》中促织化青衣童子故事,清褚人获《坚瓠集》馀集卷一《蟋蟀》,皆有论者指出其文献依据,此处不赘。然而从作品围绕促织的诸多民俗性问题,作者显然从明刘侗、于奕正所撰之《帝京景物略》中借鉴良多,而且可证蒲松龄于斗蟋蟀之有关民俗细节不甚了了甚至疏漏之处,但他转益多师,纵横捭阖,亦可见其《聊斋志异》写作的苦心孤诣之处。孟昭连先生《〈促织〉与〈帝京景物略〉》一文(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3期),对此阐发甚多,可参考。
蒲松龄对于《帝京景物略》一书甚为熟悉,其《聊斋文集》卷三有《〈帝京景物选略〉小引》一篇小文,内赞刘侗等人之文笔有云:“其所为创,不直学,才也。”可见推崇。《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中有捕捉蟋蟀的描写:“秋七八月,游闲人提竹筒、过笼、铜丝罩,诣草丛处、缺墙颓屋处、砖甓土石堆垒处,侧听徐行,若有遗亡,迹声所缕发而穴斯得。”《促织》加以借鉴:“早出暮归,提竹筒、铜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迄无济。”比较两者文字,可见渊源有自。《胡家村》中又有“坟兆万接”一语,就被蒲松龄直接用于《公孙九娘》一篇中,可证作者对《聊斋志异》反复修改润饰的过程中多所取资的认真态度。
斗蟋蟀之风从南宋奸相贾似道于秋壑堂大开风气之后,迨至明清乃至民国,社会上下皆有同好。明袁宏道《促织志》:“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每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可见风气一斑。作为一项民间娱乐,只要不过分,说不上玩物丧志,但帝王耽于此乐,则有可能误国误民,蒲松龄也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意欲进谏帝王的。比蒲松龄早生三十年的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对于“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的封建帝王做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明确批判。黄、蒲两者相较,在对待封建专制统治的态度上,前者比后者“异史氏曰”中的感慨,显然进步多了。清方舒岩评此篇云:“以苛政论,宣德间不必有其事。然宫中偶戏促织,似亦无碍于治。乌知成之破产遭刑,几至于死,而身复难存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是以事每忽于所微,而害常生于莫测。”这是从事理上加以判断,已脱离对于专制主义的批判。可见蒲翁态度在当时仍有其前瞻性的积极一面。
《聊斋志异》全注本以外,《促织》一篇也是诸多选注本的上驷之选,高中语文课本也常能觅其踪迹。然而选注者往往对于一些语词的注释却不甚了了,有进一步商榷之必要。如“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何谓“蹲石鳞鳞”?张友鹤先生《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下简称张注本)注云:“石头一块块在地下排列着,好像鱼鳞一样。”中山大学中文系《评注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下简称中山本)注云:“石块像鱼鳞那样密排着。”朱其铠先生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下简称朱注本)注云:“乱石蹲踞,密集像鱼鳞。”盛伟先生《聊斋志异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下简称盛注本)未出注,“蹲石鳞鳞”作“蹲石嶙嶙”。李伯齐、徐文军先生《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下简称李注本)注云:“即前文的‘块石乱卧。蹲石,丛聚的石头。蹲,通‘僔,聚,众多。鳞鳞,密集排列的样子。”马振方先生《聊斋志异:精选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下简称马注本)未注。实则蹲(cǔn忖)石鳞鳞,意谓石层聚叠合如鱼鳞一般,有层石相叠压的意思,如此方能与鱼鳞的状况相合。蹲,聚集,叠合。《左传·成公十六年》:“潘尫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晋杜预注:“蹲,聚也。”
“而翁归,自与汝覆算耳”,何谓“覆算”?《汉语大词典》解释:“覆核帐目。喻指清算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并以《促织》为书证。张注本注云:“再来算账的意思。”中山本注云:“等于说算账,意即追究。”盛注本作“覆算”而未出注,其馀各本皆作“复算”且不出注。在这里,“覆算”不当作“复算”,以《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最为明晰,当遵从之。以笔者所见三种白话译本亦皆以“算帐”或“算账”为译,虽不甚准确,却也差强人意。endprint
“因出己虫,纳比笼中”,何谓“比笼”?诸多注本皆无注,唯盛注本注云:“评比促织大小的笼子。清陈淏子《花镜·养昆虫法·蟋蟀》:‘初至斗所,凡有持促织而往者,各纳之比笼中,相其身等、色等。”再看白话译本如何翻译“比笼”。《聊斋志异评赏大成》(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下简称漓江本)译为“旁边的笼子”,《文白对照聊斋志异》(中华书局2010年版,下简称中华本)译为“斗蟋蟀用的笼子”,《聊斋志异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下简称上古本)译为“比赛用的瓦盆”。梁宗奎先生《也释“纳比笼中”》(载《临沂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云:“据上,我们可以断言‘比笼不是一个词组,而是两个词。‘比笼不是‘比试的笼子,而是‘比于笼的省略。‘纳比于笼是一个成分省略较多的句子,其主语为村中少年,整句成分全部补出为‘(村中少年)纳(之——蟹壳青)比(之——小虫)(于)笼,全部译出是:村中少年将自己的虫纳入成名笼中与小虫紧并在一起。这样就言之成理了。”如此一来,“比笼”是否成词都成了问题。
《汉语大词典》收有“比笼”词目,释云:“用于盛放准备打斗的蟋蟀的笼子。”并以《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七五引明刘侗《促织志》“初斗虫,主者各内虫乎比笼,身等、色等,合而内乎斗盆”为书证,似乎明清饲养蟋蟀仍用笼子。唐五代至宋,饲养蟋蟀的确多用笼,有文献可证。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金笼蟋蟀》:“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宋顾文鉴《负暄杂录·禽虫善斗》中所谓“镂象牙为笼”,南宋姜夔《齐天乐·赋蟋蟀》小序中所谓“镂象牙为观贮之”,皆可为证。南宋以后至于明代,饲养蟋蟀已改用瓦盆泥罐,以适应蟋蟀喜阴之特性,明袁宏道《促织志》以及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等文献皆有记述。饲养蟋蟀的工具称“笼”,当属于沿袭旧词,上文“笼养之”当亦属仿古之称谓。一说“比笼”源于宋代的石质“比匣”,入明后改为陶质、瓷质或澄泥烧制的蟋蟀罐,为贮存斗虫的专用器具,并非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竹篦、木条或金属丝制造的笼子。清顾禄《清嘉录》卷八《秋兴》:“白露前后,驯养蟋蟀,以为赌斗之乐,谓之秋兴,俗名斗赚绩。提笼相望,结队成群。呼其虫为将军,以头大足长为贵,青黄红黑白正色为优。大小相若,铢两适均,然后开册。”所谓“提笼”,当为“提罐”,言“笼”,沿袭古称而已。总之,所谓“比笼”,就是用于盛放准备打斗的蟋蟀的陶罐或泥罐。
“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以蠹贫”何谓?“蠹”又何所指?张注本注云:“蠹:蛀虫。这里指敲诈勒索的里胥像为害的蛀虫。”中山本注云:“蛀虫。这里指敲诈勒索的里胥。”朱注本注云:“蛀虫,这里指里胥。”盛注本未出注。李注本注云:“蠹胥,害民之差役。这里指里胥。蠹,蛀虫。旧时把暴政称为‘蠹政,把为害民众的官吏称为‘蠹吏、‘蠹胥。”马注本注云:“蛀虫,指里胥等蠹役。”再看白话译本。“以蠹贫”,漓江本译为“因为读书受穷”;中华本译为“因蠹吏敲诈而贫穷”;上古本译为“因为当上了乡长而受贫”。王树功先生《“蠹贫”别解》(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我认为‘蠹贫应解释为因读书谋取功名未遂而贫穷。蠹。这里是蠹虫,书鱼之意。”漓江本之译文或许参考了王先生的“别解”,上古本的译文则又别出心裁,可不论。其他注本或译本皆以“蠹”为“胥吏”或“蠹吏”之谓,占大多数,与“读书受穷”说堪称处于“二元对立”的地位。现在在互联网上所见高中语文教学有关课件,仍有并列两说者。有关《促织》中之“蠹”何指,竟然聚讼至今,不得要领,的确令人费解。其实只要细心检索有关工具书,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蒲松龄《聊斋志异》喜用典籍文献之词语,“蠹”即用《左传》中语,比喻祸国殃民的人或事,这里即指皇宫“岁征”蟋蟀的弊政。语本《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穆叔闻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令倍其赋。”大意是:鲁襄公二十二年的春天,鲁国大夫臧武仲去晋国,天下雨,就去探望鲁国御邑大夫御叔。御叔在他的封邑里,打算饮酒,就说:“哪里用得着圣人(指臧武仲)!我要喝酒了,而他却冒雨出行,还要那些聪明做什么?”鲁国大夫穆叔听到这一番话后,就说:“御叔他不配出使,反而对使者臧武仲傲慢,是国家的蛀虫。”于是下令将御叔封邑的赋税增加一倍。蒲松龄故意将“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三句话郢书燕说,用其字面义“飞白”一笔,令“使”从“使者”转换为“驱使”之义,从而语带讥讽地批评了明廷祸国殃民的岁征蟋蟀之弊政。如果将“以蠹贫”理解为“因蠹吏敲诈而贫穷”或“因为读书受穷”,不正确外,也消弱了小说固有的尖锐批判锋芒。
(责任编辑:李汉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