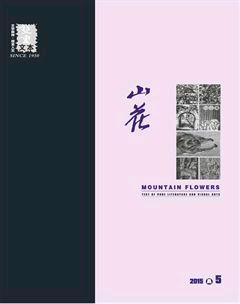写作是一种禅修
蒋一谈 行超
文学性决定作品的品质
行 超:短篇小说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文体,我听过不少写作者讨论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到底那个更难写的话题,您觉得呢?
蒋一谈:比较一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难易度会比较简单,这就好比两个人比赛跑步,一个跑一百米一个跑马拉松,完成马拉松的选手的确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体力,所以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难度显然大于一篇短篇小说的写作难度。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可能会有另一个答案:如果一个作家准备用5年的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另一个作家准备在5年的时间内写很多篇短篇小说,那么写作短篇小说会更加辛苦。作家捕捉社会信息、生活信息的时候需要运用自己的“雷达”,写作长篇小说,“雷达”可以随时关掉,可以中途休息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然后再接着写。写短篇小说不行,持续写短篇小说需要持续的文学状态,“雷达”几乎随时都要处于开启状态,这会耗费很多时间和心力。对写作者而言,写作的难度都必须由一个人来扛。
短篇小说好比一个没穿衣服的人,身材和皮肤的优缺点就在那儿,隐藏不了;而且短篇小说写作者,特别忌讳故事构想和故事风格的重复,所以每一篇作品从构思到完成,都需要仔细对待。
行 超:就写作技巧本身而言,您认为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蒋一谈:这个问题非常大,很难回答。我只能试着回答。我觉得,就故事构想而言,现代短篇小说更侧重故事构想而不是故事本身,这个故事构想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从生活出发后即刻返回的那个临界点,即出发即返回的交错点;或者说,短篇小说需要捕捉那一个将要发生还没有发生的故事状态。长篇小说更加依赖故事的延展性和人物生活的世俗性。长篇小说是世俗生活的画卷,文学的真意都在世俗里。我喜欢具有河流气息的文学作品。河流的源头是小溪小河,是缓缓的涓涓细流,越往下流淌,河面会越流越宽,越有深意,这是文学的静水深流。
行 超:我记得您曾说过:“对现代短篇小说写作而言,故事创意的力量优于故事叙事本身,它是写作者的文学DNA”。这是不是说,相比作品形式,您对故事构想更感兴趣?
蒋一谈:先有桌子,还是先有椅子的理念,这是柏拉图时代的哲学话题,延续到现在依然很有意义。人类首先要有登上月亮的理念,才会去制造攀升的工具。无是冥冥之中的东西,无生有,想象力是决定力。故事的最初构想常常来自虚空,所以在某个时间段,写作者需要无所事事的无聊生活状态。
全世界的写作者数不胜数,没有独特的故事构想,很难成为独特的写作者。我觉得,按篇幅来讲,两三千字之内的超短篇小说和字数在一万五千字至两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是最难写的。超短篇的写作更接近于禅机。现代短篇小说追求故事构想和细节呈现,不在意故事情节,所以一万五千字至两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考验着写作者的综合能力。
看似无事状态下的人和事是我喜欢思考的。那些大家习以为常的故事和人物,能否用另外的方法、另外的角度重新呈现?或许可以试一试。生活的常态是无事,是单调和乏味,是重复昨日,一天挨着一天,跟着时间的脚步。在常态之下,生活的暗流在流淌,人物内心的暗流在起伏。小时候读孔子的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是很懂。后来慢慢长大,经历了生活,才懂了些。河流不是时间,不是生活,不是文学,可是当古人把时间比喻为河流的时候,河流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河流变成了我们的时间,开始蕴含我们的文学和生活,变成某种思考方式。逝者如斯夫,这是时间和生命的流逝,更是河流本身的流逝,带着回忆的流逝,物我相合的流逝。有些写作者喜欢山,喜欢用山峦的方式思考人生,而我更喜欢水,喜欢用河流的方式思考人生。
行 超:与一些追求先锋性的作家相比,我认为您的叙述方式还是倾向于传统的,您更注重寻找人们内心最脆弱的那个部分,以一种温和、婉转、中性的叙事方式击中读者,可以谈谈您的写作风格吗?
蒋一谈:文学和艺术永远需要先锋精神,需要具有破坏和散发新鲜活力的力量。西班牙建筑艺术家高迪说过:“艺术来自自然,而在自然里没有直线。”而先锋性就是在自然里创造直线,努力创造出这种不可能。文学的传统和先锋是镜子的两面,看镜子这一面的时候,还要想到另一面,只有这样才可能写出短篇小说里的朴实的“自然”和创造出来的“直线”。我喜欢脚踏实地的作品,也在努力学习并追求故事构想的独特性和语言叙事的简洁、准确。我也希望自己能在现实主义大风格的前提下,探寻多种故事构想和叙事尝试。
行 超:现实主义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有些作家的作品看似写的是现实生活,甚至新闻事件,但却只是表层的、隔靴瘙痒的,不能真正深入现实的核心;而有的作品是魔幻的、荒诞的,但它关注的却是人类共通的问题,是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成立的,所以读者会觉得它无比真实。您如何看待文学故事和现实生活、新闻事件的关系?
蒋一谈:取自新闻事件的写作常常意味着非虚构写作,而非虚构写作的要义是基于真实,拥抱虚构。所以,遇到一个事件,如果没有想好故事结构和叙事方式,没有信心写出耐人琢磨的文学味道,还是远离为好。
你的问题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最重要的写作目标是什么?是描写现实主义,还是描写现实生活里的那些人?换句话说,作家是以笔下的人物为道具衬托出了他眼里的现实主义,还有以现实为背景托出了他心里想写的那些人?
这几年,我尝试写了几篇故事构想与新闻事件有关联的作品。2010写的《中国鲤》,故事构想来自一部纪录片:《亚洲鲤鱼入侵美国》。2011年写的《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故事构想来自马克吕布先生在北京的影像展和吴冠中先生的自传《我负丹青》。2013年写的《故乡》,故事灵感来自一篇新闻报道:一个西班牙男人深陷“9·11”灾难,他选择右边的楼梯井逃生后,内心一直恐慌,后来每次遇见路口,他都会下意识地选择往右边行走。这个西班牙男人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个人觉得,现实世界发生的新闻事件应该最大限度地归属于电视和网络传播,观众由此获得信息已经足够,而文字写作者(其实也是观众)不能有和电视网络抢占新闻信息的心理,更不能沉浸其中。文学性真正决定作品的品质,无论你写的是非虚构作品还是虚构作品。
行 超:您的小说集题词和作品文字里时常出现诗歌,都说诗歌是语言的极致表达,您怎么看待诗歌的阅读、创作对您小说创作的影响?
蒋一谈:我觉得诗歌是距离禅宗最近的文体。我喜欢诗歌,一直在读诗写诗,这些年写了两三百首诗歌。我更喜欢口语诗歌,尤其是那些简洁的平民口语诗歌。我希望通过诗歌的阅读和写作,用另一种叙述方式存储自己的情感,同时也想通过诗歌写作保持语言的温度和湿度。诗歌和小说,是一对特殊的情侣。
知识分子、老男人:孤独的现代人
行 超:您的作品里有很多上年纪的“老男人”,比如《鲁迅的胡子》《ChinaStory》《故乡》《发生》等等。这些人物处境不一,内心都很孤独,这一类人物形象在您的作品中非常突出。为什么着意描写这个特殊的群体?
蒋一谈:读完厄普代克的《父亲的眼泪》,他笔下的那些老男人打动了我,我也开始储备这方面的写作素材。之前的笔记本里,有十几位这样的人物,年龄从五十七、八岁到六、七十岁。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代人的寿命虽然比过去长,但古人的传统理念还在留存。一个人过了70岁,会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离死亡更近了。我父亲今年75岁,他时常一个人坐在那儿,静静地注视外面的世界,能坐很久。这一幕带给我更多的是无力感。前一段时间,电视台做了一个“谁是家里的顶梁柱”的生活调查,男人差不多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是时间和岁月对男人的折磨是很残酷的。女人害怕五官的衰老,男人害怕内心的衰老。
行 超:除了“老男人”,知识分子形象在您的作品里也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鲁迅的胡子》《林荫大道》《在酒楼上》《温暖的南极》《跑步》等作品,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您的小说常常刻画他们失意的、挣扎和努力承受的现实和精神现状,为什么对这个群体格外关注?
蒋一谈:知识分子是我长期关注的人物群落。世界由知识碰撞推动前进。相比过去,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比以往多很多。但是,何谓知识分子?这个话题非常大却又非常模糊。我无意于探寻知识分子的身份,因为有比身份确认更重要的事情。
我是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里,我有失败感,有自己的精神疑难。我认识的一些“70后”、“80后”知识分子,也有这样那样的无力感和失败感。相比过去,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内心更为纠结的一群人。知识是他们寻找世界、和世界对话的方式和工具,可是知识也会变成心里的牢笼和业障。我目前的作品与我的实际经历没有关联,可是在写作知识分子的时候,我觉得在写另一个自我,这种感受会让人心生沮丧。
行 超:《跑步》里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内心挣扎的知识分子,他在跑步机上奋力奔跑的场面很真实。一个生活中处处不如意的中年男人,似乎只能用最原始的奔跑与他人竞争,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和胜利。
蒋一谈:我在跑步机上锻炼身体,之前没有想过写这样一个故事。去年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路过一间健身房,透过玻璃窗看见两个男人正在跑步机上跑步,写作灵感是在那一刻来的。我想探讨一个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一个文弱的男人,面对现实的原始暴力,需要在现实面前扮演强大的父亲角色。
父亲养育孩子,这是无法回避的血液里的责任,可是父亲这个角色,这个由更多的知识支撑起来的父亲角色,在突如其来的暴力面前,会怎么样呢?他的经历和思维模式,让他遗忘了暴力和力量,他被自己的生活异化了、弱化了,但后来他知道自己迫切需要男人的那种暴力和力量,哪怕是跑步机上暂时的扮演,他也想以此努力唤醒自己、证明自己,同时安慰自己。社会现实越实际、越具有破坏力,知识分子就越需要扮演。
行 超:您的作品经常涉及到家庭的疏离、伤痛和弥合,您刚才也提到,喜欢关注家庭故事和家庭里的人物情感,可以谈谈其中的原因吗?
蒋一谈: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也是家庭中人。人生是机缘碎片的组合,国家是家庭碎片的组合,家庭碎片漂浮在国家时空里,寻找着各自的位置。和过往相比,这个时代,国家和家国的概念,生存和存在的概念,都在发生着变化,而变化间的人和事,蕴含着文学生机。
可能是因为性格和阅读偏好,我喜欢关注人物的情感世界,即使人和人之间产生的那种情感是瞬间的;因为瞬间,我喜欢“一机一会”这个词语,这是站在悬崖边的状态,而每一篇短篇小说的构想初始是这个状态。一个故事构想,要么感应到抓住了,要么就会掉下悬崖。所以,短篇小说的构思之端非常陡峭,但在写作的时候,陡峭感又不能显现出来。
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或许决定了写作者的故事选材偏好。我喜欢家庭故事,也很愿意成为一名“中国家庭作家。”
行 超:您的短篇小说,绝大多数是在描写城市男女的故事。中国的城市化起步比较晚,相应的城市文学出现得也比较晚,发展不够成熟。我个人认为,真正的城市文学关注的应该是生活在城市,吃穿不愁、物质层面没什么困难,而在精神层面出现问题的人。但是,目前国内很多作家还是将目光放在城市中的底层,他们所描写的生存问题基本上还是跟生计有关的。您的作品在这方面却有特别的表现,比如《发生》《跑步》《夜空为什么那么黑》《透明》等,都在关注城市人的精神困境。您心目中好的城市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蒋一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每一个写作者其实都是局限的,可是局限本身又给我们留下两个思考话题:我们如何在自己的局限里创造出新颖独特的故事和人物,我们如何在持续的写作中突破自己的想象和写作局限。
关于底层故事,我写过《芭比娃娃》。就像你说的,底层人物的生计问题常常排在精神疑难前面,或者说那个故事本身就是生计问题。后来,我又尝试写了几个底层故事,但中途都放弃了。这里面有一个个人写作心理的问题。我不太喜欢“底层”或者“小人物”这样的文学表述概念,我更愿意接受“普通人物”这样的表述。如果非要用“底层”人物概念,这样的人物也应该由两种人物构成:经济上的底层人物和精神上的底层人物;而精神上的卑微人物即是精神上的底层人物。在现实生活面前,在内心深处,那些社会地位高、收入高,且文化层面高的人物,内心里那种精神上的卑微感是真实存在的,或者说在某一个时空,会时不时闪现一下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更能体会到精神上的卑微感,体会到精神上的瞬间崩塌。
中国现在有4.3亿个家庭,其中城市家庭的比例今年为52%左右,城市家庭数量一直在持续增加。我曾在网上读过一个著名作家的访谈,他说他喜欢写过去的故事而不喜欢写当代现实生活,他认为当代生活很容易写,所以不写。我倒觉得当代现实生活是非常难写的,因为我们的读者是当代人,我们都在同一个时间段里,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生活感受,而作家的文字和感受很难让他们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尤其是那些有一定知识的城里人,会离开城市来到城市的最边缘或者乡村里,他们可能是在逃避,也可能想重新发现未来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有人物的地方才有故事,而未来的中国乡土文学,抑或村落文学,从题材到思想,会发生新的变化。
最开始写作城市文学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三不”原则。一,不写城市的外化符号;二,不写人物的五官特征;三,不猎奇。我想让自己不去注意或者遗忘眼睛所见的东西。
超短篇小说更接近禅机
行 超:您刚才说,“超短篇小说的写作更接近禅机”,可否展开阐述一下?
蒋一谈:写作是一个长期的思考和训练,写作状态的养护类似于寺庙里的禅修。禅修的时间可长可短,但时间的长短往往决定着心境的澄明程度。顿悟是刹那间的,是一个极短暂的理念点燃,而非一个过程,此后修行者又要开始下一个阶段的精修。我在之前的沙龙活动中打过一个比方,短篇小说(含超短篇小说)的写作类似于一个孵化的鸡蛋,小鸡足月了,想出来了,开始用小嘴敲击蛋壳,蛋壳碎了小鸡鸣叫自己出来了,但这个过程还是半机。小鸡从里面敲击蛋壳的时候,母鸡也在蛋壳外面敲击蛋壳,它们依靠感觉寻找着同一个敲击点,然后继续敲击,蛋壳在某一刻开了一个小洞,小洞显现的一刹那即是禅机。
行 超:在碎片化阅读的今天,超短篇小说或许更能符合读者的需要。最近,多家杂志推出了小小说和微小说相关专栏。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蒋一谈:小小说和微型小说(微小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存在,甚至还相当兴盛过。现阶段的文学,短篇小说写作者越来越多了,但学术界和写作者对超短篇小说的研究和研讨还刚刚开始。
小小说、微型小说、短小说、极短小说、掌上小说、超短篇小说,这些文学概念是并存的,但我本人更愿意在超短篇的理念下写作这样的作品,因为超短篇和超短裙的理念和样式很像,读者理解起来更容易。一寸短,一寸险,写作者需要在险滩行走,训练自己的感受力和想象力。
文学杂志社推出相关作品栏目,当然是好事,但谁能做好这个栏目,比拼的则是文学编辑的眼光和作家作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超短篇小说的写作方面,职业写作者的想象力和悟性不一定拼得过业余写作者。
行 超:您认为超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异同有那些?
蒋一谈:我在2009年开始写作,当时已经四十岁了,心理上有时间的紧迫感,所以有了感觉就赶快记下来写出来。写了《坐禅入门》《洛丽塔和普宁》《一场小而激动的雨》《随河漂流》等作品之后,当时也没有持续写超短篇的写作想法。后来遇到《地道战》和《二泉不映月》的构想,琢磨了好久,最后决定用短的篇幅呈现。完成这两篇之后,或者说在2013年秋天之后,我才认真考虑超短篇小说的写作规划,才正式整理这几年写出来的超短篇小说。
通过写作,我觉得超短篇小说虽然归属于短篇小说文体,但超短篇小说的心里充满了更多的幻想和诗意。就像一根横跨山谷的绳索,这一边的绳子是现实主义,另一边的绳子就是幻想主义,写作者需要踩在两根绳子上,身体可以随风晃悠,但不能掉下去。你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观众,也没有人为你作证,你从绳索上跳下来之后,把经历和感受说给别人听,别人能相信你吗?能相信你的作品吗?超短篇小说的文字感受和说服能力要比短篇小说的文字说服能力更高一些,或许只高那么一点点,因为超短篇小说有天然的寓言和童话特性。
相比短篇小说,超短篇小说的篇幅和叙事空间更为有限。舞台越小,对舞蹈者身体协调能力的要求就越高,旋转不好就会飞出去。超短篇小说的写作类似于这样一位舞者,那是既压抑身体又需要放松身体的过程,也就是说,一篇作品的文字读上去是轻松的,其实那是写作者压抑写作情感之后的产物。
我觉得,超短篇小说的文字篇幅大致如下:短的,1000字至2000字;比短的稍长一点的,2000字至3000字;比短的更长一点的,3000字至5000字;更短的,1000字以内。两三千字之内的超短篇小说和一万五千字和两万五千字之间的短篇小说,是最难把握的、最难完成的。
行 超:超短篇小说的高潮和力量是不是在结尾?
蒋一谈:对独出心裁的写作渴望,是动力也是束缚。很多时候,文字结尾不是为了营造高潮和惊讶,而是为了创造某种诗意的失落和理解。这也是现代短篇小说(超短篇小说)和往日作品的某些区别吧。我的个人体会是,开头比结尾更重要,因为有了满意的开始才可继续写下去的快感,而结尾是为开始服务的,更是开放的。
行 超:超短篇小说写作在中国似乎处于起步阶段,您认为中国作家应该在哪些方面提高自己的超短篇写作能力?
蒋一谈:这些年,读过不少中国作家的小说,总体感受是这样的:中国的小说家与诗歌的关系比较远,或者说,中国的小说与诗歌之间依然没有形成熨帖自然的亲近感。我觉得,诗歌的写作和训练非常有益于超短篇小说的想象和写作,诗歌能让写作者远离现实,与现实保持适度的紧张感和疏离感,而不被现实淹没。现在,很多年轻的小说写作者同时喜欢写作诗歌,这也决定了中国现在和未来的作家在精神气质和文学修养上大大不同于过去的中国作家群落。
现在,一些高校开办了写作创意专业和研习中心,但还没有围绕具体文体进行分门别类的教学实践,更多实施的是文学理论上的整体教学。年轻的写作者有自己最喜欢、最得心应手的写作文体兴奋点,围绕他的兴奋点进行其他文体的学养补充,或许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有了现代诗歌研习班、短篇小说(含超短篇)研习班、长篇小说研习班、随笔研习班、文学批评研习班分类之后,学生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根据自己的爱好学到最重要的写作背景知识和实际写作经验。中国高校的创意写作课程刚刚开始,相信以后的教学和实践活动会越来越专业。创意写作课,本质上是一堂文学游戏课,是想象力的头脑风暴课,老师一旦中规中矩,本愿和效果会背道而驰。
行 超:有些文字很少的超短篇小说,我阅读之后感觉像短篇小说的故事梗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蒋一谈:一个用几十个字可以说明白的故事梗概,可以用几千字重新叙述,让人物的情绪和性格进一步延宕,这是短篇小说需要做的。同样,一部一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故事和人物可以重新压缩,这也是短篇小说可以做的。
超短篇小说的写作在幻想和现实之间游离,在叙事和描写之间寻找着平衡,这种文体不是为故事服务的,而是为独特的故事构想和人物服务的。我觉得,避免作品故事沦为作品梗概,避免梗概的说明文属性,故事构想的第一口呼吸非常关键,这口呼吸是诗意的幻想和幻想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