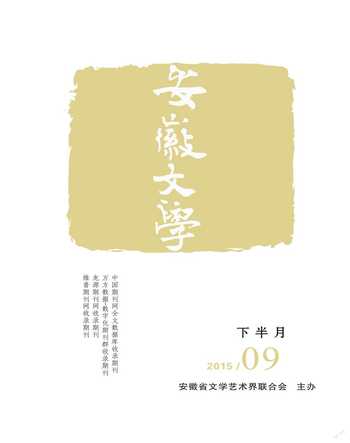论卡夫卡《城堡》的叙事艺术
杨志君
摘 要:《城堡》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叙事艺术的小说。在视角方面,它运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通过对K及其他人物进行聚焦,来叙述城堡的生活。在话语方面,它通过叙述话语与人物话语的矛盾,来揭示官方的强大势力与底层人物在官方机构面前的无力感。在时序方面,它运用了插叙的手法,叙述了阿玛丽亚一家人的悲惨遭遇。
关键词:城堡 叙事视角 叙事时间 叙事结构
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文学的鼻祖,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城堡》 是卡夫卡最后的长篇小说, 也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内容荒诞离奇,寓意深邃,揭示了人类的荒诞处境,展现了底层人物在权势面前的绝望挣扎与悲惨命运。对于这部小说,国内学者从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留下大量的成果。但借用西方叙事学理论,从叙事学的角度来阐释《城堡》的叙事艺术的,却鲜有论及。
林岗先生说:“叙事是小说文体中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在于它的故事及其讲述。”[1]正因为叙事是小说的一个更为本质地问题,故对《城堡》进行叙事分析,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第三人称限知视角
卢伯克在《小说技巧》中说:“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视点(即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可见视角在小说技巧中是极其重要的。
《城堡》是以小说中的人物视角来叙述故事。具体来说,叙述者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土地测量员K为视角,一种是以与K对话的人物为视角。
第一种情况,在小说中占主导地位。如小说以K的视角写城堡的景象:“现在他看得见山上的城堡了。衬着蓝天,城堡的轮廓很鲜明地显现出来,由于到处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银装素裹,千姿百态,使城堡显得分外明晰。此外,山上的积雪似乎比这儿村子里少得多,K在村子里行走并不比昨天在大路上好一些。这儿,积雪一直堆到茅舍的窗口,再往上又沉重地压在低矮的屋顶上,可是,山上的一切都轻松自在地屹立着,至少从这儿看是这样。”[3]透过K之眼,我们得以知道城堡的外观。因为是远观,所以显得模糊不清,以至于无法断定是住宅还是教堂——如果是全知视角,肯定对城堡无所不知,就不会出现认知上的盲点了。
小说还多次以K的视角写城堡附近村子农舍的情形,如第一章写K在城堡附近的村子漫游,想借此进入城堡,但所走的道路离城堡越来越远,显得这个村子长得没有尽头,借K之眼写道:“水蒸气终于消散了一些,K渐渐看清了屋子里的情形。这一天看来是一个大清洗的日子。靠近门口,有人在洗衣服。不过水蒸气是从另一个角落里冒出来的,那儿放着一只大木盆,K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木盆,约有两张床那么大,两个男人正在热气腾腾的水中洗澡……”[4]从引文中“K渐渐看清了屋子里的情形”与“K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木盆”这些话语中,我们便可以得知这是以K的视角在写农舍的情况。
除了以K的视角来写城堡与附近村子的情景,作者还以K来写人物的外貌。如:“从城堡方向走来两个年轻人,他们都是中等个儿,修长身材,穿着紧身衣服,两人的脸也很相似。他们脸部皮肤是深褐色的,但漆黑的山羊胡子却显得突出。他们行走在这种状况的道路上速度快得惊人,迈着细长的腿合拍地走着。”[5]
尽管作者借K之眼对这两个年轻人作了细致的描绘,却没有说出其姓名,且在后面的文中完全消失了,因而并不能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除了K自己,《城堡》里其他的人,城堡附近的村子、贵宾饭店等处所,及发生的事情,大多是借K之眼来呈现的,因而K就成了一架摄像机,透过它的聚焦,让我们得以知悉K在竭力想进入城堡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大小事件。而聚焦之外的部分,又留下了诸多情节的空白点,引人遐想。
第二种情况,采取的是书中次要人物的视角。《城堡》中大多数的故事情节是通过K与其他人物(如村长、弗丽达、奥尔加、老板娘、杰里米亚、阿图尔)的对话来展现的。而这些与K对话的人物,承担了故事的衔接与周转。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向前发展,卡夫卡让弗丽达、奥尔加、老板娘、比格尔、巴纳巴斯、培枇等聚焦人物纷纷登场,先后交叉着与主人公K进行对话。在整部小说中,K与其他人物的对话占了绝大多数篇幅。小说从第四章开始对话逐渐增多,K与老板娘的对话有时篇幅长达十多页。在后面的各章中,对话是情节展开的主要手段,也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在对话的过程中,叙述者便不再仅仅等于K,而且等于对话的另一方。就好比之前主要是用一台摄像机进行跟拍,现在添了几台摄像机,与前面的那台摄像机轮流着进行摄像。这样,叙事视角由此及彼,交替于主人公K与其他人物之间。在这种如杨义先生所说的视角的流转过程中,能够呈现出更多的关于城堡、附近村子及人物的场景,并避免了叙述声音的干扰,因而回避了价值判断、道德立场等问题,呈现出一种客观化的效果。可以说,在城堡下那个荒诞迷离的村子里,一群卑微、潦倒、懒散、庸俗的人们轮流充当小说的聚焦人物,让他们发挥“反射器”的作用。[6]这些人以“我”之眼光观察人与世界,并在言语与行动中暴露了自己的灵魂。
《城堡》中大量使用第三人称人物限知视角, 既可以让作者把自己隐蔽起来,使小说产生一种客观呈现的效果;又充分发挥了人物聚焦的作用,突出了城堡世界的梦幻与迷离,表现了人类存在的荒诞处境,以及在这种处境中人的卑微与无奈。它在形式上消除了叙述者和读者的不平等关系,“大幅度地缩短读者与作品之间的阅读距离,造成一种良好的接受心理气氛。”[7]
二、 话语的矛盾
《城堡》一书中,有不少矛盾的话语,使得小说在叙述的时候自我消解,给叙述对象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留下供人回味的空间。
小说中话语的矛盾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叙述话语的矛盾。如第十九章写道:“在这儿,没有一个人感到累,或者不如说,人人时时刻刻都感到累,但这并不影响工作,是的,反倒好像能推动工作。”[8]这一句话中“没有一个人感到累,或者不如说,人人时时刻刻都感到累”,就是明显的自相矛盾。但叙述者要突出的是,在贵宾饭店办公的秘书的“累”与为进入城堡而竭尽心智之后的K的那种疲倦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儿,那是在愉快的工作中的一种疲劳,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疲劳,实际上却是不可摧毁的平静,不可摧毁的安宁。”[9] 作者用一句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话,想要突出的是城堡官员秘书与外乡人K的区别:官员的秘书手里掌握着无权者的命运,拥有优越的地位与条件,所以他们的累是“愉快的工作中的一种疲劳”,而土地测量员K,由于地位卑微,在与官方周旋的过程中心力交悴。
另一种话语的矛盾是人物话语的矛盾。如第五章写村长回答K说:“有没有监督机构?监督机构有的是。不过,它们的任务并不是查出广义的差错,因为差错不会发生,即使偶尔发生一次差错,就像在您的事情上,可是谁又能肯定这是一个差错呢?”[10] 这里借村长自相矛盾的话来揭示官方机构所存在的问题,涉及到的是一种体制的缺陷。当任何一个普通的人遭遇到这种体制的缺陷而产生的“差错”时,他竭尽全力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却只能在强大的官方体制面前“缴械投降”——因为这种差错不是某个官员犯下的,它是官方体制犯下的,而卑微的个人不可能与庞大的体制相抗衡,被“侮辱与损害”了,也只能屈辱地忍受。又如第十五章写奥尔加对K说的一段话:“正式录用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挑选,一个名声不知为什么不好的家庭成员一开始就会被淘汰,比方说,一个人报名参加,他成年累月胆战心惊地等待审查的结果,从第一天起,方方面面的人都会惊奇地问他怎么敢做出这种毫无希望的事,但是他仍旧抱有希望,否则他怎么能活下去呢;可是过了多少年,也许白发苍苍、年事已高,他才知道自己没有被录用,才知道一切都已付诸东流,他虚度了这一生。当然,这里也有例外,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会轻易受到诱惑。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恰恰是名声不好的人最后反倒被录取,有些官员确实违心地喜欢这种野兽的气味,在招考时用鼻子嗅一嗅空气、撇撇嘴、翻白眼,这种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特别能刺激他们的胃口,他们必须牢牢抓住那基本法律全书,才能抵抗这种诱惑。不过有时这并不能使那个人获得录用,而只是没完没了地延长录用程序,永远不会结束,而且只是在那人死去以后才中断。”[11] 这一段带有矛盾性的话语,充分道出官员在录用成员的随意性:一方面是名声不好的成员一开始会被淘汰,一方面是“名声不好的人最后反倒被录取”。一个普通的人的职业前途或说命运,就这样完全掌握在没有原则的官员手里。官员在用人机制上的为所欲为,反映的也是官方机构存在的缺陷。
整体而言,小说中人物话语的矛盾要比叙述话语的矛盾普遍得多。透过这些矛盾的话语,我们可以窥测到官员的威权,官方机构的缺陷,村人对来自城堡官员的权力的顺服,外乡人K在官员或官方机构面前的卑微与渺小,及成为官方体制问题的牺牲品的悲惨命运。
三、插叙
整体而言,《城堡》的故事是按照K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子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叙述的。但在主体故事的进程中,也有几处明显的插叙。
第一处插叙是第二章写K不愿回贵宾饭店,跟随着信使巴纳巴斯向前走,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故乡的情景,心里充满了对故乡的回忆。接着便插叙了K在故乡爬墓地四周的高墙的事情:“在故乡中心广场上也有一座教堂,周围有一部分是一片古老的墓地,墓地四周围着一道高墙。只有很少几个男孩曾爬上去过,K还没有能爬上去过。他们想爬上去并不是出于好奇,墓地在他们面前已不再有什么神秘了,他们经常从它的小栅栏门里跑进去,他们只想要征服那道又高又滑的围墙。一天上午——空旷静寂的广场上阳光灿烂,在这以前或以后,K又何曾见过这样的美景?——他出人意料地轻而易举爬上了围墙;有一处地方他曾经在那儿滑下过多次,这一回他用牙齿叼着一面小旗,第一次攀登就成功了。碎石还在他脚下骨碌碌地往下滚,而他已经站在围墙顶上了。他把旗子插在墙上,旗子迎风飘扬,他低头往下看并四下张望,还掉转头去看那些插在地里的十字架;此时此地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伟大了……”[12]
这一处插叙看似跟后面的情节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却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件小事,我们得以获知K的性格:喜欢去征服有挑战性的困难——他之所以要爬上墓地四围的那道高墙,用作者的话说他“只想要征服那道又高又滑的围墙”而已。正是K的这种性格,使得他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进入城堡附近的村子遭受各种冷待与排挤时,他并没有退缩,而是千方百计去争取各种能进入城堡的机会,比如“勾引”城堡办公室主任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以获得跟克拉姆谈话的机会,因而获得进入城堡的机会。而最后K的一切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最终仍没有进入城堡,这与K在故乡能够征服那道又高又滑的围墙而给他带来的胜利的感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表现出一个异乡人在象征着权势的城堡面前的那种无力感,因而具有一种反讽的张力。
第二处插叙是在第六章,写K与生病的老板娘嘉黛娜的一番长谈,通过嘉黛娜之口插叙她二十,多年前做过克拉姆的情妇,及她与克拉姆三次短暂的交往。嘉黛娜后来一直对克拉姆念念不忘——克拉姆送她的三样东西是她活着的动力,反衬的是作为官员克拉姆权力的无孔不入,以至于在克拉姆的性要求面前,村里女性不但不拒绝,反以被征召为荣。
《城堡》中另一处篇幅更大的插叙便是第十五章。这一章几乎全是K与奥尔加的对话,而对话中又主要是以奥尔加的讲述为主。作者借奥尔加之口,插叙了三年前阿玛丽亚身上发生的一件导致她全家人陷入绝望处境的事情,以及她一家人陷入绝境后的种种挣扎。这一章里有四个小标题——这是《城堡》里唯一有小标题的一章,分别是“阿玛丽亚的秘密”、“阿玛丽亚受到的惩罚”、“求情告饶”、“奥尔加的计划”。“阿玛丽亚的秘密”写的就是三年前城堡里的大官索提尼在一次消防协会的庆祝会上看上了阿玛丽亚,便给阿玛丽亚写了封很下流的信,要求阿玛丽亚马上去贵宾饭店见他。阿玛丽亚把信撕碎了,把碎片扔到送信的那个人的脸上,得罪了官员索提尼,由此引发了一场“灾难”。具体是什么灾难,在第二个小标题“阿玛丽亚受到的惩罚”一节里才交代。那场“灾难”其实就是指突然之间,整个村里的人,凡是跟阿玛丽亚一家有关系的人,都迅速地同阿玛丽亚一家彻底断绝关系。阿玛丽亚的父亲失去了所有来修皮靴的顾客,并且被解除了在消防协会的职务,使得阿玛丽亚一家陷入了孤独、绝望的处境。“求情告饶”叙述的是阿玛丽亚一家人竭尽全力去找城堡的官员索提尼,希望求得他的宽恕。阿玛丽亚的父亲向村长、秘书、律师、文书等求情,但是都毫无作用。阿玛丽亚一家又变卖家里仅有的东西,凑钱去贿赂一些文书,结果钱全部用光了仍不起作用。阿玛丽亚的父亲最后采取的办法是:站在靠近城堡官员们车辆来往的大路上,只要有机会,就向他们恳求宽恕;结果除了患上了风湿痛,没有任何效果。“奥尔加的计划”叙述奥尔加想方设法去接近索提尼,通过“结识”官员的跟班,以期从他们那打听到索提尼的消息,以及她的弟弟巴纳巴斯之所以要去做一名“信差”(严格来说,他并不是一名真正的信差,因为他没有被任命,只是自愿这样做而已),只是为了能替阿玛丽亚“侮辱信差”(实质是得罪官员索提尼)的罪过赎罪而已。这四小节插叙,叙述了阿玛丽亚一家是如何陷入绝境,以及他们所做的挣扎,但最终无济于事的系列事件。既让我们得以知道阿玛丽亚一家人的性格与悲惨遭遇,也让我们知道巴纳巴斯做信差的缘由——某种程度上其实消解了巴纳巴斯“信差”的身份。由此,我们才知道村子里的人,不管是贵宾饭店的老板娘,还是阿玛丽亚父亲原先的手下布龙斯维克,为何都蔑视阿玛丽亚一家人。从插叙的这些情节,让我们看到官方势力的强大与无处不在,让我们看到卑微的小人物在权势面前的无能为力,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挣扎,让每一个读者深感同情。
第十五章因为插叙了阿玛丽亚一家的遭遇与命运,所以篇幅也显得特别长,占38页纸,是全书二十章里篇幅最长的一章。而全书一共200页,平均下来每章是10页的篇幅,但第十五章是每章平均篇幅的3.8倍。作者以如此多的篇幅来插叙阿玛丽亚一家的故事,是有深意的。一方面巴纳巴斯充当着K与城堡的中介人——城堡里的消息通常是借巴纳巴斯来传达的——虽然这消息是不是城堡官员发出的还值得怀疑,巴纳巴斯是K进入城堡的一条重要通道——虽然最后被证明这条通道是不可能抵达城堡的,是K最信任的人,是最能给K以希望的人,因而他的命运就与K息息相关;另一方面,阿玛丽亚一家人的遭遇,与K在城堡附近村子的遭遇形成了一种对照,他们的命运很相似,都遭到周围人士的冷漠,都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绝境,都展现了底层人在权势者面前的卑微与渺小,展现了底层小人物在困境中绝望的挣扎。因而这一章的插叙,相比前面的那处插叙,意义更为重大。
在第二十章,通过培枇之口,插叙了培枇的人生经历,及弗丽达因为K而离开酒吧之后,培枇由一个客房女侍取代了弗丽达酒吧女侍的职位,在弗丽达回到酒吧之前她是如何努力应对一切的。而且,透过培枇对K的大段独白,还插叙了弗丽达是如何从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通过成为克拉姆等手段而坐上酒吧女侍这个位置。甚至还插叙了弗丽达跟K在一起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弗丽达对K的利用,是为达到她的私人目的才选择K的。这一处插叙,一方面让培枇、弗丽达的人物形象丰满起来,另一方面,通过叙述这两个女人都想依靠克拉姆的关系而摆脱困境,也反衬了克拉姆这个从未出场的人物对城堡附近村民的巨大影响——他简直就是村民的上帝、统治者与父亲,使得村人无不对其顶礼膜拜。
这些插叙的运用,一方面可以补充故事情节,丰富人物的形象;另一方面,它们也有助于强化底层人物的悲惨遭遇,增强作品对官员及官方机构的批判力量。
总之,卡夫卡通过对人物视角的交替运用、话语的矛盾、插叙的手法,使得整部小说貌似悖理荒诞,实则真实可信,并且留有丰富的想象空间。他借用不同的人物视角叙述与习惯逻辑及常理相悖的事件,就像那是最平常的事。他通过叙述话语与人物话语的自相矛盾,来揭示官方机构影响力的无处不在,及小人物在官方机构面前的无力抗衡的困境。他用插叙的手法追叙阿玛丽亚一家的悲惨遭遇,间接讽刺官员对于底层人物的迫害。不可思议的事时常出现在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的环境和心态中,悖理的事发生得那么正常合理,和真实交织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城堡》便成了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谜语,而谜底存在每个读者的心中。
参考文献
[1] 林岗.明清之际小说的评点学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11-212.
[2]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朱乃长,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205.
[3]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一卷)[M].高乃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7.
[4]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一卷)[M].高乃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9.
[5]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一卷)[M].高乃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1.
[6] 徐晓霞,陈玉霞.《城堡》的叙事结构特征[J].长春大学学报,2007(11):61.
[7] 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29.
[8]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一卷)[M].高乃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77.
[9]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一卷)[M].高乃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77.
[10]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一卷)[M].高乃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44.
[11]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一卷)[M].高乃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45.
[12]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一卷)[M].高乃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