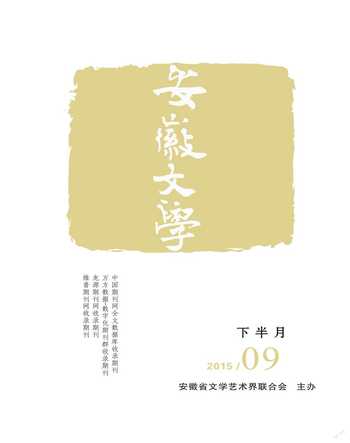从说话艺术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主人形象
徐仲秋
摘 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天才的力量震撼了世界,相较于屠格涅夫的匀称优雅,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激情澎湃,正如小说《地下室手记》所展示的一样,露骨的宣泄式的独白,在疯狂的独白中凸显了一个令读者印象深刻的与众不同的主人公形象。《地下室手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全部艺术特色,是小说,又似忏悔录和哲学论文。本文试图从小说表现方式,尤其是说话艺术切入,分析它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作用,并通过多个文本的对读,深入探讨与“多余人”、“小人物”等相关联的“地下室人”形象,并简要论述它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表现方式 说话艺术 地下室人 人物形象
《地下室手记》分为“地下室”和“雨雪霏霏”两部分,前者的论述为后者的记叙做铺垫。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里程碑,是五部长篇小说的总序。它塑造了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地下室主人。作者论及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思时如是说:“我是在狱中的铺板上,在忧伤和自我瓦解的痛苦时刻思考它。”“在这部小说里,我将放进我的整个带血的心。”①作者呕心沥血,施展其艺术才华,以独特的叙述模式,精湛的说话技巧成功塑造了地下室人的鲜明形象。
一、开门见山的自我介绍与自我否定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②主人公开篇便袒露自己,话语中带着轻蔑的语调,全不在意的口吻,甚至还有着狂妄自大与莫名的骄傲。进一步阅读发现他只是一位继承远亲一笔财产后寓居地下室的退职八品文官,是个极其卑微的存在。他是小人物,也是另一种多余人,然而却也不是罕见的个别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俄国时代的大众化存在。
“小人物”并非第一次出现,普希金的《驿站长》,女儿冬妮娅被上尉“骗走”,老人孤苦伶仃直至凄凉死去;果戈里的《外套》与《狂人日记》;鲁迅的《狂人日记》主人公也与之有着极大相似性。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前后期作品中也有着这方面的塑造。比如《穷人》,年老的公务员玛卡尔·杰符什金和自幼失去双亲,寄人篱下又沦为妓女的瓦尔瓦拉相互关照相互爱怜,然而迫于经济条件,杰符什金无法救助她以至于她只好嫁给地主为妾。“我在这么一种不定的环境里,我没有前途,我猜不透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我真痛苦。”③书信里直白的自我表露,展现了小人物的悲哀。这些小人物身上都有着令人怜悯的因子,而作品也裹挟着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弥漫着深切的同情。而此处的《地下室手记》:“我曾是个心怀歹毒的官吏。我待人粗暴,并引以为乐。”④他似乎善于运用独特说话技巧,进行自我否定并“蓄意”触碰他人的“憎恶线”。
“多余人”也是俄国文学中的重要形象,莱蒙托夫笔下的彼乔林,他是到高加索服役的贵族青年军官,苦于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因而养成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再说,人间的欢乐与灾难同我这个因公出差、到处流浪的军官又有什么关系!”⑤再如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屠格涅夫笔下的拉夫列茨基。学者曾说地下室人就是俄国的哈姆雷特,不过这哈姆雷特不是丹麦王子,不是俄国的地主或贵族,而是一名俄国的穷官吏或平民知识分子,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地下室耗子,是非英雄。作者则塑造了变形的多余人,都是受欧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脱离俄国现实,脱离民族文化根基,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多余人是贵族,地下室人是个卑微的小人物,他“小”在经济实力薄弱,他花不起钱,也爱不起女子 ;他“小”在社会地位低下,他的仆人不敬畏他,他的同学们也藐视他。
1934年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高尔基称《地下室手记》主人公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社会堕落者的典型”,但其实这种人并非个别现象,甚至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代表了俄国那个年代多数人的状态,正如他自己说“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首先塑造了真正的俄罗斯大多数人,而且首先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和悲剧的一面。他们的悲剧就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丑恶……”“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因素,这个悲剧因素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如此,因而无需改好!它表现为内心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理想而又无法达到它。”
二、循环往复的争辩“怪圈”
他不是一个人在说,也不是在对一个人说,反而像在一个大会堂进行激烈的辩论,有“我”、“我们”,“你”、“你们”,“他们”,“实干家们”,人物众多,主人公不断地给自己设置情景,然后端坐在情境里,再把相关的人物全都拖进去,这便又彰显了他的说话艺术能力,善于“建立联系”。“要知道,那些善于为自己复仇以及一般善于保护自己的人——比如说,他们是怎么做到这点的呢?我们假定,他们陡然充满了复仇情绪,除了这种感情外,这时在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别的感情。这样的先生会像一头发狂的公牛似的,低下犄角,真本目标,除非前面有一堵墙才会使他止步。”诸如此类,他提出问题,用反问引起读者关注,又通过假设来设定回答情境,解决问题后又是假设,循环往复,滔滔不绝的论述是其独特的语言魅力,仿佛是一个没有结点的圆。在这个争论的怪圈中,虽然不时有别的声音,但是明显能感到一切都是地下室人在掌控话语权,甚至在思想上企图实施“霸权主义”,时时刻刻以自我意志与意愿为首要,以自我为中心。作者通过洋洋洒洒激情澎湃的论争,迫击炮般轰入脑中的话语,具体生动塑造了一个自我主义者,在复调中读者看到了他与其他意识以及其他思潮的冲突:他对“二二得四”不以为然,他厌恶自然规律与科学,“要是我由于某种原因根本就不喜欢这些自然规律和二二得四,这些自然规律和算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仍旧是不屑的狂妄气。他崇尚自由崇尚随心所欲,《被侮辱与损害的》中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论调,与地下室人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相呼应,杜勃罗留波夫看到:对备受折磨和被扭曲的人们的“疼惜”是作家陀氏的天性,而其艺术功绩在于揭示了这些人们心灵深处“对人的本性的生动的、从来没有被磨灭的企求和渴望。”⑥作者利用复调艺术手法,不是为了代表自己的思想主张,而是试图利用多个传声筒让更多人说话,让这些人的思想在论争中得以体现,因而展现一个思维火花迸射的场面。整个复调手法仿佛打造了一部滑稽剧,而地下室人就是主角,他在自我意识中自我陶醉,“蹩脚的俏皮话:但是我偏不把他删除。我之所以写它,是因为我想这话一定很俏皮;可现在我自己也看出,我不过是可憎可厌地想借此炫耀一番而已——我故意不把它删除。”这是叙述中一特色,即不断地自我补充,在括号里进一步说明,使得主人公更加真实,使得他的思考与发言更加真实,因为没有人可能把所有的话说得圆满、无需更改,而这也进一步完善了主人公的形象,令读者更身临其境。
三、倾泻激情的话语流,汹涌澎湃的意识流
阅读《地下室手记》最深刻的感觉便是激情与冲击。读者被紧凑的而节奏感又极强的话语以及汹涌的意识冲击。读者从高强度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中认识到一个双重甚至多面的主人公形象:
其一,他自卑又狂妄,卑贱又虚荣。 正文开篇便进行“高傲的自我介绍,狂妄的自我叙述”,再如“你们大概会说,不值得同您这样的人打交道;既然这样,我也可以用同样的话回敬你们。我们在严肃地谈问题,既然你们不愿意对我惠予关注,我也不会低三下四地求你们。我有地下室。”他们话语中表现着极大的狂妄与不屑,甚至带有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问题在于我达到了目的,保持了尊严,一步都不让,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中使自己处于与他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我回得家来,感到大仇已报。我兴高采烈。我洋洋得意,唱着意大利咏叹调。”地下室主人出于无边的虚荣,对自己在涅瓦大街上给军官卑微地让路表示愤懑与无法忍受,为此专门预支薪水让自己“衣冠楚楚”去“被让路”,结果终于“勇敢”地闭着眼睛小小碰撞了一下军官,便小人得志激动不已。俄罗斯学者基尔波金指出,陀氏在这里描写的人们在大街上想让而碰撞的情节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一个插曲相关联。⑦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指出:“地下室”主人公更换外套领子的情节,可能是陀氏不知不觉从果戈里《外套》那里取材的。⑧而作者却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法,情节的重设,心理活动的层层递进,讥讽了一个虚荣的小人物。
其二,他渴望躲进龟壳与外界隔绝却又逢迎巴结,他憎恶身边的人却又惧怕他们。“我恨透了我们办公室的所有的人,从头一个到最后一个,而且所有的人我全瞧不起,可是与此同时我又似乎怕他们。”地下室主人将情感真切地直接地通过语言宣泄出来,不加修饰。正如他憎恶兹韦尔科夫甚至想要给他一记耳光,但是又敬畏他以至于甚至主动卑贱地表达歉意。主人公生活中农奴制瓦解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到的彼得堡中心城市,无法与世界决裂,因此地下室人还是重见天日了,并且思维的水龙头放开了。作者借此展现了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状态缩影。
其三,明知堕落且厌恶淫乱却自甘堕落,向往美与崇高行事下贱。“如果让我挑专业的话:我非挑懒虫和酒囊饭袋不可。”再如聚会后借钱去了青楼,他憎恶这样的糜烂,但是却放任自己干着丑陋的事情。主人公咆哮着在思想里暴露自己的内心冲突。 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欧,作者亲眼看到理性王国并没有带来普遍幸福,启蒙主义—理性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并没有作为普遍的道德观念为人接受,相反,百万富翁为所欲为,饥饿的灵魂在杜松子酒和堕落中寻求解脱。干着卑贱的事情也企图为自己辩驳,“我这时的胆怯并不是因为胆小,而是出于无边的虚荣” “‘我是喝醉了酒才到这儿来的。我急于为自己辩白”。企图与低贱行为划开界限,带有诡辩和狡辩意味。
四、 面向大众的演说
虽然整部小说基本都是独白,但在这部作品中地下室主人不是一个人,他有很多的“话友”和听众,他无所顾忌地大方地展示心理,并不停地为自己补充说明。“常常,在某个极其恶劣的彼得堡之夜,回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强烈地意识到,瞧,我今天又干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且既然做了,也就无法挽回了——这时候我竟会感到一种隐蔽的、不正常的、卑鄙的、莫大的乐趣,然而内心里,秘密地,又会用牙齿为此而咬自己,拼命地咬,用锯锯,慢慢折磨自己,以致这痛苦终于变成一种可耻的而又可诅咒的甜蜜,最后又变成一种显而易见的极大乐趣!”读者看到的便是病态畸形的心理。“如果有人打我一记耳光,我甚至会引以为乐” 小说主人公多次表达希望被扔出窗外,希望被打的想法,深刻揭示了他变态的受虐心理。作者在其“演说”中捕捉人物电光火石般的微妙心理,歇斯底里病态心理以及疯狂露骨的剖析,并将一切以话语的艺术体现,揭示了时代背景下迷惘的一代的畸形心理。 如叔本华所说,“痛苦和无聊之间拼命自我折磨并从中获得快慰的情绪。”“果戈里主要是社会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诗人。”⑨他自己却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描绘人的灵魂的全部深处。”别林斯基是毫不掩饰的描写真实,反映现实的真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用夸张、怪诞、幻想等手法来反映生活中离奇的现象,他注重本质的真实,认为虚幻的现实主义更能反映现实的本质。
同样的社会背景下,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怎么办》传播了正能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描写黑暗,直抵人心,“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不由想起《红高粱》里的描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⑩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年轻才华的全部精力和新鲜性着手分析使他震惊的我们可怜的现实的畸形现象,并在这种分析中善于表达自己高度人道的理想。作者通过精湛的说话艺术,独特的叙述方式,成功塑造了地下室人鲜明的形象,成为他笔下一颗珠宝,凝聚了他创作的艺术,在整个俄国文学时代甚至当今文坛都有着其重要作用和艺术价值。
注释
① 陈燊.书信集(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307.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M].臧仲伦,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3.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M].文颖,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6.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M].臧仲伦,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3.
⑤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M].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44.
⑥ 俄罗斯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M].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42-65.
⑦ 基尔波金.6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M].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66:513-514.
⑧ 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卷[M].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337.
⑨ 瓦列里安·迈科夫.略论1846年的俄国文学[M].1847.
⑩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
参考文献
[1]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M].臧仲伦,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2] 陈燊.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3] 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 陈燊.书信集(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5]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M].文颖,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6]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M].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 俄罗斯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M].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
[8] 基尔波金.6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M].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66.
[9] 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卷[M].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
[10] 瓦列里安·迈科夫.略论1846年的俄国文学[M].1847.
[11]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