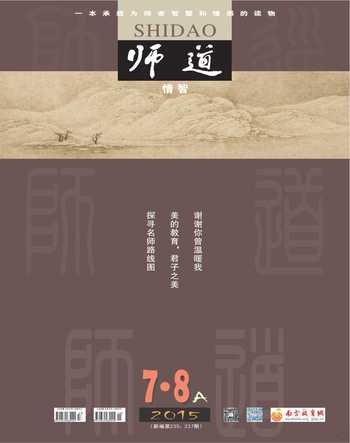他时刻追随内心的掌灯时分
何书锋
王开岭先生在《精神明亮的人》一书的《后记》中提到,多年前他做深夜节目《社会记录》时,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确保和自己的内心对话。他认为,“深夜是内心的掌灯时分,是灵魂纷纷出动的时候。相反,白天,灵魂在呼呼睡觉。一个深夜节目,若顾不上灵魂,就没了意义。”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事教育教学具体工作的时候,教师需要生命在场、灵魂出动。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听命于内心理性的呼唤,珍视自身独特的生命感受,和世俗的教育效益乃个人的“成长规划”等局于一域的利益算计保持适度的距离。
周奎英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在乎心灵感受、拥有教育自觉的理想主义者。二十多年的从教生涯让他形成了清晰的自我图像,他的生命底色愈加厚重,他在自己唯一可以站立的地方打量教育、审视教育。他的教育有着深刻的“我”的印痕,他时刻追随自己内心的掌灯时分。在他看来,没有教育的理想和信念、没有专业判断与坚守品性的教育同样地没有灵魂、没有意义。
27年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来到江苏省新沂市时集小学任教的时候,周奎英和其他青年教师一样有着“做一名好教师”的善良而美好的愿望。他虚心接受身边老教师、优秀教师的提点,努力完成学校布置的工作任务,致力于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考试中胜出……他像其他“有事业心”(学校领导语)的教师一样,想方设法提高自己教学和班主任管理的绩效。为此,他曾根据自己的预判,让学生以背诵范文的方式写“好”作文,提高语文考试的成绩;也曾以反复排演过的主题班会应对学校领导的检查,并获得“好评”……他似乎比别人更会“灵机一动”。如果按照这样的路径走下去的话,他会成为学校里的“优秀教师”,能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走上“教而优则仕”的道路也未可知。他在懵懵懂懂的初为人师的岁月里,凭着一股原始的冲力,竟然误打误撞地收获了些许“成就感”。
学习与反思让周奎英怀疑当初自己教育教学实践的合理性,并逐渐否定了自己的一些做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教师需要终身学习”远没有今天这么必须和为教师所重视,但是周奎英已开始了专业阅读——主要是阅读自行订阅的《江苏教育》《小学语文教学》等几种教育杂志上的文章。如果说通过读几本杂志来进行学习算是稀松平常的话,那么周奎英卓异于其他老师的,就是他善于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善于反求诸已、反躬自问,他有一颗明敏的、知耻而后勇的心。在和书本上的、身边的优秀教师无数次的对话之后,他把“真实”当作自己的职业灵魂,开始放任自己和环境之间存在着的抵牾或者说是冲突,他不再奢望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与他人达成哪怕是表面上的和解与平衡,他往往在任何一件可能的大事小事上拒绝领受惯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他以近乎决绝的态度否定自身业已确认的不当做法。
“好教师”的梦已至尽头,疏离由此开始,境遇随之江河日下……教育要做的本应是践行常识,但在一些学校和教师已成为应试教学坚定拥护者的时代,坚持思想自由、人格独立还是比较难的。上公开课的时候周奎英试图把它上成家常课,因而不在其他班级试上或在本班级预演,有时课堂师生的思维“断路”甚至出现教师被“挂”在黑板上或学生冷场、百思不得其解的状况,他觉得这很正常,课堂上应该呈现的就是真实的思维过程,思维训练、思维能力的培养,未必需要一种悦目的、顺畅的外部表现。教学无需遮遮掩掩,也无需过度粉饰……这样的尺度很难为外人道,更难以为外界所公允,所以一段时间过后,他的课堂教学自然而然地沦入了“不冒泡”者的行列。不惟如此,常态下的班级管理虽然师生关系融洽,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也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是由于羞于鼓噪一种亢奋的氛围,不愿将学生带入一种“荣誉至上”的心理胡同,周奎英的班级在量化评比活动中拿不到名次,卫生没人家搞得彻底,连学生拾到铅笔头、红领巾之类的好人好事也比人家“涌现”得少……慢慢地,曾经的“优秀班主任”成了明日黄花。周奎英庆幸自己的幡然醒悟,这些所谓的“失败”在他看来都是自己甘愿领受的结果。“成功”的路明晃晃地摆在那里,但他却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时常面临断崖的羊肠小路。
有一年周奎英担任小学毕业班的班主任,同时兼教语文。外校转来一些学生,要在毕业班上学。有的班主任老师几次三番地出试卷考学生,成绩好的成了香饽饽,成绩差的没人要。看到那些躲在墙边战战兢兢的孩子,周奎英说,你们都到我的班级里来吧,进我的班级不要考试。在其后的一年时间里,由于这几个后进生的原因,一直到毕业考试他班的总成绩都比平行班级低了几分——这很关键,在当时的语境下,成绩低了班级管理也很难受到肯定,一切荣誉将挥手自兹去。周奎英在上一年可是因为教学成绩和班主任工作表现突出而“留守”毕业班的呀,现在,等于自寻“滑铁卢”。但他不后悔,他说:“反正孩子一定得上学的。我最看不下的,就是孩子无助的眼神。”“在笼子里的鸟儿会奇怪地打量一只飞翔的鸟儿。”周奎英自言他一直在逃离那些华美的“笼子”,他知道最深的奴役在人的内心。他希望自己的教育作为能够经得起光阴测试和道义检验,而不是仅仅为了取得“成绩”、成“名”成“家”。
一个人只有在与他所处的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才能建立和维持自己的自我观。周奎英在脱离功利牵绊的日子里,成了教育的切已体察者和冷静思索者。如果说随着学习型社会的逐步建立,很多年轻的教师都有了新锐的思考、得体的表达的话,那么周奎英的思考和表达更贴近教育现实,更显得必要和“非我莫属”。现实中的周奎英是很反对补课、拖堂之类的占用师生休息时间的做法的——即使临近考试,他也不会组织学生中午“加课”;即使是上公开课,哪怕教学任务没有完成,下课铃一响,他也赶紧“打烊”。
曾有一段时间,他所在的学校为了迎接上级主管部门的“质量评估”,一些班级“自觉”行动起来了:要求学生提前半小时到校,上一节早自习之前的“早自习”,学校及时表扬了有关的班主任老师,盛赞了他们的“责任心”。随即,大多数班级都坐不住了,他们群起跟风而且哄抬物价般地把师生到校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一个小时。面对这种现象,周奎英忧心忡忡,他认为这是一种缺乏规则意识的表现,代表的是传统的、落后的教育观,与现代教育的要求相去甚远,同样也属于“不守纪律”之列。他深情地写道:“一个优秀教师的教育史应该是他的幸福生活史。学校管理上的人道主义即在于珍惜师生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和幸福。笔者衷心地希望管理者能够站在一个理性而客观的高度上,既引导教师科学地发展,走专业化发展之路,也引导他们健康积极地生活,照顾好自己、家人;既成就他人,也成就自己;既辛苦,也快乐……”只要看看我们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应试风潮,想想教师单调而逼仄的生存空间,想想他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感受,我们就会庆幸幸而有这样的声音在呢喃。周奎英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教育实践辩护,他也是在为常态的教育生活找寻依据——这样的木铎金声我们闻过几回?难道教师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奉献”?教师可不可以作为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和示范者而存在?
周奎英对教师的境界、教育的真谛、管理的品格等进行了大量的自觉思考,围绕教育家的问题、教育信仰、教师生活情趣、教师的心理调适等方面的问题等作过诸多论述。他的话语中到处都是自己的影子,到处都是自己曾经的生活轨迹。他反复强调教育常识,倡导教师忠于教育理想、坚守教育良知。在他心中,每一个教师都是无以替代的,都是自己教育人格的培植者,都是自己灵魂的不二言说者。教育常识一旦形成并融入教师生命,进入教师生命的年轮,那么没有任何力量会比它强大,就像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教育的一切将因此葱葱郁郁,一片葳蕤。
他曾这样表达对教师成为“言说者”的期望:“‘清鸣(他把教师不加粉饰、恣意自如的言说称之为‘清鸣)是每位教师无法让与的权利……在无需故弄玄虚,无需哗众取宠的完全由个人意志主宰的世界里,教育常识往往成了被屡屡确认的主题……对于教师队伍的普罗大众来说,我们的贡献在于捍卫了教育常识,在于抗拒了教育的‘转基因过程。”经过多年教育生活的积淀,周奎英最终成就了他的职业直觉,以及思想之颖、性情之真——他一次次地、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冲击被扭曲的教育价值观,维护着教育的本真面貌。有这样怀有赤诚之心的教师存在,对于教育而言,是一种幸运。
一个人的胜利最终只能表现为精神上的胜利。周奎英是一个真切地看清世界、热爱教育、勇于担当的教师,他忍受、享受一个人在广漠的世界上独自行走的孤独,并在此过程中证悟自己的内心,确认自己的存在。这是真实的魅力,也是最美的人生。他须臾未曾离开过自己设定的“好教师”的悲壮梦想。他所理解的自由与幸福,无不发源于对教师人格“理想国”的孜孜追求,发源于自己内心的掌灯时分。
(作者单位:江苏新沂市双塘中心小学)
责任编辑 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