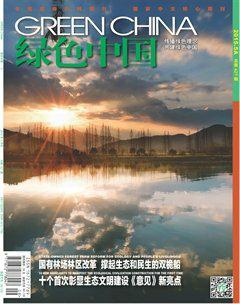我和我的宽和茶园

我是相声演员李宽,我的师父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先生。2014年4月,我创办的中国第一家相声连锁剧场——宽和茶园,在今年4月4日迎来了一周年生日。就像自己的孩子过生日一样,我对这个日子特别重视特别期待,今年3月28日下午两点,我们在永外曲艺会举行一周年庆典,4月4日在国图艺术中心与北京文艺广播21周年庆典合办相声专场。
想起来也挺冲动的,当初开办连锁相声店模式,就是想让每个人都能在家门口听相声。连锁真正的意义是把观众与剧场、观众与演员之间的障碍都解决了,堵车,停车,路途时间都把压力转给演员,观众就是个方便。
不要浅尝辄止
在相声界,我算是个小字辈。1986年生人,属虎,今年29岁。
三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我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在大杂院里被爷爷奶奶带大的,长大后知道,很多成功者都是这经历,尤其北京,胡同里的或者是部队大院的特多。
我的父亲李金祥,是相声名家唐杰忠的弟子,师大爷李建华、师叔巩汉林都很喜欢我,父亲也觉得我说相声最好。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父亲演出常把我带在身边。那时的我一丁点也不想说相声,对相声还特反感,自己心里闪过千万般带着颜色的理想,唯独没有相声这个自己最熟悉的声音。父爱重如山,当时压得喘不过气,认为这孩子肯定要说相声。
17岁那年,爸爸突然病危入院,收到了病危通知书后,家就塌了,一系列的问题袭扰而来。父亲把未成年的我托付给相声界的好大哥李金斗,意思是让我跟着李金斗学相声,有个人能疼我,看着病床上的父亲,我不忍把心中的想法说给父亲听。
没有激烈的纠结,我就从家里搬出来了,师父给我安排了住处,开始正式学艺,开始天天挨骂。三年的时间,师父不教我说相声,讲相声的历史、老一辈相声艺术家的故事还沾边,剩下的就是骂,不停的叨叨,没有一件事顺他的心,老说我。吃饭也挨说,睡觉晚不起床也挨说,我又没事我多睡会怎么了?我又没耽误事,有事我肯定早起啊。家里来人不站起来也挨说,我也不认识,我去干嘛啊?
慢慢地,我开始觉得,把相声传承下去是个有价值的事情,它是一门文化,也是一门学问。和恩师的师徒缘,我觉得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了我们爷俩的缘分,我原来是一个叛逆的孩子,不向任何人学习,师父像墨镜替我们遮挡太阳,又像魔镜让我们变得有魅力,更像一块穿衣镜,真实的认识自己和人生,让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师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我记得第一次在俱乐部说相声是2010年。但是那会儿自己理解比较局限,节目很火爆,时间很长,千头万绪说了一大堆不相干,没有受到表扬逐渐就不愿意演了。
后来一次跟师父吃饭,师父问我为何不演。我说能演。师父问能演为什么不演?于是师父主动为我捧哏,2012年在俱乐部演了十几场。师父一年内教了我十几个段子,让我的表演突飞猛进、焕然一新,走上了自己的艺术道路。
无论生活上、艺术上,师父都是言传身教。我们这些80后,晚上不睡,早晨不起,我以前一直是这样。凌晨4点多才睡,睡到下午才起床,每天就这样瞎混。根本不理解为何要早睡早起,现在明白了,我就不就此事在精神和肉体上剖析了。
师父有两句话对我影响最大,第一就是“排节目”这三个字,第二就是“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一开始不理解,觉得这些日常小事又不影响我,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只有你真正学了,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会。直到现在,我才懂得做艺先做人这个道理。这句话传了一百年、两百年,我从小就听,可是现在才明白它的意义。很多事情,只有你撞了南墙,才懂得回头。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哪个阶段都不能缺,正确的错误的都在前面等着你,没听说过谁的人生走的都是正确的道路。
不要一得自矜
师父李金斗把我带进了周末相声俱乐部的演出,还让我参与运营,学习了不少方法,积累了不少人脉,生活上也开始正常起来。一切都开始上了正轨,我那颗不安的躁动的心也逐渐稳定,开始琢磨相声了。而师父李金斗也开始对我放手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李金斗看着我在正确的路上成长觉得欣慰,觉得终于对老友李金祥有个交代了。
前两年,师父从周末相声俱乐部退休,我不仅在“说”的业务上学习着师父的“技术”,还跟着师父在相声市场上转悠,对相声这块市场有了自己的感悟,对相声的未来前景有了自己的看法。“现在的相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想,相声是最贴近生活最接地气的大众娱乐,京城小剧场相声挺多,经营好的却不多,作品首先得叫好又叫座,场子得开足够多,足够方便观众,形成规模优势,才会有自己的市场生存空间。我下定决心,提出开连锁相声场,振兴京味相声。都说艺高人胆大,但自己完全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带着十四五个兄弟忙活了一阵子,宽和茶园第一个相声剧场“永外曲艺会”正式开张。相声如何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在多元化的娱乐因素下生存?我脑洞大开,师父鼓励我们大胆创作和实践,不要怕失败。我师父永远都在改作品,像我们演的传统节目《黄鹤楼》,他每次演出都有不同的改变。现在相声市场对我们年轻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观众的笑点高了,光肤浅搞笑不行,还要说出真东西,才能稳坐市场。
同行不相轻。我联络了多个相声班社,请大家帮忙捧场。开业的时候曹云金刘云天师兄都来捧场,孟凡贵、王玥波、何云伟、石富宽、李国盛等师爷辈的名家,本门的师哥方清平、付强、刘颖等人每次来演出,更是分文不取,这让我非常感动,也让我对未来相声市场增加了信心。因为有一群这样的相声人。
宽和茶园的演出有个特点,演员们演完了自己的节目之后,都愿意在后台留一会儿,听听大家彼此的点评。我很自豪能有这样的氛围,这样的交流并不是每个相声场都有的,有一位说山东快书的演员,就是在这里听了大家的建议,将作品里的山东方言比例做了调整,又增加了时尚的笑料,结果在全国各地的演出效果都更好。
我由反感相声,到爱上说相声,经营相声,现在更把相声当成事业。每个人都有过年轻时的狂妄,都有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阶段,也都有过莫名自卑悲观的时候,我劝年轻人放慢脚步,摔跟头也是经验,不枉来世上走一遭,走好自己的一生,要是再能干上有意义的事业,就是美好的一生。
我现在要抓紧时间打造北京和全国的相声管理团队,不辜负父亲和师父的希望,这也是我的责任。我更多的想法是做一个单纯的相声小演员,把我更多的想法融入到我的作品,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我的梦想……
我上您家门口说相声
创办宽和茶园,首先来到了社区。我找到东城区永外社区。社区的陈卫兵主任提醒我,到社区演出是走基层,每场演出都会很辛苦,而且你们的经济收入也要大打折扣。我表示:“我们是年轻人,就愿意多奉献、多演出,愿意把演出送到喜欢相声的观众中去。”最终,陈主任被我的真诚打动,把管村社区活动站提供给宽和曲艺会作为平台。2014年3月29日,“永外宽和曲艺会”在永外管村社区活动中心正式开张,成为宽和茶园在北京的第一家分号。
首演当日,李国盛、方清平、何云伟、付强、李金祥等相声名家均到场助阵演出。李金斗也是一有时间就会到宽和茶园演出,为我们助阵,分文不取。石富宽、侯耀华、孟凡贵、王文林、徐德亮、曹云金等名演员也都来过宽和茶园为我们这些年轻人加油。
社区提供给宽和茶园场地,虽然不豪华但很有氛围,大概可以容纳150名观众。为了回报社区的支持,大家经过认真讨论后,都同意不以此挣钱。很快,宽和茶园就宣布,10块钱听一场相声,永远不涨价。
今年3月28日下午,北京东城区永外街道管村三站合一文化活动室内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不时传出阵阵叫好声、喝彩声。我们在这里正在举办宽和茶园成立一周年相声专场晚会。
像这样的亲民、惠民、利民的演出,宽和茶园在这里已经坚持演出了一年,每个周六的下午14点到16点,我和宽和茶园的演员们都会在永外社区演出。
“北京人都有曲艺情怀,”在永外曲艺会上,我发现很多六十多岁甚至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来看演出,有的是夫妻俩一块来,看他们坐在一起开怀大笑,很温馨。
如今,我已在京城开办了四家宽和茶园分店,在全国开了十几家相声“连锁店”。我们还会开更多的剧场,方便住在社区的居民,让大伙儿就近在家门口听相声。
“宽和”两字的来历,除了与我的名字有关以外,我在最初的想象中,这里应该是一个24小时营业的茶楼,有演出的时候观众买票免费喝茶,或者买茶免费听相声;没有演出的时候,可以看书、聊天。在这个休闲的地方,可以找到安静与平和。
我们不叫宽和相声队,不叫宽和社,也不叫宽和俱乐部,我们叫宽和茶园,是一个开放式平台,茶园吗,随便来,而不是艺术一言堂。只要具有专业技术的演员观众喜欢,我们就欢迎,我们就鼓励。宽和宽和,以宽得和。
(责编:张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