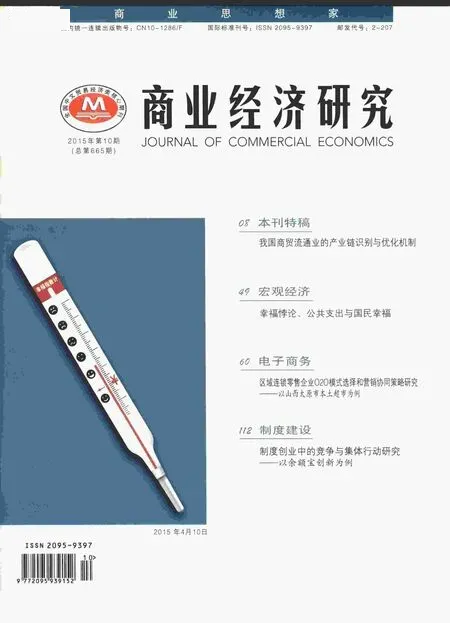幸福悖论、公共支出与国民幸福
■ 王 健 副教授 郭 靓(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430074)
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3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我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3600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56万亿,年均增速达9.8%,比世界同期平均增长水平高出近7个百分点,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国民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活富足的同时,逐渐加快的生活节奏,随之而来的各种压力,使得“幸福”成为了我国居民当今最为主要的诉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布的《2013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我国仅列第93位,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的近3轮调查数据亦表明,我国国民幸福得分依次为2.13、2.06、2.00分,呈现出下降趋势。可见我国也未能逃脱美国经济学家Easterlin于1974年提出的“幸福悖论’,即居民的幸福感并未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提高。
“幸福”二字,不仅是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宗旨所在,更是如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为提升国民幸福,近年来,众多省市各级政府将其纳入施政目标,据统计,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把提高国民幸福感作为其十二五建设最重要的目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积极主动的调节国民幸福,公共支出作为其政策取向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较之税收而言,弹性更大,调节方式更为直接有效,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我国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实证结果是否表明政府作为对国民幸福的提升有显著作用?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由2001年的19.6%逐年上升至2012年的24.3%,其规模是否越大越好?再者,公共支出中各类支出所起作用是否相同?哪些支出起主导作用?为这些问题找到经验证据,即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相关文献综述
国民幸福(Happiness),又称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学界对其的研究早先集中于社会学、心理学,而40年前美国经济学家Easterlin关于幸福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先驱性论文发现居民的幸福感并未随着一国经济增长而相应提高这一“幸福悖论”,颠覆了以往经济学家们的效用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的传统认知,引发了其极大的研究兴趣。
对于“幸福悖论”的解答,大多数学者认为除了收入影响传统效用函数之外,可能存在其他遗漏变量。具体而言微观层面影响因素有:性别、年龄、健康、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相对收入等,Paul Dolan et al.(2008)等对此有系统的描述,认为女性、已婚人士、受教育程度更高者以及高收入者自评的幸福感更高,并且年龄与幸福感的关系呈现出U型曲线。宏观层面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变动、收入不平等、失业和通胀。如Sanfey和Teksoz(2007)的研究发现人均GDP对于国民幸福的影响为正,基尼系数的影响为负。
公共支出作为解决“幸福悖论”的手段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在理论上,黄有光(Yew-Kwang,Ng,2003,2008)认为公共支出的来源是政府的强制性税收,以此来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因而能够将竞争激烈的私人消费转移至几乎人人共享的公共支出,降低了居民之间由于攀比效应所带来的幸福损失。Ed Diener等(2009)也证实,政府若能清楚了解地方居民的偏好,那么增加公共支出则能够提升国民幸福,其原因在于能降低居民的谨慎性储蓄动机,从而增加居民的主动消费倾向,使其计划的未来消费转变为当期的现实消费。更多的研究见于实证分析。Bjornskov et al.(2007)的研究显示政府支出与国民幸福负相关,其原因在于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大,意味着税收的相应增加,而税收是令人讨厌的东西。Ram(2009)运用包括转型经济体、发达国家、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145个国家的大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府支出与国民幸福呈显著正相关。Lena等(2009)的研究发现转轨经济体的政府支出对于国民幸福的影响呈非线性。即政府支出对于国民幸福影响存在一阈值,在达到这一阈值之前,作用为正。Zohal Hessami(2010)对1990-2000年间12个欧洲国家的居民进行调查,发现政府支出对于国民幸福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就公共支出各构成而言,Radcliffe(2001)通过对跨国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社会福利支出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显著为正。Di Tella(2006)对欧盟国家的政府失业救助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到,政府失业救助有利于系统地提高社会平均幸福水平。
国内学者对于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鲁元平和张克中(2010)发现由医疗、教育和社保支出构成的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为正,其原因在于能增加农民消费。其中,起主要作用为医疗、教育以及社保支出。谢舜等(2012)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基建支出对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科教文卫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于国民幸福有显著的正效应。相对而言,国内对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较少有文献进行系统的论述与分析,本文旨在对其进行分析,以期得到有意义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表1 国民幸福规模的回归结果
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
参考Di Tella等(2003)的相关研究,本文采用有序概率模型来进行分析,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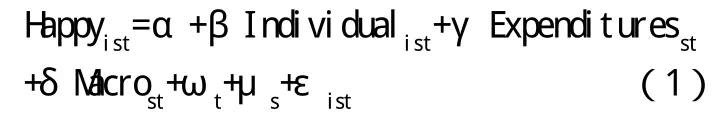
在模型(1)中,解释变量Individualist表示s省t年第i个被调查对象的微观经济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自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级状况;Expendituresst既表示s省t年的公共支出规模占该省GDP比重,也表示公共支出子类别规模比重;矢量Macrost表示对国民幸福有影响的宏观经济变量,其中s省t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以该省人均GDP取自然对数表示,还包括s省t年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另外,模型通过设定省际虚拟变量μs和时间虚拟变量ωt来控制省际和时间固定效应。
被解释变量Happyist表示s省t年第i个被调查对象的幸福感。其值取决于受访者对于问题“总的来说,你认为你自己非常幸福、比较幸福、比较不幸福还是不幸福?”(回答“不知道”以及“无回答”的少量受访者数据已剔除)的回答,受访者要求从数字1至4之间进行选择,越大的数字显示了越高的幸福感水平。
在模型(1)中,假定εist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因而只要其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则最大似然法估计出来的参数将为一致估计量。
(二)数据来源
本文幸福感数据取自世界价值观调查2001、2007及2012年的中国部分,其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实施。利用GPA/GIS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以村/居委会的户籍资料随机抽取18-70岁的人作为受访对象进行入户访问,调查范围涉及我国24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得到样本1000份、2015份和2300份。剔除无效数据后,本文选用样本数据分别为894份、1536份、2030份,合计4460份。宏观经济变量中各省市人均GDP、通胀率以及失业率数据通过2002年、2008年以及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于公共支出规模的回归结果
表1列出了模型(1)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其中Model 1a 为仅含个体特征变量的基准估计模型,Model 2a 至Model 5a为在其基础上逐步增加或替换宏观经济变量。
Model 1a 中的微观控制变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显著的,其符号与本文预期相一致。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年龄以及年龄的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分别显著为负与为正,意味着我国居民的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先下降而后上升。男性的幸福感显著低于女性。自评相对收入等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幸福感更多的源自于将自己的收入与他人的收入所进行的比较。至于婚姻状况,从模型中的边际效应可以看出,已婚者自评幸福感水平为“非常幸福”的概率要比参照组单身者高出7.86%。另外,幸福感水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逐渐提升。失业者以及离开劳动力市场者报告其幸福感水平为“非常满意”的概率要比参照组在职者分别低22.61%和8.01%。
后续模型显示,人均GDP自然对数的回归系数为正却并不显著,表明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有积极作用,然而统计意义上的不显著,意味着居民的幸福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不明显,这一实证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存在“幸福悖论”。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幸福感是个人的一种主观感受,经济增长及其所引致的物质生活质量的提升只是幸福的部分内涵,并且幸福感的提升更多地取决于相对收入。而如今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个人财富极不均衡,分配格局亟待改善。第二,经济在粗放式增长的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城市人口过度密集,交通拥挤以及犯罪率上升,乡村大量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的负外部性,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惠及大多数居民的程度,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背离。
至于通胀率和失业率,其回归系数的符号与预期一致,表明通胀率和失业率的上升均会有损于国民幸福。其原因可能在于,通胀率的提升导致居民生活成本的相应增加,而失业率的提升既使得新增失业者幸福感水平降低,也会暗示在职者失业可能性增加,而求职者就业可能性减小。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宏观经济变量在各模型中呈现出稳健的一致性,并未对主要考察变量公共支出的结果产生太大影响。
Model 2a在Model 1a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共支出项(Government expenditures),Model 3a则控制了前述的宏观经济变量,结论具有稳健性。回归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公共支出规模对于国民幸福的影响为正,表明其对于促进国民幸福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该结论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共支出可以作为解决“幸福悖论”的一有效手段,这也与西方幸福经济学者对于公共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相吻合。关于公共支出的积极作用,其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我国经济长期粗放式增长,各种社会问题的日益凸显使得人们加大了对于诸如公共安全、环境保护、通常交通、医疗保障、以及教育等公共事业的需求。另外随着市场的不断放开,经济结构与所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复杂,政府维护社会秩序所做的工作随之递增。因而内在的要求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大。其次,公共支出的来源是政府的强制性税收,其中赚的多的多纳税,赚得少的少纳税,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性,并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把竞争激烈的私人消费转移至几乎人人共享的公共支出,相对功能较低,降低了居民之间由于攀比效应所带来的幸福损失。并且转移性支出也能在一定程度少减缓如今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趋势。

表2 国民幸福结构的回归结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Model 4a在引入公共支出平方项(Government expenditures2)后回归结果显示,公共支出(Government expenditures)项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公共支出平方(Government expenditures2)项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意味着公共支出对于国民幸福所呈现出的积极作用,在历经一特定拐点之后,会显现出负面作用,即公共支出以倒U型曲线的方式影响国民幸福,公共支出增加所带来的国民幸福提升的边际收益呈现出递减趋势,其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关于公共支出对于国民幸福的倒U型影响,笔者给出两点解释。首先,过大的公共支出规模必定要以较高的税收来负担,从而压缩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这必然导致国民对于幸福的感知下降。特别是在我国老龄化人口规模正逐步扩大,已令公共财政承担一定压力的情况下。据统计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从1982年的4991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2714万人,年均增加257.4万人;老年人口占比从4.9%增加到9.4%,年均增加0.15个百分点。其次,过大的公共支出规模意味着过大的政府规模,从而衍生过于庞大的行政机构以及过多的行政人员与行政管理费用,导致更多的寻租、腐败以及其他种种无效率的结果,从而进行资源错配,导致国民幸福下降。并且公共投资也会过多的挤出私人投资。
(二)基于公共支出结构的回归结果
国内外有关公共支出的分类并没有统一的规范,并且2007年以后我国公共支出分类出现较大变动,为保持研究的连贯性和数据的可比性,本文从公共支出的具体职能入手,依据其作用目标将其分为:管理支出、建设支出、保障支出和其他支出。
在Model 1b至Model 3b中本文将管理支出、建设支出和保障支出依次带入幸福感计量模型(1)中进行回归,并在Model 4b中对其进行综合考量。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给出宏观经济变量的回归结果,个体特征变量以及省份、年份虚拟变量均已控制,如表2所示。
单个类别支出项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管理支出(ME)项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建筑支出(CE)项系数符号为负,却并不显著,而保障支出(GE)项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通过对系数进行比较发现,保障支出对于国民幸福的促进作用大于管理支出。将这3类支出共同作为解释变量的Model 4b给出了相一致并且更为稳健的回归结果。这意味着公共支出对于国民幸福产生积极作用的最主要途径为保障支出,财政收入能通过投入到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当中或者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至居民手中来直接促进国民幸福的提升。并且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保障支出中的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支出所构成的亲贫式支出对于解决“幸福悖论”的作用最为明显,其原因在于亲贫式支出不仅有助于穷人脱贫,而且还有助于居民解决其生活中医疗以及教育等最为基本的问题。近年来,由于教育、医疗以及住房的不断市场化,以及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我国居民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大,成为压在我国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攀升的房价俨然成为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而看病难的体现一是高额的花费,二是医疗资源分布的极度不均。教育对于代际收入流动性,也就是动态公平至关重要,很多农二代、贫二代只能依靠教育鲤鱼跃龙门,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阻碍了很多人平等受教育机会。这便要求在转型阶段,政府当前应当重点投入民生性支出,彻底的缓解甚至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从根本上提升其幸福感。
另外,若没有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社会的有序与和谐,国民的基本生存都难以维持,又何来幸福可言?因而管理支出也起到了间接的正向作用。对于建设支出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建设支出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以及我国基本建设方面。其初始投入巨大,建设周期长,待其建成之后效益的显现更需要较为漫长的时间段,有明显的时滞存在,故当期的建设支出对于国民幸福的影响为负,然而从长期来看,建设支出对国民幸福的提升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1-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中国部分,采用有序概率模型,考察了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对于国民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存在“幸福悖论”现象,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民幸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联。公共支出的规模以倒U型曲线的方式影响国民幸福,其规模并非越大越好。第二,各类别支出的影响程度各异。保障支出是公共支出对于国民幸福产生积极作用的最为主要的途径,管理支出也起到了间接的正向作用,而建设支出由于其初始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效益的显现需经历较为漫长的时间段,故其对国民幸福影响为负。
基于上述结论,为解决我国所存在的“幸福悖论”,本文认为政府在公共支出方面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以公共财政的要求为导向,适度扩大公共支出规模以发挥其提升国民幸福的基础性作用,弥补贫富差距拉大所带来的幸福感落差。同时注意度的把握,并且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公共支出与税收压力。特别指出一点,目前我国某些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不断膨胀、隐性债务与或有债务日益积累,应保持现有规模、提高地方公共财政安全的同时,优化支出结构,强化支出管理,提高支出效率以及行政效率。
鉴于保障支出对于国民幸福的积极作用,政府应当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安排,通过多样化的支出形式以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进一步发挥公共财政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此外,考虑到建设支出对于国民幸福的影响存有较强的时滞性,政府可通过BOT(建设-运营-移交)、TOT(移交-运营-移交)等形式,将部分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化供给。还可通过道路、楼宇命名等公共声誉回报、间接经济回报,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以控制其投入比例,从而更有效的提升国民幸福指数,使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生活,实现中国梦。
1.Bjornskov,C.,Dreher,A. and Fischer,J.A.The Bigger the Better?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ize on Life Satisfaction around the World.Public Choice,2007,130(3-4)
2.Di Tella,R.and MacCulloch,R.Some Uses of Happiness Data in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6,20(1)
3.Easterlin R.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edited by P.A. David and M.W.Reder,Academic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74
4.Ed Diener,R. Lucas,U.Schimmack and J. Helliwell:Well-Being for Public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5.Lena male evi perovi.Subjective Economic Well-being in Transition Countries:Investigat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Macroeconomic Variables.Financial Theory and Practice,2008,32(4)
6.Ng,Y.K. Happiness Studies:Ways to Improve Comparability and Some 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Economic Record,2008,84(265)
7.Ram,R.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Additional Evidence from Large Cross-Country Samples. Public Choice,2009,138(3)
8.Sanfey,P and Teksoz,U.Does Transition Make You Happy?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07,15(4)
9.Zohal Hessami.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Europe and Its Impact on Well-Being. Kyklos,2010,63(3)
10.胡洪曙,鲁元平.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2(10)
11.鲁元平,张克中.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基于中国幸福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2010(11)
12.任海燕,傅红春.有序概率模型的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和幸福感研究[J].求索,2012(3)
13.谢舜,魏万青,周少君.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兼论“政府转型”[J].社会,2012(6)
14.徐映梅,夏伦.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