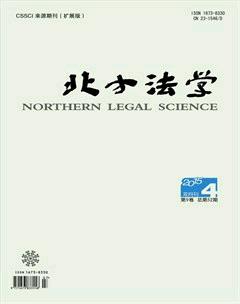行政诉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司法政治学的视角
卢超
摘要:新《行政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运作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的过程。从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政策文本出发,不难发现社会稳定压力与地方法制竞争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且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运作,也主要依赖于数字考核的指标控制而非行政法治的自我拘束。从中国行政诉讼模式变迁的大背景下观察,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根源自相同的法理,均旨在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而不再将合法性判断视为行政诉讼的核心议题。
关键词:行政诉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政策试验
中图分类号:D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4-0113-07
前言
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 。不仅如此,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的审议通过,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原本波澜不惊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一时间获得前所未有的曝光率与关注度。尽管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条款规定,但从地方司法实践中观察,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诉讼实践早已运行多年,并且各地规范性文件中就案件类型、出庭应诉程序、法律后果等诸多方面做出了细致规定,① 为中央统一的立法实践积累了大量司法经验。并且,从司法政治学的角度观察也不难发现,在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模式统摄下,社会稳定等外部压力引发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制度需求。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行政诉讼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协调和解、司法建议等制度装置上的近期拓展,均秉承了相同的司法政治原理。
一、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
从规范主义角度来看,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均没有任何一项具体条款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作出明确规定,②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是由地方政府与地方司法机关首创试验的。从司法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在当代中国司法领域中,地方法院被明示或者默许可以在正式立法之外进行司法政策的地方试验,这类地方试验在意识形态层面既需要保持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同时也允许地方司法实践中的差异创新,在政策试验过程中,地方之间往往会相互借鉴司法创新实践,通过政策模仿与学习来进一步推动司法政策的向前发展。③ 可以说,司法政策的地方试验模式是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重要机制,尤其在行政诉讼管辖权改革、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等制度改革过程中,④ 司法政策地方试验的改革模式早已屡见不鲜。
与之相比,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延续了地方政策试验的诸多共性,在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缺乏任何具体条文规定的前提下,各地出台了诸多规范性文件对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案件类型、应诉程序等事项作出殊异化的界定,体现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法治竞争态势。⑤ 在这一政策试验与地方竞争的过程中,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规定也相互模仿借鉴,逐步表现出趋同化的特征。⑥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政策试验的发起者绝大部分并非源自司法机关,而是由本级地方行政机关倡导推行的,并且该政策创设也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认可,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认真做好行政应诉工作,鼓励倡导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进一步要求“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主动出庭应诉”。可以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地方政策试验在得到最高行政机关的肯定之后,在全国进一步铺陈推广也就顺理成章。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政策尽管已在全国得到全面推广,但只有获得《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才算真正取得合法化的地位。然而《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中并没有涉及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内容,直到二审稿才增加一项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该项规定在三审稿中得以保留并获得最终通过。就此,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作为一种由地方自发主导的试验性政策,最终被法定化,这种变迁模式仍然依循了当代中国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承认的常规衍化路径。⑦
二、 各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案件类型化规定
通过对各地政府出台的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规范性文件梳理不难发现,并非所有的行政诉讼案件均要求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各地规范性文件中设定了诸多类型化限制,一般是要求社会影响重大、对于本单位行政活动将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才适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强制性规定,除此之外,各地通常均会要求本年度的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譬如《徐州市政府关于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的通知》(徐政发〔2007〕70号)第2条规定:“行政机关当年发生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应当出庭应诉。”而所谓的影响重大更多关涉的是社会稳定或者标的金额巨大事项,譬如《白山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第6条规定:“下列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应当出庭应诉: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的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社会影响重大、复杂的行政诉讼案件;涉案标的金额巨大的行政诉讼案件;对本单位行政执法活动将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诉讼案件。”再譬如《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全市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的通知(东府办〔2013〕141号)》中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首长应当出庭应诉:本机关当年发生的第一宗行政诉讼案件;案件复杂,可能对本机关行政执法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在本市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案件。”
对于社会稳定事项的重视,几乎在各地的规范性文件中均有重点强调,譬如《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行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制度的通知(盘政办发〔2013〕9号)》中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行政诉讼案件包括涉及征收补偿、社会保障、劳动权益的行政诉讼案件与重大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荆门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下列行政诉讼案件,行政首长应当出庭应诉:二十人以上集团诉讼、以及新闻媒体或者互联网关注等社会影响重大的行政诉讼案件;涉及土地或者房屋征收、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资源环境保护等行政诉讼案件。”
诸多地方对于社会稳定的事项类型划分非常详细,最为典型的譬如《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工作的通知(平政〔2013〕28号)》中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首长应当出庭应诉:因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和社会保障、资源环境保护等社会热点问题引发的群体性行政争议案件;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等重大公共安全的案件;涉及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群体性事件或者重大群体性上访的案件。”这一代表性条款基本上囊括了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触发机制的几类核心事项——农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社会保障政策、企业改制、环境污染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与公共抗争。这些社会稳定敏感事项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由于涉及到公共政策调整与重大利益分配问题,法院很难通过判决的方式解决这类“多中心议题”,⑧ 况且由这些事项触发的群体性事件与信访压力,司法系统亦无力承担,面对“社会稳定”这类一票否决的地方考核事项,⑨ 只有也必须通过地方行政首长出场的方式才能协商处理,⑩ 可以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可以视为中国行政诉讼“多中心司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B11
对于行政补偿、赔偿等涉及财政支付款项的案件,强制性的出庭应诉要求也极为常见,譬如《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通知(政字〔2014〕16号)》规定:“对于下列行政诉讼案件,被诉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或者房屋征收补偿的案件;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赔偿案件;造成公民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行政赔偿案件;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行政赔偿案件。”对于行政赔偿类型案件设定行政首长出庭的强制性要求,的确有助于法院实现协调化解行政纠纷,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尽管仍未承认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合法地位,但对于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予以了例外。B12因此,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规定可以视为行政赔偿调解条款的制度补充。
尽管从文本规范上观察,对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案件类型标准存在地区差异,各地规定繁简不一,但其实如果进一步抽丝剥茧,繁杂的类型化规定从本质上而言,均旨在实现法治主义的象征功能与实质纠纷解决功能。譬如对于年度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旁听的案件,B13 施以行政首
长出庭应诉的要求更多旨在表达一种法治进步的象征意义;而对于涉及社会稳定以及行政赔偿的案件,要求行政出庭的目的则在于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因为在地方首长负责制的现有体制下,只有行政首长亲自出庭参与诉讼,才有权力调整公共政策与行政赔偿数额,从而真正实现案件的协调和解。B14
三、社会稳定压力引发的行政诉讼变革需求
从上一章节关于案件类型化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各地条款规定中最为普遍的行政首长强制出庭类型便是威胁社会稳定、带有群体性事件特征的行政诉讼案件。对于涉及社会稳定的行政诉讼案件,设定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的强制性义务,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通过行政首长的出场促使案件的协调和解,而非单纯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由此在根源上实质性地化解行政纠纷。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观察,20世纪80年代经济分权之后,在以地方经济发展指标为竞争核心的发展型政府体制下,B15 地方政府的重心在于通过调动辖区内的各种资源推动经济增长,B16 以此满足地方官员晋升的根本需求。B17 这种分权竞争体制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地方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非经济指标的漠视,B18 而对于土地等经济性资源的过分攫取利用,B19 由此引发了官民冲突、阶层冲突与财富再分配不公等诸多难题。可以说,“中国社会抗争数量迅猛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追溯到国家功能在不同领域的收缩和扩张,实际上国家转型中发展的新职能、创制的新政策和推动的新项目无一不在催生新的社会抗争”。B20 就此可以断言,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运作机理是导致社会冲突困局的深层次根源。B21 具体来说,地方政府无论是推动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拆迁行为,还是推动市场化改革中的国企改制政策,抑或招商引资中对于环境污染类企业的吸纳,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模式是引发各类抗争行为的制度源头。实践观察中亦不难发现,当前社会不稳定因素与群体性事件往往由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社保政策调整、企业改制、环境议题等地方具体决策所诱发,B22 对于这类公共决策引发的行政诉讼事项,法院系统担负重大的维稳压力,且深嵌在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运作体制下,往往缺乏制度能力予以化解。
面对沉重的社会稳定压力,行政诉讼的制度模式亦发生了体系性变化。首先是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早已突破了《行政诉讼法》中“禁止调解”的规定,大量的群体性行政纠纷被法院通过“协调和解”的方式予以化解。B23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处理群体性行政案件的通知》中便强调:“对于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等领域的群体性行政纠纷,各地法院尽可能通过协调方式予以解决。”地方层面亦出台了大量有关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司法文件,其中均强调了社会稳定因素对行政审判模式的影响。《上海市高院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第8条第5款规定,“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企业改制、资源环保等矛盾容易激化,可能引起群体性利益冲突,或者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可能造成影响的”行政案件,法院可以进行协调。
除此之外,行政诉讼模式变革的另外一个特征则是司法建议的大量使用。司法建议在行政诉讼中最初仅仅是一项督促裁判履行的执行措施,B24 随着诉讼协调和解模式的不断深入,与之相配合,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被用于调整地方公共政策、修正规范性文件等制度目的,B25 协调和解而后发送司法建议的行政审判方式,甚至很大程度上有取代合法性审查的趋势。B26
本质上而言,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协调和解、司法建议源自同一制度谱系,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重要功能在于促成诉讼案件的实质性和解,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便明确提出“通过推动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为协调和解提供有效的沟通平台”。法院通过协调和解模式解决诉讼争议,并随后以司法建议的手段进行地方公共政策的调整,这种流水线化的制度安排深刻揭示了行政诉讼面对维稳压力的自身变革逻辑。各地颁布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中存在大量涉及司法建议与协调和解的条款,其中较为典型的条款譬如《马鞍山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办法》第12条规定:“行政首长应当积极配合人民法院依法组织的调解、和解工作,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第13条规定:“行政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各类司法建议,应当在30日内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类似条款同样可见《白山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第17条规定:“行政机关要加强同人民法院沟通和协调,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沟通交流行政审判与行政执法的情况,促进行政争议的妥善解决。”并在第13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应诉过程中发现的各类行政问题应当认真研究、及时整改;对人民法院的各类司法建议,应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及时书面报告人民法院。”《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通知》中规定:“政府法制办要建立完善与同级人民法院之间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分析行政诉讼案件受理、审判和执行情况,互通行政争议案件信息,研究讨论并为政府提供改进具体行政行为建议。”诸多地区对于不履行司法建议的行为还设定了相应的责任义务,譬如《固原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活动过程中,对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建议未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的,由监察部门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可以说,从本质上而言,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司法建议制度作为行政诉讼模式的内部谱系变革,B27 均源自社会稳定对于行政审判带来的外部压力,由此满足行政诉讼纠纷化解的功能性需求。从制度文本中也不难发现,行政诉讼这三类制度的具体条款之间存在诸多重复内容,譬如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中存在大量涉及司法建议与协调和解的条款,这也表明司法面对社会稳定的政治压力,法院对于行政诉讼模式所作出的体系化调整,这种制度调整亦可作为政治系统对法律系统存在侵蚀影响的例证。B28
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量化监督考核
绩效考核机制作为上级地方政府约束本辖区行政机关与下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手段,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B29 诸多学者将绩效考核所形成的政治束缚,视为压力型体制的一种表现形式。B30 通常来说,各地政府通过量化绩效考核手段形成的晋升压力,可以有效发挥激励与监督效应,尤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面对的是诸多繁杂的目标与指标,绩效考核是制定正确优先政策的重要指挥棒”。B31
各地出台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中几乎均存在相应的量化考核条款,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纳入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的考核范围,由此塑造一种科层监督压力,以确保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真正得以贯彻执行。譬如《江西省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通知(赣依法行政字〔2012〕2号)》规定:“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落实情况纳入依法行政考核内容,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年度出庭应诉案件数与年度被诉行政案件数的比例高低作为衡量该地区、该部门依法行政工作的考核指标之一。对连续两年达不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全省平均比例的,取消该行政机关当年度依法行政评优的资格。”同样,《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通知(甬政办〔2014〕123号)》规定:“市人民政府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和旁听审理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工作实际,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和旁听审理情况作为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体系考核指标之一。”《白山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第15条则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纳入政府年度绩效管理考评体系并量化分值。具体考评办法在年度考评方案中确定。”
作为这种绩效考核的具体化要求,各地出台的行政长官出庭应诉规定存在大量严格量化的数字指标,规定了行政机关负责人每年出庭的次数要求与比例控制,譬如《广州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暂行规定(穗府办〔2014〕46号)》第6条规定:“第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一年在5件以上的(含5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不得少于2件;20件以上的(含20件),不得少于3件;100件以上的(含100件),不得少于4件。”以及《固原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固政发〔2014〕35号)》第7条规定:“行政机关年度内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行政诉讼案件一年在5起以上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不得少于2起;10起以上的,不得少于3起。”这种政策模式是以行政诉讼年度总量为划分依据,以具体数字标准指明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的最低数量要求。另外一种政策模式则是直接概括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比例要求。譬如《上海市普陀区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和旁听审理工作规定(普府〔2014〕39号)》第3条规定:“行政机关当年度发生行政诉讼的,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次数原则上不少于被诉案件数的30%。”与之类似的还有《三门峡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定(三政办〔2013〕41号)》第7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比例不得低于本机关年度行政诉讼案件(包括一审和二审)总数的三分之一。”
从以上诸多地方出台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中不难看出,这些严格量化的出庭应诉指标自身存在的矛盾之处。无论是比例要求还是最低数量要求的量化规定,均无法从法理上去解释为何一部分案件适用出庭应诉,另一部分案件便可以不受该规定的束缚。另外,所谓行政机关年度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的强制性规定也缺乏法理依据,更多是一种形式主义与法制形象工程的表现。尽管如此,正如托马斯·海贝勒所言,“绩效考核同样亦是一种社会控制内部化、促使地方干部遵守国家价值观的拘束手段,上级政府可以通过绩效考核灌输塑造地方干部的价值观。”B32 尤其伴随十八届四中全会所做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要求“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亦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B33 在现有的地方晋升与行政发包体制下,B34只有借助中央的压力部署,地方政府负责人对于各类目标责任书之间的优先顺序才会重新定位,尤其是依法行政目标责任书才有可能从一类软指标,逐步衍化为一项带有强制拘束力的硬指标。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通过绩效考核模式来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也会存在过度形式主义、量化不合理等诸多弊端,但绩效考核手段的优势不仅体现在高度效率化特征,更为重要的作用则体现在,依法行政事项的绩效考核类型对于地方干部政绩价值观的重塑功能。B35
余论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殊政策工具,经历了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承认的生长过程,在这种特殊的司法政策试验中,地方层面通过反复的司法实践不断积累经验,为《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吸纳提供了制度运行模板。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结构的设计装置,必须置于宏观权力结构图景中观察,B36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地方发展型政府模式下,行政诉讼无法固守合法性审查这一核心议题,尤其面临社会稳定的重重压力,法院只能通过迫使行政首长出场的方式,借助协调和解与司法建议等司法装置,尽可能地修正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由此试图化解社会矛盾冲突。与行政审判体制的近期变化相一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运作逻辑反映出中国行政诉讼自身的特殊性,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制度创设自始就采取了一种司法政治的生长策略,B37而非严格依循法律的自洽逻辑,这是中国行政诉讼在夹缝中求突破的生存哲学,B38更是中国行政诉讼鲜活的制度实践样本。
Abstract:Upon the revis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the system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ial should appear as respondent in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have become a formal judicial instit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m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perspective, this system has evolved from experiments at local policy level to legislations at national leve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licy texts from various local areas,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social stability pressure and local legislative competition have played a vital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is system is more relied on index control for digital appraisal than self-restraint out of ruling of administrative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pattern evolution, the system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ial as respondent in court is based on the same jurisprudence as of coordination and mediation as well as judicial suggestions in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which aim to substantially resolve disputes rather than focus on justifiability review.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lawsuitchief executive official as respondent in courtpolicy experi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