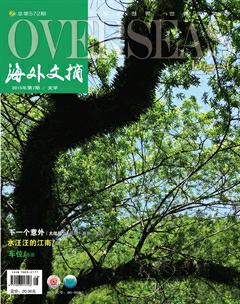十六岁,我走出了三峡
马识途
我的父亲
我们马家虽然号称书香世家,可是马家院子里的几十户后代,随着几代人的分家析产,大半已成为破落户。家道中落,住在马家院子里的男子汉,大半是只认得自己的名字,方便在按红手印时不至于按错。这些长年在田地里刨食的泥脚杆,只有在大院要举行什么仪式,又如过年祭祖,他们才从箱底翻出半新的蓝布长衫穿上,去面对书香之家的祖宗牌位。少数在私塾混过一两年,粗识文字的,能在场镇上看懂官家的告示和读懂契约文字,就算满意了。在这个大院里,真正能够继承马家书香门第的恐怕只有一人,那就是我的父亲马玉之。
我的父亲出生于前清光绪年间的1886年,小时候读过私塾,背过四书,谙习孔孟之道,后来上了新学的中学堂,除文化古典外,还读新学的《算术》、《格致》(格物致知的理化学科)和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基础的《修身》课,二十出头才毕业。
辛亥革命前后,父亲跟着一批激进分子,闹过一阵革命,大家去日本留学时,他却因家道贫寒不能出国,只捞到一个区督学,穿着长衫,夹个皮包,在乡下督学。后来从北京到省县都挂上五色旗,办起了议会,父亲去竞选,当上了县议会议员,由于他工作勤勉,被推举为议长,从此进入社会上层,成为有模有样的人物了。再后来,父亲被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四川善后督办(相当于省长)刘湘赏识,调他到重庆帮办军政训练班(有如今日的党校),刘湘任主任,父亲任副主任和训导。
父亲的积极性和能力为刘湘所赏识,于是被刘湘任命到当时土匪猖獗、豪强称霸的川西边僻小县洪雅去当县长,专治匪患。父亲在洪雅期间,软硬兼施,权谋诡计,基本上平了匪患,当地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万民伞。刘湘得知后,便把父亲调到让他头疼的家乡大邑县任县长。
和洪雅同样位居川西的大邑县,是个出产大军阀的地方,那里恶霸横行,兵匪一家。父亲带着一排人的手枪队前去上任,当地最大的恶霸刘文彩本想给父亲来个下马威,但一番较量,父亲占了上风,站稳了脚跟,深得刘湘赏识。
父亲正把大邑县治理得有了头绪,洪雅县的土匪又死灰复燃,民众上书刘湘,要求重调马玉之回洪雅治匪。于是父亲又回到了洪雅当县长。这一次,他亲自带兵上山剿匪,并且诱杀了当地的匪首,使洪雅县的治安得到恢复。他还在洪雅修路开渠,发展生产。他主持修的洪雅花溪渠,至今还在使用。前两年我到洪雅,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因为这条花渠,让他们旱涝保收。
蒋介石进军四川后,刘湘倒台,父亲也跟着垮台,只留下一块万民碑。抗战时期,偏安重庆的国民政府粮食部长,请父亲出山为重庆集运粮食,他干了一阵川西粮食专员,觉得难有成就,便告老还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我幼年的印象中,我的父亲有着颀长的身子和方正的脸,最显眼的,是他那看上去不知有多少光圈的深度近视眼镜和上嘴唇上那两撇显示出景从当时革命党人形象的八字胡。父亲经常坐在他书房的那张躺椅上,不是读古书就是读他一直订阅的天津《大公报》,还有就是捧起他那一直随身的白铜水烟袋,悠然自得咕咕地抽水烟。
那个水烟袋经常被我们兄弟擦得锃亮,那是我们能亲近有着严肃面孔的父亲的契机。
隔三岔五地,我们会争着抢着去擦这个水烟袋,然后装上烟丝,点上纸媒儿,把烟嘴送到父亲的嘴边,他抿着嘴将纸媒儿吹燃,含着水烟袋烟嘴,吮吸烟锅里点燃的烟丝,咕噜咕噜地享受抽烟的快乐。他高兴了,便会拍拍我们的脑袋,露出稀有的微笑,这就是对我们的奖赏。
但是这微笑会迅速退去,紧接着,就会听到他严厉的声音:“今天的书念完了没有?”这时,我们便会自觉地退到楼上我们的书房里去,读他让我们读的《纲鉴易知录》,以及我们喜欢看的《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小说,还有我更喜欢的《大公报》上的“小公园”副刊。
我不知道父亲从哪里讨来的那么多古圣先哲的格言,一串一串地背给我们听,教我们如何处世为人。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八个字:“胆大心细,智圆行方”。有时,父亲还要我们剪下他指定的《大公报》上的社论,要我们读给他听。
我们特别听到父亲的教诲是:“你们要自己出去闯,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因此,他有個母亲不以为然他却一直坚持的决定:在我们兄弟满了十六岁时,一律赶出三峡,到外面去闯荡,安身立命,绝对不准留在老家当游手好闲的“公爷”。我正是十六岁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走出三峡,到北平去上学的。
令我们悲痛不已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父亲乘木船去赶场,在石盘滩时船翻,落水而亡。
老辈子
我们的私塾设在马氏宗祠里。父亲叫人把大殿的一排格子窗大门取下来,大殿就成为一个十分敞亮的教室。大殿的正面靠墙有一个分成许多层和格的神龛,上面立着大小不一的我们马氏几辈祖宗的神主牌位。神龛的下面是一张神案,敬祖的香火供品就放在神案上。我们的课桌便靠在神案下。
大殿一头是老夫子的起居室,另一头的两间房,一间作为我们的宿舍,一间是已经看护宗祠不知多少年的老人的住房。因为这个老人辈分高,我们都叫他“老辈子”。私塾办在宗祠以后,老辈子就成为我们的伙夫,照管夫子和我们的生活。老辈子无事就坐在大殿门槛上,吸着旱烟,看我们读书。他不识字,却很关切地听我们的读书声,他说:“好,祖宗在上,天天陪着你们读书呢,哪个敢偷懒,看老辈祖宗怪罪你们哦!”
老辈子的脑子里,大概永远感觉到那些供着的祖宗牌位都是活着的,早晚烧香时,总是恭恭敬敬地拱着手,向祖宗牌位敬礼,并且口里还念念有词,对着这些牌位说:“您们要保佑这些后代子孙,好好读书,以后去考取功名哦。”他甚至有时会指名对着祖宗牌位说:“三房的二爷,你那个大孙子就坐在你下边读书呢,你看着点他。”
老辈子说的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听到感到有点可笑,可他却是真心诚意地和祖宗对话。而且他不仅和祖宗对话,也和他养的小动物对话。当我们听到他叫:“我叫你守在门口,你咋又溜到廊沿下来耍?”我们就知道那是他在教训那条未尽责的小狗。有时,他把鸡鸭打得乱飞,嘴里骂着:“你们这些背时的,砍脑壳的,又来偷吃了。”我们知道,一定是那些鸡鸭在偷吃他晒在石坝上的玉米粒子了。除了小动物,对宗祠院子里的花草树木,老辈子也是精心照料,好像它们都是花神树神似的。每逢过年,他都会在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鸡圈狗窝前以及宗祠大门上的门神前插上一炷香,甚至烧点纸钱。
老辈子对于没有生命的东西,也能当作活物对话。有一次,我看见他就着几粒盐黄豆就喝,一颗夹在手指上的黄豆不小心掉在了饭桌下,他弯腰去捡,嘴里说道:“你龟儿子的,我看你往哪儿跑!”他终于在凳子脚边“擒拿”住了那粒黄豆。“格老子的,我叫你跑!”他一边说着,把黄豆捡了起来,吹了一下灰便丢进了嘴里咬吃,还得意得很呢。宗祠未办私塾时,整个院子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他把这些动物植物乃至无生命的东西都当成说话的对象,想来是为了排解心中的寂寞吧。
赶考
1931年———当时没有这样的叫法,当时叫民国二十年———7月,我们下川东十四个县的七八百名初中毕业生按当时的规定,都集中到下川东军阀防区的首府万县去参加毕业会考。
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进了万县这不算很大的城市,却以为是进了大都会了,看什么东西都觉得稀奇。看见马路上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的自行车,惊呼“洋马儿,洋马儿!”奇怪,它只是一前一后两个轮子,怎么能飞跑而不倒?由于没见过电灯,以致晚上睡觉时想用嘴吹灭灯泡而莫奈何。一些乡下大户人家的子弟,说是来赶考,其实就是进城来“开洋荤”的。他们怀揣银元,到大商场去买新衣服和新鲜玩意儿,特别是那黑光锃亮的皮鞋。有同学买了穿在脚上,在街上踏得“叭叭”响,好不神气。我非常羡慕,也想买一双,谁知到商店一问,要五个大洋,那是够我一个多月的伙食费的,想到家里人的辛苦,我忍痛未敢买。不过想到晚上走夜路方便,我买了一个手电筒,拿在手头晃来晃去,很神气。但是后来到了大城市里,晚上走路都有路灯,那个电筒也就一直放着没用,白费了钱,让我深为失悔。
会考的日子到了。听说在下川东称霸的那位军阀王陵基很重视,要亲自担任主考官,要照过去考举人的规矩办。我们按规定时间来到开考的地方,那军阀王陵基果然坐在考棚外的长桌后,两旁站着点名的师爷,顺石梯而下,两边排列着提着手枪的卫队,甚是威严。
我们诚惶诚恐地列队站在距考棚几十级石梯下的街上,听候点名入场。遥望着“主考官”带领本城的军政头脑以及绅耆大佬在考棚前举行仪式,他在上面说了些什么,我们一点也听不清,但考生们谁也不敢出声。
仪式完成,开始点名。远远望去,“主考官”像审案子似的拿着点名簿叫名字,站在他旁边的师爷便跟着唱出这个名字,站两排石梯上的卫兵,一路吼着把名字传了下来。听到自己名字的考生大声回应:“到!”然后端着砚台握着毛笔,战战兢兢地低头循石梯而上。到“主考官”面前鞠躬行礼,等着师爷“验明正身”后,才得以进入考场。
我们坐在考场里,接着发下的试卷,答写起来。全场鸦静,连大气都不敢出,因为监考的不止有老师,还有提着手枪的卫兵。只要发现有谁交头接耳或作弊,卫兵便会用枪顶着拉出去,没收准考证,不准再参加会考。可以说,这次考试还真是过得硬的。
几场考试,题目虽有难度,但我都轻松交了卷,出考场后和成绩一直比较好的同学对了一下答案,自信是考得不错的,安心地等待着发榜了。
几天后,红纸榜单贴出来了,大家相约着去看榜。我们那个不起眼的农村中学,可是大大地出风头了,榜上会考合格的一百多名考生中,我们学校上榜的人数最多,占了约五分之一。而且前五名考生中,我们学校就占了四名。我的名字也排在了榜的前面,是第九名,这真是太高兴了。
回到旅馆,早有一串串送喜报的人上门来了。他们高举着印有金色贺词的红纸,大声唱喝着“恭喜×老爷高中红榜荣登×甲×名”之类的贺语,一阵鞭炮声后,不由分说地一手拉着让“老爷”们接贺词,另一只手自然是讨赏钱了。至于赏钱的多少,就看你这位“老爷”中得高不高,一般起码要给主报人一块银元,其余跟来的每人少不了一两串(一串是一千文铜钱,一块银元兑四串多钱)。对我们这些高中榜首的“老爷”,那更是道不完的喜,赏钱要的也高得多。有的阔气的给到十元之多,但给的少的还得挨报喜人咒骂。
通过会考的学子们学着老规矩,互称“同年”,相互登门拜贺。然后邀上同学朋友,到酒馆里开怀畅饮,有的甚至还合伙包有扬州姑娘侑酒的花船游江。我们没有钱包花船,就租了一条小船,带了些酒菜到船上。小船沿着河岸向长江上游划去,到了太白岩下,又顺流而下。船上学着古人那样,临风酹酒,细酌慢饮,吟诗作词。这次会考中的前几名同学当仁不让,即席吟诗赋词述怀抒愿,我也当场吟了一首古诗,现在还依稀记得其中几句:“乐莫乐兮旧相知,悲莫悲兮新别离,长江浩荡兮出三峡,燕赵驰骋兮何时归?”因为高兴,我破了家父立下的不准喝酒的禁令,放开大喝,以至沉醉如泥,竟不知何时回到的旅馆。
那一年,我满十六岁了。
走出三峡
遵照父亲“本家子弟十六岁必须出峡”的教诲,万县会考结束后,我约上两个要好的同学一同离开故乡,到古都北平去报考高中。我们三人都是在万县会考中取得很高名次的,颇有点得意,自以为至此走出三峡,就能安身立命,以天下为己任了。从那时我在过夔门时作过的一首名为《出峡》的诗———“辞亲负笈出夔关,三峡长风卷巨澜。此去燕京磨利剑,国仇不报誓不还”———中,就可见当年我们的少年气盛。其实致,我们对最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一无所知。若不是父亲托万县的朋友去“走关系”,给英国轮船上的二副“塞包袱”,只怕是我们连三张四等舱的轮船票都弄不到手,还会滞留万县,誤了北平高中的考期。
我们登上轮船,进入设在底层的四等舱。只见舱内密密地挤放着许多张上下铺的双人床。旅客爆满,一进去一股汗臭味扑鼻而来。如狼似虎的下江茶房,在高声斥骂,推推搡搡地在安排床位。那些茶房对我们这种看来有点身份的旅客,却穿着当时乡下时新的高领细腰窄袖长衫和千层底布鞋自鸣得意的样子,轻视地扁嘴斜眼相看,说着我们听不懂的下江话,大概是在嘲笑我们几个乡巴佬吧。
船快到汉口时,茶房开始叫旅客们收拾行李。茶房过来装着要替我们把行李提到船边去的样子,其实只是提了一下又放下,便伸手向我们讨小费。这时满船的茶房都出动来向旅客讨小费,大声嚷嚷的,不得开交。这哪里是讨,分明就是勒索。给一个银元他们嫌少,恶言恶语,最后在一个船上认识的旅客的说和下,每人又添了半块钱才算走脱。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拿钱买上船来做茶房的,外国老板根本不给他们开工资。
我们这一路上北平,乘船、住店、坐火车,没有少挨敲,没有少受气,最后到了北平这所谓的首善之地,明明坐洋车只需两毛钱的路程,却被马车夫赶着大车拉着我们在城里转了好大一圈儿,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吧,才找到我在北平大学上学的舅舅的宿舍,还硬敲了我们大洋两块五。这时,我才稍稍知道了一点人情冷暖,世途险恶。
见着舅舅安顿下来后,舅舅问我们一路感受如何,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地说“行路难”。舅舅意味深长地说:“这以后的路,恐怕也不容易呢!”
北平启蒙
根据舅舅的建议,我们三人决定去报考当时小有名气的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经过万县会考的考验,我们三人都相当有信心,潜心复习功课,从容应对入学考试,终于都进入平大附中,成为该校的学生。
北平大学附属高中是一所新办的高中,校长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叫宗真甫,北平大学不少老师支持他,愿意到学校来兼课。宗校长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主张开放式教育。学校不用教育部统编的中学教科书,而是由授课老师自行选编,比如我们的语文课,是北平大学的一个教授来教的,他选印了许多时新的作家比如鲁迅等人的作品,也选一些古文和诗词。而我们的数理化教材,都是用的外国的英语教本。学校除开有英语课外,还开有法语、德语课,最特别的是,还专门办了一个俄语班,在当时仇俄清共的形势下,宗校长却顶着风办这么一个俄文班,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当时,北平的一般中学,都是男女分校的,但平大附中却是男女合校,并且鼓励男女同学自由交往。课间休息时间,宗校长叫老师把同学赶出教室,做柔软体操或打排球,还特别要叫女同学出来参加。后来听说有些同学组织跳交际舞,男女同学都可参加,学校也不干涉。
让我们学校最出彩的是当时排演一部叫《白茶》的俄国话剧,剧中有男角女角接吻的情节。有人赞成照剧本演出,有人反对,决定不了。宗校长竟然同意按原剧本演出,可以出现接吻场面,不过折中了一点,就是让接吻的同学背对舞台相拥作接吻状。话剧在学校周年校庆时演出,经过《世界日报》等报纸一报道,一下子便轰动了北平,也招来遗老们的大声讨伐,说是有伤风化,宗校长对此置之不理。
宗校长认为在所有的自由中,言论自由是最根本的,学校提倡教学相长,允许学生争辩。学校不仅有自治会和班会办的壁报,还有三五个人办的同人的壁报,不仅只是议论教学事情,互相辩论一些学术见解,有的还旁敲侧击地议论起国事来。这很为一些人所侧目,但宗校长却以为这也是正常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
由于学校的民主、自由、开放,引起了北平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加上混在学校当锅炉工的特务的密报,引来了国民党宪兵三团的特务到学校抓进步学生。宗校长出面稳住特务,暗地里派人通知进步学生从学校不常开的后门逃走了。后来,北京大学召开抗日演讲会,我们学校也有一些同学参加,警察围抓了一大批人,其中就有我们学校七个学生。虽然这些被抓的学生经当时驻扎在北平的东北军的张学良将军下令全部放回,但我们学校更受到当局的重视,时不时以教育当局的名义,到学校来检查教材、课业和课外活动,包括壁报、唱歌、游艺等活动,指斥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终,这个新式学校被停办了。
我在北平大学附中虽然只学了二年,却是真正学到了东西。特别是数理化和英语学得很扎实,为我后来报考大学打下了基础。我听从老师的话,确立了工业救国的志愿。同时,又受到进步同学救国思想的感染,立志要抗日救国。这个高中和我读过的农村中学一样,为我启蒙,确定了人生道路。几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忘却这个中学,更难忘却这个校长。有一些我亲身经历的事,更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难忘。
逃亡上海
1933年初夏,日本侵略军日益咄咄逼人,在平津一带的日本兵又捣起乱来,不仅天津日租界的浪人冲出租界到处烧杀抢掠,日本驻军也出动演习,到处骚扰,北平的郊区成为日军的演习场所,日军的飞机可以随意飞临北平上空。在我们学校都能看到红膏药疤的飞机上日本飞行员伸出头瞭望。老师讲课的声音被飞机的轰鸣声淹没,师生呆眼相望,欲叫无声,欲哭无泪,北平竟然安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这时,北平的老百姓纷纷逃向南方,我们学校也提前学年考试,提前放假,听由学生自己安排,愿意离校的还发给学历证明书,以便转学。不少同学决定前往南方去上学,我和一个同乡同学二江亦决定一同前往上海,继续求学。上海一些学校比较好,那是我实现心中“工业救国”迷梦的首选之地。
但是当我们到北平东站去买票时,只见车站内外人头攒动,售票窗口南下的车票已告罄。想南下的人群根本不听车站工作人员的招呼,像潮水一般毫无秩序地涌进站台,拼命往车厢里挤。我们想到如果日本军队在天津捣乱,切断了津浦铁路,想逃难南下上海也不可能了,于是我和二江急忙赶回学校,只拿了些常用的衣被和几本教科书,提个小包,装了点干粮,又赶往车站。这时的车站,停在站台上的火车车厢里已人满为患,根本不要想再挤进去,一些人正在往车厢顶爬,我俩仗着年轻力壮,几下就爬了上去。在车厢拱顶上铺上毯子,坐了下来。
逃难的火车终于从北京东站开出了。虽然随着火车的开动,坐在车厢顶上摇来晃去,有点危险,但谁也顾不到这些了。坐在车厢顶上的人们密密地挤坐在一起,互相拉扯照应着,不致滚落下去。尤其是晚上,看到有人打盹兒,马上就会被他旁边的人叫醒,以免不慎掉下车摔死。
我蜷腿坐在车厢顶上,随着火车的摇晃,我插在长衫襟口上的钢笔被膝盖顶了出来,落在车顶上。这是一支真资格的派克金笔,是我省吃俭用一年多,又踌躇了好几个月才下决心买的,我视若珍宝,可以说,它是我南下上海所带东西中最贵重的一件了。钢笔掉落在车顶后,随着车厢的摇晃,逐渐顺着厢顶向边上滚去。我俯身伸手去抓,好不容易快要够到了,它又往边上滚去,我更伸长手去,一心想把钢笔抓住,完全忽略了安全。这时,幸好被二江和旁边一个同伴把我拉住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钢笔从车顶滚落下去,好生心痛。“你不要命了!”二江的厉喝,让我清醒,若不是二江他们拉住我,我可能会随着派克笔一起跌落到车下去,那时,只怕是我连心痛的机会都没有了。
第一次发表作品
我们终于乘火车平安地抵达上海。
上海的教育很发达,学校很多,我报考了当时在上海也算好学校的浦东中学,被录取到高中二年级做插班生。
浦东中学在上海浦东六里桥小镇,小桥流水,绿树掩映,一派田园风光。浦东中学是一个原是木匠后来成为上海建筑巨子的名叫杨斯盛的人创办的,聘请上海的名宿黄炎培为首任校长。这个学校出过不少名人和专家学者,像张闻天、范文澜、王淦昌等,听说连蒋经国也在这个学校读过。这个学校注重理科,数理化教材用英文原版,老师也用英文上课,当时的我正迷恋于工业救国,感到满意。
不过,我也喜欢语文,我入校写的第一篇作文就受语文课章老师看重。章老师是当时上海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以后,他对我的每一篇作文都细心修改,并且找我详加指点。他还叫我订由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我认真阅读,受益匪浅。
有一次,《中学生》杂志刊出征文启事,我很想去试一试,正犹豫间,章老师主动找我,要我参加这个征文竞赛。于是我写了一篇有关地方风光名为《万县》的文章给《中学生》寄去,竟然入选并在《中学生》上刊出,还收入他们编的文集中。当我突然收到六元钱的稿酬汇单时,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一篇短文章,居然得到可以抵得上我一个月伙食费的稿费。当然,这不是主要的。我窃喜的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转化成铅字出现在这样一份全国著名的刊物上。这是我发表的一篇作品。章老师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可以成为作家。但我告诉他,我的志向是将来当个工程师,实现自己工业救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