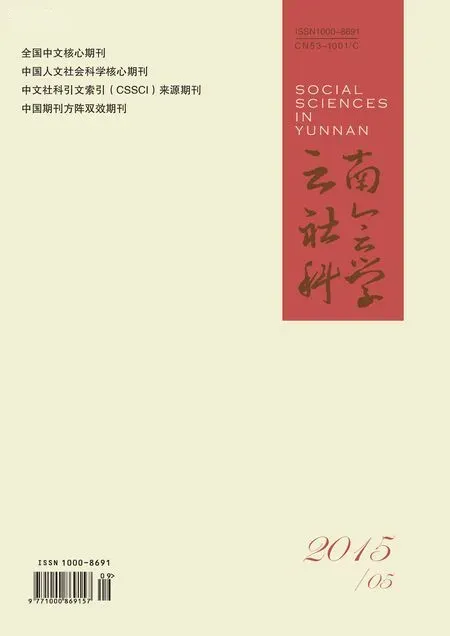“脏者”不婚:苗族关于村落秩序的文化隐喻
——云南省水富县三角村苗族“蒙”和“阿卯”支系个案研究
邵维庆
维克多·特纳认为,隐喻是发现“主观事件”的一个全新视角。*维克多﹒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刘珩、石毅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1页。Martin J.Gannon也启示我们,可以利用文化隐喻了解一个民族的主要文化特征。*Martin J.Gannon,Cultural Metaphors:Readings,Research Translations,and Commentary,Sage Publications Inc.,2000.文化隐喻方法作为一种理解文化的新途径,能够超越已有研究的局限,动态地关注国家或民族文化自相矛盾的本质和内部的价值观差异,扩展和深化对文化复杂本质的认知。本文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资料,聚焦苗族不同支系“不与‘脏者’通婚”民间话语的隐喻文本及其结构和功能指向,尝试将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引入到对苗族婚姻文化和族群关系的研究,以期拓展对苗族文化特征的动态关系把握,深化对苗族文化复杂性的认识。
从1917年开始,川黔滇3省11县的苗族陆续迁徙聚居而形成了现今地处水富县的三角苗族村。截至2011年,该村有588户2510人,其中苗族“蒙”*“蒙”,苗语西部方言川黔滇次方言苗族,自称Hmongb,当地汉族以及同村其他苗族支系他称为“白苗”或“白族”,本文用其自称的汉语音译“蒙”简称之。后文同。支系377户1639人,占全村总人口的65.3%;“阿卯”*“阿卯”,苗语西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苗族,自称At Hmaot,当地汉族以及同村其他苗族支系他称为“花苗”或“花族”,本文用其自称的汉语音译“阿卯”简称之。后文同。支系159户667人,占总人口的26.6%;汉族52户204人,占总人口的8.1%。清晰的族群边界,加之苗族两个支系和汉族总体聚居、少数杂居、点片状分布的空间居住格局,使村落中形成了“蒙”与“阿卯”、苗族与汉族两大族群关系。从迁入三角村到改革开放前的60余年间,同处一村的“蒙”和“阿卯”通过族群文化符号以及洁净与肮脏、竞争与位序、宗教与信仰等观念建构了区隔“他者”的婚姻偏见模式,与同村落的“他者”以文化偏见的外在形式保持其族群边界。
在此过程中,“蒙”和“阿卯”把日常生活中对污秽与肮脏和干净与卫生的主观感受映射到族际婚姻中,把通过身体体验获得的上-下、前-后等方位概念投射于婚配对象、婚姻生育、公共资源竞争等抽象概念上,并把不同支系互不通婚的民间话语映射到“我族”与同村“他者”具有价值观差异性和文化异质性的村落秩序中。由此,“蒙”和“阿卯”从日常生活体验、竞争与宗派地位和族群文化分类三个层面创制和实现了“不与‘脏者’通婚”文化叙事的实体隐喻、方位隐喻和结构隐喻。在现代化背景中,这种文化隐喻及其隐含的价值观念反过来又对村落的族群关系和社会秩序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脏者”的实体隐喻:基于生活体验的文化叙事
在与自然界的长期互动中,当人类从物的具体性中逐渐发展并获得抽象思维能力时,往往把具体事物的某些特征投射到抽象概念上,并借助表示具体事物的语言表达抽象的文化概念和分类系统,由此产生了实体隐喻。三角村苗族“蒙”和“阿卯”支系基于村落特定的生态环境、生存空间、族群关系和生活体验,创造了关于“脏者”的实体隐喻,对村落婚姻制度和族群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案例一:“蒙”对“阿卯”屋内外“鸡屎遍地”和“不用厕所”的叙事。说起自己的姐妹当年根本没想过嫁给“阿卯”,报告人马某某*访谈对象:马某某,“蒙”支系,男,52岁,道坪村民组,访谈时间:2010年10月。讲述了个中缘由:
我的一个姐两个妹都嫁给了白族(笔者注:指“蒙”支系,后同)。当时我的姐姐和妹妹也没有想过找过花族(笔者注:指“阿卯”支系,后同),主要是因为花族不怎么讲究卫生,你看三角坪头村民组他们住的那些房子,里里外外都是鸡屎。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后,两碗乡党委的人上来检查卫生,看到他们花族都不用厕所,解手就在房子边的坡上挖个坑坑当“厕所”,那些领导们就把他们骂惨了!他们主要就是不讲究卫生,白族就不想嫁给他们。
案例二:“蒙”对“阿卯”经常“不洗脚脸”和“穿脏衣服赶集”的讲述。报告人王某*访谈对象:王某某,“蒙”支系,女,71岁,道坪村民组,访谈时间:2010年10月。就曾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阿卯”卫生习俗方面的不满,并强调正是由于卫生习惯的差异,使两个支系间很难相互通婚:
花族办喜事那些我们一般都少有去,一般要关系特别好的才会去。花族嫁给我们白族的有极少数,但我们白族嫁给花族的我发现的还没有!你说这个社会不讲究呢,有些地方还是很讲究的,就拿“卫生”来说,他们“阿卯”就没得那么讲究,有些人经常脸脚都不洗啊!我们和他们结不结婚,跟勤快不勤快、语言通不通那些没得啥子关系,主要的问题就是卫生习惯方面的差别了。
报告人侯某某*访谈对象:侯某某,“蒙”支系,男,46岁,田坝村民组,访谈时间:2010年6月。也认为,“阿卯”的子女教育观念落后和卫生习惯差,是造成两个支系产业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也是“蒙”不愿与“阿卯”通婚的原因:
三角花族和白族在种养业方面差距呢,花族落后主要是在思想和卫生上面。我在桃子花族村民组那边看到一家人不让娃娃读书,我就批评教育他家人,他们说:“我娃娃不读书关你啥子事哦?”这就是思想的问题了。还有,他们很不讲卫生,比如说今天穿起脏衣服干农活,明天他还是穿起这些脏衣服去赶集,这就是个人素质问题了。我老父亲那会儿曾说过:“我们这个族不能灭,我们白族还是只能跟白族结婚,花族还是只能跟花族在一起”,原因就在这里。
案例三:“阿卯”支系认为“蒙”信仰端公*“端公”,川黔滇次方言苗语称“夺能”,是对某些通过阴传而非习得、具有“特异功能”,能诵读咒词、通灵画符、卜卦算命、为亡人指路、祈福求安,替病人治病消灾、驱鬼辟邪者的汉语称呼。“不干净”、“不吉利”。其实,村里苗族两个支系关于肮脏与干净、邪恶与吉利的评论和抱怨是双向的。“蒙”从先民那里继承了“端公”信仰、鬼神禁忌和祖先崇拜。“阿卯”则在迁入三角村之前的贵州威宁、赫章等地时就已皈依基督教新教循道公会,而且几乎全民信教。“蒙”和“阿卯”把两种不同的信仰深植于日常社会生活中,建构了其族际婚姻的行为边界。韩某*访谈对象:韩某某,“阿卯”支系,男,24岁,双房村民组,访谈时间:2010年6月。的看法代表了村里的“阿卯”基督教信众对“蒙”支系端公信仰污秽的基本看法:
我们信基督后,都不要鬼和神了,而且也不再信鬼、信神了。因为,他们那些鬼和神是不干净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吉利的。我从小信基督以后,最大的好处是自己的思想上开通了,对子女教育也开通了,可以接受更多的东西。读《圣经》本身就是学习,《圣经》里的东西开通得很,学习《圣经》后我们素质也就提高了。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蒙”支系基于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把“阿卯”支系的生活环境、厕所、穿衣等日常问题映射到婚姻生活和族群关系方面,将“鸡屎遍地”“不用厕所”和“穿脏衣服赶集”等行为视为他者处于某种另类和失序状态的标志。而同村的“阿卯”认为“蒙”的端公和鬼神信仰不干净和不吉利,把本支系“读《圣经》”看作是素质提高和思想开通的标志。这表明,“蒙”支系和“阿卯”支系基于对他者日常生活中的肮脏事件和不干净行为,创制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秩序的实体隐喻:洁净的人和事即为有序的、安全的和可以接纳的;肮脏的人和事即为危险的、污染性的和不能接触的。由此映射出对方处于失序和危险的状态,表达了他者与我完全不同的概念。
二、“脏者”的方位隐喻:基于竞争的族群文化“分类”
理性行为都离不开分类,文化隐喻同样是族群文化分类的副产品。“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和排斥关系的过程。”*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蒙”支系和“阿卯”支系正是在这个褒扬和肯定我族文化洁净、排斥和否定他者文化污秽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文化的分类和对族群位序的排列。更由于“污秽绝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事件,有污秽的地方必然存在一个系统”*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45页。,“蒙”支系和“阿卯”支系便在关于“脏者”实体隐喻的基础上,借助村落公共空间的族群资源竞争和族群位序争辩等事件,把日常生活叙事和情感体验升级成为对“脏者”的方位隐喻,从而把对“脏者”进行排斥和否定的行为实践,扩展为强化本族群文化优越感和重建村落秩序的一个意义系统。
G.Lakoff和M.Johnson曾强调,空间方位来源于人们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概念之一。*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Ltd.,London,1980.pp15-21.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族际互动中,“蒙”和“阿卯”把通过身体体验获得的上-下、前-后、高-低、中心-边缘等具体方位概念投射于社会地位、婚配对象、生育制度、历史传说等抽象概念上,进而借用带有方位词汇的民间话语来表达更为复杂、更为抽象的稀缺资源、村落竞争、族群认同等概念,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脏者”的方位隐喻及其由抽象概念构成的文化意义体系。
案例一:谁当一把手?谁当村委会主任?源域(source domain)为上-下域,目标域(target domain)为族群阶序。2010年初三角村两委换届选举,由于村里谁当主要领导会直接关系到扶贫款发放,安居房补助款下拨,吃低保、吃救济粮家户确定等事宜。更重要的是,谁当一把手还是村落权威和族群地位的重要标志。村委会主任的人选成为争夺的焦点。换届结果是:7名村委委员中“蒙”支系占了6名,“阿卯”支系只有1名。而且,村党总支书记由“蒙”支系的人担任,他同时还兼任了村委会主任。于是“阿卯”支系的意见很快就出现了。报告人韩某某*访谈对象:韩某某,“阿卯”支系,男,56岁,土地村民组,访谈时间:2010年10月。是村里“阿卯”支系的代表人物,他对此表达了非常不满的情绪:
这个事情我现在都想不通!我50多了,是不想干了。有时候我都不想在村委会呆了,但是因为没有我们花族的接班人。大家都说,就要老韩在村里继续干,老韩在,就没得问题!我这个人有点笨,但我干工作老实,不分种族,只要是政府发话了,就实打实地干。而且,我们这一届村委会花苗就只有我一个。我想嘛,你说我们花族落后也好,不卫生也好,白苗当了村上的书记,花苗就应该是村主任!为啥子还要他们还兼着村委会主任呢?
案例二:“娶了汉族媳妇就会‘升级’快”,“讲卫生的人就喜欢讲卫生的人”。源域为上-下域,目标域为族群地位。说起对找媳妇的看法时,村里的年轻人熊某某*访谈对象:熊某某,“蒙”支系,男,24岁,偏江村民组,访谈时间:2010年7月。这样说道:
过去是汉族看不上我们少数民族,但是我们少数民族的女孩可能看得上汉族小伙子。现在嘛,我们都鼓励苗族小伙能在外面讨汉族媳妇的,就尽量出去。我还是希望自己能选外民族作自己的媳妇。假如我找了个外民族的媳妇,就好像打电脑游戏一样,“升级”就很快,大家就会鼓励我、羡慕我,会觉得我了不起!
报告人杨大姐*访谈对象:杨某某,“蒙”支系,女,56岁,龙洞村民组,访谈时间:2010年6月。的讲述,明确表达了“蒙”文化与汉族文化是“近亲”的优越感,十分耐人寻味:
我的三个女儿都打发(嫁)给你们汉族了。一个女儿嫁在水富,一个女儿嫁在四川,大女儿嫁给后山复兴村姓黄的汉族。我的女儿们心里头不喜欢苗族,就喜欢汉族,就爱着汉族,因为汉族比我们讲究卫生。讲卫生的人就喜欢卫生的人,女儿喜欢哪个就算哪个!
案例三:“蒙”和“阿卯”谁是正宗?谁是“流宗”?源域为中心-边缘域,目标域为文化资本。报告人杨某某*访谈对象:杨某某,“蒙”,女,56岁,龙洞村民组,访谈时间:2012年1月。,曾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表达了村里普遍存在的族群历史优劣感与文化资本之争:
我们白苗祖门是汉族,祖婆是苗族。他们花苗才真正是苗族。为啥子呢,我们白苗就有“谱”,就是家谱嘛。我们记得老高祖叫啥子名字,高祖又是啥子名字……谱嘛,就是“族长”才有谱。哦,那个书是一大本的。花苗没得,花苗就是“流宗”嘛,“流宗”就是乱改乱叫名字的意思。我们的名字辈分要一代接一代转起走的。我们杨家,说的是36字转。有些杨家是6个字就转,老祖祖还在世,小祖祖(指同一字辈的新生儿)就生出来了!你说好笑吧?
报告人王某某*访谈对象:王某某,“蒙”,男,57岁,山羊村民组,访谈时间:2011年11月。的讲述证明了“蒙”支系有族谱的确是事实:
我们家祖上王正嚓和王清卯两叔子是从武陵山区迁徙到彝良和四川筠连一带来的。这次族谱修订就是由彝良和筠连那边发起搞的,当时这本《王氏家谱(正嚓-清卯)宗支》印了70册,每本大概30多块钱,是按照每家男性人头数每人10元钱凑起来搞的。我们王家是一个“字辈”算一代,到我这里都是第18代了。
然而,村里“阿卯”支系关于自己在历史上的角色和地位的说法又不一样。访谈中,报告人“阿卯”朱某某*访谈对象:朱某某,“阿卯”,男,51岁,坪头村民组,访谈时间:2011年10月。不经意间冒出的一句话引人深思:
其实呢,听我老汉儿(父亲)那会儿摆龙门阵(闲谈)说,以前我们花族是统治人的,我们才是主子,他们白苗是仆人,是做奴隶的那一支。当年打仗的时候,都是我们花族冲在前面,他们白苗只是躲在后面吹芦笙、收尸体,所以他们现在死了人要吹芦笙,我们现在哪家死了人都不兴吹芦笙。
案例四:“蒙”的“先婚后育”与“阿卯”的“先育后婚”制度。罗锅片区的报告人马某某*访谈对象:马某某,“蒙”,男,38岁,道坪村民组,访谈时间:2012年1月。曾介绍该村“阿卯”支系“背着娃娃谈恋爱”的传统生育习俗,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在风俗习惯方面,花苗大部分是生了小孩后才结婚办喜事。云南十八怪中“背起娃娃谈恋爱”也包括了他们的。他们现在也是这样的。白苗只要是生了小孩,一般就不办喜事了。
报告人刘某某*访谈对象:刘某某,“蒙”支系,男,46岁,上厂村民组,访谈时间:2010年6月。对“阿卯”支系生育习俗的讲述更是充满了鄙视的情绪:
我们白苗是先办婚事,后再睡在一起。花苗是把娃娃都有了,一般娃娃都两岁了才办酒席。花苗多数都是这样的。像我们白苗就不得行!白苗如果有了娃娃就不办酒席了,因为会让爹妈、后家的哥哥、舅舅、舅子家这一边没有脸面。有了孩子还要办酒!你孩子都背在背上了还要办酒哇?!
报告人马某某*访谈对象:马某某,“蒙”支系,男,43岁,红岩村民组,访谈时间:2011年12月。的讲述强调了“蒙”支系对待未婚先育女性的残忍做法:
花族大部分都是生了娃娃才办酒。没有生娃娃就办酒的还少得很!如果按我们白苗的习惯,生了娃娃就不能办酒了。因为,亲戚那些就会说“娃娃都有了还办酒啊!有了娃娃还要让我们去送人亲?”如果女的不办事怀了娃娃,就要被撵走,因为不准她在后家生娃娃,意思是“丢人,见不得了,赶紧滚了!”
为便于分析“蒙”和“阿卯”关于“脏者”的方位隐喻及其文化意义体系,可将上述案例内容归纳汇总,如下表。

案例内容源 域目标域谁当一把手?谁当村委会主任?上-下域族群位序“娶了汉族媳妇就会‘升级’快”;“喜欢讲卫生的人。”上-下域族际通婚与族群地位“蒙”和“阿卯”谁是正宗?谁是“流宗”?中心-边缘域文化资本“蒙”的“先婚后育”与“阿卯”的“先育后婚”制度前-后域羞耻感与族群认同
Martin J.Gannon强调:“文化隐喻应该包含大量的象征,即文化隐喻是由大量的象征活动来实现的。一个现象、一个活动、一个机构都可以用来描述一群人的价值观、态度及行为。”*Gannon,Martin J.Cultural Metaphors:Readings,Research Translations,and Commentary.Thousand Oak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2001.转引自李福印、盛春媛:《评价Martin J.Gannon的“文化隐喻三部曲”》,《外国语言文学》2003年第3期。如上表所示,“蒙”支系和“阿卯”支系便是在关于“脏者”民间话语实体隐喻的基础上,借助村落的资源竞争、族群位序排列以及婚姻生育等日常现象,创制了对“脏者”的方位隐喻,从而通过象征的表达方式,把对“脏者”具有排斥情绪和否定态度的事件映射到对族群文化分类的认识中,并建构起强化本族群价值观的文化意义系统。
首先,“蒙”和“阿卯”支系把日常生活体验所习得的上-下方位概念主动植入到村两委委员数量和村委会主任职位的竞争事件,植入到鼓励年轻人找汉族媳妇以实现“升级”、嫁给“讲卫生的人”则自己也“卫生”了等族际通婚的具体行为中,充分利用上意味着优势、成功、高级和洁净,下标志着劣势、失败、低级和肮脏的经验意义,隐含地表达了我族在村落中的位序排列和社会地位高于同村他者的象征性意义。
其次,“蒙”和“阿卯”支系借助习以为常和自己所熟悉的中心-边缘方位概念,通过“谁是正宗、谁是‘流宗’”“谁是主子、谁是奴隶”“谁冲锋陷阵、谁又贪生怕死”等历史传说,表达了他者一直都位于文化边缘地带而我族才居于文化中心,我族才是真正拥有文化资本的高级群体这一类的抽象概念。
再次,“蒙”和“阿卯”支系还动员和利用了前-后方位概念,通过对“婚前生育”还是“婚后生育”习俗孰优孰劣的伦理较量,一方面充分表达了同处一村不同苗族支系较为复杂的关于族群、宗族和家系的羞耻、荣辱等道德观念,一方面又间接强化了遵守本支系内部婚姻伦理的族群认同理念和实践,实现了经由方位概念的映射,表达更为复杂难懂的族群认同的概念。
三、“脏者”不婚:结构隐喻及其功能
在“蒙”和“阿卯”支系关于“脏者”的叙事和分类活动中,正是各族群所主导的价值观排斥和拒绝了污秽、接纳和首肯了洁净。但这种价值观是通过对“肮脏”行为和事件的主观认定和情绪反应所映射出来的观念系统,或是一种由抽象概念之间的相互映射和叠加而表达出来的所谓的结构隐喻。
具体而言,“蒙”和“阿卯”支系通过文化分类的理性行为完成了对肮脏和污垢的否定和排斥,表达了对卫生和洁净的肯定和接纳,这一过程也就是以“蒙”和“阿卯”支系互不通婚的显在结构,表达了隐含的具有文化异质性的“他者”概念,强化了具有文化同质性的“我族”意识,并使婚姻的行为边界和文化他者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婚姻的词语用于谈论族群关系和族群认同,从而创制出“‘脏者’不婚”民间话语的结构隐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创造活动还具有目的性和指向性,因为“‘脏者’不婚”其结构隐喻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对村落秩序的维持和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1.“脏者”不婚:结构隐喻分析
为什么同村的“蒙”和“阿卯”支系关于“脏者”的叙事总是围绕族际通婚的民间话语而展开?马戎的论述或许对此做出了注解:“族际通婚深刻地反映了族群关系深层次的状况,这是因为族群之间的基本差异深植于人们的群体认同观念之中,从而使人们把周围的人群区分为‘同族’与‘异族’两类。”*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6页。换句话说,正是“蒙”和“阿卯”支系基于文化差异的族群认同观念和群体分类逻辑,支配并驱使着“不与‘脏者’通婚”观念及其行为实践的演进。在此认识基础上,可以对“蒙”和“阿卯”其“不与‘脏者’通婚”的结构隐喻作进一步探析。
第一,“蒙”和“阿卯”支系关于脏者的实体隐喻通过日常生活叙事肯定了“洁净与有序”,否定了“污秽与失序”,控诉了“肮脏与危险”,召唤了“秩序与安全”,并据此突出和强化了我族与他者的文化异质性对于维持村落秩序正常运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隐含的价值观是:我族是洁净的和有序的,因而也是安全可靠的;他者是肮脏的和处于失序状态的,因此也是危险和不可接触的;村落秩序必须依靠“我族”与“他者”文化异质性的存在而得以维系。据此可以发现,“蒙”和“阿卯”的“不与‘脏者’通婚”的民间话语,正是其族群价值观差异的社会生活表达,是“蒙”和“阿卯”基于文化差异的族群认同观念在婚姻关系上的具体表现——由此可以呈现其“不与‘脏者’通婚”结构隐喻的第一个层面:源域为婚姻“行为边界”,目标域为“族群认同”观念。
第二,“蒙”和“阿卯”支系基于自己所熟知的上-下、前-后和中心-边缘等方位概念,在村落权威竞争、公共资源争夺、英雄祖先传说和生育习俗优劣的争辩中,通过对脏者的方位隐喻象征性地表达了我族的社会地位、文化资本力量和婚姻家庭伦理观优于同村的文化他者,从而表达了苗族不同支系对族群文化“阶序”的认识,并依此构建了维护本族群利益的村落文化意义系统。其隐含的文化逻辑是:族群文化具有层次性和差异性,族群文化优劣关系到竞争结果和群体声誉;族群文化优劣与时空方位因有内在的相似性而具有了其象征意义:污秽者往往与弱者、地位低下者、旁门左道者和道德沦丧者同构,而洁净者往往与强者、地位居高者、中流砥柱者和道德高尚者同构;村落秩序必须依靠我族与他者的文化竞争而得以维系。据此可以推论,“蒙”和“阿卯”支系其“不与‘脏者’通婚”的民间话语,正是他们关于族群文化分类体系和村落竞争的逻辑表达——由此可以呈现其“不与‘脏者’通婚”结构隐喻的第二个层面:源域为婚姻“行为边界”,目标域为“群体分类逻辑”。
2.“脏者”不婚:结构隐喻的社会功能
一定的文化制度及其要素构成必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概括起来,“蒙”和“阿卯”其“不与‘脏者’通婚”结构隐喻具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和特定的社会功能:
首先,作为生存观,“不与‘脏者’通婚”结构隐喻本身即反映了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苗族不同支系,迁徙聚居同一村落的历史境遇以及“蒙”和“阿卯”与川黔滇邻区特殊生态环境长期互动而形成的具有对抗性、排斥性、封闭性和地域性的文化特质。
其次,从教育功能看,它具有族群文化传承和凸显族群文化分类原则的重要意义。“不与‘脏者’通婚”结构隐喻将“族际通婚”与“族群认同”观念、“群体分类逻辑”建立了对应的映射关系,强化和凝聚了本族群内部的文化一致性,渗透并传播了基于族群符号的文化分类标准,具有维护本族群文化并对文化“他者”排斥的规劝和引导作用。这种教育功能与王明珂通过对岷江上游村寨中羌族村民对“毒药猫”女性具有污染力、破坏力和危险性叙事的分析的社会功能几近一致。*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0-105页。
再次,从政治功能看,“不与‘脏者’通婚”结构隐喻虽以婚姻行为边界为表征,但实质上映射着我族与他者的文化区隔和社会距离,因而具有了对族群文化识别与区分的重要意义,也对村落社会关系的沟通与协调发挥着重要功能,同时还影响着村落权威的确立和相关制度决策。
最后,从文化的整合与文化创新角度看,它最重要的功能还在于对重建村落秩序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正如罗德尼·尼达姆所言:“社会人类学关注的焦点是秩序,而那些系统相关的范畴,即分类,将为秩序提供标记和保护。”*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第124页,英译本导言。“蒙”和“阿卯”通过族际通婚与族群认同观念、群体分类逻辑之间建立的文化隐喻,根基在于对群体的识别,核心在于对文化的分类,而这些分类观念及其行为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族群文化的整合程度和创新发展,也将最终决定着特定社会秩序的构成和演化方向。
四、结语:对村落秩序不能言说的言说
族际通婚是婚姻行为模式的一种,是婚姻形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民国初年始从川黔滇3省11县陆续迁徙聚居而同处一村的苗族“蒙”和“阿卯”,其婚姻制度无疑是村落文化及其秩序的重要部分。然而,无论是民国年间被称为“苗子”和“苗啾啾”的这个弱势群体,还是作为同是国家话语中苗族的“蒙”和“阿卯”支系,至今彼此仍互不通婚的文化事实都以无声电影的形式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持续上演着。文化隐喻的创造似乎打破了这种“无声”的状态:“蒙”和“阿卯”通过建立“不与‘脏者’通婚”与族群认同观念、群体分类逻辑之间的文化隐喻,成为其对村落秩序不能言说的言说。
Martin J.Gannon强调:“隐喻表现出文化本身所表达的价值观,是人们重建、认识现实的基本机制。”*Gannon,Martin J.Understanding Global Cultures:Metaphorical Journeys Through 23 Nations.Thousand Oak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2001b.转引自李福印,盛春媛:《评价Martin J.Gannon的“文化隐喻三部曲”》,《外国语言文学》2003年第3期。“蒙”和“阿卯”其“不与‘脏者’通婚”的文化隐喻便是借助它本身所表达的族群价值观展开了与村落秩序重构的对话,以期认识现实和重建村落秩序。而“不与‘脏者’通婚”的文化隐喻所表述的价值观和族群观却是“蒙”和“阿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以及村落现实利益冲突的产物,正是这种文化和利益冲突的矛盾运动推动着族群之间新的合作范式的出现,从而有可能获得不同族群都普遍接受的新的村落秩序。因为“人类的社会群体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却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用以表达何为美好生活的隐喻之中以及各种范式的相互冲突和对立之中……秩序是通过冲突和较量获得的——它是各种意愿及智慧或冲突对立或团结合作的结果”*维克多﹒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第5页。。
——以云南墨江自治县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