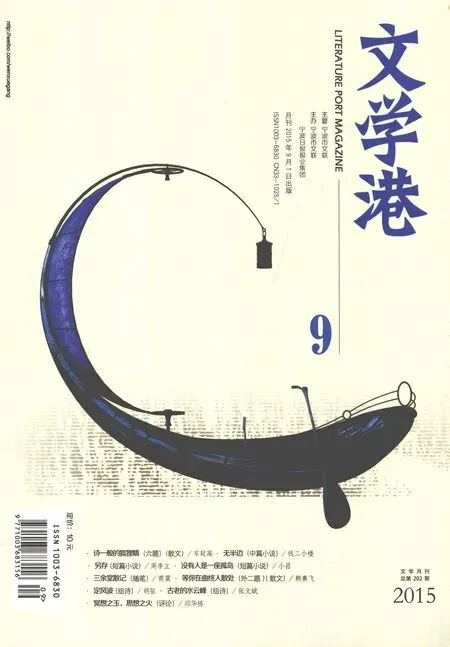喧嚣的耳朵
俞彩霞
喧嚣的耳朵
俞彩霞
一
她产下女儿,才坐两个月零七天月子,单位来电话,说人手紧,你最好早点来上班。
上班没多久,一连数天她都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这怪味便是从耳朵里钻出来的。痒痒的湿湿的耳朵,用棉签一抠,粘在上面是黄绿色的脓状液体,细细一闻,带着一丝酸腐味。她知道耳朵又发炎了。
这种现象从她读小学四五年级时就有,她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记得13岁读寄宿中学起,她的耳朵就时常流脓,坐在教室里老是用小拇指去抠那耳朵。那时候手头没有棉签或餐巾纸,她就随便用白纸头撵一下塞进外耳道,粘在纸上的是浅绿色的脓液。她没当一回事。长大后去了几趟医院,才知道这是慢性中耳炎,急性发作的时候添一下氧氟沙星之类的消炎药水。她想,肯定是小时候父亲给她洗头时不注意,水流进耳朵,细菌侵入,长期以往就变成了中耳炎。小时候她的头经常由父亲抱着在河边洗。那个年代人的人卫生意识普遍没有当今强,当然那时的河水也比现在清澈得多,村庄上的人都在河边洗头、淘米、洗衣服。
读高中期间,校医室医生给她的耳朵用双氧水彻底洗了洗,之后中耳炎来“叩门”的几率就小多了。工作后感冒时引发过数次,因为单位就在医院隔壁,她认准了一位和蔼可亲的五官科男医生,也就不再担心害怕;医生照例给她清洗外耳道,然后配一瓶氧氟沙星滴耳液,两天后耳朵就好了。
十月怀胎她最担心的还是耳朵,担心消炎药水对胎儿不利。怀孕期间这耳朵倒是乖乖的很听话,没有来找过一次麻烦。可坐完月子才两个多月,这老毛病又犯了。恰逢她产后上班,她想许是工作太累,抵抗力下降,耳道被感染了。这回看的是家附近的医院,女医生配了盒消炎药和一瓶氧氟沙星给她。正巧这天从老家赶来的婆婆患上重感冒,风风火火的婆婆几乎不曾感冒过,这回却被感冒重重击了棒。她想也没想就把药让给了婆婆,自己只添药水,心想以往就是添几次就好。
可是这一次,一连添了十多天,她耳朵里仍旧湿漉漉的,不见干燥。耳朵老是闷闷的,虽然能够听见声音,但是这声音别扭,不够与自己“亲近”,好像一间房子被糊上了窗户纸,跟外面隔膜了。这种现象以前也有过,到医院用双氧水清洗,添几次药水就好。
紧接着的一个双休日,家里进行自来水一表一户改造,她所住的小区,是全市一表一户改造的试点小区。白天管道工在她家里叮叮当当一阵,单户水表装好了,晚上全家进入梦乡。
半夜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她惊醒。半夜里来电,肯定不会有好事儿。丈夫接了电话,她忐忑不安地在旁边听。物业保安打来的电话,说你家漏水了!他在半夜巡查时发现很多水从一楼流到下面车库,判定是她家水管爆裂了。
她赶紧下床察看,不看不打紧,看了吓一跳。卧室里全是水,足足有十多厘米高!时令正是入秋,半夜她赤脚下床,一股冷冷的水直没到了脚踝处,她不禁打了个冷战。再一看,家里面全是水,真是“水漫金山”,地上放置的物品全都被浸泡到水中了。全家人开始除水,搬离家具、整理物品、擦地板,忙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跟自来水公司交涉,得知一表一户安装后水压猛增,而她家的自来水管承受不了过强的压力爆裂了。
晚上带小孩够累的了,如今还被水管爆裂给折腾。
第二天早上,她莫名地听到耳朵里开始有“丝丝丝”的轻微声响,她没在意。心想,肯定是晚上带孩子、白天工作身体疲累的缘故,休息好了会没的。
过了一星期未见好转,她到医院去看。这回女医生给她配了四盒杞菊地黄口服液,嘱咐她不要累着,要多注意休息。
可是,口服液吃完了,声音还在。
一个多月过去了,耳朵里“丝丝丝”的声音反而更响了。这声音有时候像蜂鸣,有时候像哨声,有时候像低沉的涛声,有时候像枝头的鸣蝉,惹得她晚上睡不好觉。同事给她补肾的黑豆,母亲给她滋阴的铁皮枫斗,她都吃了。可是也不见效。
再有一天,领导看到她,惊讶地说:“你的脸色好黄啊,脸都浮肿了呢!”她忙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果然黄黄的,胖胖的。她纳闷,自己是没工夫照镜子,老公每天在身边看到自己,为何也是熟视无睹啊。
她想再支撑几天,上班上到月末,以保全这个月的奖金。可是耳朵里的声音如同犟脾气的孩子跟她对着干,越来越响。耳朵成了加工工厂,里面像安装了好几部机器,同时发出隆隆的巨大响声。
她立即向单位请假休息。
第二天,三婶说打听到一个邻村的老头会看耳朵里的声音。她欣喜若狂,赶紧跟着三婶乘公交车来到邻村。沿着狭长的河岸边,再穿过一小段田塍路,她们在熟人的指引下来到一个附近的村庄。令她奇怪的是熟人并没有走进任何一家农屋,而是七拐八拐来到一间理发店门口。她好生纳闷。这理发店是间灰不溜秋的小房子,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把老旧的理发椅,地上是一些散落的头发。店里有一个大概70多岁的老头正在替60多岁的大伯理头发。老头很瘦,头发稀疏,眼眶凹陷得可以盛两个乒乓球,说话几乎没有声音,她猜可能动过手术被割掉了声带。她一眼看到那个被剃头的人披着的那件“倒褂”油腻得好像十年没洗过,苍蝇都会滑下来。那老头听明来由后不知从哪里拿出一类似眼药水瓶,一边张口说一边比划着,意思是让她坐在这把剃头椅子上。她忐忑不安地坐下,那老头把她的头拨到一侧,就把一瓶眼药水似的药水往她耳朵洞里滴了数滴就完了。然后吩咐回家后吃红枣,多吃点红枣。三婶付过30元钱,前后仅仅5分钟,她逃也似的出了理发店。坐在公交车上,她思忖:不知道这老头的药水是什么东西,不会是祖传秘方吧?怕是普通耳药水把?会过期吗?会有副作用吗?真能治好耳鸣?
越想越害怕,她坚决不再去第二次了。
二
她一直怕去医院,从小到大都怕,患中耳炎的这么多年里,去医院每每要经历一番勇气与胆怯的搏斗。她怪自己太敏感,每每去医院,就会想到死,想到癌症,想到一切可怕的疾病。而这回,她自己提出来去医院看看。
此时,正好北京有大医院的耳鼻咽喉科专家来当地医院坐诊。丈夫陪她去看,专家医生一照耳朵,只说了一句话,药物过量中毒了,然后给她配了一瓶德国进口药“都可喜”。她恍然大悟,氧氟沙星添耳的时间太长,次数太多了,一定是药液侵入内耳,造成了损害,导致出现耳鸣。那我的病会好吗?她疑惑地问。专家医生微笑着点了点头。
于是遵照医嘱,每天两粒“都可喜”。
一瓶药吃完了,耳鸣还依然继续。她又到药店买了一瓶,继续吃,两个月过去了,耳朵里的叫嚣还在。她开始疑惑、担忧。
她想去省城比较有名的大医院瞧瞧。
丈夫没有陪她去,他说他忙,姐姐陪她去的。她们跑到了省城一家著名的医院。五官科医生先是用一根细细长长的橡皮管从她鼻子里穿进去,一直通到咽喉处,她好一阵不适,想呕呕不出,想咳嗽又咳不了,完了医生说没问题。然后排长队去做磁共振,排队等候的时候她又忐忑不安,如果耳朵里长个瘤子之类的咋办?下午拿到报告单,结论是没有器质性病变。这个结论令她又喜又忧,喜的是耳朵里没有毛病,忧的是高级仪器也探不出她耳朵里的声音。她突然明白这MRI只能逮到有形的东西,对于无形的尖叫,这高档的家伙也束手无策,就如同强大的狮子对付不了停在它背上的一只小蚊子,任它戏弄吸血。她又挂了专家门诊,以为这所全省著名医院的专家对这种病肯定见多识广,可是那和蔼的女医生用耳灯照了照她的耳道后,没有配任何药,只说了一句话:“好好休息,不要让自己过度疲劳。”
她满心希望揪出耳朵里的声音,却无功而返。
回到家里,她开始研究这耳朵里的声音到底是咋回事。上网搜索,也看报纸下角的广告。平时从来不看报纸角落广告的她居然发现里边有很多专治“耳鸣耳聋”的小广告。看到某大报一则“耳鸣耳聋消失”的小广告,按图索骥打电话过去,把自己的症状向对方告知。她信心满满,内心犹如一杯充盈着甜润饮料的杯子,那满满的甜浆就是满满的希望。以前自己一直蔑视这些小广告,认为大多是骗钱的,现在自己倒要试试看,怀着宁可被骗的侥幸。不料对方直截而坦白地回复:“这样的耳鸣是治不好的。”电话随之挂了。他们居然不要赚她的钱!她感到极度失望,差一点想把电话筒给扔了。哪有不想赚钱的商家,明明不是说任何耳聋耳鸣都可以治吗,而且包含自己这种尖叫式的耳鸣。失望之后她陷入深深的恐惧:广告上说耳鸣长久不治,将会发展成为耳聋!还有就是不耳聋,一辈子生活在这样的叫嚣中,怎么受得了,还不如死掉算了!
她第一次想到了死亡。如果死了,那么耳朵里的声音也就戛然而止了,对付这个声音恶魔,只能用这等方法!她把耳朵当成自己可恶的敌人。可是这值得吗?孩子这么小,自己29岁呢,还没活到一半寿命。况且,自己向来是个胆小鬼,怕死着呢。
这么一想,她的心稍稍安顿下来,似乎感觉耳朵里的魔鬼也稍稍心平气和了些。大概它也累了,想打个盹。可是外面一串串鞭炮放过,或者一声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叫过,耳朵里的魔鬼立刻被激活了,比先前更为肆虐地咆哮着。
西医不行,尝试中医。她希望有着几千年灿烂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中医针灸能够拯救陷入困境中的自己。从报上收集到的文章中她了解到耳鸣是因为内耳神经受到损伤,耳朵里的微循环被打乱造成的,这或许是因为药物中毒而损伤了内耳神经;或许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内耳缺血,血液流动不畅损伤耳神经。或许是因为那个发大水的夜晚自己赤脚下床脚板浸冷水受寒引起的,脚板上的穴位联通着全身呢,她想。
单位里正好有一名退休的女医师以前从事过针灸,她说疗效肯定会有的,这句话让她心头好一阵暖和,就像喝了一碗甜甜的酒酿圆子。
她躺在床上,年近花甲的女医师用一根根长长的银针,刺进耳朵边的穴位里,一连刺了好几根。接着又在后脑勺、手肘部、大腿上分别刺了几根。她安静地躺在床上,想象着耳朵里的恶魔顷刻间被除掉,就不觉着痛了。她望着和蔼的女医师,心变得异常宁静,渐渐地耳朵和周围环境一样的安静,那聒噪声渐渐地变小了,变轻了,轻得几乎听不见了!
回到家里,她尽量不去关注耳朵和耳朵里的声音,她快活地洗碗、扫地、抱小孩、看电视。终于睡觉时间到了,考验耳朵的时刻又来临了。躺在床上,怯怯地关掉床头灯,头一靠到枕头上,耳朵是她不可回避的来客,就像影子无法分割她和她自己。耳朵里的聒噪声失而复来,仿佛藏得更深了。
她想这只是疗程不够的原因。
第二星期她又去医师处针灸。针着针着,她的确发现声音淡到几乎消失了,她确信针灸发挥了作用,它能够针对穴位,改善血液循环,疏通耳朵里被堵塞的血管。针灸结束后她一路骑车经过热闹的街市,来到僻静的图书馆,其实她不是来看书的,而是来听耳朵里的声音的。她独自躲到一僻静处,佯装看书,翻来翻去,却一个字都没看进去。当她仍然感受到耳朵里的喧嚣声后,她赶紧丢了书,逃也似的跑到借阅处,那里人多,外界的声音足以湮没她耳朵里的声音。
第三星期她又去针灸,第四星期又去,第五星期再去……
这样的持续了三个月,每次都是针灸的时候没了声音,走到外面就恢复喧嚣了。她仔细分析,她的耳朵对外界的声音特别敏感,外面的声音一刺激,耳朵立马开始叫嚣了。
她不再坚持针灸。
三
为了验证耳朵里的魔鬼有没有悄悄地溜走,她常常从一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试探着这耳朵里的声音突然消失,被关在门外那样。她来到安静的储藏室,希望在整理衣物的时候不知不觉中耳朵也回归了宁静,可是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借到卧室取衣服的机会,她躲在门背后倾听。这里是受外界影响最小的地方——可是依旧听见耳朵里的尖叫,满脑子都是,嘤嘤嗡嗡的,好像是耳朵里传来的,又好像是脑子里发射出来的。她感觉整个头就成了一个发射塔,发射的不是信号,而是无数根绵薄的针头。她惊慌地逃离卧室,来到灯火明亮的客厅,让电视机里的声音掩盖她心头的恐慌。
倾听自己耳朵里的声音成了她分分秒秒的“功课”,尽管她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过分在意,很多病痛是在不经意间溜走的。她期待着哪一天在洗衣服的过程中或在逗孩子玩的时候,突然发现聒噪声销声匿迹了。
可是五个月过去了,这声音还是在耳畔、在脑间萦绕盘旋,驱之不去。
她渐渐地失望了,失望演变成一份深深的恐惧。
丈夫又出去打牌了。
她希望丈夫多在家陪陪自己,这个要求在她看来一点也不过分,她需要陪伴与安慰,况且孩子才几个月大。可是丈夫流露出的那种淡漠与不屑,让她渐渐地收起了眼神里的期待,她的心是细腻而敏感的。刚开始的时候,丈夫也陪着她想办法,安慰他几句,眼神也是柔和的,可是慢慢的,她发现丈夫的眼神里多了一层霜,眉宇间因为蹙眉过多有了明显的坑洼。或许他根本没有理会自己的苦闷,他更感受不到自己的痛苦。她给他多说几遍,他开始感到厌烦。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见,揉也没法揉,再怎么表达也难以尽意。
她孤单落寞地呆在偌大的屋子里,恐惧像幽灵一样附着在她的心头。她赶紧把电视机开着,让电视里的声音盖过耳朵里的声音,努力让自己的思维和情绪跟着电视内容和情节走,这样会暂时忘记耳朵里的喧嚣。渐渐地,在外界的声响里,她睡着了。
醒来一看,床边还是空着——丈夫还没有回家来。也许,他打牌正酣着呢。
此刻屋子里特别安静,安静得可以听到绣花针掉落地上的声音。可是她的耳朵里依然是噪声一片,那家伙一分一秒不知疲倦地叫嚣着,好像拉了一伙人起哄。她赶紧捂实了被子,在被子里轻轻地啜泣。
她终于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丈夫回来了。她偷偷看了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多。
丈夫进卧室的时候,她有意翻了个身子,提示他自己还未入睡,希望丈夫跟自己说几句话。可是丈夫上床后什么话也没有对自己说,连凝望一下自己的眼神都没有,背对着自己顾自睡下了。不到五分钟,丈夫的鼾声响起。她的心里又一阵落寞,好像夜色是一个巨大的岩洞,把自己掐入洞底。她心想自己该如何安眠呢?
那一段时间,她每天倚着阳台,看小区外来来往往的人群,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是多么自由自在,潇洒惬意!她羡慕每一个过往的行人,不管他们穿着奢华还是朴素,不管他们高矮胖瘦。她甚至发现倚靠在墙角的乞丐都是幸福的,因为他至少还拥有健康,无忧无虑地晒着太阳,而自己呢,病恹恹的像霜打的茄子打不起一点精神。
她首次思考起痛苦这个深邃的名词内涵。
她想痛苦有两层:一层是肉体上的痛苦,例如疼痛,需要动手术得以根除或缓解;另一层是精神上的痛苦,自己反应强烈,可别人看不见、摸不着,也无法切身体会自己的感受。这种痛苦应该算是精神上的痛苦吧?这样想来,她宁可遭受肉体上的痛苦,这种疼痛只要用手术刀就可以解决,现代医疗条件这么发达,全身或局部麻醉,半天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或缓解。可是这小小的耳朵,根本找不到解决的良方,对精神是极度折磨。一想到活在这个世界上,还要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五十年,这个病一直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她感到深深的绝望。
四
她已经好久没有外出了,一来年幼的女儿每天需要照顾料理,二来从耳鸣开始自己的情绪很低落,连漂亮衣服都没心情穿,哪里还想外出吃饭、逛街。
偶尔一次,好朋友约她出来去咖啡馆吃西餐、喝茶。她想也好,散散心、叙叙旧,心情或许会好一点。
咖啡馆在小城的中心,紧邻着一条江,从落地玻璃窗向外眺望,小城的美景风韵毕现。里面布置得十足温馨,柔和的灯光,唯美的落地纱帘,精致的酒架。三角钢琴摆放在一个大厅里,像一个贵妇伸展了四肢闲适地躺在唯美的宫廷大床上。一位俊雅的男青年正弹奏着钢琴曲《致爱丽丝》。旁边有一个花枝缠绕的秋千,浪漫而温馨,她和同伴在秋千上荡了会儿。壁橱里展示着各式各样的饰物,富有欧洲艺术气派,她一一欣赏着。不一会儿,精致的餐盘端上了桌,烛光点起来了。温柔可人的服务员在一旁静候着客人点单需要。她顿时被这里的氛围感染了,活着真好,她想。
咖啡馆里不时弹奏着优美的音乐,或舒缓或情意绵绵,她最爱听的那支英文歌曲《卡萨布兰卡》也在耳畔回想,低沉略带忧伤。她想起了当年和男友一起陶醉在这首歌里的情景,相依相偎,也是在这家咖啡馆。只是当年弹奏这支钢琴曲的男子早已换成了别人。精美的蛋糕、牛奶、果汁、牛排上了桌,她和朋友们享受着这美好的欢聚时刻。朋友的安慰,如甜甜的琼浆玉露,在她心头慢慢地化开来,她暂时忘记了耳朵里的聒噪声。
过了一个半小时,她起身上厕所去。
曲里拐弯,她按着厕所的方向走去。朦胧的灯光下,在靠墙角的一张桌子旁,她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和一名年轻的女子喝茶。
这不是自己的丈夫吗?他怎么也会来咖啡馆喝茶?在自己的眼里,他除了上班就是饭局和打牌,似乎每次都跟一帮男人在一起。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丈夫晚上除了打牌搓麻将还有别的活动。
她突然发现自己不怎么了解身边人。
她一直都很信任他。有一次她问他晚上在干什么,他说在打牌。她问他,跟谁一起打啊?他不屑一顾地说你不认识的。她便识趣地不再追问。虽然很多次晚上跟丈夫通电话,她都没有听到发牌、摸牌的杂碎声以及男人们的吆喝声。
从厕所回来,她没有一丁点儿吃下去的胃口。借幼小的孩子在家睡觉需要照顾,她提前离开了。
耳朵里的声音没有消除,她的心里又增添了新的烦恼。丈夫是广告公司的业务主管,平时应酬较多她也理解,总跟一帮兄弟们打牌、吃饭、搓麻将,虽然她不喜欢,但也没有硬加阻止。她从没发觉丈夫有异样呀。
回到家里,她细细地回味着生完孩子后丈夫的一言一行和细微的举动。
没生孩子之前,两个人的世界确实比较温馨。没有过多的家务琐事羁绊,丈夫时常带她一起去参加朋友聚会。怀孕以后,丈夫虽然也经常有应酬邀约,她不能一同去,但她从心底里感觉自己是快乐的。打牌晚了,电话一打,丈夫不一会儿就回家了。
可是自从医院生下女儿之后,她感觉丈夫似乎变得冷漠起来。
医院最西边的一间病房是双人间,在当时是仅有的两间产科病房之一,其余都是三人间、四人间的。她和另一名产妇住在里面。她是头一天生下的女儿,对面床是第二天生下的女儿。她家请了个月子保姆,对面床没有请,是婆婆和丈夫一起照顾的。每天一早,隔壁床的丈夫就来到病房,给妻子送早餐、擦身子、喂饭菜、洗内裤,并不时抱着孩子逗着玩,对母女俩照顾得十分周到、仔细;而自己家那位,每天拎一个公文包,走进病房瞧一眼孩子,不到5分钟就出门了,也不问问自己的身体情况,或陪自己说说话。说实在,虽然自己的丈夫会赚钱,而她对面床的丈夫是个普通企业员工,但她内心很是羡慕隔壁床的那个产妇。婆婆到医院来看过自己一次,以后似乎没怎么来,她也不怎么记得了。
一年以后,偶然在街头碰到对面床的丈夫。无意中聊起当初住院的日子,那男人好奇地问:“我感觉你婆婆不喜欢孙女?我看她就来医院看过你一次,以后就没再来过。”
她说她也忘记婆婆来过医院几次,反正婆婆在她家里照应呢。婆婆来不来医院她并不在意,丈夫那时候的举动她内心里是有想法的。每次进来没啥笑容,也不多说话,在医院里呆不了几分钟就走了,好像事务特别忙的样子。后来亲戚闲聊中一句无意的话让她心里一惊:“当时我们在你家里,你生了个女儿,他都不情愿来医院多看你们。”
她的心里一阵刺痛,回想当初的情景,初露端倪。她知道婆婆喜欢孙子,在她产前就流露出想要男孩的意思。丈夫倒是从来没有在她面前表示过想要男的还是女的。
月子保姆走了以后,婆婆来家里带小孩。婆婆很能干,风风火火的,似乎一阵旋风就能把一堆家务活给搬掉。白天婆婆带小孩,晚上她自己带,丈夫很轻松,他没有一丁点当爸爸的压力,照样在外面打牌、搓麻将,偶尔来家里吃饭,饭菜都是现成的。有一件小事让她至今记忆犹新,孩子生下来才一个多月,丈夫居然事先没跟自己商量,跟朋友们一道去舟山海岛玩几天,结果因为紧急台风,他们半途折返回来了。折返回来,她才知道这个事。这让她有点不快,孩子这么小,自己产后身体不好,经常感冒吃药,他怎么能够忍心顾自去玩呢。
五
那天晚饭后,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婆婆准备了一脸盆水给幼儿洗头发。她小心翼翼地盯着婆婆给孩子洗头发的举动。她看见婆婆在给孩子淋头发的时候,因为舀的水多,流下去的水即将要将耳朵浸湿。出于对中耳炎的敏感,她特担心水流进耳洞引发慢性中耳炎。想起小时候爸爸在河边给她洗头的时候水经常进入耳朵而发炎流脓,演变成久治不愈的慢性中耳炎,再联想到自己现在的耳鸣状况,她惊慌地大声喊起来:“小心,别让水进到耳朵里!”谁知孩子爸大吼一声:“自己不动手,喊什么喊!”婆婆也在一旁嚷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抗议道:“就是要小心啊,水进入了耳朵多危险!”“有什么好危险的,自己不动手,就管发号施令!”丈夫的话顿时令她感到非常委屈,自己现在生病请假,每个月的奖金扣掉不说,每天还承受着无法想象的精神折磨,可婆婆和丈夫对她不够包容,不够体谅。
第二天早上,还躺在床上的她隐约听见客厅里丈夫说了一句话:“随她去吧!”这分明是把自己晾一边的意思。紧接着,婆婆说了一句:“那孩子去了,妈妈没去,左邻右舍会猜疑的。”她忽然明白婆婆要领着孩子回老家。她心里感到一种不被尊重的不快,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跟当妈的商量?她赶紧起床,问丈夫是不是要把孩子送到乡下老家,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质问:“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没想到丈夫恶狠狠地抛出一句:“为什么要跟你说!”“我是她母亲!”她理直气壮。

想到耳朵里的聒噪声依然存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倘若婆婆和幼儿走了,丈夫经常不回来吃饭,留下她一个人孤独地呆在家里,那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无奈,她只得追随孩子。
可是意想不到的烦恼又一次让她委屈困顿。
一个月后的一天,她发现幼小的孩子脑袋温热,焦躁、哭闹,不愿进食。一量温度,已经有38.8度了。婆婆说到村里的儿科医生那里去看看吧,那个医生专门给小孩看病的,方圆十里都很有名,他女儿研究生毕业现在也做儿科医生了。村里的小孩病了都找这个医生看的。
她跟着婆婆来到那医生家里,那是个私人诊所。诊所面积有100多平方米,两间屋子,里面摆着床铺、各种药品和医疗器械。有几名小孩在挂盐水,一个小孩坐在母亲的膝盖上等待医生配药。那医生50多岁,没有穿白大褂,也没见其他白大褂医生当助手。过了一会儿,轮到她的孩子看了。医生摸了摸孩子的脑袋,说是发热了。接着便量了下体温。她希望乡村医生不要给孩子挂盐水,果然没有,看来孩子的病不是很重,她庆幸。接着看到医生在纸上开方子,她想一定是配一点针对婴儿的感冒退烧药了。她在自己家里倒是常备着一些婴幼儿退烧药、感冒药,只是没有带来。
医生只配给她们两颗药片,才两元钱,她心想这医生蛮不错的,开药也注重节俭、适量。医生说到家里碾碎了泡在温水里给孩子喝,先一颗,过四个小时再吃一颗。她想,既不打针也不挂盐水,就两片药而已,挺好的,跟城市医生一样。回到家,她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想看看究竟是什么药。两颗大大的圆圆的药背后竟然是四个字“阿司匹林”,看得她自己的眼睛也成了这两片大大的圆圆的。说明书上也是赫然四个大字“阿司匹林”。她顿生疑惑:阿司匹林好像是治头痛、关节痛的止痛药吧,阿司匹林不是大人吃的吗,印象中从来没听说给婴幼儿吃阿司匹林哪。自己的婴儿才八个多月啊,合适吗?带着这份大大的疑惑,她仔细地看说明书——这药倒是有消炎作用,说6个月到12岁儿童可以吃。她想这药的跨度好大啊,为何不配针对婴幼儿的感冒药呢,跨度越小说明婴儿针对性越强,药性也更温柔,对婴儿也更有利,就像婴幼儿奶粉,阶段分得很细致啊。自己家里可是备着很多婴儿吃的感冒药、退烧药呢,像小儿泰诺、小儿强生、布洛芬、美林之类的,还有草莓味的甜甜的颗粒冲剂,专门针对婴幼儿的,怎么这医生家里没有呢?她仔细地看起说明书,当她看到说明书上的那一句话时,她的心简直要“嗖”地腾起来,敏感的神经再度被揪起:此药的副作用是可能引起耳鸣。我的妈呀,一看到耳鸣两字,她的内心一片恐慌,自己因为耳鸣受尽折磨,这个药的副作用居然也是耳鸣!万一孩子服了这药不幸发生了此副作用,那不是害了孩子一辈子了么?况且孩子这么幼小,都不会开口说话,即使有难受都不会表达,做妈的怎么能给孩子冒这个风险呢。不行,绝对不能!
婆婆已经将药片碾碎了融化在温水里要给孩子喝下,她给挡住了。她向婆婆解释了该药的副作用,坚决表示不给孩子吃,自己到镇上药店里去买。婆婆的脸顿时变得不好看,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人家是这里的儿科专家,看病都看了30多年了,孩子看了成千上万的,没有看坏一个孩子啊”。
“人家都培养出研究生女儿呢,也当医生了,还不懂给小孩配啥药?”
“哼,你就比医生还高明,医生的药不吃,还自己去买,真疙瘩。”
她沉默着,心里极度郁闷,现在不光为自己难受,还为自己年幼的孩子难受。
她到镇上买了小儿退烧药和感冒药。第二天,孩子的热退了,再吃点感冒药,过三天就好了。
想到自己一星期后就要上班,孩子万一感冒发烧之类的婆婆肯定要去这家私人诊所看病的,她不放心。而且没有孩子陪伴的夜晚,她肯定会万分牵挂睡不好觉。她跟婆婆表示想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希望婆婆同去,这样自己下班回来可以每天陪伴女儿左右,教女儿认字、数数、唱歌、画画等。婆婆表示老头子身体不好要照顾走不开,给她两种选择:“要么孩子留在老家由我照顾,你们尽可以放心;你若坚持自己带在身边,我可帮不上什么忙了。”
考虑了一个晚上,她决定带孩子回去。她不能想象没有孩子在身边的日子,虽然她知道带孩子回家,意味着将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对于她这样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
第二天,她毅然独自抱着孩子乘长途汽车回了家。
回到家,她马上百度搜索“阿司匹林”。词条上这样写着:如果孩子在患病毒感染性疾病时服用了阿司匹林,很可能得瑞士综合征,一种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死亡率高。所以建议不要给孩子或任何不到19岁的人服用阿司匹林!家里要常备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缓解疼痛和发烧。她舒了口气,幸亏没给八个月的幼儿吃阿司匹林。
她以为丈夫会理解自己的主张和选择。
不料丈夫不但没有站在她这边,还帮着自己的母亲责怪她这么小心眼,弄得比医生还高明。
她又一次委屈极了。
对于她把孩子带回家来这件事,丈夫显得极为不满:“你有本事自己带小孩就自己带去!”
她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丈夫不愿意她把孩子带过来,那样他就被束缚了,无法自由自在跟朋友们吃饭、打牌,他要的是潇洒。
六
现实容不得她再去关注自己的耳朵和那耳朵里的聒噪声。每天一起早,她就要操心孩子的吃喝拉撒,给孩子讲故事、看画报、玩玩具、念儿歌,烧饭、洗衣服、给孩子喂饭,带着孩子去公园看绿树鲜花呼吸新鲜空气,带着孩子去超市买各种生活用品……紧张的生活没有任何时间让她再沉浸在恐惧、忧伤与哀怨之中,甚至没有任何空隙跟耳朵打个招呼。现在她要对付的是如何凭一己之力照看好孩子。
丈夫每天依然很晚回来,回来时她和孩子早睡着了。他依然潇洒,工作之余就是饭局、牌局,包括她所不知道的活动。爱好不同,作息时间不同,她与丈夫之间的话语越来越少。
她知道丈夫是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既然你想自己带,你就自己带去,直到自己去向他妥协。后来她才明白这就是“狠”,可惜自己做不到。不但不分担家务,丈夫还不肯拿出工资卡和奖金交给她维持日常开支,家里的一切需由她自掏腰包,除了孩子的各项花费,她自己能省则省。他就像局外人一样,冷漠地站在高处,似乎一切与自己无关。她知道丈夫在故意刁难,但是她绝没有要低头的意思。
可是她不久就要去上班,总得有人帮忙带孩子啊。
她首先想到请保姆。她跑到中介公司,公司给介绍了一个保姆。
第二天早上,保姆到她家里来熟悉情况。那是个50多岁的妇女,走进她家,那保姆先是用眼白瞟四周,那眼白如一把刀子犀利冷峻,似乎立马能把贫与富剖析出来。接着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很老到地把双脚盘起来搁在沙发上,分明盘出了傲慢两字。保姆开口第一句话便是:“我以前是专门在老板家里做的,住在别墅里,月工资嘛比较高的……”“好好,阿姨你以前拿多少,我们也付给你多少。”她赶紧回应。保姆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她对阿姨说:“阿姨您现在去医院做一个肝功能测试吧,钱我会付给你的。明天就可到我家来照顾孩子了。”一听这话,阿姨的眉宇间蹙成一个小鸡爪,“嗯,那我就去体检。”她迅速挪下双腿就出门了。傍晚中介回话说那个保姆家里有事情不来了。她心里知道,那保姆因为要体检才临阵脱逃的。
她不想再招,担心再碰到此类的人。她想到了母亲,唯一的办法是请求自己的母亲来帮忙照看。说实在,她很难说出口。母亲家里确实有个保姆,为人非常善良、勤快,是她单位里一名临时工的亲戚,是她喊来在母亲家当保姆的。因为弟弟生了个儿子,侄子也才几个月大,而母亲多年胃病,身体很虚弱,照顾不了小孙子。她真不想麻烦、拖累母亲。万般无奈之下,她只能向母亲求助,母亲总是心疼女儿的。果然母亲答应来照看外孙女,只是说她带孩子只能每天窝在家里,因为母亲的胃病承受不了到外面去的折腾。她已经感激不已。
从此,早上七点一刻她出门上班,中午在单位买好饭菜骑自行车赶到家里,喂好孩子,自己匆匆扒一口立即哄她睡觉,等孩子入睡,她悄悄地爬起来赶紧去上班。下午一下班,她又赶紧回家,接替母亲带孩子。孩子吃饭得喂一个多小时,她耐着性子哄,哄完晚饭,她又要陪孩子数数、听儿歌、背唐诗,然后陪着女儿睡觉。等女儿入睡,一天落幕了,自己也累得睡着了。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她突然发现自己睡眠好多了,孩子睡着她也睡着了,她已经忘了耳朵里还有聒噪声,她已经不在乎这个敌人了!
七
丈夫依然每天晚出晚归,而她每天早出早归,两个人的生活轨迹逐渐拉大、拉远。丈夫即使偶尔回家来吃晚饭,进门逗孩子三分钟,就顾自在电脑上玩游戏或者打麻将。她若差丈夫给孩子泡杯奶粉、换条裤子,他就蹙着眉头说:“别老拿孩子烦我!”有些时候她对丈夫说,带着孩子真够累的,他竟然冷冷地说:“你不是自己要带嘛,不用跟我来诉苦的。”
她再一次沉默。她发现自己对丈夫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隔膜。她真不知道,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丈夫,心为何这般冷酷。不知道他把亲情这个词汇扔到哪个旮旯里了。有一次,实在很累的她提出让丈夫带一天孩子,结果晚上回家女儿哭着对她说:“妈妈,我要你带,爸爸今天对我大吼,像狗吠一样。”幼小的女儿居然用狗吠来形容对爸爸的不满,她感到十分震惊。抱起女儿的时候,她的泪止不住往下流。
转眼间,年关临近,快要过年了。
一次吃饭时,丈夫淡淡地问她:“今年过年一起去我老家?”
想到丈夫多日来的冷漠,对孩子的不管不顾,想到自己为孩子承受的那么多委屈,她想也没想脱口而出:“不去。”
这顿饭成了冷冷的一顿饭,一直冷到除夕的年夜饭。
大年初一吃过午饭,丈夫抱着孩子下楼去溜达了。
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见丈夫抱着孩子回家。等到下午三点多,纳闷的她打电话给丈夫,才知道丈夫没跟自己打个招呼,就抱着孩子打的去老家了,而这里距离他老家有100多公里呢。
不管是临时起意还是有意为之,你也该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吧,也太不尊重人了,这一次她心里特别不痛快。这样的不尊重,已经数不清了,积累起来就像一颗炮弹或是冰雹落在婚姻这张薄薄的纸上。
她耐着性子等了五天。这五天里,耳朵的鸣叫,仿佛乘虚出现,她捂着两个耳朵,恨不得让那个音魔在里边窒息。她想念女儿,直到五天后丈夫带着孩子回家来。
她希望丈夫回来能够心平气和地主动跟自己解释一下。可是丈夫没有一句话,依旧冷冰冰的,她显然无法释怀丈夫如此无动于衷。
于是,她主动提起:“大年初一,把孩子抱回老家,也不拿换洗衣服,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还一直等着你们呢。”
她知道,这次没有回他老家,丈夫又在耿耿于怀了。在把孩子带回家自己养这件事上,丈夫的耿耿于怀将他俩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现在,他又因这事为难她。其实不是她自己不想去,是因为丈夫对她的态度实在让自己失望。如果丈夫平时体贴安慰她,与她一起分担家务、养育孩子,她怎么会拒绝呢?
谁知丈夫的语气又冷又重:“何必要跟你说!说了也是白说!”
居然还是他有理。她郁闷极了,心里升腾起一股无名之火。两个人爆发了结婚以来第一次大吵。多日来窝着的火终于迸发出来,多日来的忍耐和忍让使她无法平抑自己内心的怨怼。她指责丈夫太不尊重人,没有爱心,没有家庭责任感,连亲女儿都不管不顾。她看见丈夫连忙去关闭门窗,她想到:耳朵像一间关了门窗的屋子,里边在大声喧闹,外边啥也听不见。
丈夫狠狠地丢下一句话:你自己去养吧,别来烦我!然后嘭的一声,摔门而去。
这一晚,丈夫没有回家。第二天,他直接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她突然明白,这一切都是丈夫的一个预谋,一个不露声色、步步为营的预谋。咖啡馆的那一幕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饭局、麻将都是烟幕弹,每一次冷战就是他用来对付她的杀手锏。每一次找茬都是其中一个预设的环节。
对于他的出走,她内心出奇的平静,因为她觉得自己并没做错什么。唯一遗憾的是,她算计不过他。
半年后的一天,她提出来,咱们离婚吧。
丈夫没有表示出多大的挽留,他说:要么要房子,要么要孩子,你自己选择。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孩子。虽然当初这个房子的几乎全部款项是她父母赞助的。但是她想,对于自己来说,孩子是最宝贵的财富,孩子的价值远远高于房子。
她毅然搬离了自己曾辛辛苦苦买下并装修的房子,同时做好了为孩子牺牲一切的准备。她暂时没告诉父母离婚的事情。她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她想:那样耳朵里的声音就不会乘虚而出。她哄女儿入睡,讲童话故事,有时,她也沉浸在童话之中。她发现女儿已经睡着了。
于是,耳朵里响起声音,她说:你又光临了。起初是一种,随后是多种,各种人呀车呀的声音,还掺杂着警报器的鸣声。她跑到阳台观察,一切静止不动,仿佛世界停止运转,一个寂静的夜晚。很可能,耳朵收藏、贮存了白天的声音,还有过去的声音,然后夜深人静,在她的耳朵里重复播放。
她不再感到害怕和绝望,看着躺在身边熟睡的孩子。她相信:明天的太阳依旧灿烂。她也相信:自己一个人照样可以把孩子养好。至于耳朵里的聒噪声,她将丢弃在记忆的角落里,当然可以像老朋友一样对待它,与它共存,慢慢适应它,直至生命消失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