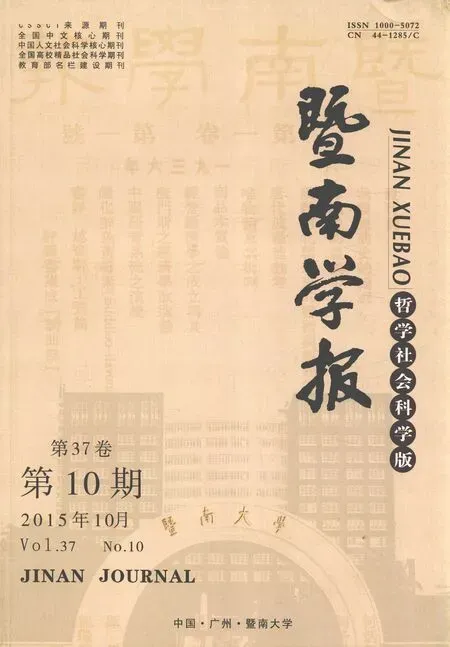近代日本基督教学校与政府关系述略
张永广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 200020)
19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的殖民扩张与基督教的普世宣教运动,一起冲击着封闭的东方世界。既作为一种传教工具又体现着西方新式教育形态的基督教学校,亦在各传教区域内广为兴办。近代的普世宣教运动同当地民族国家的形成相伴随,“政教关系”的演变即成为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之一。在近代东亚地区,中国与日本均是基督教的重要传教区域。目前国内学界已开始对近代日本基督教的历史展开研究,但尚缺乏详细考察基督教学校与政府关系的成果。本文即拟分析日本不同历史时期基督教学校与政府之关系,并进一步探寻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
一、明治时期日本基督教学校的国家主义化
近代日本基督教教育前30年的发展历史(1859—1890)以1873、1883为时间界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73年前,日本虽在美国黑船舰队叩关后开放国门,但依然延续幕府时期的禁教政策,对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传布进行严格管制。由于基督教禁令的存在,传教士活动受限。因此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教育大都为家塾形式,即使出现正规的基督教学校,规模也较小。1873年禁令废止后,基督教教育有了一定发展,规范的基督教学校开始建立。至1883年后,基督教教育由于顺应了国内欧化主义的潮流进而有了较快发展,学校规格也得到很大提升。明治初期的脱亚入欧政策,为基督教教育在日本的最初发展提供了相适宜的政治气候。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国家意识的萌发及主权观念的建立,近代日本的教育变革主要体现为政府领导下的“自上而下”运动。私立学校尽管被允许存在,但一直没有真正的合法地位。随着日本公立教育的逐渐完善,真正留给基督教教育的发展空间实际非常有限。
1890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颁布了作为国民教育道德法典的《教育敕语》,标志着明治绝对主义政权在思想上的胜利。对《教育敕语》的敬拜以及相关规章的制定无疑给信仰自由带来威胁,而稍后爆发的“内村鉴三不敬事件”,则把基督教推向被批判的境地。在“国家主义”的强势话语下,日本的基督教运动陷入困境。为摆脱社会舆论的批判,日本基督教界努力消除自身的“洋化”色彩,并竭力满足“本土”社会的需要。为此,日本的基督教会开展了“自立”运动,基督教学校也调整课程以顺应社会需要。而稍后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不仅转移了舆论的视线,使日本的反基督教运动有所减缓;更为日本的基督教界提供了向国家表达“忠诚”和参与社会“服务”的绝佳机会。日本的基督徒借助战争之机从反基督教运动的漩涡中挣脱出来,通过各种服务工作表达对国家的“忠诚”,从而赢得了国家和民众的认可;基督教教育也得到恢复和发展。1894年后日本又接连发动和参与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基督徒也有了更多的机会来表明对天皇和国家的忠诚。对战争的参与体现了日本基督教教育发展的国家主义化倾向。
日本基督教教育的国家化发展路径更主要地体现在,其不断受到文部省相关教育法令的限制,进而逐渐被嵌入进国家教育体制之中。由于日本公立教育系统的发达再加上基督教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基督教学校虽保有私立学校的身份,却已经不得不依附于公立教育之上;而且相对于公立学校的师资与设施,基督教学校也被不断地边缘化。接受文部省的政策,纳入到它们的管理之下,对基督教学校来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日本自开国以来就逐渐向强大的主权国家迈进,并建成了体系完备的公立教育体制。基督教学校在建立之初虽因其英语教育的特色以及作为新式教育的代表而受到欢迎,但之后不久就在公立学校的迅速发展下丧失了锋芒。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基督教运动淡化了其外来色彩,也使它们同国家的观念和利益保持一致,而随后颁布的《私立学校令》则又对它们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基督教学校不仅在教育行政上要受到文部省的监管,而且在具体的设施、师资等方面也要达到文部省所制定的有关规定。基督教学校被深深嵌入到国家教育体制之中。
嵌入国家教育体制之中也意味着日本的基督教学校被逐渐边缘化。在相关教育令的限制下,一些原本开办较好的基督教男校被迫接受为“指定学校”,而不能使用“中学”的名字,这本身即降低了它们在民众中的“威望”和“信誉”;再加上它们的学生在最初还不能直接升学,这都使它们遭受了巨大创伤。日本的基督教学校逐渐成为公立教育的附庸。它们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同公立学校相比,而且在同其他私立学校的竞争中也处于下风。就质量而言,它们不及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数量而言,它们也没有佛教寺院所开办的学校多。
面临这种被“嵌入”和“边缘”的局面,日本的基督教领袖也不得不承认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必须遵循两个原则:首先是整个工作应该在同政府合作的精神下开展,“不是抱着对国家教育政策的谴责和反对,而是应该有博大的胸怀,用欣赏的感激的态度来实践最高的国家理念”;其次是要同国家的教育体制相一致,尽管日本的教育系统与英美相比有很大不同,但基督教学校绝不应该是外国化和孤立的,“而应该通过耐心、努力与贡献,在国家生活中赢得尊重并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教士也深刻体会到必须紧跟政府的教育政策,否则就会丧失参与教育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为消除自身的“洋化”色彩以及满足“本土”社会的需要,日本的基督教会开展了“自立”运动,基督教学校也大都通过组建法团公司的形式继续开办,并申请当地政府和文部省的认可;因此它们也成为受国内法律约束与保护,所有权及管理权均隶属于日籍人士的本土机构。即使如此,近代日本基督教学校的整体规模也不大。
二、战前日本基督教学校的军国主义化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由来已久。1880年修改后的《教育令》中,就开始出现“尊皇爱国”的字句。1890年10月30日,日本天皇亲自颁布《教育敕语》,军国主义及其教育思想更是暴露无遗。随后日本政府即把《教育敕语》奉为教育的总纲领,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的最高宗旨,标榜天皇是道德的化身。为了把“国体精神”和《教育敕语》精神贯彻到学校,日本政府开始对学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1917年9月寺内内阁设立了直属于内阁的临时教育会议,会议的审议内容涉及整个教育制度,并针对“一战”以来思想意识的变化,决定采取贯彻国民道德、增强国体观念的国家主义方针,把“造就护国精神的忠诚臣民,来发扬国体精华”作为振兴教育的目标。
日本教育军国主义化的正式确立是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工农运动进行镇压以及对国民思想进行统治的过程中形成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民主思想增长很快,到1926年成人已经获得选举权;而俄国革命的影响也激发了日本的工农运动,促进了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潮的发展,并导致了其对资本主义的憎恨,日本社会也陷入不稳定状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更是彻底加强了义务教育的军国主义化和对高等教育的镇压。它们强制儿童和中小学生给日本军人写慰问信、送慰问袋,动员他们欢送出征士兵和持旗游行,并利用修身、国语和国史等课程作为培养天皇的忠良臣民的工具。此外,日本政府还向小学校普遍发放天皇照片,建造供奉天皇照片的奉安殿,把礼拜天皇照片和教育敕语规定为义务。而文部省又从1933年起将全部国定教科书改为军国主义内容。到1936年更是设立了“文教审议会”,开始对“关于国体观念的彻底和振兴国民精神的重要项”进行调查和审议,决定让学校变为“国民训练的场所”,把从国民学校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纳入“皇国之道”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体制中。
面对教育体制的日益军国主义化,置于其中的基督教学校自然无法幸免。1928年6月,为庆祝天皇登基,日本宗教界在东京召开会议,文部省长官和其他部门的长官都出席了会议,希望宗教团体为稳定社会思想做出贡献。1928年5月23日,文部省又专门邀集基督教教育机构及其他组织的领袖开会,虽然在名义上是鼓励基督教学校能在这充斥“危险思想”的时期继续致力于精神教育,但实际上是把它们当作进行“思想统制”的工具。基督教学校连同其他学校一样被迫开设军事课程,并由军部派遣的军事教员负责教授。以中等学校的学生为例,每星期要接受三小时的军训,自入学的第一年起至第五年毕业止;每学期有野外露营,实弹射击等练习;到最后一年,要实行兵营训练,生活完全军事化。虽然最初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校长都不赞成开设此类训练,认为这种军事操练没有任何好的效果,而且这方面的功效也可以通过其他课程,如体育课来获得;但随着军部自1931年起开始逐步控制日本政府并把其引入战争,他们也很快发现进行军事教育是政府所强加实施而又无法规避的。之后,文部省对基督教学校的思想控制越来越严。
在日本全面军国主义化的进程中,基督教学校在这一泥潭中越陷越深。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文部省对宗教教育的态度转变曾一度被基督教教育人士当作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不久他们就体察到对基督教学校的安抚只不过是政府用来进行思想控制的手段。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快推动军国主义化的步伐,基督教也逐渐沦为国家的附庸。1930年,日本政府建立了神道教系统调查委员会,意欲证明神道教高于其他宗教,从而以它来代表国家宗教的品格。起初,基督教界联合起来抵制这一创立国家宗教的做法,但这一立场因20世纪30年代远东冲突的加剧而改变。当时的基督教会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解释,日本化的基督教可以参加国家神道教的仪式,基督徒也应该将它们的生命献给天皇。这种观点已同正统的基督教义背离很大,基督徒对此解释的接受也预示着在战争期间将会与政府合作。与此同时,所有的学校都被要求设立神社,很多基督教学校因信仰冲突问题遭受到舆论的批评和政府的压制,而且政府还像基督教学校派遣陆海军军官向学生进行军事教授和军事训练。这种军事训练不仅包括操练、急行军,也包括战术和军事理论的学习;特别是每年的军营生活、实枪射击以及每年高级军官的视察。另外,在校园中也会安排执行急行军、埋伏、攻击、刺刀练习以及其他实战训练。在军事教员的宣传与鼓动下,基督教学校的军国主义色彩也越来越浓厚,一些右翼学生也展开反基督教的运动。1935年,同志社大学商业部主任因将神社中所供奉的像移走而受到极右学生的攻击;1937年初,学生右翼组织围攻大学教堂反对继续进行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同年,同志社大学校长因在大学集会上误读教育敕语而被要求辞职。同志社的这一系列反基督教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在1936年,立教大学校长同样因为误读帝国法令而被迫辞职。教内人士也清楚地知道基督教学校之所以成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全在于它们同美国的联系和基督教的色彩。在这种处境下,再想开展有效的宗教教育已不可能,在军国主义化的兴盛下基督教学校“基督化”特色的削弱也就在所难免。
三、战时体制下日本基督教学校的窘境
随着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更大范围内的扩军备战,日本政府很快把国内体制加以战时化。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本就颁布了国民精神动员令,实施精神上的统一;而后又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对战争所需要的所有劳动力、资源、资金和设施等进行统制。国家对宗教方面的管制也越来越严。1938年3月,全国宗教领袖会议在东京举行,文部大臣要求各宗教领袖与政府密切合作,对民众做好充分的精神动员。1939年4月,内阁政府制定了《宗教团体法》,规定在非常时期国家有对宗教进行监督、管制、保护与培育的责任与权力,而各个宗教在战争方面也应该更有效地与战争合作。由于长期思想统制和宗教镇压,以致这一严格限制宗教自由的法案颁布后,反对的呼声却寥寥无几。日本基督教会甚至对宗教团体法案的通过表示欢迎,认为它“最大限度地承认了自主的统治”,并对基督教的发展最为有利。日本的基督教教育逐渐被纳入战时体制下,它们虽对此表示出顺服的态度但仍遭受到来自政府的压迫,虽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但仍处于窘迫的境地,而且随着战争的深入也愈发艰难。
事实上,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基督教会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政府的行为与决策采取了支持和顺服的态度;但“基督教是违反日本国体的外教”的传统意识并未淡化。这表现在对待基督教学校的态度上就是,仍意欲褪除其基督教色彩。在1936年时,日本某杂志刊登了《文部省与宗教学校》的文章,谎称文部省已向全国各地长官发放通告,禁止在宗教学校进行宗教宣传、宗教教授与宗教仪式;学校的建立及认可需要经过严格审查,各派的宗教宣传应与国体相符等。这则通告虽被文部大臣予以否认,但因被众多报纸杂志转载以致在日本国内形成了禁止宗教教育的舆论。对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各地区政府均向基督教学校施加压力,强迫它们成为认可学校,这也就意味着要放弃宗教教育和宗教仪式。由于文部省并没有修改已有的法令,因此各地区教育长官实际上也没有权力干涉一个非认可学校在宗教教育方面的自由,所以各地的基督教学校对这一干涉进行了抵制。不过各地教育长官则通过加大对非认可学校毕业生的限制、在注册及学费等一系列问题上设置障碍来逼迫基督教学校接受认可,而如果它们再进行抵制的话就可以勒令它们关闭。
日本各地政府对基督教学校施加迫害一方面是源于基督教的“外来”色彩,一方面则是对宗教教育的不满,其最终目的是把其置于军国主义的战时体制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基督教学校也主动做出调整,以表示对政府的顺服。1938年8月,当时日本国内著名基督徒、社会改革者贺川丰彦出版《国家与宗教》一书,论述了《教育敕语》与《圣经》的关系:《教育敕语》是天国理想的具体化表现和日本帝国的统治者,理应得到民众的严格遵守,日本所有的教育都必须按照教育敕语的目的开办,但这与依据基督教原则的教育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后者在一般教育之外注重培植宗教情感”。贺川是想借此来证明宗教教育与国体相符,为基督教学校争取生存空间。在对待政府的对外扩张上,各基督教学校也表示支持,对日本政府的战时体制采取合作态度,并配合政府参与所谓的振兴满支、南洋教育以及新文化建设等。
随着战争的继续,各地政府与教育部门对基督教学校的管制与压迫越来越严,各地基督教学校的反应也不尽相同。仙台地区的基督教学校就被迫屈服,宗教教育和宗教仪式被迫停止。东北学院被要求删除建校章程中所有涉及基督教的条款,不能向学生宣称这是所基督教学校。东京的青山学院情况稍好,但为满足政府要求,也对原有的章程在语言上做了变通,将学校的目的即“用基督教训练学生”更改为“用基督教的原则来训练学生”。当然也有少数基督教学校为保存基督教的特色做艰苦的支撑,名古屋的金城女子专门学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金城女专能做到这点并非因为当地政府的宽容,而在于基督徒校长的坚持。名古屋地方政府对待基督教学校的措施同样十分严格,它们要求金城女子专门学校删除学校章程中的基督教条款,停止所有的宗教教育及仪式,“学校只是进行教育的地方,如果学生想礼拜,可以去教会”。面对政府的压迫,金城女专校长极力进行抗争。不过也正因此,学校教职员及学生每天的礼拜、早晨的祈祷会、圣经教授、布道会等一切宗教方面的行事都受到监控和压迫。宪兵队长对每个寝室进行检查,并严格监督神社参拜事宜,校长和传教士的行踪也受到它们的监视;文部省派出的两名督学官以及本地教育部门的十数名督学经常视察学校的教学内容、设施、会计等一切事务,还对校长进行诘问,劝导学校采取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教育方针。
祛除基督教色彩的压力不仅来自于校外,也来自于校内。1937年2月,大阪同志社俱乐部理事伊坪伊那太郎就组成“基督教教育改革期成会”,公开反对同志社大学的基督教教育,建议删除“基督教为德育基础”的条款,并印刷一千本小册子分发给校内外各方人士。学校教师分裂的局面在作为军事教员的陆海军军官入住校园后更加严峻,基督教学校所面临的很多困难都是直接起源于这些军官,他们形成小的党派来分化教师,并经常挑起校长与教师之间的冲突;他们还借用军队和警察的势力以求全面掌控学校。关西学院就曾一度面临这种局面,部分学校教师在一些有影响力的校友和军事教官的支持下胁迫校长小崎道雄要么删除学校的基督教条款要么辞职,他们甚至动用秘密警察来对其恐吓。小崎道雄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他并没有因恐吓而屈服让步,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给家人留下遗嘱。小崎道雄也最终在一些倾向于基督教的教师和董事会的支持下成功平息了这一骚动,“基督教依然是学校里的教育口号”。相对于关西学院的成功护校,东京的青山学院则没有那么幸运。起初,一批非基督徒和有浓厚军国主义思想的教师于1942年底采取一系列措施意欲夺取校长职位,但并未获得成功反而遭到董事会的解职。1943年4月,这些被开除的教师和另外一些反基督教的校友,联合学校的军事教员以及警察部门,一起鼓动学生罢课,并让他们公开反对学校里的基督教教学和教堂礼拜,进而要求学校校长、校友会主席和董事会主席辞职。为平息学生运动,董事会要求校长辞职并选举一位前海军军官担任新校长,以方便同军方合作。新校长任职后,立即开除了一大批教师,包括讲授基督教道德和基督教历史的教授和学校的牧师等;而且有进一步废除了英语和商业课程,代之以飞机制造和其他机械课程。
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政府对宗教管制也越来越严,1941年所有的新教派别被统编为“日本基督教团”,但圣公会却拒绝加入。这也导致其所属的学校在战争期间尤其受到野蛮的对待。立教女子学校被改作工厂和商店,教堂也被大型机器所毁坏。立教大学更是成为日本基督教学校中受压迫最严重的。1943年,立教大学更换了校长,宣布“停止七十多年来立教大学一直为基督教学校的错误”;废止艺术、文学、宗教等科,重视发展军事科学;虔诚的基督徒教师被赶出校园或解职,学生所有的民主生活被终止,除军事训练外学生没有其他课外活动;学校科学楼基座上“为了上帝的荣誉而教育基督青年”的话也被抹去。学校的教堂被用作军队的仓库,教堂中的长凳也被征用作建造防空袭的掩体,漂亮的屏风、讲道台、诵经台以及唱诗班的椅子被用作柴火。整个学校已经没有一点基督教的元素。
战时日本的基督教学校普遍受到各地方政府的严格监控,校政受到军事教员的严重干扰,学生被要求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甚至连英语也被从课程中删除。这种局面在战争的后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学校被征用、学生被征召。来自于反基督教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压力越来越大,基督教学校也充满着国家主义的形式,如废止教堂礼拜,用爱国歌曲代替赞美诗等。而且很多学校放弃对基督教的坚守,长崎的治水女子学院在战时的改变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校长虽然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但却替政府使基督教学校彻底地国家主义化,而且祛除了学校中所有基督教的影响。他关掉了学校的教会,开除了基督徒教师,让军事教官给女生进行军事训练。他还在东京召开的教师集会和长崎的报纸上公开宣称治水女子学院已经不再是一所基督教学校,删除圣经教育,并把每日的教堂礼拜变成国家主义的俱乐部会议。学校的体育馆也改造成焊接设备厂来为军方服务。
至战争后期,这种占用校舍的局面更加普遍。1944年,政府命令所有的学校只保留很小的部分,其他都给军队使用。关西校园为日本海军开放。至战争快结束时,日本的许多学校又成为战时最重要的工业地。在1945年早期,生产飞机的军工厂迁入学校礼堂和法学部的建筑。神户女子学院的室内体育馆变成战时的工作车间,三菱在战争结束前的六七个月租用了同志社的部分校园用作实验室和研究场所。宫崎女子学校校园内也被安排了一个雷达工厂。此外,日本政府还对所有学校的学生颁发动员法令,男生因为军事征召而被迫牺牲,女生也被征集到军需工厂进行工作。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学生数量也急剧下降。因征兵或征召,关西学院学生从3500名减少到只有250名全日生。战争期间,同志社的学生从6000名锐减到1500名。战争意味着悲剧,1945年美国空军对60多个日本城市进行了空袭,许多基督教学校和基督教机构都遭到破坏。投向广岛的原子弹也使循道公会的女子学校毁灭,有350名师生员工丢掉了性命。
四、余 论
综上所述,基督教学校在近代日本始终处于政府的管控之下,而这同日本民族国家建构方式密切相关。日本被迫开放国门后,便开始着力于向统一的近代国家迈进。近代日本民族意识的再造与自我完善,是通过对氏族神和氏族领袖的强烈崇拜、认同和追随来实现的。由于天皇是融全国各氏族部落为一体的最大的氏族共同体内的最高的氏神,是得到神道——神话这一传统的话语体系和话语背景支撑的“人神”;这也使得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依然没有摆脱十分落后的氏族政治的范式,即往往通过神道教仪式和氏神的介入来完成,通过神道家的参与和确立起至高无上的氏族神来实现民族认同的最大化,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实现统一民族的再造。因此,日本是通过对天皇制度的全面打造,来完成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祭政一致的国家体制意味着尊神道教为国教以及对基督教的排斥。在日本集权式、宗教式的天皇制民族国家之下,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必然面临着很大限制。基督教学校在与政府的长期交往中始终处于下风,其所本应具有的“基督化”特色也在战时体制下丧失殆尽。直到战争结束日本开启民主化进程,并用自由教育来代替军国主义教育后;基督教学校在日本的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