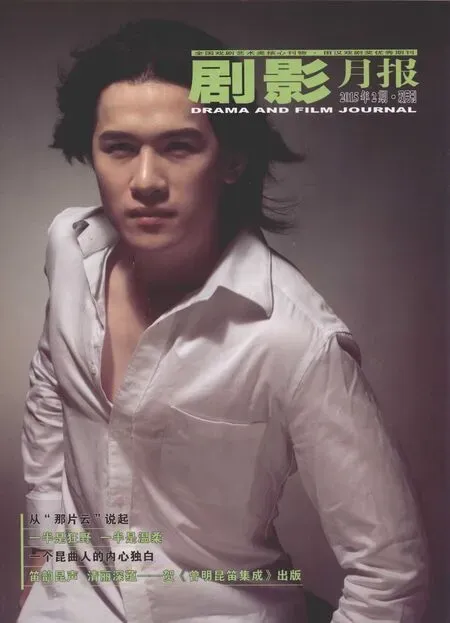昆韵美和归于宗迹
——论文化创意产业中传统戏曲演出的困境与出路
■周光毅
昆韵美和归于宗迹
——论文化创意产业中传统戏曲演出的困境与出路
■周光毅
“泽曰南湖,誉满摇城二千年;腔称水磨,风靡昆山六百年。”
周庄“古戏台”上的对联,不能不说写得极其唯美和秀丽。上句将这个江南小镇用水、用城和岁月,描绘了这个江南古镇特有的风貌;下句却是用水、用山和历史,写出了“昆曲-水磨腔”发展的辉煌和过去,百戏之祖的昆曲其中秀美和永隽,在文人骚客的眼里真是美轮美奂。今天,就在这个远离尘嚣的昆曲水乡历史舞台上,江苏省昆曲剧院的艺术家们,不间断地上演出一幕幕精彩的折子戏,让昆曲文化的意蕴永远飘荡古镇的乡土之间。然而,游客真正能驻足欣赏昆曲演出的人并不多,旅游景点的昆曲演出并不是主体,高雅艺术的陪衬恰恰显露出了中国戏曲演出的窘境。昆曲演出的冷落不在是单一的经济现象,昭示着戏曲演出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尴尬时刻。根据2013年江苏文化创意产业报告,全年度的广告收入是190.07亿,广播电视收入是259.74亿,出版发行是13377.8亿,旅游产业是655.2.9亿,动漫产业的收入是3.64亿,而整个全省演出产业收入只有1.47亿,并且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那么对于昆曲就不得不处在了从属的低位。
文化创意产业戏曲演出的困境,主要是来自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的迅速扩张,整个社会的节奏在加快和变得急功急利,人们埋头于生活带来的各式各样的竞争,而无暇顾及文化产业对社会发展的联系;另一方面影视和多媒体的技术革命,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点食“快餐文化”,剧场的演出当然就很快地成为了“奢侈品”,成为了“文化小众”欣赏的天地。除了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外,当然也有昆曲艺术本身存在的更多局限,就昆曲的演出效果来说有着双重性:其一是传统文学性的典型特征,其二是昆曲演出中的写意性风范。这两点的艺术特征在昆曲的发展中,是使其成为中国戏曲典范的基础,按照世界创意产业研究的经济概念,戏曲演出作为文化创意理论的一部分,其“文化价值”必须在实现“经济价值”的前提下,才能转变为具有“社会价值”的文化产业永续发展。
一.昆曲的文学性与现代浮躁生活的距离
昆曲的文学性是与生俱来的,其形成的模式与其它剧种不同,这种先有词后有曲的创作形态,更具有文人们笔下的思想流露;昆曲是在元剧和杂曲的基础上成长起来,这两种艺术生态首先是文学烙印,到了昆曲发展的兴盛时期,更多的文人以写昆曲的剧本和唱词为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剧作家和评论家,昆曲鼻祖的魏良辅就是典型的代表,也是中国历史上以戏曲为生活的第一人,至此,昆曲再也逃脱不了附庸风雅之路。昆曲的文学性还表现在政治上的题材,在《浣纱记》《宝剑记》《鸣凤记》等剧作里面,充斥了宫廷思想的斗争的文学性故事,普通市民阶层根本就理解不了其中的含义;昆曲中描写的爱情故事,像《桃花扇》《玉簪记》《西厢记》等剧作,都带有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嘲讽,可是草根市民却是传统文化的护卫者,所以传统的昆曲创作无论在文学上或者内容上,都与普通大众有着相当的距离。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牡丹亭《游园惊梦》是昆曲的代表,汤显祖进行的人物心情写照,其风韵的唯美和唱词的精妙,虽然成为了中国戏曲文学的绝唱,但相对没有相当文学修养的人来说,其中的隐晦和生涩也可见一斑。不仅如此,昆曲所表现的人文情愫和内容,更是贴近大多数贵族的欣赏口味,而这些人也是昆曲艺术的批评和诠释者,正是这种昆曲的普遍欣赏形态,使得昆曲的最原始的创作和演出,打上了清晰的阶级烙印。昆曲的欣赏者们循着这样的坚持,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终于将昆曲束之中国文化的顶端,结果是使得昆曲与大众的鸿沟,在后来未来的社会中越来越大。
《窦娥冤》是昆曲中少有贴近生活的剧目,但唱词中的文学性依然显而易见,而念白更是建立在合辙押韵的传统文体上,加上伴奏的独特附和形式,让整个演出显示出文人对于社会的哀怨,相对于后来移植过去的剧种的演出效果,不得不说昆曲的《窦娥冤》更表现出太多的苍凉,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昆曲文学写照的本身。昆曲大众化的改革诉求,从诞生到今天就没有间断过,从晚清以后昆曲的文学创作开始减少,到了近代更是寥寥无几,原因是具有昆曲积淀的文学家,相比起过去是越来越少。即使文革中的样板戏移植活动,昆曲既没有创作出任何的革命剧目,当然也没有移植现代文学戏剧的可能,就说明了昆曲的文学性是非常特殊的文化形态了。
昆曲作为汉文学的典型代表,在明代晚期开始被挖掘出来了,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进入宫廷,成为皇家的娱乐的主要形式,明朝皇帝不但喜欢看昆曲,更是喜欢豢养那些文人撰写戏文,对昆曲的保留和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但是在改朝换代以后,满人统治者并不能理解其中的内涵,对昆曲的私人交流演出内容,从文学的角度基本上是很难明白,于是下令禁止了这样的演出。为了生存昆曲艺人们开始了饭馆酒肆的演出,这就形成了最广泛的折子戏的改编,经管如此,折子戏的并没有降低昆曲的文学特征,相反文学精髓更是在唱腔中浓缩。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经济财富得到了重新的尊重,所以又出现了昆曲的大型演出的效果,特别是白先勇先生投资排演的 《牡丹亭》,原汁原味地在世界各地,体现着其中国文化的风范。
然而,中国社会近些年来的文化方向,在经济领先政治思想指导下,由于缺乏文化创意产业理论的支撑,社会对于文学艺术的忽视,使得戏曲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大潮,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情况,而昆曲作为文学性最强的戏曲,当然会遭到更艰难的冷落和遗忘。事实上,在当今社会中文学与经济的矛盾,在整个世界中都随处可见,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坚持,还是让经济大潮吞没自己。美国的纽约百老汇有着几十家的小剧院,上演的都是极具文学性的剧目,而且是常年不衰的演出状况,难道美国的经济没有冲击他们的文学性内容吗?在这些小剧场里面,欣赏者可能是初次的观看也可能是重复,但是演出的欣赏是建立在对文化的理解,是小众艺术相互慰藉的天堂,整正的戏曲文学在这里绽放出光辉。
在周庄的古戏台前笔者见到了昆曲的爱好者,在寒风中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折子戏,感叹着缺少观赏昆曲的机会和见识,面对这些远道而来的艺术文学的倡导者,仿佛看到了昆曲原来的美好,在这个有限的江南水乡的演出空间里,昆曲艺术的文学性魅力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新时代的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理论指出:“任何人包括科学家、商人甚至是经济学家都可以有创意。”这里要强调的其中的创意不是创作,而是对于昆曲演出整体的认识,昆曲演出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学上的创作、欣赏和批评,历史上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也一样。那么,将昆曲的演出提高到“认识经典”的层面,让昆曲回到绝唱的”文化价值“中,昆曲中演出中的“经济价值”才能够实现,这也是昆曲艺术本来的美妙。
二.昆曲的写意性与当代欣赏趣味的矛盾
昆曲的写意性表现在唯美主义的追求,首江南的“昆曲-水磨腔”调将感情中的如泣如诉,通过笛子、二胡、古筝伴奏更有风情,演出中的节奏合着观众的回应,铺陈的极具随意而有章法,让欣赏者可以闭目享受而流连于人间的悲欢离合。昆曲演员在身段的表现上,更是具有韵律的美感,他们不需要更广泛的空间,而是运用水秀、扇子、圆场和矮子功,就能将人生的更多感慨表现得出神入化;他们不需要耀眼夺目的灯光技术,也不在意美术的醒目,而是在简朴的舞台上靠人的力量个表现,演绎出文人笔下的种种情愫,唱出人生对于感情的更多体恤,昆曲的写意性也是继往开来的,并且丝毫不容来的半点娇作,正是这样的演出上的最求,使得后来的地方戏曲不等不称谓昆曲为戏的始祖,其中不但是年份上的尊敬,更多是对昆曲文学与艺术结合的膜拜。
从昆曲演员的历史构成来说,相比起其它演艺人员要求更高,昆曲的创作是与今天的有些类似的,故事的创作者通常是排演的人员,他们在构思整个作品的时候,已经对于整个演出有了想象,这就要求演员的修养能够表现其思想。除了专业的演艺人员以外,昆曲的票友组成也与其它剧种不同,成员大多是经济较为富有的阶层,包括民间的优秀乐师、演艺人员和修养教高的妓女,这些人的参与更是提高了昆曲的地位,使得昆曲的欣赏与演圈在了一定的社会高度。昆曲被社会富有阶层介入以后,早期演出中的服装华丽更是让演出锦上添花,所以昆曲的演出是“高雅”的,不仅仅来自于昆曲文学上的追求,更有整体演出的惊艳,成为了当时最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形式。
清朝中期的时候特别是乾隆年间,昆曲的表现形态很快地被皇帝发现,下诏将昆曲演出成为共同御用的娱乐,并下令宫廷的专业文官研究和撰写新的连本大戏,这样的举动当然是对于昆曲的全面恢复有着重要的作用。可是因为其写意性太强和过于含蓄,整个演出显得非常的恬静,特别是唱腔的过于委婉和冗长,加上晚清的文人在昆曲艺术上的理解不够,也没有更新的剧目出现,虽然昆曲也从“雅”在向“花”的方向做些尝试,但是禁不住本身的写意特征,开始了逐步显现出一种疲态。另一方面,真正能延续昆曲创作的文人,在整个晚清后期也是屈指可数的,昆曲渐渐地成为了宫廷戏曲的点缀,也就直接导致了“四大徽班”的进京,新的艺术形式融入了昆曲的大量的形式,但是在内容上也显出灵活,结果其演出的效果地位很快地超越了昆曲,也就出现了京昆戏曲的新剧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共中央一些领导的直接关怀下,昆曲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和重视,当然欣赏者绝对不是一般的观众,昆曲的写意形式被提高到了新的认识,于是在更多的美术门类中也出现大量的昆曲题材,中国画与昆曲的写意共同特点,很快地被挖掘出来就是了,所以在后来的昆曲演出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写意的美术设计,而中国画中也有大量的昆曲内容。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很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哲学的冲击,这种艺术的形式很快被淹没,昆曲的演出地位就成了“化石”,完全是以保留和保护的面目示人,而昆曲的写意形式也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特别是现代化演出的机关布景,演员的麦克风传达效果,让昆曲的原来意蕴成完全消失了,尽管很多艺术家对于这样的“堕落”深表遗憾,但是在大形势下的昆曲演出也是无奈的。
从文化产业创意理论上看,昆曲的写意性表现出来的“经济价值”不仅仅在演出上,文化产品的衍生效果也是现实的,中国化能够展现出其风貌,当然更多的艺术载体也是可以宣传的。美国”迪斯尼”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乐园,不但出售“动画文化”的美感,更是将其写意性的创作风格,表现在一切的旅游纪念品上,一方面在整个“产业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利润,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对于“动画文化”的发展。昆曲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可以想象的,昆曲曲目中的场景是可以再现的,那么更多的戏曲录像、中国美术、昆曲道具和历史曲谱等等,都可以在展现昆曲魅力的同时,创造出保护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当然只有想不到而没有做不到的产业理念,落实到昆曲文化产业需要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只是我们需要整体上的规划和观念的转变而已。
昆曲的文学性和写意性决定了其存在的文化价值,从几百年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个中国伟大的艺术积淀了文化的太多唯美,也给昆曲的发展和创新带来了羁绊,在今天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既然没有能力改变其本质属性,就必须以新的文化创意产业理论,在为其创造一个实现价值的道路。正如我们看到的事实,昆曲发展的现实是其唯美的演出形式,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认识经典”的价值取向,就应该让昆曲还原最初的演出形式,全部大戏的演出证明是有着市场的,白先勇监制的《牡丹亭》是今年来昆曲演出的典范,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告诉我们,“认识经典”的文化创意演出带了的经济效益,也是可以为昆曲带来丰厚的收获,当然,我们在承认昆曲二重性带来的曲高和寡局面同时,从“雅”到“花”过程中出现的折子戏形式,在不失去文化底蕴的种种情况下,即使在周庄的旅游景点不能成为主体,也为我们创造和满足观众提供了条件,为将来的“认识经典”创造出经验和机会。
“腔用水磨,拍捱冷板,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闻之悲泣,雅称当代。余特往谒之,何期良辅已故矣!”《九宫正始》的编辑之一钮少雅用这样的词句告诉昆曲的爱好者,作为昆曲的鼻祖魏良辅已经不在人间了,其中的哀鸣今天依然可以听到。这样的情绪只属于对昆曲故人的缅怀,而面对中国戏剧的今天困境,我们必须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来调整,还原昆曲的历史和发展,我们必须清楚地明白“认识经典”才是昆曲演出市场的关键,“认识经典”才是昆曲市场价值的根本,“认识经典”才是保存昆曲和发展昆曲的唯一道路,希望在将来的历史中人们永远记住,昆曲有过艰难发展的经历,而能够成为永恒的绝唱,是来自于昆曲艺术创作、演出和欣赏的责任。
本文为江苏省2013-2015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江苏省文化创意产业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项目号:2013ZDIXM020)中期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