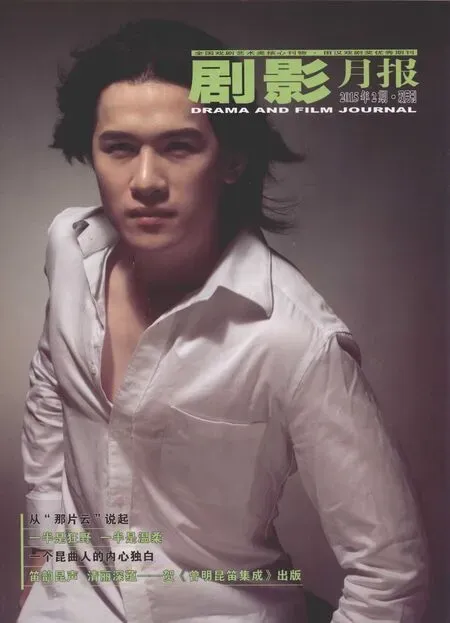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徐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徐萍
我是一位在书坛上说了几十年书的评弹演员。我也是一名酷爱戏曲看了几十年舞台演出的忠实观众。四十多年来,我一边在书坛上说书,一边在剧场里看戏,按理说,说书是我的专业,看戏是我的业余爱好,两者很难搭界。然而,回眸自己走过的足迹,现在我却深深体会到,艺术的品味在很多方面原是相通的,书台和舞台更是紧紧相连的。我通过看戏,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用到了书台上,个中的磨练以及磨练过程中的乐趣真是一言难尽。
四十多年前,我刚学习说书时,教我的先生就对我说,要成为一个说书人,首先要学好“说、噱、弹、唱”(即说表、放噱头、弹三弦琵琶、唱腔)。苏州评弹向来重视“说、噱、弹、唱”,认为这是一位评弹演员必修的功课,只要把这四项本领练扎实了,就什么书台都能上,什么码头都能去了。至于“表演”,很少有人提及。过去还曾经把演员分成两大派:说表严谨的“方口”和说表灵活的“圆口”。但是,不管是“方口”还是“圆口”,你作为评弹演员,必须按照“说、噱、弹、唱”的要求,把书说好。那时候,在我的心中,评弹就是一门仅仅诉诸于受众者听觉的艺术,因此,我很少在表演上下功夫。不仅如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书台上,还按照先生的要求,有书时规规矩矩说书,无书时严格做到 “目不转睛”、“目不斜视”。不与上手作任何眉目交流,当然更不会与台下的听众做任何感情交流。尽管当时已有几位评弹界的前辈如刘天韵、杨振雄等已在探索书台上用各种手段来丰富评弹的表演,但在当时终究还没有成为评弹界的共识。因此,像我这样小字辈的说书人,怎敢在书台上轻举妄动呢?习惯势力有强大的滞动力,至今我们还是习惯地称进书场来的人是“听众”,而不是“观众”。但是,时代毕竟是在前进的,如今,书场里的被我们称作“听众”的人,不但爱听我们在书坛上的“说噱弹唱”,也爱看我们在书坛上的“表演”。我们评弹界也把原来评弹艺术的四大要素“说、噱、弹、唱”改成了“说、噱、弹、唱、演”。多了一个“演”字,这样就不但丰富了评弹的表现力,更扩大了评弹的受众面。现在的书场里,与过去相比,多了不少年轻人,他们不但是来听书的,还是来“看说书”的。我们现在在书台上,也像舞台上的戏曲演员那样,用眼神、用扇面、用手绢、用醒木、用家牲(三弦琵琶)来传达感情,如果是双档演出,两人之间更要求配合默契,情绪必须注意连贯性,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一人在说,另一人啥都不管,只要自己不开口,就没有自己的事。对此,观众的反应是强烈的,都认为这样的书好听了,它不再是过去那样只说不演的平面评弹,而是又说又演的立体评弹了。作为演员,我们也感到这样在台上说书,气顺了,情绪连贯了,衔接流畅了,说表弹唱都自然了。但是,“表演”这一课,我们评弹演员过去都没有正规学过,现在要补,说老实话,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好得我从小喜欢看戏曲,我就把戏曲舞台上演员们的一招一式、一举手一投足都搬过来,先是生搬硬套,后又结合评弹的特点,把表演揉进评弹的“说、噱、弹、唱”中,使之融为一体,渐入佳境。在这方面,我还做得很不够。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戏曲界许许多多我熟悉的、不熟悉的的老师们,是他们教会我在书台上如何起角色,如何把人物的感情刻画得入情入理、入木三分。
评弹和戏剧同为叙事艺术,都要以故事情节作为框架来叙事抒情。所不同的是,戏剧的叙事方式一般都是以剧中的角色作为叙述主体,作者很少直接向观众讲述故事,演员更不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去评判事件或人物的是非曲直。当然,后来戏剧出现了布莱希特体系,开始注意了创作者(编剧、导演、演员)和受众者(观众)的直接交流,于是舞台的时空便出现了间离效果。布莱希特是德国著名戏剧家和诗人,在演剧方法上特别强调采用 “间离方法”(又称“陌生化方法”),指出演员不同于角色本身,演员是表演角色,是驾驭角色的,这就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把二者融合为一体。而评弹的表演正与布氏理论相契合。评弹艺人在演出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表现手法就是“跳进跳出”,既能一人多角,又能作为他者对角色进行描绘、点评。但是,戏剧这种间离效果在舞台上的体现很复杂、很麻烦,有时候舞台上要设置几个表演区,舞美灯光都要跟踪到位。因此,一般的小剧团或一般的剧目轻易不用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说到底,还是因为受到了传统戏剧以剧中角色作为叙事主体的局限,不敢完全从人物角色中跳出来,以创作者的身份直接与观众交流。遗憾的是,布莱希特没有来得及建立自己完整的戏剧体系,只留下了他美妙的戏剧理想、艺术断想和一些实验记录就匆匆谢世了。后来我国著名话剧导演李家耀先生一次去香港参加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研讨会,他为了让更多人能了解布氏理论的精髓,决定在发表论文时请一位评弹演员作为实际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最后在众多评弹演员中选择了擅说 《啼笑因缘》的蒋云仙老师。那次香港之行有两个人是出足了风头,一个是话剧导演李家耀先生,一个是评弹演员蒋云仙老师。对李家耀来说,他没想到我国的评弹艺术竟会在国际戏剧论坛上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对蒋云仙来说,不光是自己精湛的演出得到了好评,更是对布氏的戏剧理论加深了理解。
我从小学说书,那时老师就对我说,坐在书台上的评弹演员,既是说书人,又要起角色,而且不是起一个角色,而是要起各种各样不同的角色,因此在说书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跳进跳出。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们评弹的演唱风格竟与当今世界三大戏剧流派之一的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相吻合。后来,我们评弹界有很多人都在研究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戏剧界更是有不少人对评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按理30年前那次戏剧和评弹的交流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如果循此前进的话,我国的戏剧和评弹都应该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事实上,30年前的那次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次个人的艺术探索,此后引起人们的关注仍然是个人的行为。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与我国的评弹演唱风格虽然有某些形式上和叙事风格上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但它们毕竟还是有着更多的本质区别。这两个舞台艺术门类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也许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但如果成功必定会促进戏剧和评弹大繁荣。戏剧界的同志可能把这件事看得太复杂,而我们评弹界的同仁又可能看得太简单。我认为,这确实是一项既简单又复杂的事情,它需要我用毕生的心血去耕耘。如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感受,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是玉,就要花心血去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