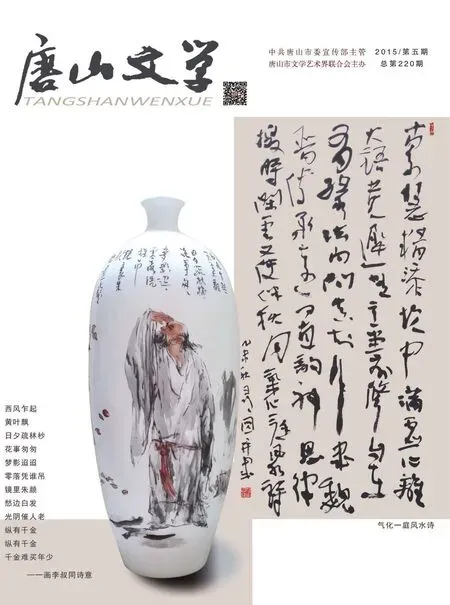《白雪公主后传》后现代叙事中的不确定原则
田克萍 胡瑞
《白雪公主后传》后现代叙事中的不确定原则
田克萍 胡瑞
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1931--1989)的《白雪公主后传》(Snow White,1967)是一部后现代主义色彩浓重的对读者不太“友好”的小说。即使在今天,它依然超出了很多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有曲高和寡之嫌。小说通篇采用了拼贴、戏仿、语言游戏等后现代叙事策略,彻底颠覆了经典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作为后现代主义、黑色幽默和荒诞派文学的经典之作,其叙事策略中的不确定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反映了对原有的秩序和结构的破坏和反叛,始终处于否定动荡和怀疑之中,揭示了后现代解构主义最重要的精神品质。”巴塞尔姆说:“我的歌中之歌是不确定原则。”本文试图从结构与情节、语言表达、人物形象、主题与意义这几个角度出发,分析自始至终渗透于作品中的不确定性原则。
一、结构与情节的不确定
整部作品借用了经典童话故事《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结构框架,但也仅仅是框架而已。作品重新对故事进行了怪异的组合安排,没有线性的故事情节发展,没有空间和时间上的一致性,没有传统小说中固定的叙述视角,也没有逻辑化的叙述顺序。小说由随意拼贴出的一百多个零碎的片段组成。所有的人物都是随机出现的,所有的事件也都是脱节错位的。作者仿佛无意去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只是在渲染一种情绪和氛围。所以小说显得无始无终,尽管最后的白雪公主羽化升天或许可以勉强算作一个结尾。
在这些不确定的结构与情节之中,我们依然可以抽出一些一闪而过的事实来概括小说的基本情节,但这些所谓的情节和大量的心理描写、无意义的语言堆积、插入的新闻报道等比起来,也只占小说的一小部分。比如:长了六颗美人痣的白雪公主与七个身材矮小的美国男人一同生活在城市森林里。白雪公主是七个男人的家庭主妇,为他们做饭、打扫卫生,还分别和他们一同洗澡。七个男人的工作是生产中式婴儿食品和洗刷大楼。白雪公主厌倦了当家庭主妇的生活,渴望被拯救。王子保尔想要拯救白雪公主却又懦弱无能,只是每天偷窥白雪公主。最后,保尔喝下了简为白雪公主准备的毒酒死去。白雪公主在保尔墓前撒花,恢复贞洁而升天。
此外,作品的叙述声音也是不确定的。作品中的叙述声音是经常变换的,时而是“我们”,时而是“我”。“我们”和“我”到底指代的是谁也并不确定。开头“我们”仿佛是七个小矮人,但在后来的叙述中又把比尔、霍德华等一个一个地排除在外,“我们”到底是谁便没有了确定的答案。叙述者“我”是一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如果说“我”是作者,与“我”是“我们”中的一员相矛盾;如果说“我”是七个小矮人中的一员,每个小矮人却又被“我”当做第三者来叙述。所以“我”也是一个未解之谜。这里便体现了后现代主义不确定的写作态度,没有固定答案,任凭读者去理解。
情节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叙述方式的游戏性。如作者在小说第一部末尾直接列出了一个调查问卷,询问读者对于作品的态度,强烈邀请读者参与到作品的创造过程中。这样,便自动揭穿了叙述世界的虚构性,具有元小说的特点,故意使读者看到小说自我形成的路径。如白雪公主说:“这个世界本身也有毛病,连提供个王子都做不到。连至少为这故事提供个合适结尾的修养都没有。”由于整部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不管读者从哪个地方开始阅读,或从哪个地方停止阅读,仿佛都不大会影响到对小说的理解。传统叙事中完整的情节已经不是小说的必要元素,从阅读体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愉悦才是更加重要的。
二、语言表达的不确定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存在主义认为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桥梁;而当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强调,语言作为经验的近似物,本身是相对的和难以限定的。所以在《白雪公主后传》中,语言这座沟通桥梁被彻底拆毁了。文本并不反映作者的意识状态,因此也无法承担作者与读者交流的媒介。正如德·曼所认为的那样,“一切语言都有修饰成分(如隐喻、象征等),因此一切语言都具有欺骗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
《白雪公主后传》的文本是充满开放性的,不存在确定的含义。读者对同一个文本可以产生许多种不同的合理的解释。小说中很多词语的含义是不确定的。文中有许多作者自己杜撰的植入文本中的无意义的组合,如“色情糕点”;也有作者对现有词语的任意改造,如“家庭煮妇(horsewife)”;有杜撰的乐队名、人名、地名等,如“新泽西奥兰奇圣普拉斯基破衣乐队”;还有许多在英语中带暗示性的双关语,比如“拧进去”、“尾部”、“轴杆”等。这些词语所指向的事物并不只有一个,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容易产生多重理解。除了词语,很多句子的含义也是不确定的。小说的叙事语调是戏谑的、反讽的、荒唐的、狂欢的。很多句子经常伴随着语词和意义的缺失,不具有逻辑性,是一种深度模式的消解。比如“牙齿……钢琴课……”, 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词语加上两个省略号就可以构成一句话,且和前面所讲的“头发黑如乌檀!但它使我紧张得要命。”没有任何关联。还有如小说最后一页标题式的黑体字所写的“白雪公主屁股失灵”这样让人费解的句子比比皆是。更加普遍的是,小说中句子和句子之间、段落和段落之间大体上都缺乏过渡,仿佛是睡梦中的呓语或精神病人神经质的喋喋不休,甚至没有标点,让人不知所云,造成语言垃圾的现象。比如:
那些男人 笨拙地走动 走动在私室和室外 姿态映在白色的屏幕上归结于困难 智力我只想要一个高大无比且风度轻逸灵活的普通英雄 部分 思想 掩饰 肢体 将个性特征印加在我的肩膀上 七个太 移动太多部分缺席 不同程度的感情释放有意安排的突然发作卑琐小人 化解 脸上思考的部分……”又如:
“非正式声明 拥有财产的困难和习俗 以某行为令你吃惊 爱的交换画下来 理解身无分文的黑皮肤的孩子 我曾经是 土匪头饰 以及昨天的问题等待着 成员 紧紧缠住想要狂热隐藏的牛奶 熔化的保安队额外危险的机会 躲藏腿底下的简历 切烙方法…… ”
另外,小说的主体还被各种毫无意义的独立于小说之外的巨大的黑体字打断,干扰了故事的进行。这些黑体字是作者随意插入的新闻报道、学术论文、法律用语甚至读者问卷。小说中词语堆砌的现象也很严重,比如“菲利浦放下他的M-16型,M-21型,M-2型和全自动的M-9型枪。接着放下他的M-10型和带枪口接合器的M-34型。接着放下他的M-4型和M-3型。”又如作者用几乎整整一页的篇幅列举白雪公主上大学时所学的各种学科名称,还有写到白雪公主一边刷牙一边猜想是哪位王子会来救她时,就一口气列举了31位王子的名称。这些无意义的词汇乃至句子的堆积,与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严整的语言结构大相径庭,表达了现实生活中语言的杂乱无序状态,让读者隐约意识到弘扬真善美的童话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白雪公主后传》可以说是各种荒诞不经的语言的大杂烩,语言呈现出碎片化、垃圾化的倾向。语言几乎是小说中人物的全部构成,也是他们所产生的垃圾。白雪公主说:“唉呀,除了我听厌的那些话,但愿世界上还有些其他的词语!”小说中每个人物的话都是陈词滥调、毫无个性,人成了信息的怪物。在后现代,“并非人控制语言或人说语言,相反,人被语言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说话的主体是‘他者’,而不是‘我’。”总之,《白雪公主后传》中的语言正是如德曼所说的那样具有欺骗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
三、人物形象的不确定
《白雪公主后传》中的人物是对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人物原型的戏仿,完全颠覆了原著中性格鲜明而活泼的人物形象特征,塑造出不确定的、模糊的、扁平的、无深度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的白雪公主虽然依然如童话里的白雪公主一般“头发乌黑如乌檀,肌肤雪白似白雪”,但身上长了六颗美人痣。她不再天真无邪,而是变成了生活空虚、有七情六欲的放荡女人。她的语言庸俗陈腐,她终日无助地抱怨和等待。她希望通过把自己乌黑的头发甩出窗外来吸引王子并改变命运。她充满了压抑感、嫉妒心和十足的欲望。最后,当保尔替他喝下毒酒之后,她便莫名其妙地羽化升天了。
七个侏儒男人的形象都是扁平性的,读者很难辨认他们的真实身份。小说中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外貌、家庭背景、个人爱好等细节描写,使人物显得缺乏真实感。人物完全没有个性,即使通过他们所说的话也很难区别他们。他们是“影子”般的形象,没有来历和身份,有时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区分彼此。比如小说第52页写到凯文与罗杰的对话时,凯文便混淆了罗杰与克兰,时而说对方是罗杰,时而又说是克兰。这种混乱的、模糊不清的、毫无个性的人物语言“取消了索绪尔符号学对立的能指与所指的区别,没有概念,只剩下语音形象,只有能指的连续,从而也取消了深度。”
王子保尔是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的形象。他虽然有高贵血统,却是个胆小懦弱的无业游民。他喜欢偷窥白雪公主的裸体,但当他看到白雪公主从窗户垂下她乌黑的长发时,又选择了逃避自己的义务。他缺乏决策能力,甚至无法对任何境遇做出正常的反应,所以也无法完成拯救白雪公主的义务。最后他笨拙地喝了简给白雪公主准备的毒酒而死去。保尔的这一形象宣告了英雄的时代的结束。现实是空虚的、混乱的、无序的,在现实中生活的人们是猥琐的、卑微的、平庸的。格林童话中令人欢欣鼓舞、充满希望的故事结局已不复存在。
四、主题与意义的不确定
二战后“上帝已死”,信仰崩溃,自我中心主义泛滥,人际关系冷漠。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人们依然自欺欺人地幻想着真善美的童话世界,这是巴塞尔姆这样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所不愿看到的。所以他在《白雪公主后传》中解构了经典童话,消解了一切对意义的追寻,挑战传统权威和道德准则,追求本质的真实,展示了剥夺生存意义的当代生活方式。在他躲避崇高、抗拒权威的写作态度之下,读者往往在其作品中既找不到确定的主题,也找不到确定的意义。他拒绝解释,拒绝深度和意义。作品不可解释,只能体验。如果一定要有意义,那么意义只在于阅读过程中的专注与沉醉,而不在于对故事情节和主题的追寻。
在《白雪公主后传》所设置的喧嚣混乱的后现代都市中,“愤怒和失望无处发泄”,人人都处于选择困境和巨大的遗弃感之中。七个小矮人认为白雪公主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生活的平静,白雪公主也宁愿死在森林里也不愿过着现在这样终日等待而救援无望的生活。人人都浮躁不安,感觉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宁可终日抱怨也不愿有所改变。原来格林童话中充满温情与爱的人际关系不复存在,小说中的人物像陌生人一般冷漠无情,互不关心,渴望去爱和被爱却又无能为力。作品中充满空虚感的句子俯拾皆是,如“整个世界上唯一有点价值的东西就是女人的美,当然也许还有吃的东西,可能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又如“他还知道孤独的恐怖,亲情的腐败和优雅的缺失。”既然后现代人的活动是无中心无意义的,那么也只有随意的和游戏性的,没有任何目标的文本才能表达出这种真实;既然无论人怎样努力也只能一无所获,那么完成任务的过程本身就成了生活的意义所在,正如小说的文本本身也同时成为了小说的主题和意义。
如前文所述,《白雪公主后传》对读者并不“友好”,作者并没有给读者准备好一份丰盛的大餐让读者尽情享受,而是把读者拉进厨房,给读者参观各种“食品”的原料,然后征求读者的意见,甚至让读者亲自动手做成自己想要的“美食”。这样,作者不必纠结于“众口难调”,每位读者都可以得到自己满意的阅读享受,只要你愿意亲自“下厨”。这正是小说后现代叙事策略的不确定性原则的魅力所在。后现代主义不欣赏二元对立,认为语言、身份、价值和道德准则都是多元化的,主张传统叙事中确定的人物与情节未必能表达世界的真相。对于不确定原则是否一定比确定性原则能更加贴近现实的真实状态,作者也并没有给出固定答案,而是把《白雪公主后传》这样的文本呈现出来作为一个回答或作为一个问题,让读者自己去评判。
[1] 唐纳德·巴塞尔姆著.虞建华译.白雪公主后传[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2] 杨仁敬.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M].青岛出版社,2004年
[3] 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M].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4] 曾艳兵.论后现代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J].台州学院学报,2002年10月,第24卷,第5期
[5] 吴晓明、商爱华.论〈白雪公主后传〉的人物特征[J].新西部,2009年第4期
[6] 项睿.试论〈白雪公主后传〉中的戏仿颠覆[J].渤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