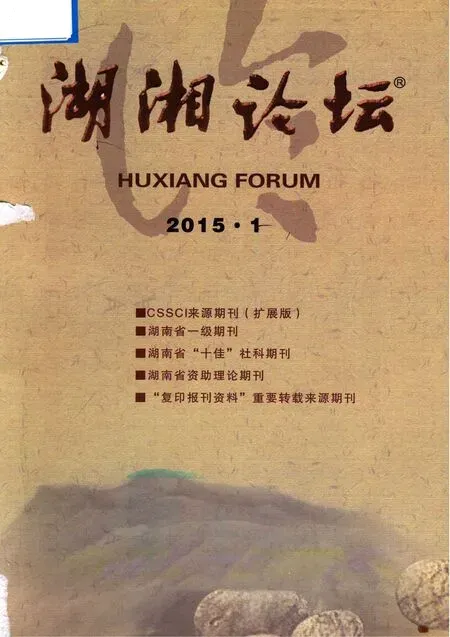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日在东亚融合过程中角色演变
杨 婵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古代最典型的东亚融合应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那时的东亚虽然偶有争端,但总的来说区域交流是非常和平与稳定的。可惜,因为19世纪西方殖民势力的渗透,中国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东亚的自然经济系统也被破坏殆尽。东亚的朝贡体系崩坏且变得一片混乱。
二十世纪初,日本在赢得了日俄战争后,成为了东亚地区的新中心。1930 及1940年代,日本以将白种人赶出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名,发动称霸东亚的侵略战争。由于帝国主义日本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殖民经济,东亚身份认同和东亚地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被迫得到“重树”。
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各国几乎都经历了一个殖民体系崩坏与民族主义上升的阶段。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东亚区域合作都没有得到恢复。缺乏无争议的领导者是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之一。日本的战败与新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造成了东亚的权利真空。这时的外在环境对东亚融合来说也很不利。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爆发,将东亚诸国推向了冷战前线,东亚地区被撕裂成了两个对立阵营。而且,美国因素也深深的制约着这一时期东亚融合的发展,一些带有区域主义特色的计划因遭到美国的反对而纷纷流产。
学界通常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东亚融合(即区域一体化)及一种为东亚各国所共有的身份认同在1990年代后期才逐渐形成。本文旨在探究作为东亚大国的中国与日本在现代东亚融合中角色的演变。
一、短暂重振:中日共同推进下的东亚融合(1997-2003)
在1997 到1999年期间,最重要的外在因素可能就是1997 金融危机了。1997年,原本为纪念东盟成立三十周年而于马来西亚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 +3)的主题也变成了如何应对这次危机。这次聚首成为东亚区域主义发端的一个契机。此后,东亚各国开始不断进行发展东亚区域主义的尝试,10 +3 会议本身也慢慢成为推动东亚一体化的核心机制。1999年,东盟接受柬埔寨作为其第十位成员,第一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这两事件标志着东南亚及东北亚内部的合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东亚全区域合作方面,1999年的10+3 发表了第一份主席声明,将10+3 升级为一个东盟成员国与中,日,韩三国间的年度正式会议。10+3 的制度化标志着东亚区域主义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东亚合作的愿望变得强烈的同时,各国对主导东亚合作领导权的竞争也开始了。
这一阶段初期的日本与中国相比,其对东亚合作的态度还是较为积极,贡献也较为实际具体。但到了此阶段后期,日本的态度逐渐变得消极,贡献也趋于象征性。1997年,虽然日本也受到金融危机的波及,可是桥本龙太郎首相却表明日本一定会坚持帮助亚洲复苏经济。为了表明作为亚洲经济大国的责任心和能力,日本还宣布了一项强有力的旨在鼓励东盟国家“自立”的援助计划。到了1998年,日本的经济形势还是不容乐观。可是,中韩这时已纷纷提出了与日本不同的援助计划。为了应对来自中韩的竞争,日本表示要成为东亚复苏的火车头,并且提出一些更加有力具体的援助计划,如总数为6000 亿日元的贷款计划。
到了1999年,日本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制度化10+3 的努力,比如,它有参与计划东亚国家在金融、预算、人才等6 方面合作,并且大力支持区域内学生的交流等等。可是,这一年,日本没能提出任何有力的促进东亚经济复苏的计划。而且,此时日本的兴趣似乎从东南亚转向了东北亚合作。比如,日本倡导将中日韩领导人会谈制度化,并且倡议东北亚国家应该在朝核问题和经济方面加强协同合作。
与日本相反,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兴趣及其在东亚的影响力在这一阶段呈逐步增长趋势。1997年,中国虽然没有提出独立的援助计划,但为了帮助受到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中国积极参与了IMF框架内的一些援助行动。江泽民也在谈话中指出,为了维护区域经济稳定,中国没有必要也不会将人民币贬值。同时,作为受经济危机波及最小的国家,中国的经济稳定也间接的促进了东亚稳定。
从1998年开始,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热情慢慢高涨起来,其关于东亚区域主义的政策也变得具体很多。比如,在1998年的10+3 上,中国就建议开展一项针对控制国际资金流的深入研究。在接下来的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谈上,胡锦涛主席表示中国愿与东盟各国开展从民间到官方的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如在建设自由贸易区与开发湄公河方面的合作。
在2000 至2002 期间,东亚经济得到复苏同时,以自贸区谈判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也得到了迅猛发展。这种形势“要求”更有力的区域主义机制。2000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首次提出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的构想。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破坏区域稳定的外在因素,如911 恐怖袭击和2002 印度尼西亚爆炸袭击之类的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可是,这些外来因素所造成的威胁也间接的增加了区域合作的愿望。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超越日本,开始在区域融合过程中担任领航者角色。在2000年中国就已经与所有东盟成员国签署了双边合作文件。在同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朱鎔基总理强调三国的政治经济在东亚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应当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中坚力量。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步伐在2001 加入了世贸组织后变得更快。同年,中国与东盟一道确立了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目标,并且定下了农业等几个重点开放领域。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谈(10 +1)上,双方还进一步就安全领域,南海争端等敏感话题开展了讨论。
2002年的10+3 会议通过了中国关于开展反国际犯罪部长级会谈的提议,中国也在会上公布了它减免亚洲借债的计划。在10 +1 框架内中国的成就也很突出,比如双方商谈决定将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也表示将率先向东盟国家开放其农产业市场。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谈中,朱总理提出了建立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提议,并且表明了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立场。
日本方面则延续了其在1999年的言行。在与东南亚合作方面还是没有太大的举动。在10+3中,森喜朗首相只是做了一些如“合作三大原则”这样的象征性谈话。对东北亚合作,特别是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的合作,还是比较积极。2001年,日本对东亚融合中的影响力可以说是降到了最低点。当年日本计划在10+3 上通过一项反恐声明。这项计划被认为是在美俄不在场的情况下,对日本东亚外交影响力的一次测试。可是这一计划却失败了,关于反恐的讨论在大会上只持续了不到10 分钟。日方认为反对者主要是印度尼西亚这样反对美国入侵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家、中国,以及与中国有着亲密关系的国家。日本与东盟有关自贸区的谈判也非常的滞后。日方因为中国与东盟自贸区谈判的顺利进行以及中国将比日本更快进入东盟市场的可能性而倍感压力。可是因为日方不大愿意通过自贸区的形式向发展总体上落后于它的东盟打开其国内市场,它只能依赖传统的ODA 援助方式进入东盟国家。
2002年,中国在区域合作方面取得的成就使日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比如,前述的中国要求朝鲜放弃研发核武器的表态以及与东盟国家签署自贸区框架协定的速度,都被《读卖新闻》等日方媒体公开地解读为中国在东亚政治经济领域称霸的表现。日本终于开始重新思考其它的东亚战略。小泉纯一郎首相提出了“携手共进”的新政策,以倡导一种强调互相合作而不是援助被援助关系的日本-东盟新关系。同时,尽管有很多实际困难以及来自日本国内的反对声,小泉还是保证日本将会与东盟国家寻求一种以自由贸易为中心的综合经济伙伴关系。
二、艰难发展:中日共同推进下的东亚融合(2003-)
在2003 到2005年间,东亚区域主义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东亚共同体的讨论也更加深入热烈。同样,像SARS 这样的外在影响在威胁东亚稳定的同时也间接的加强了东亚合作。可是,10+3的发展却在2005年左右缓慢了下来。主要原因是它作为推动东亚一体化大本营的角色在东亚峰会(EAS)——另一个旨在引领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机制——举办后变得尴尬起来。
2005年的情形不仅对10+3 和东亚峰会这两个都肩负着东亚区域主义未来的机制来说是场危机,同时也暴露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重复性建设的阶段。互相对立机制的并存,不但成为了东亚区域主义进一步前进的阻力,还有可能导致东亚的分裂。中日两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对东亚区域一体化还是不甚热衷,缘何到了2005年却为了一体化领导权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2003年,继续前一阶段在双边自贸区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势头,中国开始着手东北亚自贸区及东亚自贸区的谈判。日本在东亚区域主义领导权争夺战上的反击也于这一年正式开始。日本在自贸区谈判及签署《东南亚友好协力条约》方面奋起直追以求赶上中方的步伐。除了经济领域,日本还深入到反恐等其他领域以图增加其影响力。在与东盟国家间的特别会议上,日本还企图说服东盟国家坚持“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等原则。这一举动显而易见是针对中国的。
2004年,中国在东亚区域主义中的影响力则继续得到增强。在广西举办了首次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还提倡建立一个关于能源供应运输稳定的大使级对话机制。在10+3 会议上,中国继续为推动东亚自贸区的建设而努力。
2004年,日本在争夺东亚区域主义领导权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日本与东盟领导人会议(10+1)决定,日本东盟自贸区的谈判将会在次年四月启动。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10+3 通过了日方在次年举办EAS 以讨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提议。而很多观察者认为,日方的这项举措是为了将EAS发展为一项由其主导的新的区域主义机制,以取代深受中国影响的10 +3 机制。也就是说,积极促进EAS 的召开,是日方为了降低中国在东亚区域主义事务上影响力的而打一张牌。
2005年,中日关系因为二战历史问题降到冰点。虽然中方在10 +1 和10+3 会议上的表现还是非常积极,但当年的中日韩会谈因为日本首相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而被延迟。中方也在几大会议期间多次批判了小泉首相这一伤害亚洲人民感情行为。可中方这些伸张正义的言行却被日本言论攻击为“使得历史争端国际化”从而推进中方领导东亚区域主义的目标。
EAS 在2005年如日本所愿召开了,可它却辜负了日本对其寄予的“厚望”。中方明确表示,东亚共同体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三层机制结构的基础上,即以三个10+1(中,日,韩)为核心,以10+3 为推动东亚融合的中坚大本营,以东亚峰会为能展现东亚开放性的外围。也就是,中方希望EAS成为一个由东亚主导但允许区域外国家参与的讨论各项事务的平台,而10 +3 才是推动东亚融合的专有机制。虽然日本也提倡,在EAS 机制下,东盟及中日韩可以邀请区域外的伙伴来讨论东亚事务,可日本坚持EAS 为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中坚机制,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对话平台。
2005年的中日交锋,貌似是以日本的失败收场。温家宝总理在EAS 上畅言了中方的和平崛起战略,却几乎没有涉及东亚共同体。不仅如此,根据第一届EAS 主席声明,对东亚共同体的讨论似乎也没有被提上这届峰会议程。虽然声明提到“东亚峰会将会促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但是日本言论普遍认为这种提法非常的模糊;声明反倒肯定指出,10+3 为促进东亚区域主义的主要机制。
在2005 后,中日对于东亚区域主义领导权的竞争以及中日矛盾对东亚融合进程的负面影响还在继续并且持续至今。日本挑起的中日矛盾甚至曾几度严重威胁东亚区域主义的正常发展。比如,因为日本二战史认知问题,2005年被延迟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谈直到2008年才恢复。而在2013年,中日关系因为安倍晋三重登总理位子后主张修宪等行为再次恶化,同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随即又再生波折。而东亚各国原本期望当10 +3 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能够自然升级过渡到EAS。可被精心培育的EAS 却因为日本的私心而早产。并且,因为中日的竞争EAS 变异为了一个没有太大实际作用的对话平台,这一症状在EAS 于2010年吸纳俄罗斯美国加入后更为显著。再加上这些年美国重返亚洲,东海,南海领土争端加剧,虽然区域经济合作继续增长,东亚融合整体情况堪忧。
三、“政治供应”,“经济要求”及“外在因素”: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因素
本文建立了一个解释区域一体化现象的理论模型,以便读者更好的理解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东亚一体化现象及中日两国与此现象的关系。

区域融合理论模型
区域融合顺利进行的要素有三点。第一,自下而上的“经济要求”,也就是要求区域融合的强烈市场压力。第二,愿意且有能力推动区域融合的国家们自上而下创造的一种集合“政治供应”。在“供应”层面对融合来说很重要的条件,即在一群寻求更紧密关系的国家间无争议领导国(们)的存在。以德法为主导的欧盟的成功经验也说明了无争议领导国在区域融合中的重要性。纵观东亚各国综合实力,中国和日本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无争议领导国者”候选人。第三,有利的外在因素。区域外势力的介入和经济危机等无法为区域内国家所控制的状况都属于外在“因素”。这三个因素的变化也是九十年代后东亚融合得以重振的主要原因。经济复兴后的日本,通过战争赔偿,政府开发援助(ODA),以及直接投资与贸易,在东亚建立起了一张以其为中心的经济网络。冷战结束后,这一网络变得更加紧密,并且自上而下的形成了一种对建立一个统御区域经济事务的组织性框架的“经济要求”。冷战结束,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及“南北集团”趋势在东亚的发展等国际环境的变化则是促使东亚区域一体化飞跃性发展的首要外在因素。
再来看看“政治供应”方面。ASEAN 开始积极的在东亚地域合作中扮演“中介”角色。更为重要的是,日中两国也逐渐有了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担任领导者的实力与愿望。通过实现与韩(1965年)中(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提出指导日本发展与东南亚关系的福田主义(1977年),及以G7 成员国身份成为西方与东亚国家间中介等行动,日本逐渐地提高了其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外交影响力。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的东亚政策变得更加积极,而且,其重点也从经济援助发展方面,扩张到可持续发展和核不扩散等领域。中国方面则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倡导多边主义策略。除了大力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外,中国也表示愿意与其他国家在军事等其他领域加强友好合作。当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成长停止,日本也处于始于1990年代早期的不景气阶段时,只有中国的经济还在稳步增长。这一事实让东亚各国日益意识到,得益于中国的实力,东亚地区不但可以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大型经济体,这一经济体还可以在国际社会上发出更加有效的声音。
量变产生质变,现代意义上的东亚区域主义终于在1997年亚洲经融危机爆发后正式发足。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东亚国家对于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APEC 这样被西方势力所领导的组织的依赖大大降低,因为这些机构没有能够对它们进行有效援助。再者,危机中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让东亚各国意识到它们之间利益交错之深,以及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达成长远发展目标而进行合作的必要性。
从经济需求和外在因素来看,1997年后发展东亚区域主义的条件更加成熟。可是,东亚区域主义在高度发展了一段时间后却止步不前。中日矛盾而导致的无争议领导者的缺失,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集体“政治供应”,“经济要求”及“外在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东亚融合的进程。而无争议的领导者作为“政治供应”的特殊因素,对东亚融合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本文对东亚融合的历史追溯及现状探讨也证实了这个理论模型及其关于无争议领导者论述的正确性。在1997-1999 及2000-2002 两阶段,虽然积极程度不用,中日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总的来说都是正面的。而这两个阶段的东亚一体化进程也非常顺利——比如,东亚各国齐力战胜了1997年经济危机,对东亚共同体的热烈讨论也反映出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及对“政治供应”的急切需求。可是,在第三阶段,中日两国都变得十分积极,两国对东亚区域主义领导权的竞争也变得空前严重。两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参与变得负面。而这一阶段,东亚一体化也碰到了东亚区域主义机制重复建设这么一个发展上的瓶颈。
总而言之,当中国或日本独自领导东亚合作,或互不发生冲突的共同为东亚融合作贡献时,东亚融合则进行的顺利;而当两国开始因为竞争或矛盾而导致东亚地区一个“无争议”领导缺失时,东亚融合则受阻。希望中日两国能够摒弃前嫌,共同和谐的领导东亚融合走出困境。
[1]D.Capie.Rival Regions?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its Challenges to the Asia-Pacific (竞争地域?东亚低于注意和它对亚太的挑战)[G]in J.Rolfe,(Ed).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Honolulu,HI: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亚太:变动中的地域),2004.
[2]江泽民主席发表题为《携手合作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1997-12-16;钱其琛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富有成果[N].人民日报,1997-12-17;外交部发言人举行记者招待会[N].人民日报,1997-12-17.
[3]胡锦涛就中国和东亚东盟关系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1998-12-17;外交部发言人评东盟-中日韩,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N].人民日报,1998-12-23.
[4]ASEAN·日中韓首脳会議森首相が「協力3原則」を提唱[N].読売新聞,2000-11-25.
[5]加强合作,共图发展[N].人民日报,2000-11-26;朱镕基出席中日韩领导人早餐会[N].人民日报,2000-11-25.
[6]促进东亚合作我外长谈温家宝出访成果[N]人民日报,2003-10-9;温家宝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晤[N]人民日报,2003-10-8.
FTA、2012年までに 日本·ASEAN、枠組み文書署名へ[N].読売新聞,2003-10-8;対東南アジアで日本後手 自由貿易協定など、中国は積極姿勢で存在感[N].読売新聞,2003-10-9;「東アジア共同体」提案へ 日·ASEAN会議で日本[N].読売新聞,2003-11-12;[地球を読む]日·A SEAN首脳会議 「対テロ」連携が急務 白石隆(寄稿)[N].読売新聞,2003-12-07.
[7]温家宝出席第八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在会上发表讲话[N].人民日报,2004-11-30.
ASEAN全体とFTA交渉へ[N].読売新聞,2004-11-30;温家宝出席第八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在会上发表讲话[N].読売新聞,2004-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