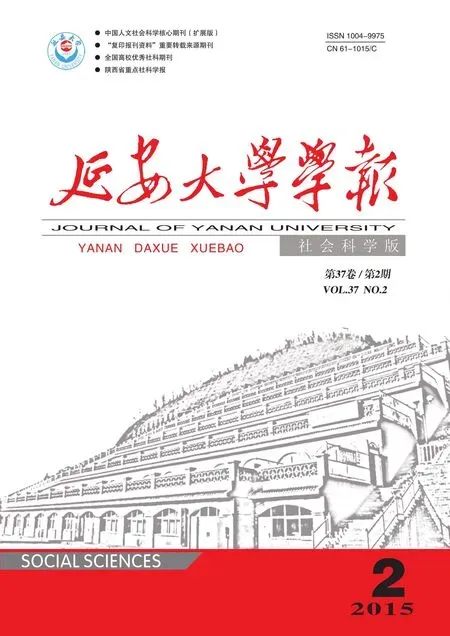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之源——基于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的理论考察
唐 鸿
(肇庆学院思政部,广东肇庆526061)
■哲学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之源
——基于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的理论考察
唐 鸿
(肇庆学院思政部,广东肇庆526061)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其理论基因尤其在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得到了秉承和升华。在对卢卡奇实践理论及主体思想的延续与深化中,法兰克福学派及存在主义理论家们展开了对物质一元论的批判,致力于把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成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从而将“物本崇拜”转向“人本关怀。”
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实践;主体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勿庸置言,卢卡奇的理论传统在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轨迹上留下深刻的历史烙印,诚如马丁·杰伊所言:“如果没有卢卡奇的著作,西方变异的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许多著作就不会统一起来。无论作者本人后来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如何,但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本开山著作,如本雅明所承认的。……无论此后的岁月中他们如何因异议而分离——他们是真诚的———研究所和卢卡奇都是在一个共同的传统中讨论着相似的问题。”[1]像卢卡奇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续者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理论家正是沿着社会历史辩证法高扬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理论路径行进的,他们信奉与尊崇实践,热衷于探寻主体性,对物质一元论展开了激烈批驳,致力于将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成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一、对实践的信奉与尊崇
实践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理论家十分关注的理论基点。在对实践范畴的理解上,两者与卢卡奇有着共同之处,一致强调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反对物质本体论。施密特认为,“不是所谓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2]在他看来,“物质的存在作为其外延与内涵上的无限性,是先于历史实践的一切形式的,但当物质存在成为对人是有意义的东西时,这种物质的存在并不是在它优先产生的地位上被唯物主义理论必须假定的那种抽象的物质存在,而是第二性的东西,是通过历史的活动所占有的。”[2]210弗罗姆则指出,机械唯物主义将世界的本原简单归结为物质,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在他看来,“马克思并不注意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把一切现象都理解为现实的人类活动的结果。”[3]马尔库塞也认为,劳动或实践范畴在马克思那里被赋予了本体意蕴,“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实证的定义几乎完全是作为与外化劳动的定义相对立的概念而提出来的。在这些定义中清楚地表述了劳动这一概念的本体论的性质。”[4]总之,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阈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本体论,并非物质一元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化了的黑格尔主义,不是竭力用另一个本体论的始基即物质,去简单地替换所谓精神这个本体论的始基。”[2]209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探讨实践问题的切入口。秉承卢卡奇的理论传统,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中,他们尽管看法各异,但大都赞同马克思关于“人化自然”的思想,将自然界理解为经过改造的、人化的自然。霍克海默认为,“自然总体”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当完全取决于人的情况、人在劳动中的关系和人自己的历史进程都被当作是‘自然’的组成部分时,作为结果出现的外在性就不是超历史的永恒范畴,而是可鄙的弱点的标志。”[5]施密特则将“人化的自然”理解为“劳动加上自然物质而构成的使用价值的世界”,[2]63马尔库塞的理解也大致相似,在他看来,“自然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的客体”,[6]因而,“自然的解放乃是人的解放的手段……从一开始我们就需要指出,自然被打上了历史的烙印。”[6]127总体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解,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所提出的“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知道,马克思自然观的本质,即在于从实践维度出发,揭示人与自然之间以实践为中介的辩证统一关系。应该说,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坚持从实践的角度来解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基本把握了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论内核。
基于对实践范畴及其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理解,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作为一种“历史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不适用于一般自然界,只适用于“进入社会再生产的历史过程的自然和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历史过程的条件的自然。”[7]施密特指出,恩格斯所倡导的自然辩证法背离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本意,“在恩格斯那里,自然和人不是被首要意义的历史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人作为自然过程的进化产物,不过是自然过程的受动的反射镜,而不是作为生产力出现的”,[2]50在他看来,“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中最本质的一切要素”,只是“由于自然产生出作为意识活动之主体的人,自然才成为辩证法的。”[2]56-57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历史实践出发来理解辩证法的理论路径在存在主义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回应和升华。萨特倡导以“人学辩证法”替代“自然辩证法”,“在萨特那里,辩证法一词无非是表示实践的主体性和对于主体的可把握性。哪里能够彰明主体性,哪里就有辩证法;无论哪里,一旦彰明主体性的途径有所涩滞,辩证法就遭受着惰性的破坏。”[8]另一位存在主义思想家列斐伏尔也认为,辩证法起源于实践,其基础只存在于社会历史活动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显然,存在主义以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为主旨的辩证法思想带有一定的的浪漫主义和唯意志主义成分。事实上,“辨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9]
像卢卡奇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在观念上信奉政治实践,热烈赞颂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工作有助于提高被剥削者的阶级觉悟,为其提供思想武器。霍克海默指出,“如果理论家及其具体研究的对象被认为与被压迫阶级形成了能动的一致,以致他对社会矛盾的解释不仅仅是对具体历史状况的表述,而且是激发历史内部发生变化的一种推动力,那么他便真正尽到了职责。”[10]同时,他们还主张哲学应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突出其对现实的关注与评判,“真正的理论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正像与理论相应的社会不能称之为生产型的社会一样。人类的未来依赖于今日对生存所持的批判态度……思想中的盲从以及坚持认为思想是一种固定的才能和整个社会中的一个自我封闭领域的主张都背叛了思想的本质。”[11]马尔库塞直言,“哲学一旦从纯理念的笼罩中解放出来,也就从它与现实的对抗中解放了出来。这意味着它不再是哲学了。但是,这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思想必须遵从于现行的秩序。批判的思维不会止息,而是采取一种新的形式。理性的努力让位于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10]294
总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理论家对实践的理解基本体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是对马克思哲学现代转换的一个延续。他们对物质一元论的批判,旨在将唯物主义改造成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把对物质本体的崇拜转向对改善人类状况的价值关怀,应该说,基本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人文关怀向度。“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12]马克思哲学不是着力于去揭示世界的本原,也不是着力于对理论体系的整体建构,而是注重于以一种辩证的方法来探究社会实践和现实世界,其基本路向是透过一切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来审悟历史和现实、凸现人作为实践主体的价值和意义,“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个工具,借助于那个工具,人的价值才在人之外得到了‘投射’,并且获得了既独立于他又高于他的一个存在。”[13]
二、主体思想的延续与拓展
主体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所热衷的理论主题,主体性原则是其构建自身社会历史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在他们看来,社会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相互结合、相互转化、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没有人的实践和参与,就没有社会历史的发展,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不可或缺。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始创至二战结束时期基本遵循的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轨迹,而其人本主义理论路径又较大程度上溯源于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中“经济决定论”思想的质疑与抨击,显现出两个明显的理论特征:一方面,承继和突出了马克思学说中关于“人”的实践性和能动性的一面,对机械决定论进行了理论上的逻辑矫正,力图恢复马克思哲学中所蕴含的历史辩证法,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将现实的人的本真存在状态作为关切点,期冀唤醒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物化”的人的“总体意识”,使之转变为一种崇尚真、善、美的“总体性存在”,从而真正实现哲学的人文关怀价值。
卢卡奇的主体思想被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理论家一脉相承,并得到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其现实与理论根基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们带来了普遍的生存危机和心理阴影;另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合理化所带来的工具主义蔓延加剧了人们的精神危机,价值理性逐步退落,物化现象日渐明显,诚如韦伯所描述的那样,“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14]在这一背景下,人的主题自然从社会历史进程中重新凸现出来,成为理论家探讨的主旋律;其二,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面世,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欣喜地发现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的理论镜像,促进了其人本主义价值的独特取向。在对马克思哲学著作中人本主义思想进行挖掘及续承卢卡奇主体思想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理论家进一步融入了由叔本华、尼采等现代西方哲学家开辟的非理性传统,以个体的生存及感性活动为新的理论切入点,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人本主义的理论重构。
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从人本主义视角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社会批判理论”或“批判的唯物主义”。在他们看来,“社会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自由和平等是其理论前提与终极目标,其目的是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历程的反思与质疑,使人从经济必然性及国家权威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从而把西方社会“改造成为一个公正的和更为人道的社会”;[15]相比较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中晚期人物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则主张通过对人的本能、爱欲等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和关注,消除异化,恢复人的本真状态。基于此,他们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蓝本,致力于挖掘其中蕴含的人本思想,结合弗洛伊德的学说,展开了一场以自由和发展、人的解放为旨意的人道主义理论探索。弗洛姆直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它的目的在于发挥人的各种潜能。……马克思关心的是人,而且他的目标就是让人从物质利益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让人从他自己的安排和行为所造成的束缚自身的囚笼中解放出来,如果人们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一关注点,他就永远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16]
同样,在存在主义理论家那里,主体问题也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问题。在萨特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难以超越的的理论体系,但它对人的主体性或主观性关注不够,尚未解决历史进程中人的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存在一定的“人学空场”。而在这一点上,存在主义则具备明显优势,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互补和共融。萨特认为,存在主义也是一种人道主义,“因为我们提醒人除了他自己外,别无立法者;由于听任他怎样做,他就必须为自己作出决定;还有,由于我们指出人不能返求诸己,而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17]另一位存在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也认为,现实或实践的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所在,主体性原则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原则。在对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驳中,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存在主义即人道主义的解释,并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融合在一起,把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人道主义和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以恢复所谓人道主义的‘哲学顶点的地位’、‘对现实进行革命批判的顶点的地位’……他把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人’、‘完整的人’阐发为‘总体的人’。”[18]总之,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同一个,但后者把人吸收在理念之中,前者则在他所在的所有地方,即在他工作的地方、在他的家里、在街上寻找他。”[19]
总体观之,卢卡奇的主体思想被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理论家演变为一种人本主义哲学。一方面,后者将哲学的功能定位于唤醒人的自觉,恢复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之上;另一方面,他们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把人的“总体性存在”作为人类解放的目标,将消除异化、实现主体自由和解放的理论路径引入文化和心理层面,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一面镜子。从30年代开始,作为批判理论的最重要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延续和提升了由青年卢卡奇等人实际引发的人本主义辩证法,致力于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并结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断拓展和深化批判的视角,直至对整个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20]应该说,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理论家强调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与马克思的主体思想基本吻合,但他们仅仅期冀从文化批判和心理重塑等非物质层面来消除异化、实现主体自由和解放,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哲学冲动。”[21]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理论家所凸显的这种人本主义理论偏向,后来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已有所察觉并进行了理论反驳,以突出社会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性,将主体消融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结构主义看来,历史其实是个无主体的过程,历史过程中呈现的辩证法并非任何主体的作用所致,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完全被物化的阶级,因此必将成为颠覆行动的主体,即‘历史的主体’(这是卢卡奇创造的一种说法)。为了消灭自己的异化,它把历史引向终结(或者说作为自由的历史的新开始),同时在实践上实现了人类大同的哲学理想。这样哲学就在毁灭中实现了自我,这实际上又回到了神秘主义思想的古老模式。”[22]遗憾的是,结构主义理论家在分析历史发展的进程时,由于只见“结构”而不见“人”,把主体的能动性完全排除于社会发展之外,为自己的思想打上了明显的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烙印,同样走向了另一个理论极端。
三、结语
综上所论,卢卡奇的实践理论及主体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得到了秉承和升华,前后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交映,共同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的理论视域。但相比较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渊薮与思想特色:其一,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理论家所面对的主要是法西斯主义对人类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和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对人的主体性的不断消解的现实际遇,因而更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的批判,以重新唤醒人的“价值理性”为基本理论坐标;而卢卡奇所面对的现实,则主要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挫败及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其理论路径主要以反思和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而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其二,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的理论背景相对厚重、学术视界相对宽广,研究路径相对多元,他们“不仅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不同程度地受到现当代哲学大潮的浸润,其中包括与叔本华、弗洛伊德等理论家的思想碰撞及与逻辑实证主义的争辩和对话等,溶入了批判传统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的主题之中。”[23]在这种多重优势的交融与互动中,“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断自由世界,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然而又坚决地捍卫它的理想,保卫它不受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希特勒主义及其它东西的侵害,就成为每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权利与义务。”[5]5
从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对卢卡奇思想的传承与拓展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如下方法论启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凸显其对社会现实的审视与批判向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建构和批判的双重重任,在建构中批判,在批判中建构,锻造了独特的理论品格。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敏锐的批判精神和反省意识对政治、经济、道德等各个层面进行了多维度的理性关注,为时代演进与社会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的思想引擎。作为时代精神的凝练表述和理论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充当为现实辩护(解释)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改变世界的前提就是对现实进行科学的批判,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向现实发出赞叹和微笑,而是提出问题,以及提出产生问题的根据,为前进扫清障碍并开辟道路。”[24]故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和研究家,一切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想真正有所成就、有所创造,必须立足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问题为中心,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这个过程就是真正立足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25]
[1][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M].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201.
[2][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1.
[3][美]弗罗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0.
[4]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03.
[5][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00-201.
[6][美]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8.
[7][美]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M].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66.
[8]张康之.总体性与乌托邦[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87.
[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9.
[10][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85.
[11]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89.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2.
[13][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15.
[14][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87:138.
[15][美]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194.
[16][美]弗洛姆.人的呼唤——弗罗姆人道主义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1:11-12.
[17][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30.
[18]吴宁.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观评析[J].教学与研究,2008(5):58.
[19][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1卷(上)[M].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7.
[20]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15.
[21]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19.
[22][法]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M].王吉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3.
[23]吴友军.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及其困境[J].哲学动态,2008(4):37.
[24]孙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路[J].哲学研究,2006(10):7.
[25]陈先达.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6(2):10.
[责任编辑 高 锐]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Lukacs in Western Marxism——A Theoretical Inspection Based on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Existentialism
TANG HONG
(Teaching Department for Idealogical & Political Theory,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 526061,Guangdong)
As the founder of Western Marxism,Lukacs'theoretical tradi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academic path of the later Western Marxism.His theoretical genes are especially inherited and sublimated by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Existentialism.Based on the continuation and deepening of Lukacs'theory of practice and subjectivity,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Existentialism criticizes Material Monism,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ransform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o a humanitarian critique of the society on the purpose of turning material worship into humanistic solitude.
Western Marxism; Lukacs;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Existentialism; practice; subject
2015-02-2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研究”(14ZDA004)
唐 鸿(1969—),男,湖南江永人,广东肇庆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法学博士。
B17
A
1004-9975(2015)02-0028-05
——《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基于国际理论家的视角》评述